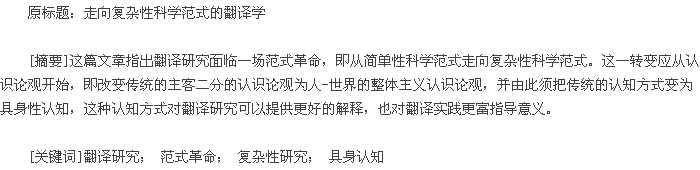
前言 翻译学面临一场彻底的革命
翻译学发展至今已面临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这将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是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革命,它将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翻译学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并引导我们面向未来做认真的思索。曾在 1994-1998 年这四年中担任国际社会学会主席的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写过一本书叫《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他在著作中批判了以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知识体系,指出: “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先决条件,对于确定性的信念是令人蒙蔽的,为害不浅的。现代科学,即笛卡尔---牛顿的科学一向建立在对确定性的肯定上面。其根本性预设为: 有一些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客观普遍法则存在,科学探索能够搞清这些法则,而且一旦认识这种法则,我们就能从任何一组初始条件出发,完满地推演出后继的和先前的状态。”( 沃勒斯坦,2002:203) 我们的近现代科学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的译学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法则”就是语言规则,“先前状态”就是原文,“后继状态”就是译文。我们只要遵守语言规则,正确运用那些现成的翻译技巧就可以进行“忠实”的再现或“等值”的转换。在这样的运作中,主体因素、社会文化和环境条件等都被消除了,这种科学被称为简单性科学。它是一种以确定性为基础,以普适性原则为指导,以分解和还原为方法的研究方式。在解构主义运动中,这种观念受到冲击,或者说被有效颠覆,如确定性被不确定性所替代,一元性被多元性所替换,普适性让位给了地方性。在现代性科学中的理性齐一的主体变成了差异性的个体主体,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也被纳入思考的范围。翻译学也从此突破了结构主义范式而走向解构主义范式,但是解构主义只是从表层结构中反映出的问题揭示了现代主义的不合理性,没有深入到人们的思维和意识的层次,以及从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改变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只是对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入手批判,还很缺乏系统性的批驳,更缺乏建构性的思想,所以解构主义思潮仅仅经过十多年的兴盛就式微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但是,解构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它终结了一个旧的乐章,虽然它没有开启一个新的乐章,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那么这个新的乐章应该是什么呢? 这就是复杂性科学,即从现代性的简单性走向后现代的复杂性。沃勒斯坦在上述那本书中多次提到复杂性科学,并把它称为 21 世纪的科学。这种科学是一个全新的范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简单性科学有所不同,它是以不确定性为先决条件的。他指出: “不确定性是奇妙无比的,……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向创造力敞开了大门,这不仅向人文创造力,而且还有全部自然的创造力。( 如果) 一切行动都落入业已注定的确定性内,我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陶醉于各种激情和各种利己主义,……会是道德的死亡。”( 沃勒斯坦,2002: 4) 显然,他的话不是危言耸听,现代性在带来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两次世界性战争的灾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泛滥、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家们为了使其成本外在化,以至于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产品质量低下等等,这不正是“道德的死亡”吗?
复杂性科学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简单性科学,沃勒斯坦指出: “复杂性科学在各个重要方面与牛顿科学很不相同: 诸如,否认可预见性的内在可能性; 认为诸体系远离平衡状态,尤其不可避免的分岔系属正常; 承认时间之矢的中心地位。但是,与我们现在的讨论可能最有关联的是强调自然进程的自建创造力,人与自然的不可区别性,以及从而断言科学是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那种追求基本的永恒真理的无根据的学术活动的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可发现的真实世界的观念,但是,因为未来尚有待创造,现在谈不上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发现,即使未来受到过去的限制,但未来却不囿于现在。”( 沃勒斯坦,2002: 90)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复杂性科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即不再是主 - 客二元分割和对立的世界观,而是把人和世界视作没有区别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也就是“人和自然的不可区别性”.
这种把世界看成人的“肉身”,而人又成了世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将引起认识论观念的彻底变化。感性问题,这一在简单性现代科学中被排挤出去的内容势必重新登场,而且成为重要角色,成为认识的来源。人们的认识必将成为具身性的( embod-ied) 认识。下面本文主要从认识观的变化和具身性认知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让它们成为复杂性翻译学范式的基底。
一、从主-客分离式的认识观走向人-世界的整体主义认识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1972: 219) 实际上这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同的选择方式反映着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和世界观,它还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我们可以从西方哲学史中看出一种是从笛卡尔开始到黑格尔的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观,一种是从狄尔泰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人-世界的整体主义认识观。
现代性科学以确定性为前提是源自主-客二分的看问题方式,这种方式割断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只是用人类发展的最高层次,即心灵与精神层次来与世界对话,忘记了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
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1972: 233) 在简单性科学中,所谓的“人”,并非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虚构的人。这一点正如复杂性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指出的,“一个结构主义的或阿尔都塞式的论断可以合乎逻辑地达到这个结论: 人是不存在的,这个概念涉及一个虚构、一个幽灵和一个常识中的幻影。这个结论根据其前提是和谐一致的,但在下述意义上是荒谬的,因为排除了使它能够设想人的事实材料和有关观念,它得出了人的不存在”.( 陈一壮,2007: 10) 那么,在简单性科学中的“人”又是指什么呢? 它指的是“我思故我在”中的“思”,即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这是典型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它将承载心灵的肉身与之分开并将肉身排除在外,忘记了人的心灵、意识是随着人的整体共同发展和进化而来的,人的大脑并非是上帝额外赐予人类的。人的内在世界的发展是在自然的外在世界内进行的。德国哲学家布鲁诺·伏格曼指出:“人类就交织在生命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在这条进化链中,人是与整个进化之链前后相连的一环。
人所以为人,要归功于过去的许多世代,亦即过去的全部生命。”( 伏格曼,2001: 14) 莫兰也说: “原人进化过程不能仅仅被设想为生物进化过程,或仅仅是精神进化过程,或仅仅是社会进化过程,而应当被设想为是遗传、环境、大脑、社会和文化相互干预产生的多方面的形态发展过程。”( 埃德加·莫兰,1999:43) 所以,身与心是不可能分离开来的,身体是人的“第一自然”,它以物质形式承载着心灵,它既有心灵的潜能又有物质的潜能,是二者有机结合的最高现实性。身体不但是使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且也是使人介入一切自然活动的主体。身体是人向自然开放、与外部交换能量和信息的条件,也是使人的精神力量向自然界展示的主体,世界是通过身体赋予人的。心灵离开身体就失去了依存条件,也无法向外界显示自身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心物分离的二元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主客观分离的看问题方式,才能走出简单性研究问题的方式,取而代之的将是身与心、人与世界作为整体的范式,大脑在人体之中并与它不断交换能量和信息,人的身体又在世界之中,并以身体为中介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这种观念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已成为一个基本观念。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尼古拉·哈德曼在《存在学的新道路》一书中,将世界的构成分为物质的、有机的、心灵的和精神的四个不同层次,而且每个层次都有其构成性物质和存在范畴。物质层次是由无机物质构成,其存在范畴包括空间和时间、过程和状态、有实体性和因果性、动力构造与动力平衡等物理特征; 在有机层次中,构成成分是有机结构,其存在范畴是适应性、合目的性,有新陈代谢、自我调解、自我再造、类生命、类稳定、变异等生物学特征; 在心灵层次的范畴显示了行动和内容、意识和无意识、快乐和忧伤等生命特征,这一层次的构成主要是灵长类等的高级动物;最后的精神层次只是由人构成的最高存在层次,只有这一层次的存在物才具有思想、意识、意志、意愿、自由、评价、人格等精神内容和特征。这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是每个较高层次的范畴都必须依赖于较低层次的范畴,而低层次的性质特征也都向上一层次延伸,即在最高层次的人类精神范畴应拥有所有下面三个层次的性质和特点。哈特曼就是用层次范畴理论阐明身与心、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的。( 哈特曼,2007: 24-30)复杂性科学就是以这种整体主义观念作为基础的。莫兰就曾指出,人是“在人性中整合了动物性,在动物性中整合了人性”,人不仅具有理性的思维,同样有感情和情感,有想象力和欲望与激情,人就是一个多样的、统一的复杂性整体。他说,“人是一个生物的存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的超生物的存在,生活在一个语言、观念和意识的世界中。但是对于这两个实在,即生物的实在和文化的实在,简单化的范式迫使我们或者分离它们,或者把最复杂的东西还原为比较不复杂的东西。因此,人们在生物系中研究生物的人,把它作为一个解剖学的和生理学的存在; 人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中研究文化的人。
人们将大脑作为生物器官来研究,人们将精神 themind 作为心理学的功能或实在来研究。人们忘记了一方没有另一方也不存在,甚至还有一方同时是另一方,虽然它们被用不同的词语来探讨”.( 埃德加·莫兰,2008: 59)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译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我们研究语义问题时不去思考语用问题,研究词语时又忽视句法,研究句法时又不去考虑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在讨论文化时忘掉了文化因素常常隐藏在词语和语篇之中,脱离文本去谈文化,在强调文本时,作者就必须“死去”,在强调读者时,文本都显得多余,如此等等。这些显然都是受简单性思想的影响,缺乏整体主义看问题的方式。
复杂性科学强调人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的特点,但人和世界又不可分割,人的进化与发展是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完成的,所以人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特征。莫兰曾指出,“人的多方面构成使他内含了大脑-精神-文化的相互作用的圆环,理性-感情-欲望的相互作用的圆环,个人-社会-族类的相互作用的圆环。人类具有共同的统一本质,但在自然形态上,特别是在文化形态上又是多样的。人的可塑性还使每个人包含着多重潜藏的可能性格,使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可形成不同的心理性格或扮演不同角色”.( 陈一壮,2007: 100-101)我国老一辈哲学家张世英曾把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与人-世界的整体主义认识方式做过对比。( 张世英,2004: 23-26) 他认为主客二分认识方式有如下三个特点: ( 1) 具有外在性,即人与世界彼此分离,各自独立,人只是世界的旁观者; ( 2) 体现人类中心思想,主张主体是主人,客体服务于人,听命于人,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备于我”; ( 3) 认识功能是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惟一桥梁。这种认识不仅排除了人的各种感性认识,也抹煞了人的情感和欲望、主观目的和道德伦理等等,使人成为理性的存在而没有非理性的任何特征。与此相反,人-世界整体主义的认识方式有不同的特征: ( 1) 人与世界的内在性关系,即人融于世界之中,是它的一部分,尽管人并非与世界同时形成,但只有有了人,世界才有了意义,它们是彼此相互规定和相互构建的关系;( 2) 人与世界的非对象的关系,即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人,世界也不再是人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 ( 3) 人与世界万物的相融相同。这就是前面所论述的,在宇宙进化的四个层次中,虽然人作为精神层次具有最高位置,但它以下的各个层次的范畴和属性特征无一不可以在人的身上找到,人不是超越它们而独立存在的。正如莫兰所说: “这个复杂过程向我们表明人类的产生不仅是自身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适应的产物,而且是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和结合的结果。”( 陈一壮,2007: 96)身与心的弥合也必然导致人与世界的弥合,因为身体是内部承载心灵而对外部世界开放和沟通的中介。这样,传统的认识观就变成了具身性认识。
这种具身性认识是把存在论与认识论结合的结果,即从事认识活动的主体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也被卷入认识之中,人既是认识者也是被认识者,既是主动者又是被动者。身心的弥合,必然导致具身性的认知。
二、具身性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是对标准认知理论的挑战
具身性认知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兴起的一种新的认知理论,在它之前流行的认知理论现在称为标准认知理论,它也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学科,是上个世纪中期才刚刚开始的,现在具身对标准认知又发起了挑战。我们都知道对认识的研究历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想要解决“我们知道如何知道”的问题。一般说来,研究知道什么不一定是困难的,难的是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因为这必然涉及我们大脑的组织构造、工作机制、运行轨迹等等,而这一切又须利用大脑的活动去了解( 知道) .
一旦认识者同时又成为被认识者必将造成难以超越自身的困难。标准认知科学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因为它正如 1980 年版美国百科全书所说的,是“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学科,即研究人接受、编码、操作、提取和利用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知觉、语言、智能、表象、思维、推理、问题解决、概念形成和创造性的科学”.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限定在信息加工的基础上,并把大脑看成是类似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认为人与计算机在功能结构和信息加工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涉及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存储和提取,信息加工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等等。所以这种研究基本上是以两者的比较与模拟来研究人的认知过程的。这样的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脑在人的身体中,而人的身体又在世界中,它不是一个悬浮和孤立的结构,身体是外界一切信息的来源,它与大脑相互作用并交换信息。上述的标准认知理论给人感觉是大脑只是一个被动加工器,而且一切活动只是心理活动而与物理活动无关。范·盖尔德曾给标准认知作过如下描述,他说,“因为认知系统只在符号表征中运行,因此人类身体和物理环境可以抛开不予考虑,人们有可能将认知系统看成是一个其功能不过是把输入表征转化为输出表征的、自主的、无身的、无世界的东西进行研究”.( 劳伦斯·夏皮罗,2014: 139) 具身性认知是把身体提高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它成了人始终不可或缺的成分。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把身体的概念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他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做心理 - 物理事件或事态,其核心内容是给人类经验的东西确立和赋予意义,而意义的实现给心理-物理的性质提供了最终意义和价值”.( 汪堂家,2012: 276) 这里所谓的心理-物理就是指身心的合二为一的整体,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是以身体为中介的,它一方面承载心灵,另一方面又以物理形式置于世界,形成心理 - 物理的认识方式。
所以杜威说: “事实是,经验的器官,即身体、神经系统、双手和双眼、肌肉和感官是我们接近非人的世界的手段。”( 汪堂家,2012: 277) 杜威的哲学属于经验自然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经验是人类事务的惟一材料,因为人的意识并不与世间事物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身体的各种器官与它们打交道,只有身体才一方面与事物相通,另一方面又与意识相通,是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中介,否则我们的意识无法同外部世界建立连接。同时,身体也不仅仅是被动的接收器,而是能主动影响经验对象的施动者,经验中的人的因素是通过身体来赋予和实现的。我们知道人们的意识也往往需要经验的验证和证实。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当我们产生了虚假的意识时,如做梦,或我们听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好( 坏) 消息,为了证实它是否是经验世界中真实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掐一下大腿,看是否有疼痛感。这就是用身体的感觉来验证意识中的事情最为常见的情况。这说明身体与意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具身性认知被提到认知科学中来,并形成对标准认知的新的挑战。
哲学家安迪·克拉克也是一位具身性认知方面的先导者,他认为这种认知具有六种属性,其中心思想是说身体并不是大脑的纯粹容器,或者说得好一些是脑活动的贡献者,事实上应该把身体看作在产生认知时的脑的搭档。身体融合了被动的动力学,组织了信息,并决定了有助于创造知觉体验的独特的感官特征。身体和脑对它们之间的认知劳动进行了分工,分担了单凭自己无法完成的过程。( 劳伦斯·夏皮罗,2014: 73) 而法国认知科学家瓦雷拉,加拿大哲学家、心智科学家汤普森以及美国心理学家罗施,三人在1991 年合著了《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and Human Experience) 一书,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具身性认知的奠基之作。他们先从具身行动的概念入手进行说明,指出“使用具身这个词,我们意在突出两点,第一,认知依赖于经验种类,这些经验来自具有各种感知运动的身体; 第二,这些个体的感知运动能力自身内含( embodied) 在一个更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的情境中。使用行为这个词,我们意在再度强调感知与运动过程、知觉与行动本质上在活生生的认知中是不可分离的。的确,这两者在个体中不是纯粹偶然地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演化合为一体的”.(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2010: 39)另一位认知学家艾丝特·西伦对具身性认知作了一个更具体的定义,她说,“说认知是具身的,这意味着它产生自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从这一观点出发,认知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体验,这些体验源于具有特定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其中知觉和运动能力是不可分离的,并且它们一起形成了推理、记忆、情绪、语言以及心智生命所有其他方面被编织其中的一个母体( matrix) ”.( 劳伦斯·夏皮罗,2014:61) 从以上诸人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认知的具身性就是把脑、身体和环境世界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认知的动力系统,不是仅把认知任务交给大脑去完成,而是把它交给这三者,在它们相互作用中去完成。进行具身认知研究是晚近的事,但对身体各种感官关注却是在以前的不少艺术家和哲学家那里就得到了重视。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早就在他那部著名的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对视觉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 “视觉不仅是眼睛的事情,谁都知道,理智的记忆和思考总是伴随着视觉,而思考则总是以实体来填补呈现在眼前的空洞形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2009: 50)语言文字所给予我们的是抽象的符号,但它们却唤起读者的记忆和联想与想象,用他曾经历的世界的经验去填补这些空白,同时引起相关的情感。
这一过程显然不是大脑能独立完成的。试想一个天生的盲人如何用想象去体味大海的苍茫,高山的雄浑? 一个天生的失聪者又如何体会《命运》交响曲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 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和经验的世界给予了我们真正的意义,文学作品只不过是通过语言文字将它们再现出来,所以人们说雕塑、绘画、舞蹈是表现的艺术,文学是再现的艺术。劳伦斯·夏皮罗批评标准认知科学时说: “一种对语言的理解---它反映了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是从源于供给量的能力建立起来的,而供给量的意义是身体属性的功能。所有这些思想者都确信,标准认知没有并且也不可能阐明某些基本认知现象---颜色知觉、概念习得、语言理解---因为它忽略了具身性的重要性。”( 劳伦斯·夏皮罗,2014: 25) 这里夏皮罗所说的“供给量”就是人们的世界经验,供给量越充足,人们对世界理解得越深刻,经验也越丰富,所以缺乏生活阅历或没有情感经历,涉世不深的人很难去读懂一些文学作品的内涵,也难以用他的经验去填补文学留给我们的空白。由于经历与经验各人都不尽相同,有时会带有私人性质,所以读到一句话,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根据他们的经验而产生不同的联想与想象,那么他们对它的理解也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增加了理解或翻译的复杂性。瓦雷拉等引用马克·约翰逊的话说: “理解是一个事件,在其中一个人有了一个世界,或者更恰当地说,理解是一系列正在发生的相关意义的事件,在其中一个人的世界出现了。这种理解观念很早就被大陆哲学所认识,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中。但英美分析哲学由于把意义看成语词与世界之间的固定关系而始终抵制这种倾向。它错误地认为: 只有一个超越了人的具身性、文化的纳入性、想象的理解和定位于历史演化中的观点,才能保证客观性的可能性。”(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2010: 120)海德格尔的“此在”是一种“在世的存在”,实际上就强调人与世界的整体关联,而不是大脑的意识功能和与之不相关的外部世界相对立。伽达默尔所强调的对话参与者的“前理解视域”也是以个人以往的经历与经验去参与文本阅读并与文本对话。所谓视域融合并非是两个视域的契合,而是有争辩、有交锋、有碰撞、有被说服、有膺服,最后是读者原来视域的扩大甚至改变,从而生成新的意义。所以,翻译,甚至是普通的阅读,意义是不可能“确定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一个物体就是相连属性的一个集合”.( 皮亚杰,2005: 102) 约翰逊也说: “意义包括了具身经验的模式和我们感知力( 如我们的知觉或自我定向的模式,以及与其他物体、事件或人相互作用的模式) 的前概念结构。”(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2010: 120) 我想这两个人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尤其是他的“前理解”概念。
在翻译这种跨文化的交际中,不同文化同样会给翻译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对濡染于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来说,对同一个事物,人们会有不同的联想和想象,甚至不同的情感。这不是表现在事物的概念上,而是表现在观念上。我们知道,从概念上来谈翻译是十分容易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用来表示事物概念的词语无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概念。但观念则很不一样,尤其是文化观念,它无声地向人们传递着一些信息或情感,这些信息和情感是生活世界潜移默化地传递的,同样也有具身性质。
夏皮罗在他的著作中举了两个常见事物,“钥匙”和“桥”.他指出它们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中居然文化观念大相径庭,虽然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相互对应的概念。他指出“钥匙”在德语中和表示“阳刚”之类的形容词一起使用,如“硬的、重的、粗糙的、金属制的、锯齿状的、有用的”等等。但在西班牙语中,它却与阴性的词连用,因为它是阴性的,可用“娇柔、小巧、可爱、闪亮、金色”等词语修饰。同样,“桥”也是一样,文化和情感很不相同,在德语中“桥”与美丽的、优雅、脆弱、安宁、漂亮、纤细等阴性词使用; 而在西班牙语中该词却含有大的、危险的、长的、强壮的、结实的、矗立的等含义。如果两个欧洲国家的语言都有如此不同的文化内涵,那么,中国和英美西方的文化差异又该如何呢? 可见文化观念的形成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亲身( 具身) 体验形成的。所以具身认知已从各个方面颠覆了标准认知的观念。可以说,标准认知仍然没有摆脱笛卡尔式的认识观念,而具身性认知则走出了主-客二分的窠臼。
三、具身性认知与翻译活动
我们强调具身性是努力恢复被抽象理智掩盖的感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为在传统认知中感性经验完全被理智抽象了,文学语言不同于哲学语言之处就在于文学语言是可感的,而哲学语言则是不可感的。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艺术和文学是可见的( visible) 文本,而哲学文本是不可见的( invisible) 文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学是“感性的诗学”,而哲学则是“思辨性”的。文学、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它的存在是为了被感知,被作为它的欣赏者的我们感知。……它是只能实现在知觉中的一种感性事物的存在”.( 杜夫海纳,1996: 615)在标准认知中我们把它们当成“作品”了。这里“审美对象”不同于“作品”,“作品”是可以作为客体进行客观研究的,如我们可以研究它的结构、它的主题、它的组织材料的方式、写作的背景或时代特征以及作者写作意图或他的出身和背景等等。但是这些与成功地翻译一部作品关系不大( 当然不是说没有一点关系) .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来翻译,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文学语言虽然也是用文学符号进行创作,记录了人们所经历的事件,所体验过的事物,但这些文字是富于感性的文字,是可见、可感、可触、可嗅的文字,它们能唤醒人们的回忆和记忆,让过去的经验和经历在身体中“复活”,用想象和联想让它们再次真实地“重演”,而不是用理智判断去代替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不是用知识来说明知觉,而是从知觉出发去说明知识。我们为什么说“春风又绿江南岸”要优于“又到”、“又入”、“又满”、“又过”呢? 这就是因为这个“绿”字是可见的、可感的,它唤起我们对“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江南春天景物的联想,而“入”、“到”、“满”、“过”则不能,它们失去了与事物的原始联系,而“绿”字却把视觉变成一种景象、一种思想。梅洛-庞蒂说:
“思想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 梅洛-庞蒂,2007: 63) 这里梅洛-庞蒂为我们指出了知觉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可见者的本性就是拥有严格意义的不可见衬里,使它作为某种不在场呈现出来”.( 梅洛-庞蒂,2007: 86-87)例如,乔纳森·尼古拉斯有一篇散文,The FirstSnow,写一位父亲和襁褓中的小女儿在黎明前一起在房间里观赏第一场雪的情景。孩子的母亲仍在睡梦中,父亲抱着女儿轻轻地来到楼下厨房,在那里观看女儿出生后迎来的第一场雪。他抱着孩子下楼时那一句是这样写的:
He carried her downstairs,counting the creaks onthe way. Together,they settled in at the kitchen table,and adult in him slipped away. Two chilidren now,they pressed their noses against the glass.
句中 counting the creaks on the way 是指为了不打扰妻子的睡眠,这位年轻的父亲没有打开灯,而是凭借查数木楼梯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悄悄下楼。
这就是用他的身体动作在说话,在表达他对妻子的关心和爱意,这种不可见的“衬里”,是把背后的思想和情感传达出来,这种思想和情感在文本中是“不在场”的,在场的只是查数楼梯所发出的响声和蹑手蹑脚地下楼的脚步动作。我们只能从这“在场”的“数着楼梯发出的响声”来推测“不在场的”,即为何要数响声呢,因为屋里尚暗,怕下楼伤了婴儿; 那么为何不开灯呢,因为那样会影响妻子。如果没有这种“衬里”和“不在场的”思想和情感与爱意,那么,这段描写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见到的两个译文中,居然都把这句话译成:
他抱着小女儿往楼下走,小心翼翼地,唯恐弄出一点声响,他们在厨房的餐桌边站定。此时,他觉得心中那种成人的感觉溜得无影无踪了。现在是两个孩子,鼻子贴着玻璃看雪。
译者可能觉得,楼梯弄出响动会影响妻子睡眠,所以就明目张胆地改变了原文,变成“唯恐弄出一点声响”.说明译者没有弄清楚作者正是用动作在说话,在表达内心的思想,只是作者把这些作为“不在场”的“衬里”来处理。只把身体的动作呈现给读者,这种动作是感性的、是形式,而“衬里”和“不在场”的才是思想和情感。杜夫海纳指出: “形式永远是感性的形式。因此,它介入材料之中,材料的效果就是感性。……这时形式已经是意义了。……所以意义和感性的这种统一就超越了自己,变成表现,亦即审美对象的最高形式和它的意义的意义。”( 杜夫海纳,1996: 174)我们学习具身性认知对于我们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深入学习这种新的认知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本质,以便更好地做好翻译工作。当然,这一理论是十分复杂的,要举的例证也不胜枚举,因篇幅所限,不赘述。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 复杂性思想导论[M]. 陈一壮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埃德加·莫兰。 迷失的范式: 人性研究[M]. 陈一壮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布鲁诺·福格曼。 新实在论[M]. 张丹忱译,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1.
[4] 车尔尼雪夫斯基。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 周扬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 陈一壮。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评述[M].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6] 杜夫海纳。 审美经验现象学[M]. 韩树站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7] 劳伦斯·夏皮罗。 具身认知[M]. 李恒威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9] 梅洛-庞蒂。 眼与心[M]. 杨大春译,上海: 商务印书馆,2007.
[10] 尼古拉·哈特曼。 存在学的新道路[M]. 庞学銓译,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11] 皮亚杰·加西亚。 走向一种意义的逻辑[M]. 李其维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瓦雷拉·罗施。 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M].李恒威等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3] 汪堂家。 哲学的追问[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4] 沃勒斯坦。 所知世界的终结[M]. 冯炳坤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 张世英。 新哲学讲演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