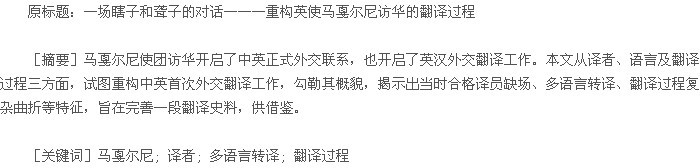
1 引言
为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联系,扩大对华贸易,1792 年 9 月 26 日,受乔治三世国王派遣,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领规模宏大的使团踏上了访华征程,开出了中英两国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清廷则藉此机会极力操控英国使团,企图将英国纳入朝贡体制。由于双方相互了解甚少,且各怀目的,这次外交不啻为一场“瞎子和聋子的对话”,并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次外交成为中英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虽有学者涉猎英使团访华的翻译研究领域,并出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王辉,2009;葛剑雄,1994;王宏志,2009),但仍难一窥此次外交翻译工作的全貌。本文从译者、语言及翻译过程三个方面系统重构中英首次外交翻译工作,勾勒其概貌,揭示当时合格译员缺场、多语言转译、翻译过程复杂曲折等特征,旨在完善一段翻译史料,供借鉴。
2 译员
毋庸置疑,译员是任何翻译行为的主体。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都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在物色翻译人员上面颇下了一番功夫。
英方在筹备使团的过程中就深感寻觅合适译员之不易。在 179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向中国派遣外交使团的决定之后不久,英国外交大臣邓达斯在1792 年 1 月 8 日指示马戛尔尼尽快着手罗织翻译(Pritchard,1970:275)。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随即被派往法国巴黎( ibid:278),随后又辗转到意大利,最终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①(Chi-nese College) 物色到两位中国神甫,周保罗(PaoloCho) 和李雅各②。这两位中国神甫不懂英语,但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正好使团中少数高级成员懂拉丁语。斯当东说他们“能胜任其母语与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之间的翻译”(ibid,292),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评价过于乐观。
使团抵达澳门后,翻译周神甫害怕为外国人工作受中国政府惩罚,执意辞职,并与两位搭船回国的华人神甫上岸,只剩下李雅各一位翻译。李神甫并非理想人选:他少小离国,对中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中文水平不高,且完全不熟悉清朝官场礼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梁栋材 ( Jean-Baptiste-Joseph deGrammont) 在写给驻澳门西班牙办事处的信里谈到英使团失败的原因,说问题“可能出在李神甫(娄门)身上,他对宫廷礼仪习俗全然无知,甚至不如他的英国主人”(戴廷杰,1996:138)。斯当东也承认,李雅各不熟悉中国的官方话语和文书规范,不能圆满地完成翻译任务,有时甚至把一些客套话误解为认真的承诺(Staunton,1798,Vol. II:136;Vol. I:330)。
副使的儿子、大使的见习童子、12 岁的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自参团后便一直跟几位中国人学中文,进步较大,“需要时,他的确能充当一名相当可以的翻译”(佩雷菲特,1998:88)。这样,英国使团访华期间的翻译工作就落在李神甫及一个英国小孩的肩上(同上,88)。
清廷对翻译工作也非常重视,但情况不容乐观。
乾隆 57 年(1792 年)10 月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有关英国国王遣使来贡的奏折后,乾隆皇帝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执,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军机处档案:91)。次年 8 月,皇帝专为翻译的事下了一道谕旨,称“英吉利国遣使航海远来祝寿纳贡,照例令监副索德超前来热河照料通事带领,著赏给三品顶戴。至索德超业经加恩,所有监正安国宁著一体赏给三品顶戴,其索德超带同前来之西洋人贺清泰等,俱著加恩赏六品顶戴”(一史馆,内阁档案:10)。清廷为传教士们加官晋爵,成立了以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为首的、由 7 名欧洲传教士组成的“翻译团队”。然而,这些传教士不懂英文,而且像索德超这样的葡萄牙人出于嫉妒,仇恨英国人,对英使团提出的正当要求百般阻扰,且在使团离开中国之后,仍散布谣言,力图破坏英使团的声誉(马戛尔尼,2006,36 -37)。
当然,英国人也有支持者,法籍和意大利籍传教士们对英使团的态度则友好得多,如第二道敕谕的拉丁译文出自法籍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和罗广祥(Nicholas Joesph Raux)之手,他们把原文的口气译得和缓些,并在事后写信告诉马戛尔尼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敕谕中塞进一些对英王陛下致敬的词语”(戴廷杰,1996:137)。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对待英使团的态度各异,主要与他们本身的宗教利益和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相关(袁墨香,2006)。总之,清廷的译员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嫌,很难做到忠实客观。
中英双方都不具备本国职业外交口笔译人员:英方聘请了不懂英文、汉语也蹩脚的中国人作为翻译,而中方启用了不懂英语的欧洲传教士作为译员。
英国人来华贸易可追溯到 17 世纪 30 年代③,然而160 年过去了,中英双方却还不具备通晓双语的翻译人才,这主要是中国明清两朝实行“闭关锁国”造成的。明末海禁,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曾一度希望英王詹姆斯一世能写封信给中国皇帝,获准英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但该公司驻万丹(Bantam)的主管在 1617 年写信泼冷水说,“没有中国人敢翻译并呈递这些信件;根据该国法律,这样做是要获死罪的。”(Mores,1926,Vol. I: 10)后开放港口通商,但仍严厉限制外国人与中国人接触。英国商人与中国官员交涉需通过中国通事,但中国通事大多英文水平低下,操一种新奇难懂的“中英混杂行话”(pidginEnglish) ,且地位低贱,稍有差错,轻者挨骂挨打,重者 投 监 砍 头 ( Bannister,1859,129,131; Morse,1926,Vol. I: 97,103) 。
正因如此,为拥有自己的翻译,1736 年英国“诺曼顿号”船长于宁波贸易时,曾留下一英国少年,让他偷学中文,此人便是洪仁辉(James Flint)。没曾料到,此举导致了 1759 年的“洪仁辉事件”④。之后为“防范于未然”,清政府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1759),其中第四条规定,“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积弊”(一史馆,《朱批奏折·外交类》第 37 号)。在广州的外国人受到更加严密的控制,而中国人就更不敢与外国人交往。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时,之前洪仁辉、末文和巴顿(Thomas Bevan and Barton,1753 年由东印度公司派往南京学汉语) 等英国苦心经营培养出来的译者均已作古,所以使团无法物色到理想译员。
清政府虽然有培养译员的外事机构,如清初设立的会同馆和从明朝接手过来的四译馆,分别主管朝贡外交和翻译事务,但除使用汉字或东方语言的周边朝贡属国外,四译馆根本不可能胜任涉及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18 世纪初,中俄交涉日趋重要,清廷于 1708 年设立了俄文馆(在 1862 年并入同文馆),还于 1729 年设立了翻译馆,“教授旗籍子弟以拉丁文,俾能在中俄交涉中任译事。”(费赖之,1995:690)。但据钱德明神甫说,翻译馆“仅存 15年,诸馆生从未任译员”(同上,515)。这些举措都是因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没能培养出能应对半个世纪后以对付英国为主的外交翻译人才。因此,当马戛尔尼使团在 1793 年叩开中国的大门时,清廷照向例,沿旧制⑤,派出久居宫中、不懂英文、不了解英国实情的葡萄牙等国传教士来负责翻译工作。
中英首次外交翻译是在合格翻译人员缺场的情况下,由临时拼凑起来的不懂英语的译员们完成的。
3 语言
双方译员都不懂英语,语言障碍是中英双方面临的巨大困难。所幸在十八世纪末,拉丁语仍在天主教会中占主导地位,中英双方译员的同门宗教背景,使他们都掌握了拉丁语。双方沟通时并不是中、英两种语言间的互换,而要借助第三种语言———拉丁语来实现:通常是先把中文或者英文翻译成拉丁文,再换成双方各自想要的语言。
这种翻译模式所带来的语言方面的复杂性和译员配置的多元化,由下列事实可见一斑。英国使团到达天津白河入海口时,为接洽上岸事宜,派出翻译李雅各、懂拉丁语的赫脱南(Hüttner,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和坎贝尔少校(Campell)与中国官员接触(Morse,Vol. I:326)。这其实就是一支“多语翻译小分队”。
事实上,中英双方多采用这种中介语翻译模式进行交流,极其不便。在英国人看来,正是复杂的翻译程序减少了乾隆皇帝对英使团的兴趣。副使斯当东推断,“皇帝同特使直接谈话的次数不多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礼节上的限制,也不是由于皇帝对欧洲事务不关心,而完全是翻译上的麻烦,使谈话无法正常进行”(斯当东,1994:406)。在觐见仪式上的一幕也印证了斯当东的推断:双方谈话需几道语言翻译,非常麻烦,所以乾隆皇帝询问英使团中是否有能直接说中国话的人,当小斯当东被领至御座前讲了几句中国话后,乾隆异常高兴,竟将随身所带的槟榔荷包赐予小斯当东(同上:368)。
多重语言障碍不仅体现在口头传译上,书面文件的翻译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英方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经过多重翻译,备有多种版本。据考证,清廷收到的“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就有英、汉和拉丁文三种版本;而马戛尔尼有关觐见乾隆的仪式照会竟然有中、英、法和拉丁文四种版本,因为当时法语是欧洲通用的外交语言(Pritchard,1970:334)。中方的文件也经过多重翻译,首先由传教士翻译成拉丁语,尽管使团中有不少成员懂拉丁文,但有些文件最终仍被翻译成英文。经过如此几重转译甚至重写之后,文件原义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在南归途中,马戛尔尼于 1793 年 10 月 21 日拜访了负责护送英使团的大臣松筠,就第二道敕谕中有关“欲将英吉利宗教传到中国”的敏感内容(Granmer Byng,2000:166 - 7)进行交涉。为确保出使成功,以维护英国在华贸易利益为重,马戛尔尼从未提过传教问题,所以觉得被冤枉了。松筠解释说,“至少在中文和满文的文本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如果在拉丁文本中出现如此内容,那么它应是翻译失误或中伤”(ibid:167)。其实,第二道中文敕谕中确有不许传教的内容(一史馆,军机处档案:172 -5),拉丁文翻译并无错误,松筠借多重翻译易致不实来推脱。在翻译史上,这也许是以翻译错误为由,掩饰谈判分歧的少见例子。
语言障碍所带来的困扰使英使团苦不堪言,英国想要与中国正常交往,就必须首先解决语言问题。
1793 年 11 月 20 日,马戛尔尼在从苏州到广州的途中与长麟会晤,递交给他一份草案,提出改善广州贸易现状的 11 点要求,其中第 9 条是“准许中国人用中文向英国商人灌输知识,使其能更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和习俗”(Morse,1926,Vol. II: 253)。马戛尔尼巧妙的外交辞令,外柔内刚,不仅是对《防范外夷规条》中有关内容的挑战,而且透露出通盘掌握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主张。这说明拥有丰富近代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充分认识到语言和文化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
4 翻译过程
由于双方译员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双重语言障碍,翻译活动进行得异常艰难,特别是一些重要文件的翻译,其过程可谓曲折离奇。
4. 1 百灵致两广总督的信件翻译
1792 年 9 月 20 日,马戛尔尼使团起航的前 6天,一支由三人组成的秘密监督委员会已到达广州,他们向清廷报告英使团将前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消息。秘监会主任波郎(Henry Brown)将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致两广总督的信函交给广东巡抚郭世勋,信函有拉丁文和英文两个文本,郭世勋收到信函后,马上把拉丁文本交由一位中国通事翻译,而英文文本则交由行商和英国专员一起翻译(Pritchard,1970:289)。郭世勋在确认了英国遣使访华的信息后,当即奏明朝廷,并附上信函的拉丁文和英文原文以及两份中译文。这两份由郭世勋组织人员进行翻译的译文内容大致相仿,即英国为了补祝乾隆八十寿辰而派遣使团到中国来,并借此机会讨论有关两国商贸事宜,两份译文都正确地传递出了信函的主要内容⑥。乾隆令在京西洋人重译这两份信函,结果译员只认识拉丁文本,不认识英文文本,译文经核对与郭世勋的译本大概相同(一史馆,军机处档案:91)。清廷对文件进行校译甚至重译并非偶然现象。清廷档案中记载,英国国王写给乾隆的表文以及马戛尔尼递交的呈词等文件都经过在京传教士的查核或者重译(同上:14;203)。
4. 2 礼仪照会的翻译
马戛尔尼以何种礼仪觐见乾隆皇帝,中英双方分歧很大:中方希望马戛尔尼行磕头礼;马戛尔尼却提出条件,假如坚持叫他磕头,那么,一位同特使身份地位相同的中国官员必须朝衣朝冠,在英王御像前行同样的磕头礼。为阐明此意,马戛尔尼向清廷写了一份照会。由于事关重大,“为避免由于误解而发(产)生不利影响,必须把它最正确地译成中文。”(斯当东,1994:321)使团翻译李雅各中文生疏,更不熟悉官场文书的体裁格式,显然不能胜任翻译照会的工作。据斯当东所述,照会的汉译是在罗广祥神父特请来的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的帮助下完成的(同上:324)。这位中国教徒古文造诣高,熟悉官文格式,完全能够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但他很害怕参与国事得罪官方,更怕笔迹被查对出来招致祸灾。最终,这份照会经极富传奇色彩的过程翻译出来:英文原件先由赫脱南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李雅各译出汉语大意,再由中国教徒对其加工润色,使其符合中国官方文件的行文路数和格式,最后由小斯当东誊一遍并签名作为正式信件。
一切完毕之后,为使中国教徒放心,当着他的面撕毁中文原稿(同上:324)。
照会翻译的复杂程序并非特例,后来这一切又在热河重演。由于和珅有意回避,不给马戛尔尼商谈正事的机会,后者只好借助信函与之交流。李雅各找来一位中国人,向他口述了马戛尔尼信函的大意,那位中国人再将其“之乎者也”地加工成合乎官文格式的函件,再由小斯当东抄写并签名,最后作为正式信件送出(同上:375)。
这次中英外交活动中的文件翻译大都在中国“朝贡制度”强势话语权语境下展开。不管是交由中方进行翻译还是英方自己提供译文,经过复杂的翻译程序后,行文最终须遵循中国官场话语规则和格式规范。这样,英方不可避免地陷入语言陷阱,因为中国官方话语和文件格式本身就有尊卑贵贱之分,如英国的信函为“禀”、中国皇帝的答复为“敕谕”、提及“大皇帝”要提行顶格等。英方的翻译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归化了,而这一归化的严重后果是,英方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置于朝贡国的地位。
尽管中英首次外交所经历的蹩脚翻译并非导致英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访华所定的基调及亲自操控,通过语言和翻译产生了预期效果。正如一英国人评价马戛尔尼使团时所说的一样,“使团受到中国人超乎寻常的友好接待仅是计谋,他们以此鼓励重复如此令人愉快的访问。英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未引起重视,这从不断施加在广州的英国人及其他外国人身上的傲慢和侮辱就可看出。给中国人留下的仅有永久性印象是,英国被迅速列入了朝贡国名单。”(Pritchard,1970:377 -8)
5 结语
基于译者、语言及翻译过程而对中英两国首次外交翻译工作的回溯表明:双方都没有合格的翻译人员。英方在出发之前匆忙找来没有任何翻译经验、甚至根本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充当翻译;而清廷则依仗不懂英文的传教士任翻译。不合格的译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多种翻译语言和复杂的翻译程序。由于双方译者都不懂英语,于是产生了以拉丁语为中介语言的间接翻译;由于英方翻译中文水平低下,再加上清廷严格控制国人与洋人的交往,一份文件除了要经过两重语言转换,还需专人对中文加工润色,并另请他人誊抄签名。中英首次直接文化碰撞在翻译上的反映是“归化翻译”策略。中方持强势话语权主动归化英方,而英方则由于有求于中国,翻译不力,难逃被归化的厄运。这些都对当下翻译研究和实践探讨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