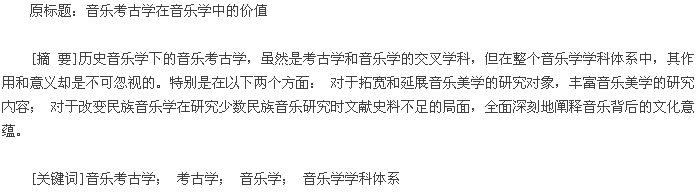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 1930-1931 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 杨荫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 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第一分册·夏商) 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 民俗学) 、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 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 “它( 音乐考古学) 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 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 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
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 300 万年的历史; 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 17 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 4000 年左右。从 300 万年前到 4000 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 “开( 夏后启) 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
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 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25 支骨笛,据碳 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 8000-9000 年; 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 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
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 20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
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 “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
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 “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鼍也”、《诗经·大雅》: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3015 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 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 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 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 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
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 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 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 考 文 献]
[1]李纯一。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6.
[2]王光祈。 中国音乐史[M],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9.
[3]李 凌。 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杨荫浏[C]. 台北: 中国民族音乐学会,1992: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