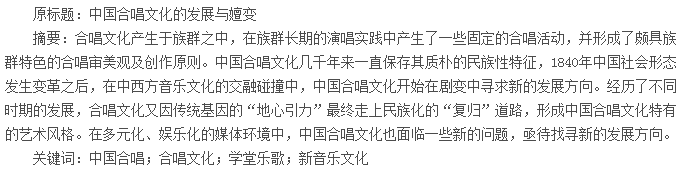
合唱是一种多声部音乐,是声乐演唱的形式之一。
合唱文化产生于族群之中,在族群长期的演唱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固定的合唱活动,并形成了颇具族群特色的合唱审美观及创作原则。中国合唱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族群中形成的,必然要受到这个族群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的影响,受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制约。
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巨变,合唱文化必然随之改变。“音乐作为特定时代的生命表现,它总是特定文化的产物”[1].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碰撞中,中国合唱文化曾一度脱离本民族的音乐传统,在剧变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又因为传统基因的“地心引力”最终走上民族化的“复归”道路,形成中国合唱文化特有的艺术风格。
一、中国合唱文化的原始形态
多声部民歌可视为中国合唱文化的原始形态。因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器乐、乐舞的偏爱,社会礼义道德对多声思维的束缚,致使多声部民歌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形式简单、无创作规范的萌芽状态。也恰恰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原因,中国原始合唱始终保持其质朴的风格,往往随性而至,有感而发。不求音乐形式的丰富和缜密,只求“音随心走”的洒脱状态。
值得肯定的是,多声部民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在中国古代已产生了多声审美意识。在中国传统的社交活动中,氏族间、村寨间会自然地形成一些固定的歌队,在长期的合作中产生了声部的分工,这种声部分工由最初的“依感觉走”逐步走向固定的二部或多部合唱,歌队成员在合作中摸索好听的音程关系。“在这种无数次的往复实践过程中,歌手们逐渐形成了演唱多声部民歌的心理习惯和审美要求,这正是多声审美意识的产生基础和形成多声艺术思维的一个必经过程”[2]24-25.
“‘好听',是民间歌手对审美要求的最自然、最朴素的表述方式,也是他们对艺术美的追求目标。”[2]25劳动号子粗犷的声线和豪迈的气势是劳动者对自己勤劳美的肯定,是劳动者心中最美的音乐;布依族多声部民歌“上脆下莽”的声音安排,“公母分明”的声部特色,“两音相糍”的音程关系是他们认为产生好听音乐的原则;藏族、侗族、傈僳族、羌族等在演唱多声部民歌时无论人数多少高声部只有一人,且由演唱功底强、经验丰富的歌手担任,是因为他们认为众人做低声部来烘托个人高声部所发出的和声是最美的。中国原始的合唱也没有固定统一的创作技法,从“大混唱”的状态过渡到有组织、有分工的“合唱”,多声部民歌的形成依靠的是千百年演唱实践总结的经验。即兴性、自娱性强,没有太多舞台表演的思想,流露出的是“重情感表达、重写意思维”的音乐审美观。
多声部民歌这种“自流”式的生存方式是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人们生产劳动方式制约的,当中国社会无力阻挡帝国主义铁蹄肆意践踏时,多声部民歌这种生存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摧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及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民俗、审美情趣的转变,多声部民歌逐渐出现了消亡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合唱文化的消失,历史淘汰的是无法适应新环境的乐种。
有的多声部民歌在发展变化中融入了新的元素,有的则依然保持原始的风貌,在一定的社会需求下继续生存。
众多的多声部民歌成为展现中国音乐民族性的重要素材,犹如一个家族基因一样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在音乐创作中发挥作用。它是中国合唱区别于世界他国合唱的关键所在。在多元化的音乐文化环境中,是它的存在使得中国合唱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展现出原本属于自己民族的绝代风华。
二、中国合唱文化的发展
(一)学堂乐歌中的合唱文化
“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并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主要途径,仍应以随着新制学堂的建立而产生的学堂乐歌为主。”
[3]28自学堂乐歌开始,中国合唱才开始正式步入多声部音乐的轨道。尽管学堂乐歌中真正的多声部歌曲数量很少,但它开创了中国多声部歌曲创作的先河。正是有了学堂乐歌,中国的合唱才开始起步,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一步步走向成熟。自学堂乐歌开始,中国合唱一改之前在民间“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它先作为人们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武器,在中国音乐教育中赢得一席之地,从此走上“主流”道路,最终成为音乐文化产业中一项重要的艺术精品。
学堂乐歌中的合唱审美观可概括为“富国强兵”、“优美流畅”.“富国强兵”的审美观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反映社会现实、号召性及政治意义浓厚的革命歌曲中。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为了唤起青少年学生、士兵、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音乐课的开设都具有极为神圣的使命,注重通过歌唱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在完善其人格的过程中发挥作用。”[4]
所以,学堂乐歌的情感表现多以振兴中华民族、抵御外强侵略为主。无论是词作者还是演唱者,关注的都是歌词内容的政治意义。很少有人从内心的情感体验来思考学堂乐歌的音乐价值,也很少有人从审美的层面去思考合唱的创作。学堂乐歌中也有少量作品是引领学生热爱生活,宣扬男女平等,倡导新文化,反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等等,学堂乐歌本身也背负了很多其原本不该承担的教育和宣传意义。在辛亥革命以后,学堂乐歌的内容才开始向符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及审美需求方面转变。
在创作技法方面,学堂乐歌绝大多数都是根据现有的曲调填充新词创作而成,曲调多来源于日本、欧美,少数曲调来源于我国民族音调。受作曲者创作水平与艺术修养的局限,很多自作词曲的学堂乐歌实际上也没有受到学生更多的喜爱。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教学水平较低,只有极少数作品会配以简单的钢琴伴奏,大多数曲目是没有伴奏的。由于作曲家也处于学习西方创作技法的初级阶段,所以创作出的合唱曲目难免显得青涩、生硬,音乐语言贫乏。这一时期在创作技法上能够有所突破的代表人物是李叔同,也可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合唱始于李叔同的创作,“优美流畅”的审美观便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最具代表性的曲目就是自作词曲的三部合唱《春游》,创作于留日归来从事师范教学期间。其他的曲目还有《归燕》(四部合唱)、《西湖》(三部合唱)、《采莲》(三部合唱)、《春夜》(齐唱与二部合唱)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旋律优美流畅,歌词清新质朴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二)新音乐文化影响下的合唱文化
所谓新音乐文化时期,指的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各种类型的音乐团体和学术性音乐社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各地,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相继成立。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以称为“新音乐文化时期”.
音乐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合唱作品所占的比例也日渐增高。伴随着国外留学生的归来,中国合唱的艺术性在此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合唱大体上存在两种风格:一是民族韵味较强、曲式结构较为复杂并堪称经典的合唱。这类作品旋律多流畅隽永,脱离当时战乱的社会环境,如一汪清泉,流淌于硝烟弥漫的尘世。二是深刻披露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对现实表达强烈的不满,以“音乐唤醒人民大众团结一致”为创作宗旨的群众歌咏。中国合唱的发展自此也走上了专业合唱与业余歌咏活动两条要求不同、风格迥异的发展道路。
“合唱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富大众化的艺术,是最易凝聚人们内心情感的艺术手段”[5].在新音乐文化时期,中国合唱形成了“抗敌”和“民族性尝试”的审美观。“抗敌”审美观主要体现在黄自和聂耳的爱国合唱作品中。
黄自的合唱作品的艺术特色鲜明,而聂耳的作品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被广泛传唱,鼓舞了大众的士气,更坚定了人民反帝爱国的信念,是那一时期人们坚强的心灵支柱。“民族性尝试”的审美观体现在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无伴奏男声四部合唱《目连救母》以及《西风的话》等学生歌曲中;还有江定仙的《春晚》,李惟宁的合唱曲《夜思》(李白词)、《渔父词》、《玉门出塞》(罗家伦词)等。这些作品凭借生动流畅的旋律、温文尔雅的语句得到了青少年的广泛喜爱。同时,这些作品在演唱用声上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选题都是中国本土的诗歌、故事、风景、民俗。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也显现了黄自“中西合璧”的创作精神。
在双重审美观的影响下,中国合唱创作技法有了“民族化”的倾向。一个是创作题材多选自古诗词或民谣故事;二是不再选用外国曲调填词,而是在民间小调的基础上进行和声编配。例如,音乐家萧友梅的合唱套曲《春江花月夜》(张若虚词,1929年),采用中国传统的多段连缀结构,和声织体建立在西方大小调系统之上,这样大胆的尝试为后来大型合唱作品的创作打开了思路。这一时期合唱作品的创作特点是情感抒发在其次,“民族化创作”则置于在首位。这无疑与当时深受压迫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切的关联,另一个原因则是面对多声创作思维,中国乃至东方民族都是欠缺并需要学习的。由于当时的很多作曲家尚处于对西方作曲技法的学习阶段,对于“中西融合”的创作技法未能融会贯通,所以优秀的作曲家寥寥无几。
除黄自以外,这一时期对合唱创作领域贡献最大的音乐家便是赵元任。在对我国民间音调进行和声编配方面,赵元任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人。他创作的作品如《五更调》、《孟姜女》、《凤阳花鼓》等“对在艺术创作上如何使用西方多声创作技巧同我国传统音调结合积累了最早的实践经验”[3]128.不仅如此,赵元任还在合唱作品中运用调性的变化来体现情感,这在中国合唱界属于首创。他在大型合唱作品《海韵》的创作中,将主题形象感情变化的每一阶段配以不同的调性和声色彩,以表达曲中主人公情绪的变化。这部堪称合唱精品佳作的《海韵》,至今仍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合唱文化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咏唱合唱的热潮。在左翼音乐工作者的领导下,“业余合唱团”与“民众歌咏会”先后成立,这两个组织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起着领导和推动作用。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吕骥、孙师毅成立了“歌词曲作者联谊会”,吕骥、麦新、冼星海、贺绿汀等人又组织了“歌曲研究会”,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创作歌曲。很快,“抗日救亡”的歌声传遍华夏大地。
1938年,“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一个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冼星海、张曙等音乐工作者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日音乐活动中,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抗日热潮已达到顶峰的情况下,合唱的审美观也全部集中在“抗日救亡”这一宗旨上。吕骥、周钢鸣等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明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要“走进工农群众的生活中去”,音乐要“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6]143所以,这一时期的合唱表演多是人数众多、气势雄伟,声音洪亮,号召性强。在合唱的创作上,当时音乐界对其创作方法和目的的要求是“指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乐观的前途,使唱的人和听众明白他们应走的道路,欣然地一齐走上前去”[6]143.因此,这一时期小型的二部合唱曲比较受欢迎。如张曙的《洪波曲》,贺绿汀的《干一场》,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和《游击军》,舒模的《军民合作》,向隅的《红缨枪》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合唱水平有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号召人民抵御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对合唱的创作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要求。实际上,形式简单的合唱曲更容易传唱,易于在短时间内学会,并赢得大众心灵的共鸣。这一时期的合唱作品还有陈田鹤创作的齐唱曲《巷战歌》(方之中词)、二部合唱《兵农对》(卢冀野词),江定仙的齐唱曲《打杀汉奸》、合唱《为了祖国的缘故》等。
当然,虽然形式简单的合唱作品更容易受到群众的喜爱,但并不说明这一时期合唱的创作水平会停滞不前。贺绿汀的混声四部合唱《游击队歌》凭借其旋律的律动、和声的饱满及歌词的豪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贺绿汀还创作了一首无伴奏合唱《垦春泥》,充满了清新明丽的乡土气息。夏之秋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吴伯超的《中国人》,何士德的《渡长江》,章枚的《勇敢队》等合唱作品的产生也都显示了中国合唱的创作水平在稳步提升。而真正能证明中国合唱创作有一个质的飞越是冼星海、郑律成、马可、杜矢甲、何士德等人的大型合唱作品的创作。冼星海广为人知的大合唱“三部曲”《黄河》、《生产》、《九一八》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日的斗志。而郑志声以《满江红》(岳飞词)为题材创作的大型合唱曲(管弦乐伴奏)则预示着中国合唱的发展还会有新的突破。
(四)国统区与边区的合唱文化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音乐运动也随之转为“地下”.在国统区内,很多宣传抗日思想的音乐刊物被勒令停办,特别是在“国共合作”局面破裂之后,很多演出活动也被禁止,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歌咏团也被迫解散。因此在国统区内,就出现了一些讽刺意味浓厚的小型合唱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宋扬作词作曲的《古怪歌》。该曲以幽默、嘲弄式的手法,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种种丑陋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披露。与此相反,即便是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边区,各种与合唱相关的艺术团体却大量成立。如“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延安合唱团”等。还有一些艺术机构先后出版了《边区音乐》、《歌曲》、《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为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积极努力。这一时期的大型合唱作品如马思聪的《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等,陈田鹤的清唱剧《河梁话别》(卢冀野词,1943年)、陆华柏的《挤购大合唱》(黎维新词,1948年)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进行深刻的痛斥,对反动当局腐朽统治表达极度的不满,以及对战争必将胜利,一切压迫及腐朽势力终将垮台的坚定信念。
在经过“抗敌”、“民族化初探”、“抗日救亡”等审美观的洗礼之后,面对外来音乐文化,中国的合唱开始了找寻蕴含自身美学特征的道路。很多留学归来的作曲家,对于自己创作的音乐有着深刻的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多的作曲家意识到民族性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合唱审美观也随之表现为“民族性的诠释”.
在前人对多声音乐的一系列创作尝试成功之后,对民歌的多声化探索在40年代正式步入正轨。以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和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为首,出版了《中国民歌选》等民歌集。这些书籍对于民歌的和声化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很多作品至今仍有其影响力,如江定仙编曲的《康定情歌》、陈田鹤编曲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谢功成编曲的《绣荷包》等。
着名作曲家马思聪曾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的风格特色之外,极端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她有着丰富的音乐宝藏,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份遗产是我国作曲家特有的礼物,是所有作曲家的命根。”[6]235同样作为海归作曲家的谭小麟也一再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兴德米特”,“我是中国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6]236作为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着名作曲大师兴德米特的得意门生,谭小麟在和声语言上开始突破传统大小调功能和声,并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和古诗词特点,创作出的作品力求清雅古朴,在音乐方面寻求更为大胆而灵巧的韵味和律动感。他的合唱作品《挂挂红灯哦》(刘大白词)、无伴奏合唱《正气歌》(文天祥词)和《江夜》(唐·李白词)等,既有西方创作技法的“洋味儿”,又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音乐气韵,这些作品当时在我国音乐界也是新颖独特的。
这一时期优秀的合唱作品还有张文纲的混声四部合唱《壮士骑马打仗去了》,吴伯超的混声四部合唱《中国人》、女声四部合唱《暮色》(歌德诗、郭沫若译),江定仙的混声四部合唱《悠悠鹿鸣》(诗经词)、陈田鹤的混声四部合唱《蒹葭》(诗经词),黄晓庄的合唱《往哪里逃》等。
(五)建国至文革时期的合唱文化
建国初期,人们沉浸在幸福生活的喜悦之中,长久压抑之下的自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释放,更多的群众歌曲蜂拥而出。如热情洋溢的《歌唱祖国》(王莘),赞颂幸福生活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李群、张文纲)、表达对祖国热爱的《我爱我的祖国》(庄映)等等。
这一时期政府的文艺方针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百姓生活的悠闲,政治环境的安定使得这一时期的合唱形成了“幸福赞美”的审美观。为了便于群众广泛传唱,众多群众合唱歌曲仍以二部合唱为主,但旋律呈现出自豪、喜悦、赞美的特点。而艺术性强又能体现文艺方针的作品则非赞扬人民军队和以毛主席诗词为题材的合唱莫属。如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表达的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赞颂;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则是据毛主席诗词编配乐曲,正面歌颂毛主席的名作。即便是在“文革”时期,这种“幸福赞美”式的审美观依然有增无减,只是作品的含金量大大下降,优秀的合唱作品凤毛麟角。
值得一提的是郑律成的合唱套曲《长征路上》,以及田丰的大合唱《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这两部大型合唱作品尽显中华民族特色,旋律朴素凝练,与“文革”时期那种虚无的浮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族化”的审美观在这一时期依然在延续,如浸透古香古色的《阳关三叠》(王震亚改编)、抒发草原辽阔壮美、自由之情的无伴奏合唱《牧歌》(瞿希贤改编)、展现民族风俗及民族热情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麦丁改编)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给人“余音绕梁”的听感,而且多年以来在中国舞台上经久不衰。
(六)改革开放以来的合唱文化“文革”过后,随着各项关于音乐文化政策的调整,合唱活动也随之丰富起来。一些“文革”期间被迫停止的各种大型汇演在“文革”之后很快兴起,文化部、中国音协等文艺领导部门还举办了“全国合唱节”,促进合唱在全国的复兴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带回了更多的国外新潮的创作技法。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归来,作曲家对西方创作技法的掌握与运用也越来越纯熟;随着中国本土音乐元素的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乐理知识研究的深入,中国合唱作品愈发能够体现本民族的特色,在声音及舞台表演上逐步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品格。
作曲家对于采风而来的民族旋律,在保持其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并融入了现代音乐创作的新元素,使得合唱作品音乐内容更加丰富,表达形式上更具活力。
这一时期的合唱审美观念依然是“民族化”,难得的是中国合唱的审美观出现了“重写意思维”、“重情感表达”的回归。只是这种“回归”后的中国合唱有了更高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它在融合西方创作技法的同时不失本民族情韵,并利用不同的创作技法增添本民族的合唱音乐意蕴。例如,女声合唱《一窝雀》(刘晓耕)的旋律具有云南建水彝族曲调的音乐风格。曲中用急促的旋律与弹舌口技将伐树时鸟儿们惊慌失措的情景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听众为之焦灼。而结尾处对“彩云之南”的鸟雀们自由与快乐的描绘又会使人内心感到祥和。这前后素材的对比不难让听众产生对自然的珍爱之情。这样的作品还有充满浓郁内蒙古草原风情的无伴奏合唱《八骏赞》
(色·恩克巴雅尔),律动性强的节奏安排以及语气助词的灵活运用展现了草原上奔腾的马群的自由气派。陆在易的合唱作品是在西方的调性系统中刻画中国景色的优美和雄壮,陈怡的合唱作品则是更多的加入了现代创作元素,西方无调性音乐、中古调式与中国五声调式的混合,使得陈怡的合唱作品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玄幻的民族情韵,颇具时代特色。
三、当下中国合唱文化发展的症结
中国合唱发展至今,它的成果值得肯定。随着音乐媒体的发达,更多时尚的元素被加入到合唱中来,合唱除了多元化的特征外,还呈现出娱乐化的趋势。越来越多时尚性强、大众化、娱乐化的合唱形式受到人们的追捧与喜爱。只是这种过度的娱乐化、大众化的合唱形式是否能够长远发展?它对于中国大众合唱审美观念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例如,越来越多的合唱团在表演中加入了很多表演动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合唱表演的观赏性,但是,表演动作的加入一定要以不影响合唱音质为前提。而且,表演动作的设计应该以歌曲内容为依据,而不是与歌曲表达的情感相脱节。拿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公益活动《玉兰油梦想合唱团》来讲,我们肯定它对社会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但就其表演形式来说,明星演唱、合唱团伴舞伴唱难道就是合唱了吗?是这项公益活动的名字值得商榷,还是其中的合唱表演形式应该改良?有的合唱节目为了不影响合唱的音质,在真正的表演中依然采用假唱的形式,这对于合唱理念的传播是极为不利的。“’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过度泛滥,所造成的不平衡现象,使人类社会走向失根的危机”[7]!中国合唱产生伊始就被冠以“和谐”的象征,是倡导和谐、宣传民族文化的一个途径。所以,当下我们不能纯粹为了迎合媒体、迎合大众的需要而改变合唱的本质。媒体对于大众的审美是存在一定导向作用的,新的时期音乐媒体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引领大众的音乐审美情趣是当下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娱乐化泛滥的结果是对中国合唱民族性的担忧。如何在娱乐化与民族化中找到中国合唱发展的契合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音乐媒体的发达与炒作,中国合唱的风格定位和发展方向又成为高校教育值得深思的一个大问题。“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教育思想则是教育行为的指导原则,直接决定了文化发展的结果”[8].固守所谓的“高雅”合唱难免面临“曲高和寡”的境地,因为它对欣赏者的音乐修养有很高的要求,而中国大众对于“高雅”合唱的欣赏程度不高,面对复杂的多声音响以及与五声调式迥异的无调性音乐、半音音乐等,中国大众感到“刺耳”并难以理解。这种现状依靠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改革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很多中小学的音乐教材依然使用简谱,这是多声音乐艺术发展的一大障碍。“当下的中国合唱,必须走大众性的审美文化之路,再从大众化、通俗化提升为精英文化、精英合唱发展”[9].“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大众性的娱乐化趋势,高雅的合唱艺术要想在广大的群体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大众的文化消费”[6]236.要适应时代的需求,中国的合唱也要融入时尚、简约的元素。如何在保持合唱本质的同时不与时代脱节,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并且也对合唱的创作提出了创新要求,对高校合唱教学更提出了挑战。
参考文献:
[1]刘桂珍.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重构[J].甘肃社会科学,2011(4):147.
[2]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
[4]周淑真.中国合唱艺术中的文化功能探微[J].中国音乐,2010(3):168.
[5]田晓宝.中国合唱艺术的现代性[J].音乐创作,2008(5):127.
[6]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赵琴.音乐文化的危机[J].音乐研究,1998(4):76.
[8]沈恒.发掘深层结构,阐释音乐文化[J].中国音乐学,2009(2):65.
[9]田晓宝.当下中国合唱的多元化发展道路[J].中国音乐,2009(4):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