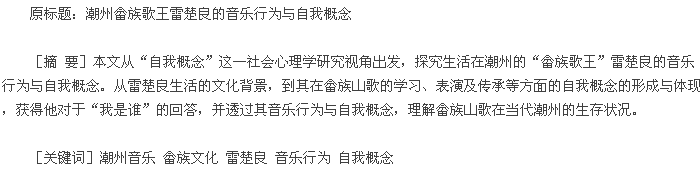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它看到的问题是“我是谁(who am I)”,并希望从这个小窗口,窥视它与人、社会、文化整个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自我概念不仅包括当下我们“是谁”的自我图式(self-schemas),也谈及我们将成为何人。①具体而言,它包括“我是谁”、“我有何特征”、“是什么创造了我个人的历史”、“我还可能成为什么”等与此相关的观点、思想和信息。②本文将从这个小小窗口,探究生活在潮州市文祠镇李工坑村的一位名叫雷楚良的村民在畲族山歌的学习、表演以及传承等方面的行为与观念——这是位79岁的老人,他的身份可不一般,在当地人称“畲族歌王”。同时,本文还将透过他的音乐行为与自我概念,理解畲族山歌在当代潮州的生存状况。
一、缘起:研究雷楚良自我概念的原因
出于与各种机缘的遇合,笔者选择“自我概念”为阐述雷楚良这一个体的音乐行为与观念的角度,原因有三。
第一,保留更多与潮州畲族民歌③相关的文化信息。雷楚良是目前潮州畲族居住地唯一能演唱畲族民歌的人,年事已高,然而未有传人,潮州畲族民歌濒于消亡边缘。尽管当地政府及文化单位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由于存在的各种经济难题以及对其保护的出发点和方向问题,整体看来进展并不顺利,或者可以说停滞不前。
学者们也在做潮州畲族民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目前涉及潮州畲族民歌的着作和文章也有若干,但从已有的潮州畲族文化与音乐的文献可以看到,较为深入的理论性研究还很缺乏,且重复性高。从中可见对畲族民歌收集得最早的是潮州市群众艺术馆的陈焕钧先生。陈先生在20 世纪 80 年代为“三套集成”④中的民歌卷,走访了潮州市及现梅州市丰顺县⑤的畲族村落,记录下了一批畲族民歌,并在1990年和雷楠刊出了一个油印本《潮州凤凰山畲族民歌》①。这也是最早以潮州凤凰山畲族民歌为题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的专题报告。此后,由于年老歌手的相继离世和其他一些原因,对畲族民歌的采集几乎无出其右。之后能见到的几本相关着作如《畲族与潮州文化研究》谈到了“畲歌与潮州歌谣”的样貌及两者之间关系,但对“畲歌”、“畲族民歌”和“潮州歌谣”的界定模糊,甚至其中还夹杂一些谬误和论证的不严谨,所列举的谱例也是引用前人;②雷楠、陈焕钧于2006年正式出版的《凤凰山畲族文化》有一章谈到“凤凰山畲族的民歌”,为在油印本基础上充实而成,相比之前的油印本,内容丰富了一些,包括对民歌谱例的分析以及民歌的分类;③由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编的丛书《潮州凤凰山畲族文化》则基本上是对前者的重复。④综观以上着作,大多数停留在概观式介绍的层面,未涉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人文及思想层面的展开。而涉及潮州畲族民歌的期刊文章更是鲜见,仅有的几篇也是在谈到潮州畲族民俗或文化时将畲族民歌略略带过。因此,对现在潮州畲族区唯一能演唱畲族民歌的歌手的研究,可保留更多与潮州畲族民歌有关的文化信息。
第二,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视点。这里的研究特殊性,是指今天潮州畲族民歌的演唱者,仅有雷楚良一人的特殊情况;而这个研究视点则指对个体的考察研究。民族音乐学研究多数建立在对音乐群体的观察之上,以群体性的文化叙事来构筑音乐文化。然而在音乐民族志中,对个体音乐家的着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原因就如杰西·罗斯金(Jesse D. Ruskin)和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在其《音乐民族志的个体》(TheIndividual in Musical Ethnography)一文中所述:
第一,在进行田野考察时,研究者与个体音乐家一起工作,并依赖在特定音乐社区中显得最为特别的个体音乐家。第二,因为有些社区处于全球化和政治不稳定和“解辖域化”的诸多压力下,就如阿尔琼·阿帕德雷(ArjunAppardurai)所提到的,民族音乐学家已被吸引到个体音乐家研究中。这些个体音乐家在尝试理解他们正在崩溃的世界,创造新的个体认同并将自身融入新的社会形态。第三,民族音乐学家属于重视专才并限定个体成就的亚文化。第四,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引领民族音乐学家去强调个体的力量和差别,也认识到个体在研究者深入的音乐社区中的自身角色。⑤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个体音乐家研究中,核心人物或说关键人物(key figure)显得尤其重要,他们往往能帮助我们从“理解个体的音乐经验这一个点”,到达“理解个体对于音乐民族志叙事结构的重要性”⑥。因此,笔者认为,畲族歌王雷楚良这一关键人物在畲族音乐文化中扮演的关键的音乐角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畲族山歌在过去几十年以及当下的生存现状,并由此带出有关畲族音乐存亡的一系列的思考。
第三,研究者本人的研究兴趣与取向。自从2008年7月对雷楚良进行第一次采访后,这几年来,每逢寒暑假和年节,笔者都会回到潮州李工坑村拜访他。在长期的田野作业中,笔者逐渐在老人对自己的音乐行为的知觉,对自身所扮演角色与社会身份的认知,以及周围人(包括同族同村、当地文化工作者、外来采访的文化工作者、政府文化宣传单位)的看法和做法如何影响他的音乐行为等问题上产生浓厚兴趣。也许我们在实地考察中经常接触到的本土音乐家基本可分为两类:一为先锋精英式——这类音乐家对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的音乐行为也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们会探问本土音乐的出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考虑文化的承继;另一类则为平民精英式——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浅浅的意识,会在本土音乐的表演上随大流,在音乐行为的价值和自身成就的标尺上,体现出一种平民式关怀,当然在是否传承的问题上也就较为放任自然了。从笔者的观察来看,雷楚良属于后者。在很多作者把目光投向先锋精英式人物时,这类平民精英式人物在民间的代表性有时反而显得更为突出。这也正是笔者为何感兴趣于从“自我概念”的角度,来展现个体音乐心理和行为的原因。
二、背景:雷楚良及其所在畲族居住地
第一次见到雷楚良老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双特别有神、炯炯发亮的眼睛。这是一个高瘦但浑身充满活力的老人。为了表达自己歌艺的不减当年,他戴上红色棒球帽,双手叉腰,挺起胸膛,张口便唱。一曲完毕,问他的畲语唱的是什么,他说歌名叫《唱李工坑》:“李工坑啊李工坑,山青树也青啊,泥墩起楼是矿坑,水稻种在半山腰啊,社员劳动有劲头。嗬……”李工坑是潮州市潮安县文祠镇的一个畲族小山村,建在海拔约400多米的半山腰上,坐北朝南,四面环山。
李工坑村民以前主要以农耕和茶业自给自足,但这些年来农业逐渐被抛弃,种茶卖茶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柑橘、橄榄种植等也是收入来源的一部分。
由于农耕和种茶辛苦,也很难满足现代人的经济需求,现在大部分年轻的李工坑村民外出到汕头、潮州市区或周边地区打工;一部分村民由于孩子在文祠镇中小学读书,也通过买房或租房的方式移居文祠镇中心。留守李工坑的只有近十户人家约五六十人,老年人居多数。
人去楼空,不在节日中的李工坑村分外宁静。近几年来,市、镇政府部门强调以特色化的民族生态区旅游业来带动经济,在这样的政策与宣传下,李工坑村多了许多来自汕头、潮州市区及周边其他城镇的客人,特别在周六、日,访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时候,圹埕上会停上二十几辆大小汽车。游客大多是从网络或电视上看到李工坑村慕名而来的——这里的“名”,便是“畲族”这个让人颇觉神秘的名称。
事实上,潮州畲族几乎都已汉化。除了中老年人和少数年轻人在村中仍用畲语交谈之外,潮州话已成为李工坑村民的日常语言;他们原本很有特色的服装和头饰也早已消失,如今在节日或大型接待会等重要日子里穿的服饰和姑娘们戴的头饰,是村民为了迎合畲族旅游点的建立,以及建设“民族陈列馆”的需要,从福建畲族处买来的。①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世代相传的《祖公歌》(《高皇歌》)是他们寻祖归宗、身份认同的依据。从《高皇歌》来看,畲族的来历颇为神秘。传说其祖先盘瓠是高辛娘娘耳中诞下的虫,后变成龙,为高辛皇帝取得敌人首领的人头,而得到皇帝三公主的婚配。因为皇后没有信守七日变身之约,在最后一天偷看金钟里变身的盘瓠,而使其成了“人身狗头”的模样。后盘瓠带着妻子,以及被皇帝赐姓“雷”、“蓝”、“盘”、“钟”的三男一女后代,迁居潮州凤凰山上,世代耕作,免纳赋税。因此,畲族子孙都认为自己是盘瓠王的后代。带着这样一种神秘的归属感,畲族人以珍稀的“畲”(也作“輋”)为荣。
李工坑畲族村以春节的正月初四为其“闹热日”,每年这个时间,山里每个“大客厅”都会摆上好几桌,大的家庭甚至十几桌,用以迎接到访的亲戚和朋友。在这一天,外来的陌生人也可以受邀上席,感受山里人的朴实与热情。另一个盛大民俗节日是“招兵节”,这个民俗仪式约三五年举行一次,目的是祭祀祖先,并为本村驱邪祈福。“招兵节”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在举行之前,需要筹措资金、拜访法师并请法师算卦以确定日期等。
由于雷楚良辈分高、懂本族礼仪,他在这些盛大的节日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更由于他这些年作为“歌王”名声在外,在重要场合中,他的山歌演唱显得不可或缺。
三、叙事:雷楚良自我概念的形成与体现
决定我们的自我概念的,除了遗传,还有社会经验,这些社会经验包括: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社会身份;我们与他人所做的比较;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周边的文化。②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考虑以上因素,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雷楚良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扮演、与他者的比较和他者对其之评价、周围文化的影响,来叙述雷楚良自我概念的形成及体现。
(一)雷楚良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扮演
雷楚良是个地道的农民,在未满10岁时就已帮助家庭做农活,在畲山“种田驶牛”、“割谷布稻”。在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文化教育对他而言是相当奢侈的。除了不算长的一段外出打工的时间,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座畲山中度过。
依雷楚良自述,他少年时代所受过的教育加起来不超过两年。那时交通不便,山里孩子上学类似于上“私塾”,由乡里出钱请先生常驻本乡教课,并负责先生的住宿伙食,最初上课地点就在村里的“公厅”。曾经有很多先生到过他们那里教书,有潮州人也有客家人,上课的语言是潮州话,畲族话在当时仅限于在本族人之中交流。
一二年级学生学的常识课内容有如“小小猫,跳跳跳”,“农民种田,工人做工”等等;另有识字课,用“红纸库”来学写字,也就是现在的描红本;算术课则教怎么打算盘;再“学高一点就有教尺度、写信,教写称呼什么的”①。因为总是要种田,加上当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他那几年书读得断断续续,从九岁一直读到了十四五岁。期间上课地点不断变换,从本乡“公厅”,到山后邻村“毛岭”,又到文祠的“上荣”,连他舅舅“大山”那边也曾去读过,但都读不久。1949年后,他又到夜校学习,时间也只不过半年。因此,在雷楚良看来,自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山里的农民”。
唱山歌在雷楚良的生活中,最开始只是一个爱好,一种劳动间与劳动之余的消遣。即使他读书不多,但笔者能看到他即兴创作的能力。畲族民歌的音调是相对固定的,歌词则可以根据不同生活场景与听众进行即兴创作。于是笔者问,既然读书不多,为何还能进行山歌的创作?他解释说主要还是得益于后来的夜校学习,而且那时潮州的潮剧、歌册②,以及村里老人们的畲族民歌演唱,也对他的畲歌演唱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儿童和少年时代断断续续受的教育,开启了他对知识的渴望,所以在读夜校时,他“不懂的就问老师”。他进行山歌的即兴作词的“字”就是从夜校学的。此外,“听潮剧,听老人唱歌册,就学唱几句歌册,学唱几句潮剧,学来学去的,就会了”。在他的畲族民歌学习中,一位名叫“阿泉”的长胡须、绑着辫子的老人对他影响最大——“他会唱山歌,很像歌册那样子的,用畲族话。他的尾腔拉得不长,板数拉得不长”,“另外一个老人,已经不记得名字,他就拉得长一些”。年少的雷楚良积极学习山歌的演唱,如他所说:“我当时就听他们唱,自己就学学看成不成,一句半句的。”有几首儿时听到的畲歌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如《风吹磜》、《摇儿歌》和《手指歌》等。畲歌,在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中,为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对于一个朴实的农民来说,他甚至只在潜意识中去领受这份快乐,口头上的“快乐”对他而言,则是过于华丽的辞藻。
山歌演唱不但开启了雷楚良下半辈子不一样的人生,还因此赋予他另一个社会身份——“歌王”。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语言学家、文艺研究者先后来到李工坑畲族村。据雷楚良介绍,他最早接触的是广东省考古队,之后是民族学家施联朱和他的音乐家太太,他们都听到了雷楚良的歌唱。当时陪同考古队前来的有一位名叫施策的文艺工作者,在潮州文化馆工作。他曾经想组织一个畲族民歌节目,让雷楚良进京参加国庆会演,后因“文革”开始而取消。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畲歌演唱屡遭禁止,雷楚良只能偶尔在田间地头悄悄地、以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量哼上几句,自娱自乐。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潮州文化馆的陈焕钧先生为了民间歌曲集成找到了他,希望听他唱歌并录音,当时的雷楚良仍不敢公开演唱。在陈先生的再三保证下,他才唱了几首。在之后的接触中,陈先生又录了一些畲族民歌,这些歌曲,有几首被收入《中国民歌集成·广东卷》。③而雷楚良重新投身他的爱好,是在1990年11月他到闽东参加畲族文化艺术节之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开始到福建、浙江等地演出和参加比赛,还参加了很多电视台、电台的录像和录音。很多民俗研究者都关注到雷楚良的演唱,将其纳入对潮州畲族独特文化的观察之中;潮汕各地的媒体、新闻工作者纷至沓来,“畲族歌王”的称号随后出现在很多报纸杂志上;之后香港、澳门,甚至海外媒体和人类学研究者也慕名而来。也许在雷楚良的早期生活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畲歌演唱者”会成为他的重要角色,他在晚年收获了名气,有了沉甸甸的成就感。
同时,这些采访者的到来,也时刻提醒着他的另一个角色——那就是畲歌传承人,然而,截至目前,这个角色并没有“山歌演唱者”那样成功。最初,他教一对孪生小孙女唱山歌,在李工坑村想以民俗文化拉动旅游业的那段时间,两位孙女与他一起,用歌声接受采访和宣传。但这只是一时,孙女要上学,没有时间学下去,如今她们已经记不起学过的那几首山歌了。他还收过两个女弟子,2004 年国庆节,他还带着她们在潮州慧如公园登台演出,如今,她们一个嫁到汕头,一个还在村里,可是她们已经不再唱歌。本村会畲语的年轻人,要么外出求学或打工,要么对此不感兴趣。过去村里有小学的时候,雷楚良会去学校教孩子们演唱畲歌,孩子们还曾经去潮州市庵埠镇表演,但这几年由于村里人口太少,不再设小学校,学生转移到了山下的文祠镇上读书,这个教习也中断了。
他说:“浙江、福建那边的专家跟文化馆的人说,你们这里现在剩下这么一个乡宝,每个月要给点钱给老人,让他好传授几个(徒弟)”,“经常(有人)提意见,但是总是没有啊”。由此可见,不管是收徒弟,还是办学经费,都是难题,对此他也很无奈。眼下荒芜的景象,让笔者想起蓝雪霏《畲族音乐,一个极需扶贫的角落》中曾提到的有关畲歌的生存现状:“畲族音乐,曾经创造了它的辉煌。而今天,当历史的巨轮以变速的节奏驶进二十世纪末时,我们不得不说它正面临着一片贫瘠的尴尬”①。
近两年来,雷楚良心里有了一些落寞,他说“山歌过时了”,笔者问他为何这么说,他回答:“旅游没搞成,就没有了;有关部门也不怎么重视;还有安徽、江西也没有来邀请(去表演)。”曾经镇上想发展旅游业,雷楚良是张名片;曾经文化部门需要政绩,雷楚良是个乡宝。现在牙齿掉光,人老声嘶,“他们也不太感兴趣了”。这使人感叹,政策人事时时在变,纵使文化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去年拜访雷楚良时,他说有了一个男徒弟,在北京读书,假期就回来学习山歌演唱。这让人仿佛在天色渐黑的四周,看到了一小盏灯光。
(二)与他者的比较和他者对其之评价
比较,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念头或意识了,却在我们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经常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放置自己的位置,甚至设立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 Festinger)在《社会比较过程理论》一文中提到:人们通过社会比较来定义自己是否富有、聪明、矮小。
②社会比较解释了我们的自我概念。③在采访中,雷楚良毫不吝啬地真诚表扬了他去过的那些畲族地区对音乐文化的重视,也毫不掩饰他对于山歌演唱的自信和自豪。
福建是雷楚良最早去且去得次数最多的外省。1990年11月,他受邀到福建省宁德市参加福建省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那是他第一次以畲歌演唱者的身份,踏上畲乡同胞的土地。在那里,他受到畲族同胞的礼待,体验到作为一位畲族人的荣耀,感受到作为一位会用畲语演唱畲歌的畲族人的自豪感;在那里,他也发现了潮州畲族失落了的歌唱和文化。尽管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到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祖地,他们祖公的坟地在凤凰山,但是,作为畲族文化特征之一的畲歌,在当时的潮州,能演唱者已寥寥无几;由于汉化,他们甚至没有了自己原来的服装和头饰,一些畲族的祭祖仪式也在被逐渐淡忘。与福建畲族对待“祖公文化”现状的比较,唤醒了雷楚良对潮州畲族文化与畲歌的记忆。在这一次的交流中,与他者的比较让雷楚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名畲族歌手存在的价值,并在一种不甘心看到潮州畲族文化遗失的心态引导下,利用畲族歌手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为恢复潮州畲族文化而奔走。从宁德回来之后,雷楚良开始张罗已经被本村人淡忘了的畲族“招兵节”,“找政府,跑宣传部、统战部、文化馆”,“筹备经费”,“跑了几十趟”④。那时除了村里几个老人,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该如何操办了,他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跑了多次丰顺凤坪畲族村,请来法师蓝金炮(法名“法通”),于1993年12月成功举办了曾停掉41年的“招兵节”。在“招兵节恳亲大会”那天,他站到了台上,为来宾献唱畲族山歌。
这些经历帮助雷楚良进一步明确“我是谁?”“我的位置是什么?”他对自己的表演也越来越充满信心。福建宁德艺术节之后,他还去过福州、泉州、漳州、福安、福鼎、晋江、安溪等地。每一次交流,他都非常自信,“有人叫我唱,我就手叉腰,放大大声就唱”。他评价自己:“并不比他们唱来差,个个都说‘你的声喉怎么那么好’,‘潮州的畲族山歌好听’!”
雷楚良也在不同场合演唱畲歌。他去过汕头大学接受汕头电视台的录像采访,去过潮州慧如公园搭台为游客表演,还去过电台录制节目。2008年7月采访他时,他说他刚刚参加完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三月三”民歌节,还接受了浙江台的采访。“(记者)问我今年几岁,我说七十三。他问什么(时候)开始唱,我说从奴仔(小孩)就听那些胡须很长的人在唱,我就记下几句,学了一下。后来就很多年没有唱了,改革开放后才又开始唱了。他们问你的声喉怎么那么好?我说我现在要是年轻,一里路外的人都能听到。”他还依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评价那里的女孩子唱的畲族山歌“不是原生态”,他认为“真的山歌声音是高亢的。她们声音猫猫的(意为声音太小),听起来不像”。在那个民歌节上,他凭借一首《担水歌》获得银奖。拿奖对七十多岁的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更喜欢在众人面前分享他的爱好,得到更多赞扬。
来自专家和领导的好评,也经常使雷楚良内心充满欣喜和骄傲。这些赞誉,是他认识和提高个人自尊的途径和反映,“自尊,是我们监控和反应别人的赞扬的心理计量器”⑤,也是他自我概念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2011 年的招兵节恳亲大会上,他演唱了一首《敢唱山歌敢大声》。他告诉我,北京的、省里的专家和市里文化馆的领导都说他唱得好。“我唱的时候,他们还在灰埕⑥拍(摄)我。向军馆长说不错,焕钧也说好”,“专家们都说我唱得好,我没什么赚,赚专家的夸奖再好不过了”。
看到老人像孩子一样神采飞扬,笔者笑问“那您觉得自己唱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自己唱得不错。我是牙齿不好,上面的假牙总是要掉下来。我要不是没牙齿,我能唱非常大声,拉腔拉非常长啊!”不但如此,他认为自己年轻时唱得还要好,“我在这边老路唱,那边新公路听得清清楚楚。我年轻时歌喉是相当好,唱相当大声,唱到相当远的地方”。
还有一点让雷楚良感觉特别自豪的是他经常上电视,汕头电视台、南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都曾经播放过他的节目,因此当他走在潮州的街头时经常会被人认出。“全潮州的人都认识我了,在百货大楼买一件生衫(T恤),(他们)总看我,说‘阿伯,你是那个唱山歌的吧?’去饮食(店),也总(有人)看,问‘你唱山歌的?’去西车站,的士司机向我招手,叫我过来。我说我不搭车。
他说,‘不叫你坐车,你唱两句山歌来听吧’。我说,‘你认识我啊?’他说,‘电视里经常播你,怎么会不认识’。
滨江长廊成堆的三轮车,常常跟着我,个个都认识我。我觉得认识我的人真的很多,有好几万人。无论我去哪里,他们都认识我。”这些目光和声音,不断加强雷楚良对自身音乐行为的认识。
与他者的比较和他者对其的评价,在“我是谁”的问题上为雷楚良寻找答案,也帮助他完成了从一般平民到平民精英的转型。
(三)周边文化的影响
文化对于行为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歌王雷楚良的自述中,可看到畲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对他山歌演唱的影响。考察这两个因素对他畲歌演唱的影响,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他的自我概念的形成。
畲族文化的孕育 畲族由于历史上的多次迁徙,形成“今天分布于闽、浙、赣、粤、皖五省的部分山区”①的局面,这种散居局面及与汉族的交错杂居,使每个地区的畲族语言有所区别,从语言来辨识族别的形成比较困难。然而,共同的盘瓠信仰在不同地区畲族同胞中产生了心理联结,并依此帮助他们找到文化归属感。就如施联朱所说:
畲族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巩固其共同心理,往往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风格的特点。如畲族家喻户晓地流传着“盘瓠传说”,并把这个传说记载于族谱中,反映在“高皇歌”里,以及通过龙头祖杖、凤冠、习俗等标志,反映了畲族原始社会残留下来的图腾信仰,而且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畲族的独特标志,使畲族中的成员都感到是属于同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这种亲切心理。②如今,传统畲族服装头饰、婚嫁、殡葬等习俗在潮州畲族中几乎消失,但图腾信仰的确立文化身份的作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采访中雷楚良提及最多的“祖公”盘瓠和图腾信仰,便是识别他所唱畲歌的文化身份最主要的方法。他演唱的一些歌曲,如《爱唱山歌敢大声》、《凤凰山上日头红》等,歌词中不管是“畲”字,还是“凤凰山”,都刻上了潮州畲族的烙印。
他用较为严肃的语调向笔者讲述祖公的由来,描述他们珍藏的不愿向外人展示的祖图,并举畲族信仰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纪念祖公盘瓠的“招兵节”仪式的例子……似乎这些方面,才是完整展现他作为一位畲族人的文化背景。
雷楚良说,若是姓“雷”、“蓝”、“盘”、“钟”,便知是同拜一个祖公,亲切感油然而生。在共同民族心理的影响下,畲族的族群团结也有不一般的体现。畲族“内部非常团结,经济上的互助传统极其突出,没有什么剥削关系”③,这在雷楚良幼时从老人那里学的一首传统畲族民歌《催眠歌》中也有体现。他向笔者讲述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过去造房子、劳动、挑肥,村里人都会相互帮助,如第二天某家要去挑肥去泼稻,叫到谁去帮忙,被叫的人是绝对不会推脱的,而是晚上早睡,第二天早早起来帮忙。《催眠歌》说的就是:孩子啊,你快快睡、快快睡,妈妈明天早起去挑肥(参看下页谱例)。
由于与其融合的周边语言不同,不同地区的畲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这使不同地区的畲族人沟通起来仍有困难,但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畲族同胞,都会非常热衷于寻找自己语言中与其他地方畲族的共同点,这是让畲族人找到归属感的另一因素。雷楚良说,他们之间仍有很多语素相通,见面时会用一些日常用语,去试探能否与对方沟通,如能发现个别一致,则双方都会非常高兴,就明白是找到了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同地区畲语唱出的畲歌呈现出了不同样貌,他们仍旧认为畲歌是族人沟通的桥梁。他们接受着不同地区的演唱风格的差异,又享受在相同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中。在“畲族”这个特别的族群及其文化孕育下,雷楚良作为畲族人的音乐行为有了解释的出口。
汉族文化的濡染 潮州的畲族在文化上受潮州文化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同样突出地体现在信仰方面。潮州畲族除了盘瓠信仰,也同时接纳了汉族的一些民间信仰。笔者在考察中发现,潮州地区多信奉“三山国王”,部分潮州畲族居住地也是如此;潮州市意溪镇河内雷厝山还信仰“感天大帝”。
潮州的畲族在语言上与潮州方言“曾经有过密切的交流和融合”①。历史上的畲族,由于较为封闭、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原因,有着“极强的自尊和严重的自卑” ②,一般只在族内通婚,因此曾经有过这样一条规定:凡嫁入畲家的汉族妇女,入乡随俗,一年之内能学会畲话者被舆论认为是好媳妇。③潮州的另一个畲族居住地归湖镇山犁村的一位已故畲族歌手文香姆,就是汉族童养媳,6岁到畲族居住地后,在半年内即学会畲语,并能兼用畲语和潮语演唱民歌。现在的畲族由于生活方式与潮州汉族趋同,已无婚俗禁忌。
就是在这种畲、汉文化的交融下,雷楚良的音乐行为与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潮州音乐的影响——歌唱风格总会与演唱者的个性与生活经历联系到一起——他提到了童年时代从老人那里学唱的畲族歌曲带有“歌册”的味道,从他演唱的部分畲歌来看,总体风格上受潮州歌册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他也在客属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在畲歌演唱时融入了客家山歌的一些特点,例如在歌词的创编和歌唱的拖腔上;再加上他性格比较开朗外向,在审美趋向上会比较自然地偏向容易取悦人们听觉的长拖腔和气息……而在文香姆的录音记录中则听不到这些演唱特征。
④雷楚良认为自己即兴创作的词有部分是受潮剧和歌册影响,这也一点都不出奇。旧时潮州妇女绝大多数为文盲,她们当中学会读书写字者,多是因为听歌册、读歌册。过去的潮州婚俗喜好“做四句”——也就是类似四句体的诗句,追求每句句尾或第一、二、四句的押韵——在婚礼的各个环节做句、唱歌,以增加婚礼的气氛。“做四句”既有用工整的七字句式,也有按音韵填词不拘泥于七字句式的,就像雷楚良顺口念来的“姨甥嫂欢喜端茶来,老丈喝了欢喜哉,你左手生银右手就来发财,我就垫你个红包小小个”这样类型的一些创编。这一类的歌词创编方式在雷楚良的山歌创作中较为普遍。
在李工坑畲族村,村民也习潮州大锣鼓,并在年节的时候,用类似于游神赛会的形式,敲锣打鼓、迎神游神送神。雷楚良正是锣鼓队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并负责司鼓。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有时过年会去潮州观看游神赛会,村里也曾经请过大锣鼓师傅传艺,以增添年节热闹的气氛。村里“公家”买有大鼓、斗锣、钹等乐器,这支锣鼓队伍曾经有过一定的规模,而现在部分乐器破损,村中年轻人外出学习、打工居多,只在过年回家,因此锣鼓队伍很难再组织起来。在雷楚良的卧房里,放着椰胡、秦琴等潮州音乐的乐器,他偶尔弹奏这些乐器自娱,山里没有合乐的乐友,他就听着收音机,跟着电台的潮州弦诗齐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雷楚良歌唱行为和观念与畲族文化、汉族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理解了他的自我概念如何通过音乐行为得到不断的确立。
四、“我是谁”:雷楚良的音乐行为与自我概念
通过阅读前文,我们也许会觉得雷楚良很热心于畲族文化事业,对自己的畲族音乐和文化有一个较为积极和深刻的认识,并试图在音乐表演和传承中奉献一己之力。可是,他是否真的对自己的音乐行为有这种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回答“我是谁”这个有关自我概念的本质问题?根据前文叙事,这一部分将通过对他音乐行为的解释——他为什么要做?以及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来对他的音乐行为与自我概念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我就是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尽管被那么多光环笼罩着,雷楚良仍旧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所以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从与他的交往中,可以看到他作为山里农民的简单、朴实和热情。他独自居住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屋中——这间大约10平方米的平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囊括了会客厅、卧房、厨房、餐厅等多种功能。有访客时,他就搬上一个凳子给客人,自己则坐到对面旧式“眠床”的床沿边上。在客人比较多的节日当中,他便将会客地点改到“公厅”旁边的厢房里,坐在旧式茶几上泡茶、与访客唠家常。每次去山里拜访他,赠送给他香烟、麦片等礼物,他必定回赠自己辛苦采摘、烘制的茶叶或腌制的橄榄菜。当笔者需要在山里居住时,只要说一声,他就会让家人或者邻居把自家最好的房间腾出来。有时太久没有联系,他从山里出来,也会带上礼品到笔者家中探望笔者的父母,询问笔者几时回去。“种田驶牛”一点也不妨碍他歌唱的爱好,他的乐观、开朗和喜爱表演的性格,让他对与音乐相关的事物投以关注。这让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还是一位爱好畲族音乐文化的畲族山民。
第二,“我是一个爱唱山歌的畲族人”。他说自己唱得最好是在年轻时——“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人过去山那边种田,或者是去巡水(看看田里有没有水)。扛着锄头,走在山边,有时候自己唱得自己觉得相当好,山有回音,听起来相当好啊。自己听了总想唱”。
在不能唱山歌的时期,他只好偷偷在田边小声“自己唱来玩”。在生活艰苦的年代,能填饱肚子就已不错,几乎没有山里人会去关注唱歌等精神上的娱乐。在采访中,雷楚良说过,“以前一直种田,哪有想到今日这样”。在与他的妹妹交谈时,她也说“以前(几乎)没有听到他唱歌,是这些年这里来请、那里来请,才听多一点”。对他而言,务农是正业,唱歌只是爱好和生活的调剂品。他小时候学村里的老人唱畲歌,对能否学成并不太在意;年轻时去种田,在山路上、田埂边,唱上几曲,自己感觉不错也就罢了;中年时因“文革”不敢唱,不唱也就不唱了;现在年老不再务农,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畲族文化事项,但也是“有来请就去,没有来请就这样”。
第三,“他们叫我畲族‘歌王’”。当然,“歌王”是报纸等新闻媒体给的称谓,但也已经慢慢成了雷楚良自我觉知的一部分——他对这个称谓是接受并享受其中的。接踵而来的关注,使他慢慢从他人眼中的“他是畲族歌王”,成了自己眼中的“我是畲族歌王”。他说,浙江、福建畲族“来了后谁也不找,他们说就找这个唱歌的歌王,让他来唱”。那些为了体验“原生态”而来到畲乡的游客,“一进门就找阿老(老头),问阿老在哪里?”更别提来自广州、北京、香港等地乃至国外的文化研究者了。随着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他也开始积极思考如何进一步挖掘自身潜能和畲族文化,除了成功组织“招兵节”以外,他还思考如何将记忆中的畲族舞蹈“踏草舞”重新编排。“歌王”称谓带给他荣耀,也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带给他责任和担当。
但是,他对所谓的责任和担当并不是非常清晰。也许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记录、保存和继承民族文化等才是责任和担当,或者拿奖、弘扬民族文化算是责任和担当,可这些宏大概念离雷楚良还比较遥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无所谓”。他坦言“觉得自己可以去唱歌赚玩,住宾馆、有吃的,出门有小车送来送去,还可以唱歌,就行了”。参加活动有时还能得到一些物质和金钱上的回报,例如参加汕头演出时带回了一条近千元的毯子;在汕头红宫那里表演,获得两百元报酬;在汕头唱《深坑深》得到了八百多元,还有烟、茶、煮茶的壶、领带夹、电台的纪念章等。在经济和人情两者之间,他首先选择人情,就像他对待我这个年轻的研究者。然而,他也偶尔抱怨有些媒体太过吝啬,采访了他几个小时,最后才给了他四块小月饼。于是在一些人看来,雷楚良有一些所谓的局限性。
他也不太在意畲歌是否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他始终把传承的事情,寄托于是否为政策需要、政府是否扶持等因素,一旦得不到相应的支持,他也就觉得无须努力了。可是,遇到想学畲歌的年轻人,他还是会张开双臂,他不会焦急地考虑生前身后事,只是秉持着淡淡的“想学,你就来”的姿态。
他也是一个比较顺应时势的人。当他看到畲歌受到汕头、潮州各地电视台的关注,便很主动地告诉他们“有‘踏草舞’,这是以前踏草时跳的舞蹈。他们要是重视,我就能搞得出来。……锣鼓、弦诗、小钹小镲都加进来,才好听”。他的畲族山歌有逐渐被遗忘的时候,他觉得“山歌过时了”,认为可能当“畲族”这个话题总被人们拿出来说的时候,就不新鲜、“没味道”了。可是他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始终保持着一个单纯的状态,刚显出那么一点失落感,话题马上又转向来畲族村的游客对他这位“歌王”的喜爱和追捧。
总而言之,雷楚良首先是一个平凡的农民,然后才是潮州畲族居住地的“畲族歌王”,也许他还是潮州畲乡最后一位畲族歌手。他的生活经历帮助他获得自我觉知,帮助组织他与音乐相关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实现他希望做的那个自己。也许他有时并不能深刻地表达或理解他为何以这种歌唱的方式来展现他自己,有时候,那种由无意识的、内在观念所发出的行为,也会与他有意识的、外在的解释有所不同。可是,通过他有关畲族山歌的叙事可以看到,他过去的普通和曾经的辉煌,裹挟着浅淡的文化意识,形成了他与山歌演唱相关的自我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他作为潮州目前唯一的畲族歌手的音乐行为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