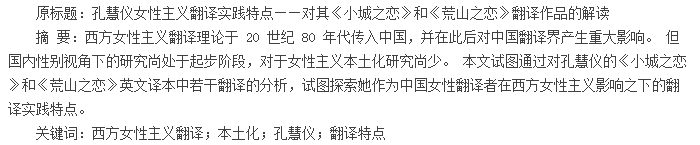
一、引言
性别差异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话题, 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成为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由于“女性”与“翻译” 处于社会与文化的边缘地位, 话语权长期缺失, 西方女性主义者敏感地意识到二者间的相似性,纷纷从性别视角讨论其对翻译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同时大量女性主义者也从事翻译实践,因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给予她们重要启发, 使其重新审视文化偏见,在译著过程中自觉“恢复”、“还原”女性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原文与译作处于平等地位, 译者需忠实的对象既非原作者也非读者,而是由作者和译者构成的创作整体。 这种观点,相较之前的基于语言学,重在功能、结构等对等的翻译理论不啻是一种创新。 而在翻译批评方面, 由于发现了Simone de Beauvoir 著作的误译现象和对湮没于历史中的女性翻译者的重发现, 女性主义者匡复历史,指出女性在对话语霸权的抗争中,为翻译及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译论者以开始相继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纷纷撰文对其理念进行介绍推广。 但遗憾的是,国内的研究尚停留在资料梳理、理念阐述阶段,对女性主义翻译本土化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对孔慧仪的《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英文译本中若干翻译为例子,试图探索她作为中国女性翻译者在西方女性主义影响之下的翻译实践特点。
二、孔慧仪与《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
《小城之恋 》和《荒山之恋 》均出自王安忆的小说《三恋》,一度被视为情色小说。 然而以如今的角度看来,触及性这一话题,更多的是为表现女性在极端压抑环境下,禁忌之恋强烈地唤醒了她们沉睡于心底的自我意识。 虽历经屈辱苦难,这些女性依旧顽强地直面命运,选择人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中的男性沉湎情爱,一旦面临社会指责唾弃,则懦弱不堪,不是逃之夭夭就是丧失意志。
《小城之恋》 的情节为同在一个文工团跳舞的青年“她”和“他”,因长期的练功相处使二人之间产生爱意,陷入疯狂的纵欲中。 “她”因怀孕,被团里发现,却抵死不承认与“他”有关。 生下两个孩子后,“她”变得坦然平静,以平凡的母爱洗涤了过去岁月中的“不清洁”。而“他”则在逃避中日益消沉狂躁,反而陷入命运的牢网中。
《荒山之恋 》则讲述已婚的 “她”与 “他 ”之间发生婚外情,继而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中,作者刻画“她”魅力四射,极其擅长与男人调情;而“他”则自闭害羞。
因而从二人调情到深陷其中,“她” 无时不处于主动,甚至在最后选择自尽时,男子所做的也仅是对 “她”意志的消极顺从。 作者刻意“倒置”男女爱情主导权,强调了女性在情感方面超乎男性的坚强执著,以自我选择的死亡超越似乎不可违逆的分离。
孔慧仪在访谈中说,“在翻译女性作品时,有一种每一个细胞都投入的感觉, 也就是说作品无论在知性、感性和直觉等方面,都完全牵引着我”,尤其在翻译《小城之恋》时,她“一边译一边哭”。 在译本的前言中她谈到自己对王安忆创作意图的理解,即“女性生而饱受困苦孤独,男性则独享荣耀美名。 然而女性在凄苦中的忍耐,在彷徨中的坚韧又何尝不是在人性层面上对男性的超越呢”?
三、《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的若干翻译例子列举
(1)她对照着前后左右的镜子,心想:以为她丑陋是绝对不公平的,以为她粗笨也是绝对不公平的。 (王安忆,2001:111)She looks into the mirrors around her, and thinksto herself:it’s unfair to say I’m ugly, and it’s unfair tosay I’m clumsy.(Hung,1988:7)这是《小城之恋》中女主人公在练功房中对镜欣赏自己舞姿时的自我安慰。 由于小时练舞方法不科学,她身体走样,变得肥胖粗壮,因此受尽嘲笑,内心自卑压抑。 唯有对镜独舞时,她才能借由舞衣的映衬掩饰自己的身材缺陷。
在孔慧仪的翻译中,她将第三人称的 “她”替换为自述中的 “我”, 一改原作中作者客观而疏离的笔法,将译者声音与女主人公心声融为一体,着意抒发了少女对他人评议的不满、怨愤。 同时显示了译者强烈的性别意识, 和因此产生的对主人公的同情和认同。
(2)可是他是那样刻骨地想念她,她虽不像他那样明确地想念,却是心躁。 (王安忆,2001:134)Yet how he yearns for her! And though she doesnot long for him as obviously as he does for her, shebecomes agitated.(Hung,1988:35)孔慧仪在《小城之恋》的翻译过程中,将两个 “想念”分别译为“yearning for”和“long for”,这里固然有避免用词重复的考量,但两个英文短语在含义上的微妙差异也不容忽视。 短语“yearn for” 意为 “to have astrong desire for something,especially something that is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get” (LDOCE,1997:1663), 而“long for” 指 “to want something very much,especiallywhen it seems unlikely to happen soon”(LDOCE,1997:845)。 也就是说“他”的“想念”虽强,但理智上基本已否认可能性,而女性“她”的“想念”更绵长,即便一时看不到实现也会坚守信念。
从中可见译者的女性意识,即她明确区分了男性女性在情感、理智上的差异,且在主观上更为认同女性对情感的坚贞恒定。同时这两个短语也对后文情节构成暗示,“她” 在产下孩子后毅然与不堪的过往决裂,以恒久的母爱守护儿女与自己;而“他”则在对过去的凄惶恐惧中,郁郁终生。 这里展现了译者对作品内涵寓意的理解,她相信女性在苦难挫折中的坚强与勇气。
(3)他需要的是那种强大的女人,能够帮助他克服羞怯,足以使他倚靠的,不仅是要有温暖柔软的胸怀,还要有强壮有力的臂膀,那才是他的栖息地,才能叫他安心。 (王安忆,2001:38)He needed a strong woman,one who could helphim overcome his shyness,one on whom he could de-pend,one who could provide not only a soft,comfortingembrace but a pair of strong arms.That alone could behis resting place,that alone could set his heart at ease.(Hung,1992:49)《荒山之恋》 中羞怯孱弱的男主人公遇到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心里涌起一阵波澜。 原文中作者在总起一句后,使用六个短句,以逗号连接,每两句意义句式相对,句意逐层推进,以工整的行文表现了女性作者特有的绵密心思和细腻的写作风格。 同时,也通过句式的铺排,凸显了“他”敏感内向又脆弱自卑的性格特征。 孔慧仪在翻译时,则连用三个“one”在重复中强化女性的主体性,似乎在描绘一个特定女性的特征而非男性视野下对某类女性的特点归纳。 而“thatalone”句则选择完全依照原文 ,凸显男性的被动消极角色。 这再次反映了译者强烈的性别认同,通过改变句式,传达自己对于两性能力、地位的思考。
(4)大声吞泣着反复说道:“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她搂着他的头,用嘴唇梳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她是那样的爱他,珍惜他,可是从此她的心缺了一块,再不能弥补了。 她为她的心的缺陷暗暗哭泣。 (王安忆,2001102)...and cried loudly, saying repeatedly, “Give me achance,give me a chance.” He was helplessly ashamedof himself; he despised himself. And because of thatshe seemed too lofty for him, too distant. He too wasalone.
She took his head into her alms and brushed herlips against his tangled hair.She loved him so much,shecared so desperately for him,but from now on her heartwould never be whole again; there was a crack whichcould not be mended. She cried secretly for her brokenheart.No one knew her pain.And no one knew his pain.(Hung,1992:128)这是《荒山之恋》中男主人公向妻子坦承婚外情后,妻子痛苦不堪却又一心宽恕的场景。 原文在首句描述男子的悔恨情状,其后视野逐步转向妻子,由外向内,最终以妻子被撕裂重创的心为结尾。
而在译文中, 译者刻意补充了男子的内心独白,强调他的悔恨、羞耻。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慧仪还加入了原文中未曾提及、因自卑而产生的疏离寂寞感。 而在最后,补充的“no one knew her pain”再次强调妻子隐忍痛苦时的坚韧,吞咽苦涩时的辛酸。而“And noone knew his pain”则照应前句,表现二人间心灵已丧失默契,无法进入彼此的状态。 同时又与“He too wasalone”构成照应关系 ,暗示男子更大的痛苦在于对另一位女子依旧情深,以致在忏悔时还禁不住为分手而抱恨。 译者在此的加译,补充了自己对男女主人公情感状态的理解。她认为男性的懦弱无法使其直面自己的欲望,而女性则因爱而坚守婚姻,饱受折磨。这种观念来自其女性意识,在对女性的同情中译者完成了自己对原作的增写。
综合以上例子,可发现孔慧仪作为中国女性翻译家, 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其翻译实践呈现的特征为:
(1)翻译作品选材上大多以女性作者和女性题材的作品为主。孔慧仪的西方教育背景使其性别意识较早地被唤起。 而作为女性,生活于中西文化边缘的香港,这种成长经历又使她对于女性的边缘地位予以关注, 又因个人经验而对女性题材的作品更加敏感,对女性观点更为同情。但同西方女性翻译者有所区别的是,孔慧仪所选取的作品通常来自主流女作家,这与西方翻译先锋作品、“政治不正确”作品和被重发现的女作家作品的倾向是不一致的。由此可见当西方女性主义者看重作品的政治意义, 希冀改变政治现实时,孔慧仪的女性立场更为温和保守,她一面希望女性重新发现、定义自己,又一面看重传统社会对于自己女性观点的认同。
(2)翻译理论上孔慧仪受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影响更为深刻。 诚如 De otbiniere-Harwood 所说:“需使女性视角在语言中可见, 才可使世界发现女性的存在 。 ”(make the feminine visible in language so thatwomen are seen and heard in the world. (1991:117))孔慧仪作为女性翻译者确在翻译中采用了多种方法、步骤使女性观点凸显。 但从上文的具体翻译案例来看,译者遵循的翻译原则并未逾越中国传统翻译观。中国现代翻译研究中,马建忠提出“善译”的翻译标准;严复提倡“信、达、雅”;鲁迅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瞿秋自强调“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陈西滢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林语堂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 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
“第一是忠实标准, 第二是通顺标准, 第三是美的标准”;朱生豪极为重视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傅雷反复强调 “重神似不重形似”; 还有钱钟书的 “化境”,“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都着眼于以精到的言说方式忠实地表达作品内涵。孔慧仪在翻译中强化了女性主义观点,成为作品内涵的重要部分,但翻译原则依旧是传统翻译观的延续,看重表达、意境。这与西方女性翻译者遵循原作、译作构为整体,翻译时尤其要体现译作的创作目的理论有着不小的差异。
(3)翻译实践上孔慧仪将女性视角有机地融入译文中。 通过以上四个翻译案例的列举,我们发现相比原作者,孔慧仪在处理作品时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女性观点。 她保持了女性作者细腻绵密的文风,却使作品的情感色彩更加浓郁,强烈地流露出个人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女性执著精神的肯定。 但这与西方女性主义强调女性被压迫现实、呼唤政治平等的立场仍有相当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