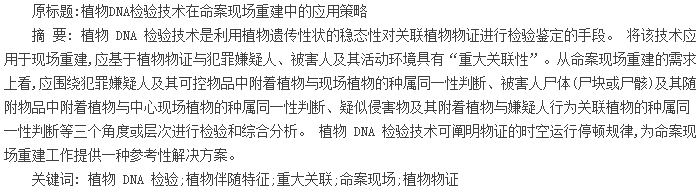
1、 引 言
DNA 检验技术的成熟和检测方法的不断创新推动了人类及其他生物物种 DNA 技术的广泛应用,一系列基因工程学科的奠基与突破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DNA 技术引入侦查领域提供了可能及现实路径。
当前,现场勘查中植物物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建构有待于引入植物 DNA 检验技术。 公安部于 2011 年颁布了《公安机关侦办命案工作规范》,要求在重点勘验检查命案中心现场的同时,注重勘验检查外围现场和关联现场,尽可能发现和提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尤其是微量物证和生物检材。 对于露天现场的尸体,首先要查明尸体所在地是否为杀人主体现场,有无移尸迹象;如果有移尸情形,应根据现场遗留的拖拉痕迹、脚印、交通工具痕迹、血泊(滴)等以及尸体上的附着物质,特别是非现场的外来物质,分析行为人使用何种方法、运用何种运载工具移尸或抛尸及其路线,由此循迹查找杀人主体现场和相关场所。 植物是犯罪现场重建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环境证据和过程证据。 作为一种常见的生物检材和证据类别,在命案现场勘查中,借助植物 DNA 技术手段,可阐明物证的时空运行停顿规律,这对于查找破案线索、划定侦查范围、确定侦查方向往往具有建设性意义。
2、 植物 DNA 检验技术的进展略述
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植物中存在稳定的亲本印记现象,即父本或母本的某些等位基因在子代的表达不同,具有不对称性,因而成为印记,且具有持久的传代能力。 表观遗传学研究亦提出了发育生物学中的一些关键机制,如小分子 RNA 可以引导 DNA 甲基化染色体组蛋白修饰,导致序列特异性转录基因沉默;泛素化酶的突变抑制 siRNA 指导 DNA 甲基化以及转基因和转座子的异染色质沉默,这些调控机制在细胞分化和状态维持中起到关键作用,为植物感知、传递体外的逆境信号,进而胁迫应答、加工处理、激活信号的传导途径,最终诱导大量防卫和逃避反应的基因转录表达。 随着植物 DNA 检验技术的发展 ,用DNA 数据研究系统发育已逐渐成为专家普遍接受的方法。
2003 年,加拿大学者 Paul Hebert基于线粒体细胞色素 C 氧化酶基因 CO1 的多种优点,提出了利用基因片段鉴定植物物种的 DNA 条形码(barcoding)的构想,并随后发起了奠基性的“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
DNA 条形码的核心是建立基于基因片段鉴定生物物种的标准。 它不仅是传统物种鉴定的方法论补充,更重要的是因其采取数字化形式,使样本鉴定过程能够实现自动化和标准化,从而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易于利用、识读的系统。近年来,10 个国家的 52 名科学家根据对 75 科 141 属 1 757 种植物共约 6 286 个样本的 4 个 DNA 候选条形码片段(rbcL, matK, trnH-psbA 和 ITS)的引物通用性、序列质量和物种分辨率等的综合分析,发现 rbcL、 matK 和 ITS三个质体DNA候选条形码片段具有较高的通用性,其中,ITS 具有最高的物种分辨率,与 rbcL、 matK 与trnH-psbA 质体DNA 条形码片段的任何一个组合均可分辨 69.9 %~79 . 1 % 的 物种 , 显著 高于 rbcL + matK 条 形码组合49.7 %的分辨率。 从类别上看,ITS 在被子植物中的通用性较高,而在裸子植物中稍低,有望成为种子植物的核心 DNA 条形码(rbcL+matK+ITS),这项研究显示出利用多种样本取样和不同遗传方式的基因片段开展植物 DNA 条形码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随着多种显微成像技术的迅速发展,现已能以低成本测定多种植物的基因组序列和 cDNA 文库序列。 可 以预见,与分子证据相结合的植物 DNA 分类与 DNA 条形码技术将引发物种鉴定识别理论的一次革命性变化。
植物 DNA 技术越成熟、越完善,就越能服务于正确鉴定物种和发现新种的基本目的,从而演变为植物物种分类及亲缘关系鉴定的一种常规策略。
DNA 数据的取得与 DNA 提取方法直接相关。 自1961 年 Marmur报道用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和氯仿从细胞中分离提取 DNA 样品的经典方法以来,研究人员对制备高纯度、完整 DNA 样品的最佳方案进行了长期探索。 刘塔斯等总结了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的几十种植物的 DNA 提取方法, 如十六烷基三乙基溴化铵(CTAB)法、十二烷基硫酸钠(SDS)法、高盐低 pH 法、碱裂解法、Zigenhagen 法、Dneasy PlantLiets 法 、S 法 、脲 法 、Draper & Scott 法 、Cscl 梯度法、CTAB/Cscl 梯度法、苯酚法、试剂盒法等。 因用于提取植物 DNA 的材料部位、存放年限(新鲜程度)、老嫩程度、所含化学成分以及物种生理代谢特性的不同,植物 DNA 提取方法也各异。 从实践和科研需求的角度考虑,理想的 DNA 提取方法应该具有简便、高效、经济、快捷等优异性。
3、 现场勘查中应用植物 DNA 技术的法理基础
将植物 DNA 检验技术应用于现场重建,从应然的角度看具有正当性,但从实然的角度观察,必须确定待检测分析的植物是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的“关联物证”,它必须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原理,这是实然层面的首要法理基础,关联性规定了证据力问题,为植物物证的采用标准;第二个实然层面的法理基础则规定了植物物证的证明力问题,即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待证问题,这是植物物证的采信标准,也往往成为对勘查中发现的植物是否启动 DNA 检验程序的判断起点。 采用标准(证据力)和采信标准(证明力)是包括植物 DNA 检验技术在内的所有鉴定技术应用于现场勘查的理论前提。
3.1 关联植物物证的采用标准:证据关联性原理
相关性是所有证据都必须满足的可采性要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的证据法中都强调相关性。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证据法中开宗明义,明确规定证据的关联性,而普通法则通过判例或者成文法确立关联性规则,如澳大利亚《1995 证据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关联证据的特点是“如果该证据被采纳,可以合理地(直接或间接)影响对诉讼中系争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评价。”但是,证据法意义上的关联性只是侦查机关在勘查办案中是否应用植物 DNA 技术的起码判断。 事实上,考虑到植物 DNA 检验技术的现状,侦查人员需要进行一些使用价值上的预判与评估,如:待证植物物证对于划定侦查范围、确定侦查方向、突破侦查僵局是否具有较大证明效度? 能否通过 DNA分析鉴别该植物物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植物进行 DNA 分析应基于植物物证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活动环境具有伴随特征和回放历史及其片段特征的“重大关联性”。
3.2 关联植物物证的采信标准:同一认定原理
根据触物必留痕、犯罪行为必取一定形态的基本规则,进行植物 DNA 检验的目的是对人、物等的时空关系、活动轨迹以及法益保护关系等进行判别。 物证同一鉴定在比较环节存在一个隐性逻辑论证过程:只有证明两个事物的特征点相同或者没有发现本质性差异特征,就可得出两个事物存在同一性联系的结论或者证伪。 因此,应围绕关键问题展开分析,如:这一植物为什么出现在现场? 本来在什么地方? 它怎样来到的? 出现在不应当出现的地方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是何种植物的哪一部位?等等。回答这些问题,有些可能不必进行 DNA 鉴定,但很多问题如果能从 DNA 鉴定的角度切入,可能会产生更强的证明力。 在同一性检验过程中,必须确立一定的取样策略,并注重质量控制措施,减少影响因素,防止 DNA 污染,确保 DNA证据的客观性。
4、 植物DNA技术在命案现场重建中的应用方向
在命案现场勘查中,死亡性质、现场生物物证、杀人地点(第一现场)、死者身源、死亡原因、作案过程(包括抛尸过程和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等是关注的重点。
植物 DNA 鉴定技术有助于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尤其可用于判断分析杀害行为过程、主体现场与关联现场环境、运行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尸体等)轨迹等。在命案犯罪现场重建的碎片化场景拼贴中,如果说人类DNA 技术叩开了分子层面证明犯罪的主门, 那么,某种意义上,植物 DNA 技术可谓开启了一扇视窗。 命案现场重建中的植物物证可提供判别被害人死亡前后、行为人到案前后活动的一个参数,即植物物证是该环境、该地点的植物,通过植物的同一认定,进而建立起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与物(侵害物等)及环境的关系。 如果以中心现场为原点,被害人死亡前后、行为人到案前后活动可以下图简要列明(见图 1)。 基于此,可简要确立植物 DNA 检验技术在命案现场重建中三个基本应用策略。

4.1 行为人及其可控物品中附着植物与现场植物的种属同一性判断
图 1 显示,命案中行为人、被害人和侵害物的时空运行停顿规律既是一个量的时空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空区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或激变或错综的渐变)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空区段。 行为嫌疑人及其可控物品中附着植物可能经由如下三种过程产生: 一是行为人在中心现场杀害被害人,遭遇被害人一定程度反抗的过程中,行为人及其可控物品附着了现场的一种或多种植物及其组成部分。 二是行为人杀害被害人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而将被害人尸体或尸块抛弃,抛尸过程中刮蹭或粘附了中心现场至被害人尸体最终抛弃地(多数为被害人尸体被发现地)路程中的一种或多种植物及其组成部分。 三是行为人在中心现场逃匿,直至被抓获归案现场,其身体及其可控物品特别是衣物、包裹、车辆刮蹭或粘附了逃匿路程中的一种或多种植物及其组成部分。 基于证据的关联性,上述三种情况下的关联植物物证都有鉴定价值,但从证明杀人行为和中心现场重建的需求上看,第一种情况下的植物物证具有关键性。
在发现犯罪嫌疑人及其可控物品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在其可控物品中发现与现场环境的植物种属具有伴随特征后,可以启动植物 DNA 技术对发现的可能关联植物(如果实、树叶、树枝等)进行同一性鉴定。
1992 年 5 月 3 日,2 名晨练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处沙漠的废弃试验场中发现一具女尸,该女尸颈部缠绕一段电线,尸旁不远处草丛中遗有一个 BP 机。 经警方公开辨认,确认死者为非洲裔女性丹尼斯·约翰逊。 通过对 BP 机的追查,发现马克·伯根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讯问了伯根,伯根承认一次驾车中约翰逊曾搭过他的车,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并发生过争吵,但拒绝承认杀害约翰逊,并以已经 15 年没去过那个沙漠中的试验场为由,否认到过案发现场。
警方追查到伯根驾驶的那辆皮卡车,发现车中的电线与约翰逊尸体缠绕的电线为同一类型电线,伯根的嫌疑增大。 本案中,尽管皮卡车已被清洗,但警方还是在车后厢中发现两颗帕洛佛迪树的豆荚果实。 为证明该车到过案发现场,警方邀请专家证人对豆荚果实进行鉴定。 专家对现场周边所有的 42 棵帕洛佛迪树分组取样,并与皮卡车上发现的豆荚进行多态性 DNA 随机扩增检测比较。 结果显示,每棵帕洛佛迪树都具有自己独特的 DNA 分型图谱,而豆荚的 DNA 与尸体边上的一棵被刮蹭过的帕洛佛迪树的 DNA 具有同一性。 结合皮卡车前杠碰撞痕迹检验的结果,间接证明这辆车到过案发现场,这就使陪审团确信伯根未到过现场纯属谎言,最终结合其他证据以一级谋杀罪判处其终身监禁。 这是美国首次将植物 DNA 鉴定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的文献记载。
4.2 被害人尸体及其随附物品中附着植物与中心现场植物的种属同一性判断
从犯罪嫌疑人及其可控物品中发现植物物证,进而启动植物 DNA 鉴定,无疑属于一种“倒查”的行为模式。 实践中,命案现场勘查多数是一种从被害人尸体(尸块或尸骸)到犯罪嫌疑人的“正查”行为模式。 侦查人员依据各种植物的木质、树皮、树叶、花粉、孢子、果实等进行现场重建在实践中屡见不鲜。 1987 年,八宝山公墓抛尸案中,北京警方在尸包里发现了树根、潮虫、泥土等物证,技术人员对现场环境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分析: 树根是加拿大杨树萌生枝的树根,因此可确定尸体被埋葬过的地方有加拿大杨树并且长有萌生枝;尸体手脚有脱皮现象,这是溺死后的尸体现象;潮虫生长在人类居住区,一般凌晨出来觅食,说明尸体此前曾被埋藏在人居环境里;石景山的土样酸碱度等指标与尸体上的泥土吻合,因此确定尸体曾被埋在石景山某平房附近,该处应该是个大院,院内有长着萌生枝的加拿大杨树。 犯罪嫌疑人把死者头颅(后查明抛弃在丰台区某苗圃)、衣物等另行处理,且整个处理过程繁琐(行为多、周期长、空间大)而隐蔽,说明行为人不急于“脱手”,心境从容,思虑周全,有切断“循着死者找关系人”这一破案途径的故意和动机。
进一步说明行为人预谋时间长, 具备隐秘分尸处所,且与被害人相识,曾有过一段已被外人知晓的相处过程或某种联系,或有外人曾发现一方出入过对方居所(包括临时住处)等情况。 这起案例显示,植物 DNA 检验手段的启动除受制于证据形态多样和种类丰富等原因外,还与警方能否找到现场与特定地点的植物样本有直接关系。 图 1 简要描绘出植物关联物证的地理或物理分布与尸体(尸块或尸骸)的线性关系,侦查人员需要判别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是杀人中心现场,还是分尸、移尸或抛尸现场。 勘查实践显示,被害人尸体(尸块或尸骸) 存在一个以中心现场为起点的空间运行轨迹(该轨迹若为 0,则表示尸体未被移动),其运行期间伴随的植物(甚至可考虑微生物)可反映尸体的运行轨迹。 如果希冀植物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考虑各种植物物证的检验结果为侦查乃至法庭采信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4.3 疑似侵害物及其附着植物与犯罪嫌疑人行为关联植物的种属同一性判断
在命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往往既具有相似性和继承性,也具有值得重视的特异性、层次性和多样性,除杀人外还可能具有侵财、侵物等直接或间接目的。 如 1999 年银川郊区特大爆炸袭警案中,行为人对被袭击的巡警遗体进行了大量翻动,行为人到底在找什么?是钱还是其他什么?如果是抢钱,工作状态中的巡警一般身上不会带很多钱,但却配有枪支,因而推测其直接目的并非抢钱,而是劫取枪支,爆炸杀人仅仅是其实现犯罪目的的手段。 同时,行为人为实现犯罪目的,常常会同时侵害现场周边的物体,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或破坏现场环境。 如渝、湘、苏特大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元凶周某某具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为躲避侦查和抓捕,周某某常在目标城市周边的野外坟地搭帐篷宿营。 犯罪活动必然引起生物、物理和化学变化,各种变化之间客观上存在关联性。 现场存在各种形态的物质和痕迹是犯罪活动的产物,能反映犯罪活动的事实。 从犯罪携带物的角度看,对疑似侵害物及其附着植物与行为人行为关联植物的种属进行同一性检验,可能会找到破案线索,其指明了“以物找物再找人”这样一种划定侦查范围、确定侦查方向的路径模式。 野外现场勘查中常遇见行为人制造、抛弃、遗留的植物痕迹或物品,如野果皮屑、树皮刻标、攀爬、溜划、践踏的痕迹、狩猎装置或工具、植物采集遗迹、取火灰烬、取水工具、取木痕迹、取土痕迹、休息痕迹等各种遗存。 对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植物物证应深入研究,其制造、遗留、抛弃与嫌疑人加害、逃匿行为具有时空指向性和对应性。 不依循属种划分的定制,植物在现场重建中的类别主要是野生植物类、农作物与蔬菜类、花卉与水果类、水生与海生植物类等。 DNA 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分析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所留,判断其野外(室外)犯罪、生活或被害情况以及行为人遗留植物物证的时空特征等。 在野外(室外)命案现场勘查中,一旦判明植物痕迹物证与案件发生、存续具有“重大关联”,可尝试聘请相关领域的植物 DNA 专家协助破案。
5、 讨 论
法医学上有诸多应用植物学知识的实践探索,如口腔植物残片、胃内容和肠内容中植物性食材的种类、来源、加工方式、饮食习惯等的分析判断、硅藻种类和来源的识别、木屑与花粉鉴别、毒性植物侵入过程解析,等等。 研究植物 DNA 检验技术不仅具有基础理论意义,也有实际应用价值。 植物 DNA 检验技术在现场勘查工作中的应用,既需要侦查人员强化利用植物物证的意识,另一方面还需要鉴定机构不断完善植物 DNA 检测方法,最好能够建立一套从组学水平上阐明与人类生境密切的植物类群生命活动全貌的信息库。
植物 DNA 技术作为一个新生的法庭科学分支,尚待大量实证探究与构建。 我们对植物的研究很多停留在人工控制的环境,对自然环境中植物的生理和发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与动物组织相比,植物组织含有较多的多糖和其他次生代谢产物(酚、酯、萜、色素等),这不利于获取高质量的 DNA 图谱。 另外,植物DNA 技术的发展需要相关学科技术的协同支撑 ,其中,植物代谢组学、DNA 分类学、DNA 条形码物种鉴定检测方法、高特异和高分辨观察方法、计算机技术和高通量筛选技术融合、数据库建设、质量控制体系等学科方面的发展程度均可能影响到植物 DNA 技术在现场重建中的应用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