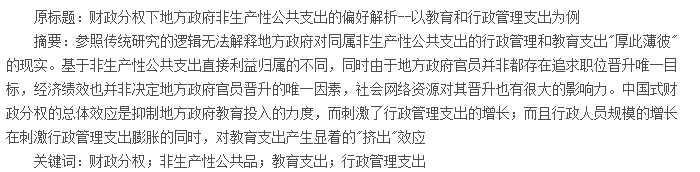
早在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文规定"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但是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长期未达到上述文件、法律规定的指标。直到2012年末,全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2万亿元,首次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4%的目标。而1978-2006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年均增长速度约为20%,在财政总支出的占比由4.71%上升到18.73%,在相同时间段内,经济建设支出、文教费类支出的增长率分别10.5%、16.71%.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教育投入相对不足与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现象引起公众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
在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现实中,义务教育、行政管理等公共服务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其中,1998-2006年间,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占国家教育支出的比重由91.65%上升到93.82%;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也由78.03%上升到84.36%.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税种、税目和税率基本上都由中央政府决定,地方政府取得预算内收入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在支出方面,除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法定支出,中央政府并没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偏好对我国教育投入不足和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现实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有关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模式与公共品供给关系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既有研究基本都按以下逻辑展开:首先,地方财政分权改革导致了"跑部钱进",从中央政府获取财政资金支持是第一位的,辖区内居民的满意度被放置在次要的位置,也就是有学者指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是"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在发挥作用,而是"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成了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指标[1].其次,基于不同公共支出的经济绩效是有差异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性公共支出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益,当期投入当期就能见到经济效益,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外溢性,不能在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内产生经济绩效,是为一个地区发展打基础、着眼长远的投入。再次,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分灶吃饭"的财政分权改革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热衷提供基础设施类能当期见到经济绩效的公共品的供给,而忽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这些"见效慢"的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
遗憾的是,关于财政分权与典型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却很少有研究者给予关注,更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同时,现有研究也无法解释我国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支出"厚此薄彼"的现实。因此,需要我们另辟蹊径,才能找到地方政府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为何偏好行政管理支出、轻教育支出的合理解释。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为辖区内居民提供公共产品更有效率、更有比较优势,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本区域的情况更了解,具有信息优势;公众可以自由迁徙、"用脚投票"选择福利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辖区居民具有同质偏好等。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看,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仁慈政府"假设是靠不住的,辖区内居民福祉最大化并不是地方政府的首要追求目标,政府官员也是追求"个人效应"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可能从政治决策中设租、寻租,以获取个人的好处[2];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还把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引入财政学的视野内,认为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实现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居民福利的相容。实践中,Shah et al.
(2004)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腐败、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的现实后果要取决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包括权力关系)。同时,在民主宪政体制不完善的国家,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有时不但不能改善公众福利水平,反而有可能导致公众福利水平的下降甚至恶化。
既然财政分权的后果取决于现实的制度安排,那么,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支出的影响,也应该以中国财政分权模式的制度特征作为切入点。
首先,与标准的财政分权理论相伴随的是政治上的联邦主义,而中国的财政分权模式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集权紧密结合。因此,在中国,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能量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奖惩,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追随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实践中,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众的需求,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进行专项转移支付和财政奖励等措施(例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级财政的支农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我国还出台过"三奖一补"政策,其中包括: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一部分资金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的力度,抑制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主导和进行了六次大型的行政机构改革,力求控制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特别是1998年,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我国全面铺开,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压缩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加大教育等公共支出的力度。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性,在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导向下,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应该会加大教育等公共支出的力度,而抑制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
其次,在标准的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间会出现"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但在我国上述"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还非常不完善。其中,由于中国行政机构缺乏足够的弹性,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能很好地对居民的偏好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做出相应的调整,居民"用手投票"机制是失灵的;同时,由于中国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品皆系于户籍,居民"用脚投票"机制也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是对上负责,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即上级政府通过考评下级政府的相对绩效来对下级政府官员实施奖惩。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增长的强大压力,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以GDP为主要政绩的机制[3].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分权模式还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地方政府之间"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模式的缺失,同时形成"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其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以GDP绩效为主要指标。
按照Keen and Marchand(1996)等的研究,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属典型的非生产性支出,它们对地方政府官员任期(或当期)的经济增长无直接贡献,从吸引流动资本的角度与其他生产性公共支出相比也无明显的优势。其中,教育支出由于其收益的长期性和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对拉动短期GDP的增长效果有限,地方政府官员出于竞争的需要和对任期(或当期)政绩的追求,实践中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同样的,在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和以GDP为主要政绩的考核机制下,即使中央政府和辖区居民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官员自身也应该会主动抑制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否则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
以上分析表明,参照既有研究的逻辑,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和教育支出不会表现出"厚此薄彼"的现象;退一步说,地方政府即使对教育支出积极性不高,但也应该会抑制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这显然与我国公共支出的现状不相吻合。
二
实际上,行政管理和教育支出虽然都属非生产性支出,但是利益归属存在差异。行政管理支出更多地与政府官员的福利直接相联系,而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非生产支出更多地与公众的福利相联系。同时,分权下的中国还存在以下社会现实:其一,地方政府官员并非只存在追求职位晋升这一目标,而同时存在其他目标;其二,经济绩效也不是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如社会网络资源等,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也存在重要影响。
首先,由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利益归属的不同,地方政府官员并非只存在追求职位晋升的唯一目标,地区资源禀赋和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前景的差异等原因,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都存在扩张行政管理支出的可能(只是不发达地区这种倾向可能更加明显),在财政支出总量既定时,必然导致教育等公共支出的不足。
从契约理论角度出发,锦标赛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是,代理人必须面临共同的风险冲击,即竞赛的起点应该类似,否则锦标赛失灵。所以,我国现有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以GDP为主要政绩的机制,如果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距过大,弱势地区可能"破罐子破摔"、放弃竞争;因为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富裕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但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的,在晋升的机会"渺茫"时,会寻求替代的办法进行福利的补偿。以上观点得到田伟和田红云(2009)、丁菊红和邓可斌(2009)等实证研究的支持。在我国越是那些初始经济社会条件落后的地区,地方官员似乎会更多地伸出"攫取之手",如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通过变相的手段将公款挪为私用、利用拥有的资源控制权进行炫耀性消费行为等。
还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机制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省区的资源禀赋特征,而且依赖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禀赋特征(包括年龄、任期等)。同时,地方政府官员行为背后都遵循着稳定存在的科层制逻辑,在政府"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中,当政府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在职务上继续晋升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部分升迁无望的"天花板官员"可能会寻求替代的办法进行福利的补偿。也就是说,即使在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由于也存在官员晋升需求的无限性和晋升机会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也可能出现变异。
其次,由于经济绩效并非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唯一因素,社会网络资源等因素也是影响其晋升的重要因素,公众在政府官员晋升的博弈中处于"失语"状态等原因,进而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和教育等公共支出的不足。
结合我国现实,经济绩效可能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肯定不是唯一因素。其中,Opper and Brehm(2007)对我国1987-2005年间在任的省委书记、省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是人际关系而不是经济绩效,提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人际关系假说".国内学者陈潭和刘兴云通过实地调查,也阐明了基层政府官员晋升往往是前台与台后多重原因作用的结果,派系关系、政治背景、社会网络等后台因素往往能左右基层干部的晋升,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处于一种"缺席"与"失语"状态[4].
而人际关系或后台因素的构建又直接与行政管理支出相关。在地方政府辖区内,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其任务和责任也存在差异,存在对不同部门领导考核机制的难题,而且下属的评价对部门领导的前途也有一定的影响("民主测评"),这也导致部门领导为了维持稳定的政治支持,对下属行为的异化(例如"三公消费")采取一种放纵的态度。国内学者袁飞等人的研究认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目标,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要更为多样化,他们需要在提供有效公共品与满足特定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之间做出权衡,以建立本地的政治支持网络。这样,在财政支出规模一定时,维持和改善地方政府官员人际关系或后台因素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可能导致教育等公共支出的不足。
因此,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效应是刺激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而抑制了教育支出的规模。而且,行政人员规模的增长在刺激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同时,对教育支出存在显着的"挤出"效应。中国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机制造成一种反向激励效应: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加大教育支出的同时,抑制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扩张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时,抑制了教育支出力度。由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刚性,地方政府在可支配财政资金增长的同时,都相应减少了二者的支出水平。结合其他财政支出项目对二者的影响,基本建设支出对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存在显着的"挤出"效应;作为典型的民生支出项目,医疗卫生支出与教育支出存在显着的"攀比"效应;人口老龄化问题对行政管理支出产生了更高的需求。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高速发展,市场化改革导致"企业办社会"模式的推出,都显着促进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显着减少了教育支出规模。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追求和谐稳定的总目标导向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着刺激了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5].
财政分权改革是国际的趋势,分权改革的必要性和优点已经得到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检验。虽然财政分权在当下的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笔者并非否定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而应该发掘导致其不良后果的制度安排并进行改革和创新,使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达到一种良性状态,进而改善公众的福利水平。第一,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公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进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或晋升等都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二,改革现有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包括改变此前存在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提拔以GDP为主要政绩的考核机制;同时,截断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利用社会网络资源等因素拓展晋升机会的可能。第三,继续扩大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职能,适当压缩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规模;深化和巩固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压缩行政人员规模。
参考文献:
[1]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2]Yingyi Qian,Gerar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5).
[3] 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2005(1).
[4] 陈潭,刘兴云.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整治[J].公共管理学报,2011(2).
[5] 江克忠.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