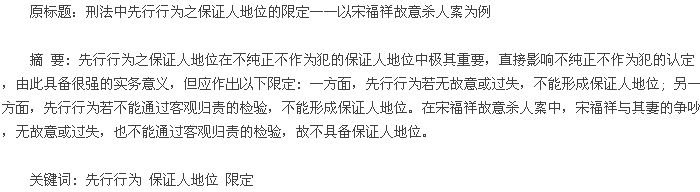
引言
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一种特殊的构成要件类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其表现形式与犯罪论体系构造均与作为犯相异。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犯罪论体系中,保证人地位可谓判断核心。[1]保证人地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用语,其含义等同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作为义务的来源( 根据) ”。我国刑法学应当逐步摆脱前苏联刑法学的束缚桎梏,逐渐与德日刑法学接轨。因此,笔者在文中使用“保证人地位”的用语,来替代“作为义务的来源( 根据) ”的提法。因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采取宽泛界定,大量不作为被定罪,其合理性大为可疑( 如宋福祥故意杀人案) 。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自斯笛玻尔首创以来,[2]虽存在的合理性已受质疑,但笔者不纠结其中,先予承认,再以宋案为例具体探讨其限定问题。
近年来德国对先行行为的限定有松缓的趋势,但详细考察之后,发现德国保证人地位的类型与我国情况迥异,其具体分为八种: 特定近亲关系、特定共同体关系、自愿承担保护义务者、结合保护义务的特殊公职或法人机构成员、危险源的监督者、管护他人者、危险前行为、商品制造人责任。而我国的保证人地位类型只有四种: 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可见,在德国,先行行为被扩大之后,一般也符合其他类型的保证人地位,不会扩大刑罚的范围。在我国,若扩大先行行为,并不会与其他类型的保证人地位重合,这会扩大刑罚范围。比如,行为人买来粉碎机,置于四合院中公用场地作业。以德国的保证人地位来分析的话,行为人不仅具备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也具备危险源的监控者这种类型的保证人地位。因此,不能以德国扩大先行行为的趋势,来反对我国对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限定。
一、案件事实及判决
2003 年 6 月 30 日晚,宋福祥酒后回家因琐事与妻李霞争吵并厮打。李霞说: “三天两头吵,活着倒不如死了算了。”宋福祥说: “那你就去死吧。”李霞找寻预备自缢之板凳时,宋福祥请邻居叶宛生前来规劝。叶走后二人又发生吵骂厮打。李复寻到用于自缢之长绳。宋福祥意识李欲自杀,却无动于衷,直至板凳响后方起身靠拢,但未采取任何措施,乃离开现场到一里以外之父母家中告诉双亲,待家人赶到时,李已死亡。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公安分局刑事鉴定: 李霞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自缢) 。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福祥目睹其妻李霞寻找工具预备自杀时,应当预见李霞将发生自缢后果而放任其发生,在家中仅有夫妻二人之特定环境下,被告人宋福祥负特定义务,放任李霞自缢身亡之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情节较轻,故依《刑法》第 132 条之规定,判被告人宋福祥故意杀人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二、学者观点及分析
对此案判决,陈兴良教授持反对态度,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共用一个犯罪构成,但两者在结构上有差异,要填补这种差异,必须考虑等价值性问题。作为义务及其程度难以对等价值性作出科学判断,应在作为义务外寻找判断标准,判断标准是不作为人的原因设定。在不作为人故意或者过失设定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情况下,由该不作为实施的犯罪和由作为实施的犯罪在构成要件方面就是等价值的。对于宋福祥案,不能以作为义务程度的高低,作为判断宋福祥是否构成不作为之故意杀人罪的依据。关键是要看其妻自杀死亡的原因是否宋福祥故意或过失设定的。夫妻吵架,不足以成为自杀死亡的原因,自杀死亡是李霞本人行为的结果,因此宋福祥的不救助与故意杀人罪之间不具有等价值性。”[5]陈兴良教授从等价值性的角度来判断宋福祥是否具备作为义务,可谓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讨论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判断标准,陈兴良教授未从表述上直接沿用因果关系说、保证人说或违法性说等任何学说,而提出不作为的原因设定说。
此说应用于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类型,表现为对先行行为作故意或过失、客观归责的双重限定。详言之,先行行为不仅应为故意或过失行为,还应与所致风险具备相当因果关系。但不作为人的原因设定说,就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特定犯罪论体系而言,可予适用,对其他保证人地位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能否理所当然地适用呢? 如果硬性适用的话,是否有不当限缩不纯正不作为犯之虞呢?这是有探讨余地的。
张明楷教授明确支持判决,认为: “宋福祥听到了妻子上吊自杀时的凳子响声,这表明其妻子的生命面临危险; 由于妻子是在自己家里上吊的,而家里又没有其他人,这说明妻子的生命完全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行为; 宋福祥确实可以轻易的救助妻子。这些都足以说明宋福祥的作为义务程度高,或者说负有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件的作为义务。”[6]张明楷教授通过论证李霞的生命紧迫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从而认为宋福祥的作为义务程度高,从而负有救助义务。但是,张明楷教授的论证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逻辑上讲,作为义务程度的高低,在行为人具备作为义务之后,才能去判断,在作为义务的存在与否获得证明之前,何来作为义务程度高低之说呢? 若张明楷教授意在通过论证李霞的生命紧迫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从而认为宋福祥负有救助义务并且该义务的程度高,但即或如此,救助义务的高低已经没了有意义,因为具备该义务就表明宋福祥处于保证人地位,这已能为宋福祥的入罪提供依据,无须提及宋福祥作为义务的高低; 另一方面,李霞的生命紧迫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怎能成为宋福祥具备救助义务的理由呢? 若推而广之,凡处于危险状态的人,只要其生命紧迫依赖于他人的救助,后者即产生作为义务,保证人地位就会无限的扩大化,这是危险的。
可见,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由先行行为类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特殊构造决定,必须予以限定,否则将导致刑罚制裁的不合理性。陈兴良教授对本案作出的结论,笔者赞同。
三、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限定
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限定,可从多角度展开,现仅从故意或过失、客观归责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 一) 故意或过失的限定
先行行为是否具备故意或过失,旨在厘清不具备故意或过失的先行行为能否形成保证人地位。以威尔泽尔为代表的目的行为论者认为,构成要件行为无法纯然客观地与主观相切割,相反,故意或过失决定了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成立。至此,目的行为论者提出了目的论体系,改变了新古典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中只有客观不法构成要件的状况,嵌入主观不法构成要件。此后的犯罪论体系中,都包含主观不法构成要件。[7]主观不法构成要件包括故意、过失或目的。先行行为欲形成保证人地位,是否必须出于故意或过失呢? 对此,李海东教授认为先行行为不必出于故意或过失,[8]但林山田教授持反对态度。[9]笔者认为,先行行为是否必须出于过意或过失,关键在于其“行为性”。就自然意义而言,作为犯与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具备相同的原因设定,也就是说,虽然两者在风险的创设与实现之间的具体流程不同,然而,先行行为如同作为犯的行为,对风险起着一种“本原动力”的作用。概言之,先行行为与作为犯的行为一样创设了法益侵害的原因设定。另外,就风险的创设与实现之间的具体流程而言,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明显比作为犯复杂,那么,就更不应该对先行行为宽松审查。先行行为既然能形成保证人地位,则如一“阀门”,如果“阀门”不牢,无论其后如何严格限定不作为本身,恐怕也会不合理扩大刑罚范围,不可不慎。因此,先行行为与作为犯的行为应受同等严格的限定。
贝林提出客观性构成要件后,受到迈兹格、麦耶等人批判,最终由目的行为论者将主观要素从罪责中复制到构成要件中。[7]从此,不管犯罪论体系如何演变,构成要件中始终包括主观构成要件,行为与故意或过失结下了不解之缘。将这一点推导至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也要求其不能脱离故意与过失。人的身体举止如果没有故意或过失,就作为犯而言,当然不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 同理,先行行为如果没有故意或过失,自然不能为其产生的危险负责,先行行为责任的范围仅能涉及事先预见的结果。[10]虽然先行行为后的不作为也应具备故意或过失,但不能因此否认先行行为也应具备故意或过失,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严格地同等限定的必然之义。
具体而言,先行行为具备故意,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先行行为时,对先行行为可能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这一点有认识,但希望或者放任其先行行为的实行与法益侵害危险的出现; 先行行为具备过失,是指行为人基于各种防止侵害法益的危险出现的注意义务,应注意不要引起侵害法益的危险,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轻信能避免,从而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出现。
本案中,宋福祥与其妻李霞的争吵,对李霞随后自缢的风险来讲,不具备故意或过失,由此不具备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
( 二) 客观归责的限定
先行行为,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行为人应排除风险的实现,否则应承担责任。这就是先行行为类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归责原理。但从而衍生问题: 先行行为与所致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
仅靠条件说就能解决问题,还是应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德国关于因果关系认定的通说是条件说。[11]条件说是由奥地利诉讼法学家格拉泽创立的,德国帝国法院法官冯·布里进行了充实。[12]条件说常被表述为: 导致一个结果的各种条件,在具体结果没有被取消就不能想象其不存在时,都应该看成是原因。或者说,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的,是结果的任何一个如果略过它,则具体形态的结果便不能够成立的条件。[13]条件说建立在一种“去除法”的公式上面: 刑法上的原因是指造成该具体结果所有不可想象其不存在的每个条件; 反之,若可想象其不存在而结果仍会发生,则非刑法上之原因,即无因果关系。条件说基本出发点是一视同仁,亦即,所有造成结果的条件都是等价的,不许区别造成结果的原因是“原因”或“近因”,是“典型的”或“纯属意外的”原因。[3]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A( 条件) ,B( 结果) 就不存在的话,A 就是 B 的原因; 如果没有 A( 条件) ,B( 结果) 存在与否无法确定的话,A 也是 B 的原因。条件说受到的批评首先是,该理论扩大了刑事评价对象的范围。[10]随后作为补充规则,相当因果关系说被德国弗莱堡市医生克利斯首次提出。[2]相当因果关系说强调,行为与结果之间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详言之,以一般的经验为客观判断,若该原因在通常情况下均足以造成该结果,则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反之,若该原因在通常情形下,并不一定会造成该具体结果,尤其是该结果完全偏离常规者,则不相当。[3]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互为补充,方可最大限度找出导致结果的原因。德国最高法院认为,犯罪论体系的第三阶层———有责性对故意或过失已严格限制,不必以相当因果关系来克服限制条件说宽泛之弊,所以不采纳相当关系说。但条件说的宽泛性,表现于主客观两方面,前者涉及主观相当性的缺乏,如故意或过失,后者涉及客观相当性的缺乏。因此仅强调故意或过失,尚无法全面克服条件说宽泛之弊。如今此问题已通过犯罪论体系的革新———客观归责理论的出现得以解决。[14]犯罪论体系在德国经历了五个阶段:
古典体系、新古典体系、目的论体系、新古典与目的论相结合的体系、目的理性体系。其中,目的理性体系中首次出现了客观归责理论。在客观归责理论代表性人物罗克辛提出的目的理性主义犯罪论体系中,客观归责紧随因果关系,共同致力于组成客观不法构成要件。
客观归责理论包括三段规则: 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实现法不容许的风险、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15]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表述。不过,客观归责以制造不容许的风险来替代行为,一方面,说明了对结果无价值的重视。结果无价值是指法益侵害或危险。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最终落脚于“风险”,充分表明了对结果无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行为无价值的限定。因为“不容许”二字,表明了对“违背义务”的强调。
而“违背义务”恰好是行为无价值的内涵。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社会相当性,即一般人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日常生活行为,则不认为制造了法不容许的风险。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指因果关系的设定。
其下有一条重要的子规则: “有些情况,实际上并未实现风险,或者所产生的非典型性危害后果属于完全特殊性质,或者其发生流程极度地超越了所有的生活经验,以至于不能从理性的角度对此加以预计,对这样的情况必须否定客观上的归责性。”[13]也就是说,如果结果超越一般人预料地发生,就不认为实现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这是从相当因果关系有无的角度,来判断法所不容许风险的是否实现。
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是指被排除被害人自我答责。被害人自我答责是德国刑法学中的一个理论,其认为: 只要被害人的任意支配着损害结果的发生,损害结果的发生仍然处在被害人的行为所能控制的领域之内,就存在着被害人对不发生损害结果的优先负责性,就要由被害人自己对所发生的损害结果予以答责。[16]也就是说,如果被害人自主自愿地选择了其法益被侵害,就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客观归责理论对先行行为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运用其蕴含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根据许玉秀教授的观点,因果关系以条件说为架构,而客观归责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架构,包容并取代相当因果关系说,以限制客观不法构成要件的适用范围,这实际上是限制条件说的理论。详言之,客观归责的核心部分为“创设风险”,即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至于“实现风险”,交由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2]可见,对行为进行客观归责,自然包括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适用。
从最全面的角度而言,对先行行为进行客观归责,从而判断能否形成保证人地位,应沿用其判断公式: 不允许的风险的创设、不允许的风险的实现、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一共要经过三个环节的检验:
不允许的风险是否创设、相当因果关系是否具备、被害人是否自我答责三个环节。如果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属于社会相当性行为,或者与所致法益侵害的危险之间不具备相当因果关系,或者被害人对其法益侵害自我答责,先行行为则不能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据此不具备保证人地位。
本案中,宋福祥与其妻李霞的争吵,是日常生活行为,属于社会与法律应容忍的范围,正如期待他人乘坐飞机失事死亡而劝告其登机一样,行为人没有创设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另外,宋福祥的争吵与其妻的上吊死亡也不具备相当因果关系。最后,宋福祥的妻子自主自愿地选择了上吊身亡,应自我答责。
因此,宋福祥与其妻吵架的先行行为不能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排除保证人地位的形成。
结语
本文以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为例,承认先行行为类型保证人地位的存在价值,但对之作出以下限定:
一方面,先行行为如果没有故意或过失,不能形成保证人地位; 另一方面,先行行为如果不能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也不能形成保证人地位。换言之,先行行为若能形成保证人地位,应通过以下流程的检验:
( 1) 行为人必须对先行行为具备故意或过失;( 2) 先行行为必须不能具备社会相当性; ( 3) 先行行为必须与所致法益侵害的危险之间具备相当因果关系; ( 4) 被害人没有自我答责。
可见,宋福祥与其妻的争吵行为,因不满足以上流程的检验而不能形成保证人地位,由此不具备先行类型的保证人地位。同时,宋福祥也不具备我国刑法通说规定的其他三种类型的保证人地位: 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有人可能认为,我国《婚姻法》第 22条规定了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这成为夫妻之间应当救助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诚然,“抚养”一词背后的含义是: 夫妻之间通过帮助对方的物质生活,从而让其生命得以继续存在。从目的解释上讲,夫妻之间在另一方有生命危险时不救助,显然不利于对方生命得以继续存在。然而,刑法目的解释如果超越了语词“可能的含义”,成为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应当禁止,以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从“抚养”的语词来看,很难认为其在字面上包含了“救助”。因为“抚养”是指从物质上供给其生活,“救助”
是指遇有危难时救其脱离险境,这是两种含义。至少在语词上,“抚养”超越了“救助”可能的含义。那么,将抚养义务解释为救助义务,就成为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不能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是能形成保证人地位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据此,宋福祥对其妻李霞没有任何类型的保证人地位,无须对李霞的死亡负责。一如陈兴良教授所言,法院判决宋福祥构成故意杀人罪,实为道德战胜法律之结果。
参考文献:
[1]陈兴良. 刑法学知识的转型( 学术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许玉秀. 主观与客观之间[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3]林钰雄. 新刑法总则[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