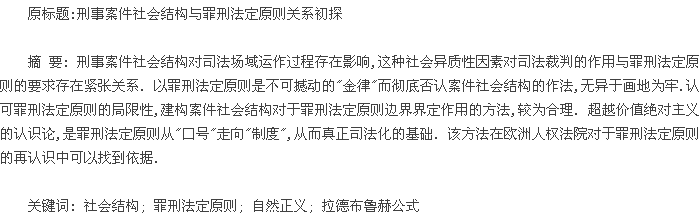
20 世纪上半叶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 (LegalRealism), 对传统大陆法系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规范的法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并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批判法学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法学研究的对象冲出了逻辑的藩篱,逐渐向经验前行. 在法律现实主义的队伍当中, 受行为法学的影响, 布莱克(DonaldBlack)教授以"科学的法学研究"为基础,发现了司法过程中案件的社会结构. 在布莱克看来,一直被看作人类行为的事物可以视作社会生活的运作行为. 每种社会生活皆为一项数量变量,在不同的社会位置或方向上有更多或更少的量[1]. 具体到司法场域当中,除了以规范分析为基础的法律的技术特征---法律准则具体应用于实际案件过程外,每一案件还有其他社会特征:谁控告谁? 谁处理这一案件? 还有谁与案件有关? 每一案件至少包括对立的双方(原告或受害人以及被告),并且可能还包括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如律师和友好的证人)及第三方(如法官或陪审团). 这些人的性质构成了案件的社会结构[2]. 案件的社会结构对案件的裁判结果往往具有重要影响. 布莱克的发现,将由于司空见惯而置若罔闻的司法裁判过程中的重要要素重新置于显要位置. 中国有学者以案件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发现了案件的法理学裁判模式和社会学裁判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法理学的裁判模式是显性的,社会学的裁判模式是隐性的. 隐形的社会学裁判模式为显性的法理学裁判模式提供社会、 现实的支撑;显性的法理学裁判模式为隐性的社会学裁判模式提供规范、合法的形式[3]. 在刑事司法场域中,自由谈论案件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始终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掣肘. 那么,要真正在刑事领域展开案件社会结构的探究,必须首先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回答:社会学的裁判模式是否与罪行法定原则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如果存在,是应当彻底否认案件社会结构的作用,还是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进行调节? 如果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定灵活适用的空间,案件的社会结构又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刑事案件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案件的社会结构, 导致了社会学的裁判模式.这种裁判模式偏重经验,是对传统的法理学裁判模式的补充. 案件社会结构的发现与司法实践中纯粹规范方法的局限性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司法过程,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的过程,而是一个发现裁判规范的过程. "发现法律不仅仅包含在法典中查找法条和获得解答, 法律推理与法条检索并不相同,而且发现法律也不是非人格化的,技术化的,科学的过程. 为了了解法律,必须训练一种重要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一种未被具体的和可计量的规则和程序所束缚的大脑功能[4]. "即发现法律的过程,与案件的异质性社会结构具有较大的关系,需要将逻辑与经验,规范与事实相结合才能接近最为合适的裁判结果. 但是,一旦将个案异质性的社会结构纳入到规范选择和解释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法官或者学者都无法忽视悬在刑法学人头顶的利剑---罪刑法定主义.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一般以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表述,是近代刑法最重要的原则. 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要没有制定法的规定,就不存在犯罪与刑罚,或者说,能够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只限于制定法[5]. 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起源于法国 1789 年 《人权宣言》, 其拉丁语的表述为"Nulla crimen sine lege,Nulla poena sine lege". 在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兴盛和 20 世纪初的萧条、两次世界大战, 随着人权保障的理念被各国逐渐接受,罪刑法定原则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①. 虽然在表述和要素上,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以经验主义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都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两项基本的内在要求:(1) 法律必须为公民提供公平的警告(fair notice);(2)法律必须限制武断的司法权力[6]. 只有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内在要求的行为,才在实质的意义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则,即便在形式上与"罪法定"或者"刑法定"发生了冲突,也不能武断的声称行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用罪刑法定主义的两个内在要求来对刑事案件的社会学裁判模式进行检验,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异质的社会结构) 与罪刑法定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首先,在具体个案中,广泛考虑案件的社会结构作出裁判, 会导致司法判决陷入纯粹经验主义泥潭,从而危害到公民对于法律的预测可能性. 同样性质的案例,由于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而最终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的作法与罪刑法定要求是彻底相悖的. 例如,着名的许霆案与名不见经传的何鹏案,案件的规范结构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二者的社会结构不同,导致了在量刑上的巨大差异,这无疑危害了司法的可预测性②和公信力[7]. 其次,从大陆法系不信任法官的传统出发,非规范的社会结构会大大增加法官在选取规范和认定事实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具有任意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公民的自由是一种潜在威胁. 尽管法律现实主义认为法律是法官的行为或者对法官行为的预测的观点或许具有某些经验性的价值,但是其忽略了已经存在的法律的重要性,因此缺乏一个能够评价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员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的标准[8]. 即案件的社会学裁判模式,无法确证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考虑案件的社会结构,而不会滥用自由裁量权利. 这样,案件的社会结构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种方案是限制甚至取消案件的社会学裁判模式,从而维护罪刑法定主义内在要求, 另一种方案是设计一种模式,使案件的社会结构能够与公平警告 (fair notice)和限制武断的裁量权相结合.
第一种方案, 从罪刑法定是刑法最基本原则出发,否定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任何侵犯. 有学者认为,不可预测的刑法对于国民而言,不是自由的保障,而是生活的牢笼[9]. 以此为出发点,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表明,异质性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了法官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这是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所以,实现定罪量刑公正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异质性社会结构对定罪量刑所带来的影响,避免量刑的社会学模式发生作用[10].就连发现案件社会结构的布莱克本人,面对不同案件中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的歧视,造成司法上的不平等现象也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方案:"一个方法是通过法律合作社团的引入改变案件的社会结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法律的非社会化改变处理案件的过程,第三个是社会的非法律化改变法律权限本身,以期待法律系统的歧视和不平等减至最少[11]. "第二种方案,建立在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基础上, 在社会结构较为特殊的案件中,允许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即案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上的灵活性.
选择第一种方案还是第二种方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容许任何侵犯的铁则? 还是罪刑法定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当其作为手段的本体与其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允许罪刑法定与其他社会价值进行妥协? 只有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做出解决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之间紧张关系的尝试.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案件社会结构
发挥作用的基础尽管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并非是刑法要实现的终极目标. 罪刑法定的存在是以其实现一系列目标的功能价值为基础的. 罪刑法定原则的目标可以分为 4 部分: 第 1 部分是保障人权;第 2 部分是提高政府治理的合法性;第 3 部分是通过将立法权分配给恰当的部门, 以保护民主制结构;第 4 部分是明确刑事定罪要实现的目标[12]. 因而,有学者认为刑法理论当中的首要原则是选择自由(principle of free choice),为了维护公民选择的自由, 刑法学中存在 4 个在地位上并列的基本原则:第一,罪刑法定原则;第二,行为主义原则;第三,责任原则;第四,个人责任原则[13]. 既然罪刑法定原则并非最终目标, 并且有与其相并列的原则存在,那么罪刑法定在理论上就存在与其他原则或者与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具有明显的正确性,(在法律实践当中)律师和其他司法参与者仍然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考虑到提供保障的角色,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出现了困境[14].
仅仅通过理论分析罪行法定的局限性是不够的,要真正揭示出罪刑法定原则与其他重要价值的冲突,需要在实践中寻找法院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选择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践. 这样的实践必须具有两个属性:一是作出实践的法院所在的国家必须接受罪刑法定原则,二是这种突破不是偶然的枉法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未来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具有指导意义的行为.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在对于民主德国(GDR)边境士兵案中法律推理方法的选择, 符合本文的要求.
1990 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之前,两国曾经达成协议,关于统一以前发生在民主德国境内的犯罪行为,适用民主德国的刑法,除非在个案当中联邦德国的刑法对于被告人更为有利. 这种方法在通常意义上的犯罪中,没有出现实质性问题. 但是这 种 情 况 在 所 谓 的 " 政 府 犯 罪 (governmentcriminality)",即民主德国的官员和士兵的行为根据民主德国的法律是适法的,但是根据联邦德国的刑法被视为极为严重犯罪的场合,却发生了变化[15]. 在柏林边境士兵案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统一之前,民主德国通过《边境法案》授权士兵对试图越过柏林墙进入联邦德国的人使用致命性暴力,因此如果根据统一协议当中的规定(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民主德国的刑法,那么士兵的行为当然不构成犯罪,但是对无辜公民射击的行为是对正义彻底地违反,不处罚士兵,裁判结果会与正义发生冲突;处罚士兵,就是溯及适用法律,与罪刑法定原则提供公平警告的内在要求相冲突. 与战后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类似,德国联邦法院和宪法法院认定此类案件中士兵行为构成犯罪①.
德国联邦法院和宪法法院在论证士兵行为构成犯罪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推理模式:第一种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法学模式,第二种是运用拉德布鲁赫公式(Radbruch Formula).在第一种模式中,法院试图通过解释,否认《边境法案》的效力. 通过宪法的视角,法院提出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与暴力程度相关),来论证边境法案并未允许士兵对非武装企图和平越过边境的人使用致命性暴力[16]. 这种传统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受到了广泛批判,显然这样的解释是为了入罪而做出的解释,没有考虑民主德国边境法案的初衷.考虑到各种批判意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开始探求一种非实证主义进路. 其法律推理的核心可以在拉德布鲁赫公式中找到[17]. 拉德布鲁赫公式是德国法哲学大师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二战之后,为了解决纳粹法给法律实证主义带来的危机而提出的方案,该公式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立法和权力为保障的实证法具有优先地位(相对于正义),即使其内容不正义且不能给人民带来好处,除非法律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无可容忍的程度,这样"有缺陷的法律"必须向正义让步.
第二阶段, 在法律甚至没有尝试靠近正义,或者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在公布的法律中被故意背叛的场合,这样的法律就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 就法律而言,包括实证法,必须被定义为一个根本目标是服务于正义的系统和制度[18].
从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推理出发, 自然正义(nature justice)应当作为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实证主义方法的安全阀(safety-valve). 将正义准确置于法律体系的分层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在德国法律体系各个部分发挥着作用,且成为了法律解释的一个指导性原则[19]. 在柏林边境士兵案中,德国最高联邦法院和宪法法院,认为民主德国的边境法案违反了自然正义,从而不能作为免除士兵行为责任的事由. 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必须为公民提供公平警告,即公民可以通过法律来预测自己行为后果,在本案当中,边境士兵的行为具有实证法支持,在司法中否认实证法的适用, 破坏了士兵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测可能性,这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是相悖的. 因此,有一部分边境士兵,根据欧洲人权公约(ECHR),向欧洲人权法院(ECtHR)提出申诉,认为德国法院的作法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欧洲人权法院在 Streletz,Kessler,Krenz 和 K-H.W. 判例中认可了德国法院采取拉德布鲁赫公式进行推理的做法①.
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起源于欧洲,"罪刑法定"作为基本人权已经写入了欧洲人权公约 (ECHR),欧洲人权法院认可拉德布鲁赫公式的作法,展示了罪刑法定与自然正义之间,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矛盾. 罪刑法定原则显然不是普适的真理,在适用罪刑法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罪刑法定所追求的目标,考虑到公平正义,也要考虑到案件中的异质性结构. 因此,承认罪刑法定主义的局限性,探索案件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主义之间的关系,存在必要性.
三、社会结构:罪刑法定主义疆域的边境线
从表面上看,拉德布鲁赫是从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探讨规范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实际上拉氏的首要目标是对于法官行为的指导,而不是分析法律的本质属性[20]. 在柏林边境士兵案当中,拉德布鲁赫公式解决的不是民主德国法律是否符合自然正义标准问题,而是是否应当选择适用民主德国法律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要求问题. 如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的界限? 根据"统一协定",在普通犯罪中适用民主德国刑法典, 不存在罪刑法定主义问题, 但是在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边境士兵案中,罪刑法定与自然正义的冲突成为了一个重要争议点.
是不是在普通案件中不存在正义与法的确定性之间的冲突? 答案是否定的. 士兵案中,士兵身份的政治色彩,导致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存在被突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换言之,罪刑法定主义的边界应当从案件事实中寻找.
案件的社会结构作为司法场域中规范之外的经验要素的集合,正好为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自我限制的标准. 罪刑法定原则与自然正义及其他重要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是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限制的原因,而自然正义与其他社会价值在个案中的体现,则依赖于具体案件中的异质性社会因素. 这样,案件的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被一种相互制约、 相互界定的建构性的关联所取代. 这是社会结构对罪刑法定主义的限制性作用.
在进一步探讨社会结构的功能之前,必须明确以下 3 个问题:
首先,应当将案件的社会结构与规范刑法学中的经验材料相区分. 传统的规范刑法学并非不重视经验性的材料. 例如,张明楷教授曾指出:(规范的法律意义)并非传统的法学方法所说的,仅仅隐藏在制定法中,隐藏在抽象而广泛的意义空洞的法律概念中,相反的,为了探求此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生活事实[21].
因此,罪刑法定并不意味着机械地适用法律,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教条主义同样是格格不入的[22]. 但是,规范刑法学对于案件事实探讨的范围, 必须囿于犯罪构成或者规范刑法学理论.
案件的社会结构中很多要素,是无法被传统的规范法学所包含的.
其次,应当突破社会学对于案件社会结构研究的范式. 社会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重描述,轻建构. 现有的研究更多是通过调查、数据揭示案件社会结构发生作用的模式,缺乏对于案件社会结构的理性思考. 事实上,在发现案件的社会结构之后,如何规制这种结构发挥作用的机制,如何利用这种结构达到合理建构司法过程的目标,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连一向主张法律科学研究方法的布莱克,也试图为案件的社会结构寻找一个理性主义的归宿,提出了"社会时间(social time)"的概念. 布莱克认为,犯罪与刑罚的现象是"对"与"错"之间的冲突(conflict),导致这种冲突的基本原因是社会时间变动[23]. 与布莱克的作法类似,在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互动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案件的社会结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而是其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肯定案件社会结构对罪刑法定范围的限制作用,并不是否认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允许社会结构中的任意要素发挥作用,那么就并非是在限制罪刑法定原则, 而是彻底否认罪刑法定原则. 认为案件的社会结构能够控制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并不意味着任意"量"上的案件异质性结构都可以对罪刑法定原则产生限制作用,否则,同样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即应当在质与量两个层面对社会结构的作用进行限制. 在质的层面,仅允许能够反映自然正义和公共理性的社会异质性结构对罪刑法定原则发挥影响,非理性的偏见、少数人或团体的私利、不合理的民意和舆论等不能稳定表现社会正义的因素,不能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限制性因素. 关于民意与舆论的问题需要进行补充说明,并非一切民意或舆论都不能发挥作用,事实上,民意与舆论正是社会共同体对于正义认识的表现形式,只有不理性、被操纵的民意和舆论才是限制适用的对象,因此需要对民意或舆论的内容进行实质判断. 在量的层面上,为了权衡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与社会结构所表现的价值,可以借鉴罗尔斯提出 的 新 认 识 论 方 法①, 即 反 思 性 均 衡 (reflectiveequilibrium)[24],具体地说,罪刑法定作为一种法治的传统可以作为任何一个判断者内心中的原初信念,这种信念能够解决大多数案件,但是当异质性的社会结构表现出自然正义价值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场合,更有可能会对原初信念做出修正,只要这种修正能够获得合理的解释.
四、结语
劳东燕指出:"罪刑法定原则明文宣示于刑法已有多年, 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却仍不过是社会主义法制橱窗里的展品. "由此,她提出了一个困扰着规范刑法学多年的疑问:"罪刑法定的宗旨和要求如何从抽象的逻辑世界走进具体的生活世界[25]"这种困惑来源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 中国刑法学界存在一种普遍的认识, 即罪刑法定是一种具有至高地位的、不可妥协与折中的、单一的终极价值. 这种对于罪刑法定价值绝对主义的认识论, 导致了在运用罪刑法定原则的时候, 特别是当罪刑法定原则与自然正义或者其他社会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难以作出选择. 任何突破罪刑法定的企图都被视为离经叛道,这样罪刑法定原则变成了一种口号, 因此不可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只要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单一的主流价值,就不能允许任何质疑,因此反而会限制罪刑法定发挥作用. 就像盖尔斯敦指出的:"一般来说,追求单一的主流价值,无论代价是什么,都会导致片面性的后果,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也很少有人能接受[26]. "实际上,罪刑法定原则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面向, 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 (negative principle oflegality)认为,法律系统的最高关注点应当是防止国家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公民, 而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positive principle of legality)应当追求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即强调司法需要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27]. 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理念,是因为忽略了罪刑法定的积极侧面. 只要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与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相关,就应该直面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 在克服这种局限性的过程中,罪刑法定原则才能从神坛走向生活,刑法学才能走出价值绝对主义的囹圄. 刑事案件的社会结构,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
参考文献:
[1] 布莱克. 正义的纯粹社会学[M]. 徐昕,田璐,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68.
[2] 布莱克. 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 郭星华,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
[3] 张心向. 死刑案件裁判中非刑法规范因素考量[J]. 中外法学,2012(5):1021-1045.
[4] Scott J S. Legalit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37.
[5] 郑泽善. 刑法总论争议问题比较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6] Marc Ribeiro. Limiting arbitrary power:the vagueness doctrine in canadian constitutional law[M]. Vancouver:UBC Press,2004:39.
[7] 赵秉志,张心向. 刑事裁判不确定性现象解读---对"许霆案"的重新解读[J]. 法学,2008(8):41-52.
[8] Francis A A. The habits of legality: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0.
[9] 张心向.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刑法运作实践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3.
[10] 汪明亮. 论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J]. 现代法学,2009(5):78-90.
[11] 李瑜青, 张善根. 论在社会结构中的司法与超越---兼评布莱克的 《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 》[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8(4):3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