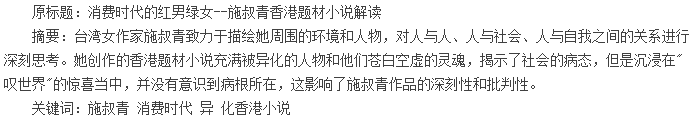
施叔青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5年到1976年,这期间的作品主要以她的家乡鹿港小镇的风土人情以及男女情欲、婚姻家庭为创作题材。白先勇在《约伯的后裔》序中说:
"死亡、性和疯癫是施叔青小说中迴旋不息的主题",她早期作品受当时台湾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弥漫着卡夫卡式的梦魇气氛。1977年,施叔青跟随丈夫到香港生活,以香港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开始了她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她创作的丰收期。华洋杂处的国际化大城市香港,多种文化兼容并蓄,互不干涉,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施叔青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引起了她"叹世界"的兴趣,施叔青说:"我觉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象香港这样有利我的写作。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的社会比较封闭,没有香港的'国际性',我也住过纽约,但在那里寄人篱下,很寂寞。"只有在香港,"置身华洋杂处的社会,叹世界的本性出现了……"白先勇在《驱魔---香港传奇》序中说:"施叔青选中香港作为她的写作题材,算是挖到了一座所罗门宝藏".
施叔青的香港题材小说为我们打开了看世界的一扇窗口,通过对日常生活及男女情爱的描绘,反映了物质极度丰富的消费社会里红男绿女们的空虚灵魂。第三阶段是1994年以后,施叔青重返台湾寻根,创作了史诗般的《台湾三部曲》。她皈依佛教,为台湾高僧圣严法师作传《枯木开花---圣严法师传》,开始在宗教层面探寻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纵观施叔青的小说,就像白先勇所说的,"透过她自己特有的折射镜所投射出来的一个扭曲、怪异、梦魇似的世界。光天化日之下社会中的人伦、道德、理性,在她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那是一个不正常、狭窄的,患了分裂症的世界……".施叔青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世界,在她的小说中充满被异化的人和他们苍白的灵魂。她揭示了社会的病态,但是她自己可能沉溺在"叹世界"的惊喜当中,而没有认识到病根所在,缺少自觉的反抗意识和批判意识,也没有提供治疗社会与人性的良方,这些影响了她作品的深刻性。
一、消费时代人的物化
波德里亚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人们被物质所包围,生活在虚假的物质丰足的狂喜之中,消费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主要生活内容。马克思说:"在商品世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拜物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集中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人们对自身的崇拜变成对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一种独立的、控制人的强大的异己力量,在马克思眼里,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主宰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就像原始社会的人对图腾的崇拜,不同消费品,如服装、首饰、包、手表、汽车等扮演了图腾的角色,传递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信息。"在西方物质社会……个人的身份受到他或她的物质财产的符号意义之影响,也受他/她与这些财产的联系方式之影响。物质财富也说明了他/她属于哪个群体,而且还是在社会物质环境中寻找其他人的手段。此外,物质财产向人们提供了关于其他人社会地位的信息。""人们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并不仅仅是对自己可支配的货币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什么、怎么来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也就是说,是自我认同的表现".
消费决定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我想象的塑造。
《维多利亚俱乐部》中维多利亚俱乐部采购部主任徐槐和总经理威尔逊勾结贪污,大肆收取供应商的回扣和贿赂,一切只为了贪图更好的物质享受,他的人格是完全被金钱所控制的物化的人格,他的生活中除了追求金钱,再也没有别的人生目的和理想。他第一天到维多利亚俱乐部上班,下班后便立刻为自己买了一条皮尔·卡丹的领带,这是他的第一件名牌,也是他的身份象征。
后来他发现皮尔·卡丹在名牌中属于最低的档次,便开始以消费阿曼尼和登喜路为荣。如果没有这些名牌,他便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他的自我价值只能通过消费名牌来实现,是物质富裕而精神匮乏、自我丧失的人。
徐槐喜欢购物,在购物中得到存在感和满足感。"出门旅行,徐槐在异地相距遥远的商场疲于奔命,便格外想念香港购物的种种方便,没有一个都市像香港一样集中,两部路便可以从一家走到另一家,任你精挑细选,一天走下来,丝毫不疲倦。……每次出门回来,徐槐必须到他经常流连的商场转过一圈,把他熟悉的名牌店一排看过去,才真正觉得回到家了".
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从物质极度匮乏的大陆移民到香港的上海人,徐槐始终摆脱不了对贫穷的恐惧,对资本主义社会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充满赞叹和满足。"徐槐滑进一个充满乐音的商场,穿燕尾服的银发洋人,腰板挺直坐在黑亮的钢琴前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池中绢印版画展览介绍一种崭新的技巧,乘着玻璃升降机上楼,这商场的推销术更上一层楼,一家家小而精致、独沽一味的专卖店,去惯百货公司的徐槐一类的常客,梦想不到能够独立成家的物品,在这儿分门别类,各立门户成专卖店,伴着池中的音乐与艺术,购物变为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不再是单纯地为需要而采购".
就像社会学家所说的:"百货公司不仅仅是商品被购买和销售的地方。除了推动'文化资本'的买进之外,它们形成了公共空间和被看景观之巨大延伸的一部分。这些公共空间和被看景观包括国际展览会、博物馆、画廊、休闲公园和不久后诞生的电影院,它们提供了惊人丰富的便利、娱乐和视觉快感。人们造访这些地方就像受到旅游的吸引,因为这些场所本身给予了兴趣和快感,它们就像现代性的纪念碑".
任何消费都是发生在一定空间里的消费,包括私人消费空间和公共消费空间,其中公共消费空间是生产与消费发生关系的桥梁,是商品价值能否最终实现的地方,为了迎合消费者需要,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消费空间的设计日益受到重视。"消费空间是一个朝圣空间。
人们对不同的空间,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和情感依赖性,如对于家、家乡、所读的学校等等,人们都会倾注一定的感情,并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情感依赖。这些空间因而成为人们的'中心',被赋予神圣的价值和意义。消费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消费者的'中心'.对于那些以逛商场为休闲活动的消费者来说,消费空间显然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和心理支持".
对徐槐而言,逛商场类似于"朝圣",消费空间则是他的"圣土".
施叔青描绘香港"是个人世间不常见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除了吃就是讲究穿着,争逐名牌,触目尽是鳞次栉比的商场货品,找不到一间可以消磨片刻的画廊或书店"."然而,在这种物质过分膨胀的地方住久了,成天价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的,无非是商品,久而久之,人被同化,虚荣了还不自觉,犹自沾沾自喜,相互炫耀".
徐槐把物当作生命,害怕被物质世界抛弃,采购主任被停职一个月后,他走进商场,感慨"那种昔日与物连在一起,人在货品中游走,伸手随便可触摸、变成物的一部分的归属感没有了。闪亮的银柱折射出自己被切割的影子,支离破碎,购物的方式日新月异,已经分工细致到这种地步,他落伍了,跟不上潮流了".这种在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的危机感迫使他被物质欲望所控制而必须不断赚钱,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演变成后现代商品化时代的"我买故我在",消费成了人的本质,消费及其消费品成了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而且是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所以徐槐不满足于系一条皮尔·卡丹的领带,而必须消费更高档的阿曼尼和登喜路,才能体现他的社会身份和价值。施叔青所描绘的正是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完全被物质所控制的图景,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人们苍白而空虚的灵魂。
在消费时代,爱情也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
徐槐追求情人马安贞时用物质引诱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用物质来俘虏她?第三次见面,徐槐捧来精装的日记,她烫金名字的缩写,然后是杏黄哑面信笺,她的全名反白浮现在右上角,西洋贵女的派头,接下来是巧克力、香槟,假公济私奉献给她","如此周而复始,徐槐忙着教她叹世界,以致无暇倾听她的心声",最终她成了徐槐的玩偶,"她透过徐槐的眼睛来看世界,他是她行动的主人,她没有了自己".在物质享受面前,马安贞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成为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主体意识的人。她贪图徐槐给她提供的物质享受,徐槐贪图她的年轻漂亮时髦,这种缺乏精神沟通,以欲望而不是情感为基础的畸恋正是现代社会的怪胎,爱情双方更多考虑的是实际利益和欲望的满足。在《情探》中,同样是从大陆到香港的书报发行商庄水法,半生劳碌,中年事业有成,生活悠闲富裕,在一次酒宴上偶遇一小报女作家殷玫,惊为天人,想在她身上抓住青春的尾巴,寻找年轻时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爱情,摆脱平淡乏味的婚姻生活,释放临老最后的激情,结果殷玫却是个半卖身的妓女,只要给钱都可以和她上床,性只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她在和庄水法交往的同时又勾搭茶叶商人汪大达,借口想买楼向汪大达借十万,被汪大达一口拒绝。庄水法心目中浪漫神秘古典的女神形象瞬间倒塌,他失落地走在雨中的香港,香港这座繁华至极的城市用金钱的力量无情地打破了他的爱情美梦。《愫细怨》
中的愫细作为一家设计公司的白领丽人,经济独立,但是精神上依附男性,缺乏独立意识,洋丈夫狄克有外遇后,她精神上没有寄托,很快投入商人洪俊兴怀抱。香港土生土长、中学毕业后就到美国读书的愫细,在二十年前从大陆移居到香港、靠开印刷厂起家的洪俊兴面前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接受的是不同的中西文化的教育,但在香港却奇妙地相遇和融合。
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天长地久基础上的爱情,而是一种苟且的、及时寻乐的露水姻缘,他们为了满足各自的欲望走在一起,和《窑变》中方月和姚茫的关系一样。在这种关系中,男性作为引领者,带领女性走进一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享受世界。"从认识之后,洪俊兴一直是她的主宰,愫细由他领着,去的场合全属于洪俊兴的领地,她被带去自己永远不会找到的画廊,把中国现代名家的画介绍给她,他陪她到博物馆、拍卖行看瓷器、古物展览,当然,还有数不清躲在巷子底,一家家烧出地道潮州菜、广东小菜的小馆子。愫细不能否认短短几个月洪俊兴引领她,进入一个前未去过的境地,她是在一寸一寸地被吞没。"愫细陷入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当中,一方面对洪俊兴不满,一方面摆脱不了欲望的桎梏,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面前,她的这种反抗形式显然是软弱和无力的。
《香港三部曲之三·寂寞云园》中的富三代黄蝶娘的曾祖母黄得云只是个妓女,靠出卖肉体起家,通过经营房地产获得巨额财富,跻身上流社会。黄蝶娘自认出身豪门巨族,看不起靠自己奋斗往上爬的中小资产阶级。她出于好奇心参加了一个职员的聚会,认为"一屋子俗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那晚的客人都是银行、会计行、股票行的中层职员,也有两个是政府部门的低层公务人员。虽然一个个身穿皮尔·卡丹的牌子,喝红酒,谈音响,黄蝶娘一眼看出这群中年的专业人士,全都出身寒微,他们没有祖荫家世做后盾,而是靠苦学申请奖助金受完高等教育,甚至海外留学回来。他们凭着一张文凭,加上干劲冲天,力争上游,正在一步步往上爬"1家庭、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所进的学校、所属的会所、甚至教会相濡以沫,他们是消费时代的新族类,崇尚设计师的名字,以所穿的名牌来识别定位,以设计师的风格来代表自己。"中产阶级的兴起正是现代消费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构成庞大的消费人群,他们的消费欲望和购买能力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消费文化的新主角。
施叔青无意间揭示了消费时代中产阶级的实质和面目。
黄蝶娘纡尊降贵地交结了一个中产阶级男友,是一家连锁快餐店推销部经理,却对他百般玩弄,毫无感情,以看对方笑话为乐,可以讲是一个完全被上流社会异化、已经没有健康心理和不知爱为何物的女性。在她眼里,香港大学的文凭、学生运动领袖、标榜贫穷节俭、参加保钓、中文运动、反贪污争取社会公义等活动都是可资嘲笑的对象。她的眼里,一个人只要不是出身上流社会便天生低贱,无论他们后天多么努力和有才华都无法洗掉身上天生的印记与原罪。上层社会成员对底层社会成员或者经济发达地区人对经济不发达地区人没有来由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实际上正是他们精神空虚、庸俗浅薄、除了家庭资源与城市资源外毫无个人能力与自我意识的表征,是完全被环境异化和控制的人。她看不起各行各业专业人士的勤奋与拼搏,看不起他们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男友表明自己是坐火红法拉利跑车的女人而不是坐普通日本轿车、到快餐店吃盒饭的女人,"平生无大志,以玩乐为正职,冬天要到瑞士去滑雪,夏天到人间仙境去避暑",亮明了自己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以后,得意洋洋而去。但是她的这种对社会与他人毫无贡献的自我得意和炫耀只是一种自我被异化的浅薄无知而已。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物化"的后果概况为:(1)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人们的职业越来越专门化,他们的生活囿于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这使他们的目光很难超越周围发生的局部事件,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2)对物的追求窒息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他们面对的现实不再是生动的历史过程,而是物的巨大累积;(3)它使人丧失了创造性和行动能力,只能消极地"静观",物的力量压倒了人的主体性。
这种物化的现实使人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施叔青笔下的人物正是一群被物化而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人: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他人;只知道追求个人利益,贪图声色犬马的享受,毫不关心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沉浸在物质世界中而没有任何精神追求,成为灵魂苍白而空虚的被物欲吞噬的人。
二、自我价值的失落与寻找
"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雕刻的铭句,哲学家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步。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新的、间接的答案。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为了发现人的本性或本质,必须摆脱一切外部的和偶然的特性。"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
而且,如果任何这些东西确曾与人相关,那么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不过事实上,一个人越是从容不迫地使自己排斥这些和其他这样的东西,他也就越善。"人的本质不依赖客观环境,一个认识自我的人应该能够突破金钱财富地位环境等等物质障碍看到自己的内心和灵魂。
施叔青笔下的人物显然还不能摆脱外在的偶然性和物质的吸引,生活在迷茫困惑当中而不能自拔。
《窑变》中台湾小有名气的女作家方月跟着丈夫移居香港,丈夫很快在香港的股票交易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环康乐大厦四十二楼拥有一件摆满盆景的漂亮办公室,而方月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为了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体现自我价值,方月带着在台湾出版的两本小说集去应聘香港博物馆出版部中文助理编辑,开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方月对新生活充满憧憬,沉浸在好奇心和新鲜感当中,在给台湾友人的信中写道:
"大学时代把自己关在租来的小房间,对着稿纸喃喃自语,直至深夜犹不肯罢休的方月,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来了香港这几年,总算为自己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开始弄瓷器,很时髦、很贵族的玩意儿。"对婚姻失望的方月爱上姚茫---一个文物收藏家,为他丰富的中国文物知识折服,但是姚茫同样是个生活在物质欲望中不能自拔的人,只不过他把玩的对象是更加高级的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正是金钱的力量,使珍贵的古董文物成了供私人买卖的拍卖会上的商品而失去固有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他的住家"里面完全改修过,黑白强烈的对比,完全是现代的冷硬线条,特别设计的灯光打在一屋子的瓷器古物,使方月有如置身现代化的小型博物馆。为了节省空间,几面墙全被挖成空心,镶入一层层玻璃柜,由上而下,像神龛一样供奉着主人的精心藏品".文学评论家施淑一针见血地指出:"同样由于钱,这个以它的虚幻形式凌驾人本身的力量,可以使人的生活和生命彻底博物馆化".
姚芒有一颗"被那异己的力量挖空了的心",方月想在他身上寻找安慰和自我价值只能是缘木求鱼,注定失败和失望。
方月一步步走进物的陷阱,姚茫顺手送给她的小礼物,往往就是一条迪奥的丝巾、古奇的鳄鱼皮带、甚至以镶工闻名的卡蒂亚真金耳环……香港五光十色的生活更是令她叹为观止,她"很为纳尔逊家的宴会,那份荒诞神话般的色彩所迷","圣诞夜,她特地从附近天主教中学,请来白衣银冠的唱诗班,群集花园,站在星空下大唱《弥赛亚》。纳尔逊太太连中国新年也热烈庆祝。除夕夜,只见她通身一片红,拖地红绸旗袍,发际之间还插上一朵朵小红绒花,她把家里也布置得像新房一般,古董店买来的八仙喜帐高悬门梁,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乡下人做被面用的的土红大花布,用在圆桌上当台布。每位客人前面水晶杯下还压了个红包,也真难为纳尔逊太太这一份心思".施淑评论道:"给这现代社会生活加工成荒诞神话的不是人的想象力,而是钱,那流通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里的血液,那矗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神庙里的唯一物灵。是钱,这个把人的力量转换成它本身的力量,而后以自己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非人的力量,使富裕的纳尔逊太太可以把她的一年四季都变成中西文化的嘉年华会。也是透过钱的法力,她可以把中西宗教节日,象陈安妮'脱胎换骨'的古典美人扮相一样,来个内容和形式的颠倒,使它们充满纯粹消费性的荒诞神话的色彩。
"作为女主人公的方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和金钱的力量显然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一直到台湾画家何寒天的出现,才使她从对物质世界的迷醉当中惊醒过来。何寒天批评她变得很俗气,"看你这一身穿戴,又浅薄又做作,要是你走在中环人群当中,我还真认不出来呢!""你以前的神采、灵气,全不见了",要求她重新创作,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何寒天的话给方月带来巨大的冲击,使她意识到沉溺于物质当中的生活无异于行尸走肉,意识到姚茫终日与冰冷的古物为伍,家里缺少人气,"架子上的瓷器渗出阵阵寒气",她终于离开姚茫的家,坐在出租车里"笔直地朝前看".方月因为迷失自我而痛苦仿徨,却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别尔嘉耶夫说:"人要获救,人的本质和价值的重心必须发生根本的转移,即必须从外在的自然实体移至人内在的精神。"方月要想获得解放,必须从物质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找到精神自由发展的空间,回归本真的自我,不被社会同化,具有反抗社会的勇气和批判社会的能力。马尔库塞认为物质需要并不是人的本质需要,人不但有物质追求而且有精神追求,这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却把物质需要变成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虚假需要,这种虚假需要变成了社会"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结果把人完全交给了商品拜物教的世界,并在这方面再生产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它的需要".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对商品的崇拜和人的异化,人的自我价值失落,就像施淑所说的,"可是到了香港,当人的尊严、人的意义眼看就要彻头彻尾的没面子的时候,作为一个作家,施叔青的创作者的意识起了作用:那无政府主义的物与物的生死场必须理出一个头绪,被颠倒了的世界必须再颠倒回来".施叔青看到物质社会对人的巨大的同化力量,她试图唤醒作品中的主人公,寻找他们失落的自我,让颠倒的世界再颠倒回来。
李子云认为"施叔青的作品常常掺入相当浓厚的主观色彩,而她对她笔下人物与社会环境的态度又常常呈现明显的矛盾。她对那个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环境既厌恶又欣赏,她对这群未能摆脱依赖惰性的女性既藐视又同情。特别是对于某些香港豪华聚会、交际场合,以及高级服装店、酒楼、餐厅的描写,有时脱离了表现人物的需要,过分铺排渲染,让人想到施淑所说的'叹世界'.
这'叹',显然不仅止于好奇,还包容有欣赏、赞叹之意。这种'叹世界'的态度,也就影响了作者进一步揭示造成人物悲剧的原因,与作者对于她所'叹'的那个世界的深刻的批判".但是瑕不掩瑜,施叔青以她的生花妙笔,敏锐的眼光对周围的人与事进行严肃的思考,写出香港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写出他们苍白而病态的灵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