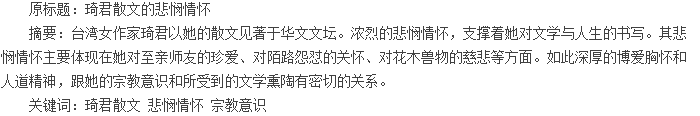
作为台湾散文的杰出代表,琦君共出版了《琴心》、《烟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千里怀人月在峰》、《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自选集》等近20本散文集。她的笔端流淌着袅袅柔情,夹杂着淡淡乡愁,其作品清新隽永,质朴秀雅。
自从琦君出道以来,大陆、台湾及海外有很多学者、作家对她的散文进行过研究,大部分论文聚焦在琦君怀乡散文上,潘梦园的《魂牵梦萦忆故乡---试论琦君怀乡思亲的散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从琦君出版的《琦君寄小读者》散文集很容易联想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再寄小读者》,有很多学者对冰心和琦君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主要观点集中在童心、母心、佛心等共性的关注上,并对琦君在此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做出了较为独到的分析,徐婷婷的《承袭中的突破与创新----论冰心影响下琦君的散文书写》算是一篇力作;研究论文中不乏对琦君散文创作风格、审美意蕴、叙事艺术、语言艺术等方面进行分类研究的,甚至有许多对单篇名作如《髻》等进行精细研究的,当然也有对她散文进行总体研究的。就总体研究来看,方忠的《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琦君散文论》无疑是比较独特而有价值的,不仅对琦君的怀旧忆人散文做了详细的分析,对其中表露的"乡愁"母题有独到的看法,而且对她独特的风格以及语言做了艺术性的分析。
笔者视野里,尚没有发现有学者对琦君的"悲悯情怀"做过专门的研究。台湾学者作家杨牧在《留予他年说梦痕·序》中曾把琦君和鲁迅搁在一起做过简单比较,其中出现过"悲悯"一词,但没有深入分析。在我看来,琦君的散文具有浓烈的悲悯情怀,主要体现在她的慈悲之心、博爱胸怀、人道精神等方面,这跟她的宗教意识和文学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悲悯情怀的艺术体现
陆机《文赋》中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意在说明文以情生,情因物感。而琦君散文中的悲悯情怀正是她从自身出发,感知外物内化而成。她的身上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这种爱体现在至亲师友之间、陌路怨怼之间甚至对花木兽物的关爱。
(一)对至亲师友的珍爱。兄弟的早逝使她对生命更为敬畏,对周围的人更加珍爱,对命运坎坷者更是寄予深切的同情。《金盒子》是琦君的代表作之一,它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回忆了早逝的哥哥和幼弟,文章中流露的手足亲情感人至深。
金盒子里装着作者与哥哥、弟弟的玩物,在她看来这是最珍贵的宝物。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个盒子,痛失手足的悲哀仍会不可遏制地涌上作者心头。这种亲身经历的痛苦带来的对生命的感悟是深刻而持久的。至亲的离世是琦君人生成长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正是这一点,让琦君更加体会到人世间要有更多的爱来消弭悲痛。
琦君有很多优秀的怀念老师的散文,印象最深刻的是写她的启蒙老师叶巨雄先生。这位笃信佛学的老师既严厉又和蔼,对于他唯一的女弟子十分关爱。离开老师三十年后,她收到老师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和照片时,回忆起往事,不禁泪流满面,这泪水饱含着琦君对老师的感激和思念。可以看出她对老师的感情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地点的转换而减淡,反而愈加浓烈。
在琦君的众多怀旧散文中,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散文是一大亮点,例如其笔下聪明绝顶但又玩世不恭的表叔、善良豪爽的长工阿荣伯、慈祥乐观的外祖父等等,其中《一对金手镯》非常具有代表性。作者回忆了和她吃同一妈妈乳汁长大的小姊妹阿月,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而命运却南辕北辙。当十八岁求学中的琦君回到家乡时,阿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和抱着幼儿的阿月在月下聊起各自的经历,"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不禁为阿月流下了"伤感的、无奈的泪".这流露出琦君对阿月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那晚,她还执意地和阿月睡在一张床上。这种同情和行为,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种以平等的角度出发的切实得令人心痛的关怀爱怜,从中透视出琦君的博爱胸怀和悲悯情怀。
(二)对陌路怨怼的关怀。对至亲师友的爱怜或许无甚特别,因为这种爱怜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但对于陌生人或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是否还能慈悲、宽容、博爱呢?琦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做到了常人一般所做不到的。
在《粽子里的乡愁》中,琦君回忆故乡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短短千字文,她却花了一半以上篇幅描绘了乞丐上门乞讨粽子的情景:"每回看到乞丐们背上背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对于乞丐,大部分人是厌恶鄙弃,可是儿时的琦君就对乞丐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是深刻的,以至于到了暮年还念念不忘那乞丐背上背着的婴儿,这种悲悯情怀是基于平等基础的一种本能的同情。
《两位裁缝》中写自己遇到一位诚实勤劳但不幸的裁缝,她"自恨无力量帮助她母子脱离困境,也为人世的不公平,好人常受折磨,深感痛心".成年的琦君依然保留那份可贵的悲悯之心。生活中萍水相逢的人都能勾起她的同情,她常常为许多人的不公命运而痛心不已。
琦君曾在司法界工作达26年之久。她经常访问监狱里的犯人,并和他们沟通。她体会到监狱的教化教育要比正常的学校教育付出更多的耐心与爱心。琦君始终带着仁爱宽容之心去看待她碰到的各类人,即使是与她毫无关系的囚犯也尽力用心感化。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宽容悲悯正是琦君的大爱所在。
说到对怨怼的爱,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她与姨娘的关系转化。琦君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娶回一位貌美时尚的姨娘,从此小琦君和其母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在著名的散文《髻》中琦君真实展露了自己和母亲所受的伤害。"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直抿嘴笑,父亲就直皱眉头",而姨娘梳的各种各样的头,"引得父亲笑眯了眼".
在琦君幼小的心灵上,父亲和姨娘对母亲的伤害难免使她伤心怨恨,但是在后来的散文中,我们看到她对姨娘的恨渐渐转化为同情。这位曾经剥夺了母亲大半生幸福的姨娘,在晚年陪伴父亲走过了二十多年后却孑然一身,这时琦君的怜悯之心取代了最初的怨怼,且看她对母亲与姨娘关系变化的描写:母亲和姨娘因为父亲曾经背对着身子梳头,互不理睬,而在父亲死后却惺惺相惜、相依为命。这要有什么样的胸襟和信仰的力量才能化解其中的怨怼呢?这其中,不难看出琦君散文悲悯情怀的广度和宽度。
(三)对花木兽物的慈悲。除了对各类不同人物的悲悯以外,琦君散文中的一花一木、一兽一物皆可为悲悯的出发点,以《柚子碗、盒及其他》、《虎爪》、《家有丑猫》、《寂寞的家狗》、《人鼠之间》等为代表。她爱狗,爱猫,爱鸟,爱鱼,爱蚂蚁,爱蟋蟀,爱树木,爱小草,爱鲜花。琦君认为:"随时随地,放开胸怀,与大自然山川草木通情愫,与虫鱼花鸟共哀乐,才能与人情物态起共鸣。"《柚子碗、盒及其他》描绘了幼年各类小器物,作者的爱物之心显现无疑。在她眼中,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各有妙处。对于柚子皮,她也能物尽其用,说出它的许多好处。而对于小动物,琦君更是注入了极大的爱心。《虎爪》中因为对小老虎的怜悯,年幼的琦君甚至不忍戴辟邪佑安的虎爪。
琦君对于任何生物兼怀恻隐之心。从琦君的各类散文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她的广博爱心,这种慈悲情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使人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得到心灵净化。她说:"我更默祷人类能尽量发挥仁慈的本性,爱惜到最细小的生命。佛家说得好,'为鼠常留饭,惜蛾不点灯'.如果真能有此伟大博爱精神,不但社会上不会有许多残杀案件,就是残酷的战争也可以避免了。"正是有了此种悲悯意识,琦君的散文才有了别样的审美意蕴。
总之,散文家琦君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声誉,不仅是因为其散文风格细腻温婉,更让人称道的是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于爱和美的感悟与追求,为读者营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心灵栖息地,而且她的博爱之心、人道精神、慈悲胸怀渗透在其散文的每个角落,悲悯情怀提升了琦君散文的审美价值。
二、悲悯情怀的形成原因
琦君散文的悲悯情怀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跟她的宗教意识和文学熏陶有关系,也离不开她的家庭环境和成长历程。
(一)宗教意识。琦君原名潘希真,出生在浙江永嘉的一个旧式大家庭里。父亲潘鉴宗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而母亲则是传统的农村妇女。琦君曲折而漫长的人生经历以及浓烈的宗教意识,是促使琦君形成作品中悲悯情怀的重要力量。
琦君的出生地瞿溪乡是一个宗教气息相当浓厚的地方,"我家乡的小镇上,有一座小小的耶稣堂,一座小小的天主堂。由乡人自由地去做礼拜或望弥撒,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当然两处都不去".琦君幼时就与父亲和哥哥分离,大部分的时间同母亲在一起。作为佛教徒的母亲,她的人生态度无疑给予琦君很大的影响,后来琦君也成为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佛教教义对她的影响很大。
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中,人生便是一个苦海,人会经历生老病死的种种苦难。幼弟和哥哥的夭折,父亲北上回来时带回了小妾后冷落了琦君母女,以至于幼年琦君就承受了很大的悲痛。成年后,家乡的许多亲人包括父母的相继离世,战乱年代家园不存,古籍难以保全的焦虑不安,是琦君遭受的一系列重大打击。尽管如此,在她的散文里却处处体现着一分从容淡定,这恐怕跟琦君自小受到佛教苦难意识的耳濡目染有关:生死的无常感以及瞬间幻灭的虚无感的深切认识,使得她内心充满着悲悯情怀。佛教有因果循环报应之说,即种善因得善果,促使信众通过博爱万物来修身处世。琦君的母亲便是这样,不小心踩死了一只小鸡也要归罪于自己。琦君眼中的母亲有着善良的本性、旧时代女性的美德,是全村的模范。从不杀生的母亲恪守着佛教徒的种种戒律,对万物的不忍之心与其本身母性的善良相结合产生了对众生的悲悯,这种悲悯深刻地影响到了琦君。而琦君自己,小时有着众多爱她的人,除了母亲,哥哥、父亲、外公、诸位叔伯,甚至长工阿荣伯、乳娘对琦君也很疼爱,浓浓的爱伴随着琦君的童年,这些都促使琦君以爱报恩,结下善缘,不断修行。用大爱来看待万物,自然就多了一分悲悯众生的情怀。
在琦君众多的散文中,很多情况下多会提到她的伟大的母亲。读她的散文,眼前时常浮现母女俩被姨娘欺负的种种情形。在《压岁钱》中,我们看到姨娘仗着琦君父亲的宠幸克扣小琦君的压岁钱,母亲虽然生气却克制忍隐让,"抿紧了嘴唇一声不响,眼里噙着泪水",而更多的时候母亲则是用打坐念佛来化解痛苦,念到最后,"脸容显得那般的平静安详,紧缩的眉峰也展开了,嘴角浮起宽慰的微笑。在那一片刻中,她的忧愁烦恼,真个都化作灰尘了".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琦君从小就学习佛教教义,并对教义有着深切的理解和感悟。后来又上了十年的基督教学校,虽然中西两种宗教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对万物的悲悯以及对众生的宽恕是宗教中共通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琦君一生在宗教的熏染之下,容易产生对万事万物的悲悯,这些都体现在她的散文之中。
(二)文学熏陶。宗教对于琦君影响之深不言而喻,但是琦君也并没有像她的母亲那样带有封建迷信般地信仰佛教,用它来解脱自己人生的不幸。看透世态万象后对人生的独特领悟,琦君悲悯情怀的形成还有赖于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对她的熏陶。 在这一点上,父亲直接影响了她。琦君的父亲潘鉴宗是一个传统的儒士,他酷爱收集经文碑帖,对佛经也有研究。父亲在琦君哥哥不幸夭折后对琦君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上私塾使得她有了一个扎实的古文功底,也为琦君的文学认知、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父亲之外,必须提到琦君的两位国文老师。
第一位是她的启蒙老师叶巨雄。他是一位通晓佛学的儒生,虽然他在琦君上中学时便出家做了和尚,但他的教育对琦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琦君就是在母亲和这位启蒙老师的教育下,逐渐对佛教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并受到启发。每当念到最后两句"慈爱之神乎,吾将临汝矣"时,琦君就好像有一种悲悯慈爱笼罩全身、登临幸福彼岸的感觉。
第二位则是琦君的词学恩师夏承焘先生。夏承焘字瞿禅,从他的表字中就可以看出他对于佛法禅理有相当高的追求。他的许多诗词都让琦君难以忘怀,特别是"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都当以温存的心,细细体味".
两位精通国学的老师通过古文诗词、佛学禅理,以文学的形式让琦君进一步懂得有限的生命中悲悯大爱的重要。
另外,琦君的二堂叔在她文学观的形成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鼓励琦君多看小说,多用白话文创作。琦君看了不少通俗小说和翻译的外国名著,凄美哀伤的爱情故事让她很感动。"他又送我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害我读得涕泪交流。"而且琦君每回读小说总是认为"小说并不难,只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细腻敏感的内心触动着琦君博爱悲悯的情怀,它是对自身生命的联想,也是对人间万事万物的慈悲,还有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感动。琦君散文有对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爱怜,甚至叙及人鼠之间成了朋友;有对导致她母亲一生不幸的姨娘的宽容,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有对"蜘蛛与蜜蜂"的慈悲与善良……琦君的散文世界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那种对于世情的通达悲悯的情怀,让读者久久不能忘怀。
总之,琦君散文的悲悯情怀是在宗教与文学两方面的共同合力下形成的。佛教与基督教的博爱与宽容,文学中的世情练达,兼之漫长岁月里对于人生的独到感悟,共同促成了琦君作品中的悲悯情怀。
三、结语
琦君的散文在台湾文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近20多本散文集的畅销不衰体现了其散文独特的价值。伴随着台湾社会的飞速发展,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趋向扭曲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等人性恶的种种表现,这些对于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琦君的散文就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她的散文既有文字和情感的阅读美感,又能以温柔敦厚、悲天悯人的表达使读者领悟真善美的存在价值。琦君曾说:"我却有一个信念,文学的最高境界,应与宗教汇合,凡是真的、美的,必须是善的。即使写丑陋也只基于关爱。"可以说,琦君散文的悲悯是"真",是"善",也是"美".
当然,关于琦君散文也有很多批评声音,诟病最多的是她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人生,只是看到了事物美好的一面,而没有揭出更多的病苦。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琦君创作的局限,而是她有意为之的,我们都知道她的成长并不缺少苦难的洗礼。幼年丧兄,青年双亲去世,后又遇战乱远离故土,正如她在《写作回顾》
一文中所说:"抗战期间,我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避乱穷乡,又经历了许多惊险,在工作中,我也领略到人间炎凉与温暖的滋味。"但琦君将亲身体会的人生丑陋面隐去,而在作品中描绘积极光明的一面,体现了她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和对人生真谛的思索,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悲悯呢?琦君还说曾"把人生美化得离了谱。但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够多,为什么不透过文学多多渲染祥和美好的一面,以作弥补呢?"琦君的想法太有道理了,用精神性的东西来拯救当代物欲横流的世界,虽然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但是生活中不能没有这种信仰。
如果人人以怨抱怨、以牙还牙,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琦君说,如果人人都能表现一份慈悲与善良,那么人世间就会充满一片祥和而成为天堂。这也许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吧!如今,琦君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散文透露出的悲悯情怀值得深思和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