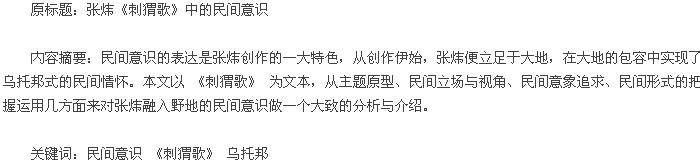
张炜是一个立足于大地的歌者,在这样一个追求物欲的时代,他的作品像一丝丝清新的风吹过文坛,而 《刺猬歌》 中呈现的民间意识也为文坛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指向与借鉴。
一. 《刺猬歌》 中的民间立场与视角
“民间”概念最早是由陈思和在20 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他在《民间的浮沉》 和 《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做了系统的阐述。陈思和将文学史分为庙堂、广场、民间三部分,打破了庙堂与广场二元对立的局面,民间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陈思和指出了民间的三大特征:1.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2.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3.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民间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自在。在自由的范畴中,原始生命力在面对苦难时抒发的淋漓尽致,民间力量尝试去跨越或是征服。而在自在范畴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衡量标准,虽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其自发自为性,使其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实现了民间话语的真实感和自在性的统一。
在 《刺猬歌》 中,廖麦与美蒂的生活方式便是民间自由自在的体现。廖麦为了与美蒂在一起,反抗着来自唐童的追捕,四处流浪却毫无怨言。这些像“怪物”一样的东西,让廖麦感到了压迫,他更渴望的是回归自然,走向和谐与真实,走向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张炜不急于向人们传输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而是做一个立足于大地的歌者。他写廖麦与美蒂交合的场景,这样一种原始生命力迸发的过程在美蒂一句“逮着汉子了”中达到高潮,他们在自然中获得新生,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与崇敬;而写珊婆,她为各类活物接生,最后“儿子们都投入了她的怀抱,她文化程度并不高,都在经验中自由自在的活着,成为尊重的精神支柱。”在 《刺猬歌》 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这也是张炜对民间意识的肯定与支持。
二.主题原型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一些用西方的“原型批评”理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1957年,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出版了《批评的解剖》,这使原型理论由心理学走向了文学意象理论。而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十分兴盛,这就为原型理论的中国化因素提供了重要前提。西方“原型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联系成为民间文化的永恒话题。张炜的 《刺猬歌》 在这方面运用较为娴熟。
(一) 人与自然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因此,在民间故事中,人与自然及其他生命的关系在想象世界中得以共存与延展,并因人的存在而蒙上了道德化、伦理化色彩。主题原型多与善恶相报、忠厚仁爱相联。体现在“动物报恩系列传说”和“感恩与负义”等故事类型中。
在 《刺猬歌》 中,人与动物和睦共处,与动物结婚,在动物怀抱中寻得归宿的内容比比皆是。他们用情感维系彼此,共同克服困难,共创幸福生活。在文中,廖麦与刺猬精美蒂由一见钟情到孕育生命再到情感危机,与人类夫妻间的情感并无差别。而霍老爷“晚年筑了一面大火炕,睡觉时左右都是野物,当然也有个把姨太太。他睡前或醒来都要亲一亲兔子的小嘴,从六十岁开始不再吃一口荤腥,主要食物是青草,像畜生一样。”他在大自然中获得新生,在共处中换取真心。
张炜不仅构筑人与自然及其他生命间平等的亲情及爱情,体现原始生命力在大地上的勃勃生姿,同时也对世俗的丑陋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感恩的动物”与“负义的人”的主题原型在文中也得以体现。以唐童为代表的天童集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建设“紫烟大垒”,开矿凿山,使原本葱郁的森林变成光秃秃的土地,动物失去了住地,变得无处可归,于是人与自然及动物和谐相处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紧接着人们的住地也收到了影响。青山绿水不再,于是人们也在自然界面前受到了惩罚。这样一个在现在看来常见的母题却被张炜用人与灵性动物的奇异故事中讲出,深刻性让人反省。
(二) 人与仙道幻境
张炜文章充满着奇幻色彩,受道家奇幻故事及海洋文学影响较大,在 《刺猬歌》 的写作中也毫不例外。其中就有徐福出海及精灵附体的神怪故事。
霍公用尽最后力气造楼船出海求仙,留下了不少传说,成为“半仙之人”,而唐童造楼船求三仙岛,虽最终到达的是三叉岛,却在岛上努力寻找徐福后人。建立徐福求仙的旅游景点,在经济目的完成的同时并不缺乏求仙求药的心理活动。
另外,珊婆与唐童的对话中也有三个字体现了“仙道”的影响———信狐仙。他们相信狐仙会带来准确预测,带来好运。这种敬畏神灵的意识在文中很常见。 《神灵附体》 一章中,金童公司的女领班“本是一个端庄秀丽之人,这会儿衣服都抓破了,敞胸露怀的,脸上全是垢物”。阴阳先生说她被狐狸附体了。这般表现似乎在神怪小说中颇为常见,张炜将其移植并加以创新,增加了文章的神异色彩。
(三) 民间传说原型
在 《刺猬歌》 中,也不难见民间传说的影子。廖麦与美蒂的爱情主线就受到了田螺姑娘这一传说的影响。农夫拾到田螺,用心养护,为报答农夫,田螺幻化成人形,来为农夫做饭,后被农夫发现,两人结为夫妻。而后来喜欢田螺姑娘的蚂蝗精前来搅局,将田螺姑娘困于洞内,农夫与伙伴们采用盐攻的方式,打败了蚂蝗精,终与田螺姑娘幸福相守。而在 《刺猬歌》 中,廖麦与美蒂相互吸引,结为夫妻,却有唐童搅局,使廖麦躲于外地数年,最终在美蒂的帮助下回到了村子。与传说不同的是结局。这也体现了张炜的创新之处。结局并不完满。美蒂终于把持不住自己,在利益的诱惑下,归顺了唐童。而廖麦也因故乡情结,一心报仇。两人的互不理解使美蒂返归了美好的大森林,两人最终失散了。这种借鉴但为突出主旨的创新过人之处,使 《刺猬歌》 在原型塑造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 《刺猬歌》 中民间意象的追求
在具有民间意识的作品中,通常会从故乡入手,来写自己熟悉的风土人情,张炜也不例外。可在《刺猬歌》 中,融入了对童年意象的追求,使小说更加丰满圆润。
(一) 故乡
1.母亲
写到故乡,不禁要诉说一下母亲。母亲是爱的代表,是故乡思念的核心所在。 《刺猬歌》 中,最突出的母亲形象是珊婆。她奔波于大森林中,为各类动物接生。于是七个后生脱颖而出,印证了她对乌龟样老人说的话:“可我用不了多少年,也会儿孙满堂的。”珊婆的母爱在接生中得到了巩固,虽沉默,却依旧奉献自我。而珊婆对唐童的爱也是充满母性成分的。她为唐童调理身体,为其讲道理,陪她看电影,做他最坚实的后盾。虽这份爱也存在着不妥之处,但仍能体现出母性的回归。母亲的第二大体现便是美蒂。
她与廖麦的孩子小蓓蓓是其掌上明珠。小蓓蓓寄托着她向前发展的梦想,同时也是故事走向复杂的象征。廖麦在外逃亡时,美蒂独自一人生下孩子,拉扯孩子,却最终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生活而顺从了唐童,违背了自己单纯的内心。因此,她对孩子的爱既是真挚的,却又是矛盾不已的。
另外, 《刺猬歌》 中还存在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角色———廖麦外出逃亡时遇到的老婆婆,她将廖麦当做亲生孩子看待,给了他想要的生活,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这是朴实母亲的代表,也是失去孩子、思念孩子而不得的可怜母亲的心声。
2.家园
故乡与家园并不相同。故乡更多地寄托了淡淡的哀思与心情。而家园是一个地理位置,它由情感维系,失去家园便失去故乡,失却了根。
《刺猬歌》 中写到的家园别有意味。开始时,家园由森林和农家共同组成。在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中化为一体,达到共生。而在天童集团开始开发后,森林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模样,“紫烟大垒”也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于是,家园不再成为家园,恐惧之情油然而生:
“眼看这青蜮蜮硬邦邦的物件一天天垒起来了,看上去就像塌了半边的山包、像悬崖、像老天爷的地窖,像被关公爷的大力砍了一宿的怪物头颅,龇牙咧嘴,吓死活人。”
于是,家园被毁以其特殊寓意表征了工业文明对乡村的破坏,对人心的损坏,家园不再,再多的“紫烟大垒”又有何用呢?家园成为警醒人们的表征。
(二) 童年
《刺猬歌》 采用时间顺序,在对比中突出了主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写到美蒂的童年。美蒂的童年是穿着小蓑衣度过的。“那一身蓑衣毛儿在霞光里奓着,金光闪烁”。她那时候单纯、敢爱敢恨、不谙世故。小蓑衣是衣服,也是纯洁的象征之物。而长大后,美蒂脱掉小蓑衣,走向社会,开始由简单走向复杂。她最终未能经受住唐童的诱惑,背叛了廖麦,也背叛了自己。文章最后,她又穿起了小蓑衣,回归自然。这种前后呼应的方式,不禁让人想起了蒲松龄笔下婴宁的“笑”。婴宁的“笑”像美蒂的小蓑衣一样,象征着单纯与纯净,而当婴宁从田野被带入人间家庭中,便再也不笑了,失去了纯洁的表征,直到最后复又回归自然,“笑”便自然而然常伴左右了。
这样一种童年失去复又得到的表现,反映了作者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认知。自然中孕育的是单纯、清洁的生命,而工业文明虽在发展,却使人变得复杂与充满矛盾。因此,张炜构筑的乡土乌托邦也由童年这一意象得以体现。
张炜 《刺猬歌》 中的民间情怀在意象抒发、原型表达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是立足大地的歌者,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有民间生存的淳朴。在两者的结合中,实现了乡土乌托邦的构筑,实现了民间歌唱的自然与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