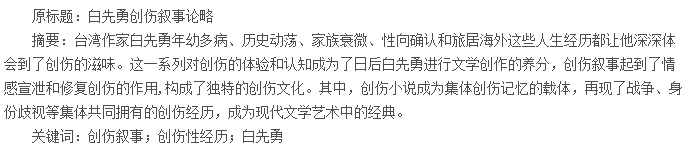
白先勇一生跌宕起伏,他出生名门却因历史动荡、家族衰微、年幼多病、同性恋身份和海外留学这些人生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为世所遗、历史沧桑、人生无常、被放逐和身份认同困难。这一系列对创伤的体验和认知成为日后白先勇进行文学创作的养分,成为他小说中创伤性叙事的根源。白先勇小说的创伤叙事是他在遭遇现实困厄和精神磨难后的真诚的心灵告白。也只有通过真诚的心灵告白,心灵的创伤才能得到医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
一、白先勇的创伤经历
(一)年幼多病:“被人摒弃,为世所遗”
白先勇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母亲马佩璋是官家大小姐。贵族的血统和优裕的生活本该注定着他人生的一帆风顺、无忧无虑。
可是,年纪轻轻的白先勇却患上了肺病。在那个谈痨色变的年代,白先勇被单独隔离在一幢小房子里,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养病,偷偷窥探外面的欢声笑语。白先勇自己回忆这段生活时,感伤地写道: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起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①繁华与孤寂的强烈反差,使得白先勇年幼的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感。虽说这时他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仍停留在混沌的阶段,但这段生病的创伤经历便使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了雏形。
(二)历史动荡:历史沧桑感
白先勇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爆发,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接着又是四年国共内战。他的童年便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度过的。白先勇随同母亲在广西老家,躲空袭、跑防空洞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湘桂大撤退和国共内战爆发后,白先勇举家迁移,辗转各地,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香港等地居住。白先勇回忆时说:我重回“人间”之后,就碰到一连串的动乱,随着家人的迁徙,从上海到广州到香港再到台湾。你知道,青少年每到一个新环境,总会产生适应的问题。而且当时我在语言上也不适应,一下子是上海话,一下子是广东话,一下子是台湾话,令我更感觉无所适从,到处都自觉outofplace。276动荡不安的时局和“逃亡”式的生活对白先勇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创伤,在被遗弃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历史沧桑感和不安定感。
在大陆的时候,白崇禧得势,白氏家族力量雄厚。
可是当撤退到台湾后,家族势力每况愈下,军事力量与政治地位不复存在。白先勇无疑也感觉到了家族的衰微:“我刚到台湾时,看看新居,肚里不禁纳罕:哎哟,怎么住进一个小茅屋子里去!”273-274白先勇亲眼目睹了家族的破败、人事的迅速变幻。这种创伤在他心中刻下深深的“人生变幻无常”的烙印:我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感到世界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人世之间,事与物,都有毁灭的一天。
(三)性向确认:青春鸟的放逐感。
青少年时期,白先勇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自身性取向的与众不同———确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民众对“民主”“自由”等字眼噤若寒蝉,同性恋被看做是有伤风化,同性恋者在社会上被排挤、被歧视、被驱逐、被压迫,背负上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骂名。作为一个刚刚成年的大学生,白先勇认同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便要承受巨大的无形的社会压力。
“我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还觉得是一种骄傲,有不随俗、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我想我跟很多人不同,有些人有同性恋的问题,因为社会压力,觉得难以启齿,抬不起头来。但同性恋对我来说,造成我很大的叛逆性,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虽然白先勇坦承自己以同性恋身份为骄傲,不认为是羞耻,但社会的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铺天盖地的压力促使着白先勇对同性恋群体被放逐的生存境遇和创伤体验进行思考。
二、白先勇小说的创伤叙事
(一)离家去国之伤
《台北人》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史”,⑤里面的人物都与国民政府撤退台湾这段忧患重重的历史有关。他们都是当年跟随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并在台湾定居下来的,其间与至亲至爱的分离、与故土的割裂、与本土文化的格格不入等等经历都使得他们饱受创伤。这就注定着这一代人,无论是上层贵族、军官、知识分子、商人,还是下层的舞女、士兵、仆人,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记忆,而这些创伤的记忆又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现实生活。
《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是这群饱受动荡离乱之伤的“台北人”的代表。作为曾经的将军夫人,曾经的南京名角,钱夫人本来有着大好的青春年华,技压群芳的歌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大将军的恩宠,可是在经历了迁徙台湾、钱将军离世的创伤之后,好景不再。她的旧相识赖夫人和窦夫人都在台北混得如鱼得水,唯独钱夫人像没了根的野草,独自栖居在冷清的南部。离开那片故土后,她的心境是孤苦的,不然怎会觉得“刚去红玫瑰做的头发风一吹就乱了”,“身上那件墨绿杭绸的旗袍颜色不对劲儿”,“台湾的衣料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柔熟”,“嗓子哑了”。面对着窦公馆里奢华设宴的排场,钱夫人脑海里浮现的却是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公馆帮桂枝香过三十岁生日酒的场面,挥之不去,历历在目。《岁除》里的赖鸣升经历国军撤退后依然沉湎在过去战场上的光辉事迹中。
他的境遇令人悲悯,从前在大陆时是国民党长官,撤退到台湾后不受重用,拿了退役金之后还被花莲的山地女人骗得精光,只能借酒浇愁。
(二)时间流逝之伤
《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台北人》的开篇之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尹雪艳总也不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⑦作为上海百乐门曾经红遍半边天的舞女,到了台湾之后依然大红大紫,“公馆门前的车马未曾断过”,追求她的男人都排着队来讨好她。尽管离开了曾经扎根的大上海,历尽沧桑往事,尹雪艳却毫发未损,不因世事变迁而变化,而是冷眼旁观着人世的变幻。
“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相互宰割”。尹雪艳就像个超脱世俗的精灵,见证着人世间所谓美人和英雄长存的神话一一破灭。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无情的岁月把从前上海百乐门的玉观音金兆丽变成了如今台北夜巴黎年过四十的金大班。看到任黛黛变成了风光的老板娘,她只能感慨自己多走了二十年的远路。在风月场打滚了二十多年,曾经心高气傲拒绝了千年大金龟潘金荣的追求,如今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小靠山。因为,她不再是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兆丽了,“四十岁的女人不能等。四十岁的女人没工夫谈恋爱。
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国葬》里的秦义方年轻时曾是李浩然将军最信任的副官,跟随李将军“从广州打到了山海关,几十年间,什么大风大险,都还不是他秦义方陪着他度过去的”,怎么说也是威风过的。往事终究是往事,几十年过去了,他变成白发苍苍、不中用的老侍从了,被将军撵出门,就连少爷见到他也像陌路人一样。
(三)畸恋放逐之伤
《孽子》里以阿青的视觉展现了同性恋者被放逐并追寻自我的故事。阿青与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猥行为后,经历了被学校放逐,被父亲放逐,被社会放逐的辛酸历程。学校勒令其退学,父亲拿着枪骂道“畜生!畜生!”把他逐出了家门,社会对他这种人更是不提供任何容身之处。为了生计,他只能沦为娼妓,躲藏在新公园的那个黑暗王国里。放逐对于阿青来说仿佛是无可逃脱的命运:“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乌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后尘,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
在这个黑暗王国里生存的都是被放逐的“青春鸟”:李青、小玉、吴敏、老鼠、阿凤和龙子……被放逐的创伤使他们有着“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也促使着他们一生都在追寻:寻父、寻梦、寻爱。
三、白先勇创伤性叙事的意义
(一)集体记忆的书写
白先勇小说的创伤性叙事书写了一代“流浪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1949年国民政府败走大陆,一代人离乡别井,寄身异地,或在台湾寻找容身之处,或漂洋过海到欧美国家避难,成为了无根的流放者。他们一边饱尝流离失所的伤痛,一边怀抱着重临故土、与家人团圆的希冀。当时大部分迁台作家尚未从流放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他们选择逃避现实,盲目接受政府宣传的“反攻复国”神话,所写作品都是大团圆结局式的,拒绝描写伤痛,与现实严重脱节。而白先勇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继承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主张还原现实,把历史和人性说清楚,让集体记忆得以记录并鲜活地保存下来。《台北人》和《纽约客》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通过对人物的遭遇和内心独白的描写,成功刻画出了“流浪的中国人”的众生相,书写了这段特殊时期的集体创伤记忆。这种创伤性叙事担负着保存历史真相、认识理解过去的任务。
(二)情感创伤的修复
白先勇小说对于集体创伤记忆的书写,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传承记忆,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个别的创伤体验,来达到宣泄情感和修复集体创伤的目的。创伤性叙事具有创伤重演和消解功能。“通过重复创伤体验,记忆逐渐消解创伤的痕迹,自我逐步走出笼罩心灵的荒漠”。
辑讹辊白先勇以写实的手法反复描述“人类心灵的痛楚”,②276将人类痛苦的创伤遭遇和失败的命运结局一再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这种见证———倾听的交流模式,赋予创伤体验以特定意义,帮助受创人群恢复与集体、世界的联系,从而促使他们实现心理重建,达到修复创伤的效果。
(三)创伤文化的审美创造
从审美角度来看,白先勇小说的创伤性叙事具有创伤美学的特征。作者结合个人的创伤性体验,对创伤进行深度的审美观照和理性反思,挖掘出“创伤”的幽暗的美。白先勇善于运用烘托手法表现创伤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疏离;利用意识流手法来表现创伤人物的自我分裂和创伤思维的混乱;运用时空并置、叙事省略手法来表现非线性的创伤时间。对创伤的细致、独到的描写,体现出白先勇浓厚的悲悯情怀以及超越创伤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3]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4]白先勇.孽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5]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