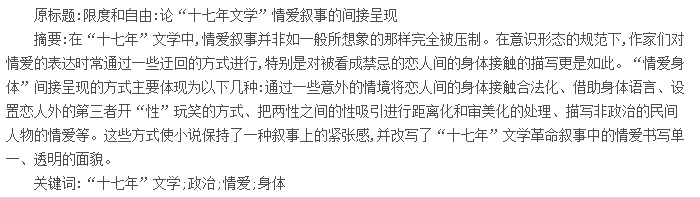
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 《昨日的世界》中曾写道:“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 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 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 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 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 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 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 ”[1]
这说明,越是禁欲的时代,欲望的积压以及由此导致的表达和发泄的冲动就越是凶猛,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对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一时期的这方面的状况都有反映。 而在当时,文学是如何反映情爱的真实状况的呢? 毫无疑问,无论在怎样的时代,生活不消失,人的情爱世界就不会消失, 只不过由于环境的限制它在文学中的呈现会变得艰难曲折。
在“十七年”文学的情爱叙事中,由于男女之间的情爱通常只能限于意识形态化的情感表达,个人化的情感以至恋人间的性爱表达在“十七年”文学中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禁忌, 但难以回避的是,情爱的自然发展过程不能不涉及性爱和身体,这就形成了“十七年”文学性爱描写的特殊状况。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世俗幸福的感性生活只要在叙述方面把握得当, 同样也构成了1950、1960年中国红色文学重要的叙事兴奋点。 革命神性与世俗幸福,在许多的革命传奇故事中相安无事,不过,这种相安无事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存在着许许多多叙述的‘关口’。 ”[2]
因此,正是由于不愿意放弃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观照, 作家们有时会采取一些曲折的手法、间接的方式来“合理”描写男女间的情欲包括身体接触, 在不逾越意识形态规范的前提下完成了作家的创作需求。 特别是在那些比较有民间立场和注重日常生活情趣的作品中,对“情爱身体”的描写也相对较真切自然。 “情爱身体”的间接呈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最为常见的是,作家常通过设置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 《山乡巨变》 中作者对盛淑君和陈大春的恋爱场景的描写就是如此。 小说中盛淑君是个对革命工作积极热情的农村姑娘,她直率奔放,“象一匹脱缰的野马,欢蹦乱跳,举止轻捷。 ”盛淑君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主动热烈的, 她对村里积极进步的男青年陈大春一往情深,可陈大春却是一个粗心迟钝的人,对盛淑君的深情熟视无睹, 盛淑君苦于久藏在心中的爱情一直没有机会表达, 也为两人的关系总也没有任何进展而焦急, 因此找一切机会和陈大春单独接触。 对于作者来说,一方面不能回避他们之间爱情发展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又囿于时代的写作禁忌,难以直接写这对恋人之间情爱的场景。 于是,周立波设计了这样一幕来完成他们恋情的“突变”:一次晚上约会,盛淑君踩到一条长长的东西,吓得往大春身上扑,后来才看清是一条树棍子。 这还只是一次铺垫,而后,作者又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写到了发生在两人间的关键性一幕:……不知不觉,走下了山岭,他们到了一个树木依样稠密的山坡里。
她只顾寻思,不提防踩在一块溜滑的青苔上,两脚一滑,身子往后边倒下,大春双手扶住她,她一转身,顺势扑在他怀里,月光映出她的苍白的脸上有些亮晶晶的泪点,他吓一跳,连忙问道:“怎么的你?好好的怎么又哭了? ”“我没有哭,我很欢喜。 ”
她含泪地笑着,样子显得越发逗人怜爱了,情感的交流,加上身体的陡然的接触,使得他们的关系起了一个重大的质的突变,男性的庄严和少女的矜持,通通让位给一种不由自主的火热的放纵,一种对于对方的无条件的倾倒了。
他用全身的气力紧紧搂住她,把她的腰子箍得她叫痛,箍得紧紧贴近自己的围身。他的宽阔的胸口感到她的柔软的胸脯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在剧烈地蹦跳。她用手臂缠住他颈根,把自己发烧的脸更加挨近他的脸。一会儿,她仰起脸来,用手轻轻抚弄他的有些粗硬的短发,含笑地微带善于撒娇的少女的命令的口气,说道:“看定我,老老实实告诉我,不许说哄人的话,你,”稍稍顿一下,她勇敢地问:“欢喜我吗? ”他回答了,但没有声音,也没有言语。
在这样的时候,言语成了极无光彩,最少生趣,没有力量的多余的长物。一种销魂夺魄的、浓浓密密的、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的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写成为:“做一个吕字。 ”[3]
与很多同时期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情欲的压抑不同,《山乡巨变》 所描写的情爱充满着与小说整体风格一致的真实自然感, 陈大春虽然有和梁生宝相似的迂腐和不解风情的性格, 也有和梁生宝一样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牺牲精神,但由于周立波并没有如柳青那样要把陈大春塑造成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宏愿,因此,盛淑君也比改霞幸运得多。 最终,在“盛淑君一有机会,就要缠住他, 总是想用女性的半吐半露的温柔细腻的织成的罗网把他稳稳地擒住”的攻势之下,陈大春还是跟随自我的感性本能欣然接受了爱情的降临, 他原本准备28岁之后再谈恋爱的革命理性泡汤了。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出,此前两人在集体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个体生命的愉悦在此被敞开,陈大春甚至后悔这种幸福来得太迟。 在这段描写中,“吓”和“滑”成为人物非自觉的身体接触的合理借口,它一方面尽量避开了意识形态的禁区,另一方面也自然地催化了两人的感情发展。
爱情是因为男女之间“性”的吸引,而不可能完全是因为男女双方革命信仰的一致, 即使是革命信仰完全一致的男女, 他们的情爱仍然要回到个体的身体上来,对此,作家可以巧妙地表现,这在一些非主流的民间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如《苦菜花》中,德强和杏莉是一对两小无猜的朋友,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两人之间逐渐萌生了爱慕之情。 一次为了躲避敌人,两人藏进一个窄小的山洞, 这对情窦初开的男女因为特殊的情况才发生的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无疑促发了两人之间的爱情:石洞又黑又小。
德强叫杏莉先进去,杏莉不敢;德强爬进去后,她才紧贴着他的肩臂偎靠着趴下来。德强感到她的胸脯在剧烈地跳动,她喘出的大口热气,喷到他脸上。两人听着敌人叽哩呱啦地从头上走过,枪声渐渐远了,才舒了口气。德强一转脸,嘴唇正触在杏莉的眉毛上。
杏莉这才发觉,她的脸几乎是贴在德强的脸腮上,而身子是全倒伏在他怀里了。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杏莉一抬头,咚一声碰在石头上。德强忙把她的头撩住。
两人都笑了。[4]而即使在如《艳阳天》这样阶级斗争激烈、政治立场鲜明的作品中, 也有类似以这种看似 “无意”的方式表达的男女情爱的场景:“韩道满一躲闪,把马翠清闹了个趔趄。韩道满连忙伸手拉马翠清;用的劲头猛了一点儿,这一拉,顺着劲儿把马翠清拉到自己的怀里了。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少女的温暖,电一般地传到他的身上。又像是怕她跑掉,身不由主地把姑娘搂住了。 ”[5]
因此,尽管思想的禁锢使“十七年”小说在表达情爱时非常节制, 但在这种整体上比较有节制的情爱描写中,偶尔闪现的身体情欲的光芒,反而会显得更加耀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情欲描写的控制并不完全就是表达的阻碍, 适当的规范反而能够增加小说的艺术魅力, 这也正如情爱本身需要控制一样。 《山乡巨变》中的下乡干部邓秀梅就和盛淑君推心置腹地谈过 “情爱” 和理性的关系:“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 不过,要是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里,好象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 ”邓秀梅的这一经验之谈同样也正是周立波对待文学中的情欲描写的态度,只要“控制得宜”,作家的表达反而比那种没有约束的表达更能够具有 “文学性”:含蓄婉转、意味深长。 《山乡巨变》中的一段描写就特别富有这样的意味: 邓秀梅与盛淑君两人在深夜长谈之后才休息,“两个年轻的女子,体质都好,身上又盖了两铺被子,睡了一阵,都热醒了,盛淑君把她两条壮实的、微黑的手臂搁在被窝外,一直到天光。 ”看似不经意的生活化的描写,却在一句“燥热的身体”中透射出青春的激情和欲望。
其次, 借助身体语言表达情爱。 在特殊环境中,爱情不能用语言表达,眼神、语调、表情、动作等身体语言就具有了重要的功能。 在《林海雪原》中,白茹在向少剑波暗示、传递爱情中身体语言具有重要作用, 如小说中写剑波看到白茹完成任务回来,“满心喜悦,但他硬装着不耐烦的样子。 ”少剑波听完白茹的汇报夸奖她,“白茹含羞带笑,斜视了剑波一眼,低下了头。 ”当白茹确认了剑波对她的感情后, 无论少剑波如何粗直地管教和训斥她,“在白茹听来,内中都渗透了‘你是我的,我怎么说你都成’这样一种含义”。 正是因为直接表达的不可能, 小说更增加了两性之间通过丰富含蓄的身体语言来相互吸引、试探、猜测、想象的过程。
小说中, 白茹作为小分队的卫生员对少剑波的身体健康和卫生习惯的关心和干预, 少剑波对白茹工作的指导甚至“批评”和“不满”(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特别的关注)都暗藏着爱情,是战争年代爱情的特殊表达方式。 革命恋人之间的感情如细小的分子,散布在革命事业之中,正是因为难以把革命和个人的情爱完全分离开来, 这其中才会充满一种张力,这也是《林海雪原》在惊险传奇的战斗之外还能给人留下关于爱情的深刻记忆的原因。
在《林海雪原》中,当这种感情的婉转交流积蓄到一定时候, 更加大胆的带有色欲的对身体的“凝视”[6]就出现了: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的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剑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
她自己的药包搁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帽已离开了她那散乱的头发,只有两条长长兼作小围巾的帽扇挂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
少剑波的心忽地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绪顿时被这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二十三岁的少剑波还是第一次这样细致地思索着一个女孩子,而且此刻他对她的思索是什么力量也打不断似的。[7]
如此精细且带有窥视色彩的身体描写在 “十七年”小说中并不多见。 两性之爱是以身体之爱作为前提的,“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 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徐志摩语)少剑 波对白茹的爱情已经势不可挡, 他选择通过写诗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感情,在小说的“雪乡抒怀”一节, 一向严肃庄重的少剑波在日记中写下了赞美白茹身体之美的诗句[8]:
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路润月季花。
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
双目神动似能语,垂髫散涌瀑布发。
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
……
尽管诗中对白茹身体之美的赞美随即转换为对白茹作为“女英雄”的赞美,但后者却是前者的一种延伸,政治话语中夹杂着私人感情,所以当白茹偷看到这首诗后,心中暗喜,由此而确认了少剑波对他的心意。
再次,“十七年” 小说常通过第三者开玩笑的方式来间接表达英雄人物被掩饰的情热。 这缘于作家既希望能对不被意识形态认可的情爱有所表达,又不希望这种表达“破坏”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于是,就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展露人物的心曲。 在《山乡巨变》中,作家在描写下派女干部邓秀梅时多要突出她性格的沉稳和干练,在这种情况下, 作者在处理她和新婚离别的丈夫之间的感情时就必须讲究技巧, 同时也要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于是在小说中,作者就设计了一个围绕夫妻信件展开的情节。 新婚夫妻之间的通信应该是表达私人情感的, 但在一个私人空间被公共化的时代,并无私人情感可言。 丈夫给邓秀梅的信,写了密密麻麻的5张纸,大部分谈的是工作,只是在信的结尾处透露出一些个人的感情:我虽说忙,每到清早和黄昏,还是想你。
有一回,我在山上,搞下一枝带露的茶子花,不知为什么,闻着那洁白的花的温暖的香气,我好像是闻到了你的发上的香气一样。亲爱的秀梅,来一封信吧,仅仅划几个字来,也是好的。[9]
可想而知, 邓秀梅写给丈夫的信中所写的同样也只能是理性的革命工作, 为了对这种被遮蔽的情感加以表达,小说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正当她写信时,被爱开玩笑的盛清明看见,盛清明便模拟邓秀梅的口气开起了“写信”的玩笑,盛清明的这封热烈的情书是这样 “写” 的:“我的最亲爱的家杰:你近来好吗? 想不想我? 我这里朝思暮想,连做梦也都看见你呀……”“我想得要死, 想得要吃水莽藤, 寻短路了……”“你快快来吧, 我的亲人……” 尽管这种直露的表白并不符合邓秀梅的性格,但作者设置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无疑巧妙地说明新婚夫妻之间的思念之情是人之常情。
通过第三者开玩笑来间接表达情爱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情境下, 但基本套路是相同的:《创业史》 中常跟在梁生宝身边爱说爱笑的有万经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打探梁生宝和改霞关系的进展;《苦菜花》、《山乡巨变》等小说中,新婚夫妻在结婚仪式上周围的群众也常开一些性玩笑。 这种表达方式制造了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 在当时普遍偏于紧张的政治化的描写中它起到了松弛和润滑的作用。
此外,是通过距离化、审美化的方式来表现情爱的身体。 如果说情爱中恋人的身体接触是人性的本能,那么,不逾越时代规范却又把这种本能的身体情欲升华为一种纯净的人性之美的也是对情爱身体的间接表现。 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就是“十七年”文学将身体禁忌的负面意义转换成正面意义的最完美的案例。
在《百合花》中,小说对小通讯员的性格描绘始终围绕“羞涩”展开,“羞涩”也制造了身体之间的距离。 小说写女文工团员“我”被小通讯员护送到前沿包扎所,因为是年轻的异性,一路上小通讯员对“我”始终若即若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 ”身体之间的距离恰恰是因为两性之间的吸引, 小说制造了颇有紧张感的空间距离,小通讯员纯朴无邪的性情跃然纸上。
后来,小通讯员为包扎所向老百姓借被子,和新媳妇之间发生误会,同样因为“羞涩”,慌乱中衣服被新媳妇家的门钩挂破。 新媳妇随即给他补洞他却逃掉了。 而在小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一针一针地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异性之间“身体”的吸引很快被升华为一种超越身体的人性之美。
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如“十七年”的许多小说那样把这个为革命而牺牲的普通战士的 “躯体崇高化”,而是通过新媳妇的举动给这个普通战士的身体以尊严,这显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表达,这种表达在当时的创作风气之下体现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百合花》淡化了政治主题,而将生命最简单的存在———身体的存在凸显出来, 并由此来呈现人性的单纯、善良和美好,身体的审美化观照是在超越世俗情欲的距离感中产生的, 这篇作品因此也被人称做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最后,“十七年”文学对情欲的真实、自然的描写, 往往在一些非政治性的民间人物身上有更多的体现, 性爱所体现的生命的激情和人性的美好由此而被呈现出来。 在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中,王柬芝家的长工王长锁和王柬芝的老婆 (杏莉母亲)产生了爱情,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爱情是不道德的;相反,他们认为这种感情是真挚、崇高的,“为维护在他们的心灵上认为是最高贵的野性的爱情关系,使它不受损害,不受沾污,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让外人知道, 不能使他们的纯挚私情受到羞辱。 ”后来,他们的偷情被王柬芝发现,王长锁和杏莉母亲非常害怕,“为了保存共同的爱情不惜牺牲了一切。 这种爱情关系已经和他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为了保存他们的爱情,王长锁后来上了王柬芝的圈套,替王柬芝送了情报。 对于这样的民间人物来说, 爱情关系超过了其他的一切,然而,在小说中,缺乏政治意识的民间人物往往容易被敌人利用,这样,原本疏离于主流话语的情爱描写又重新回到了主流的轨道上来。
同样,在《苦菜花》中,另一对穷苦人花子和老起的爱情也是如此。 共产党员、妇救会长花子从小被卖到王唯一亲戚家当媳妇,丈夫是个傻子,经常被打骂, 八路军来后, 她离开了婆家回到了王官庄, 并与当年在婆家救过她的长工老起产生了爱情,花子是有丈夫的人,他们的恋爱自然不会为道德观念所容,于是他们只能暗地里来往:
然而,那淳朴真挚的爱情,随着年岁的成长,却如火触焦柴那样,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它要冲破束缚着它的铁环,爆发出美丽艳红的火花!
一天夜晚,在偏僻的荒山沟里,两个人挨着坐在岩石上。 繁密的小星儿,闪着调皮的眼睛。秋夜的微风,通过凉露,吹着草木叶,发出催眠曲似的簌簌声,一阵阵向他们身上扑来。花子不由地打个寒噤。老起忙脱下夹大袄,披在她只穿着一件单褂儿的身上。
花子看着他只穿着一件背心的健壮胸脯,没有说话。她那双温柔盈情的眼睛,使他明白了她的心意。老起心跳着挨紧她,她把夹袄披在两个人身上。他感到她那柔软丰腴的身子热得像热炕头……这个强壮的穷汉子,第一次得到女人的抚爱。他才发现人类间还存在着幸福和温暖。一朵苦难野性的花,怒放了![10]
冯德英在描写王长锁和杏莉母亲、 花子和老起的情爱时都使用了“野性”一词,可以看出,作者对民间自由的性爱充满了表达的热情,但是,作者毕竟肩负着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的双重压力,因而会在叙述上作一些弥补, 以使情爱叙事能向政治叙事尽量靠近。 在《苦菜花》中,花子的婆家是地主家庭,她的婚姻本来就是封建包办婚姻,老起是有正义感的善良的长工, 于是在党组织的主持之下,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 特别是在花子和老起结婚后,作者又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情节作为“弥补”:日本鬼子把村里的男人都抓起来, 让女人用亲吻的方式认丈夫,剩下的全部杀掉。 花子为了救革命干部姜永泉,毅然把姜永泉领了回去,而把自己的丈夫留在了人群之中。 由此,崇高的革命行为重塑了这些民间人物的精神境界, 这些人物身上在情爱叙事中所闪烁的人性光芒此时已被政治叙事所赞颂的革命品质以及牺牲精神所取代。
中国民间文化对理想情爱的理解不外乎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对情爱的品质要求则不外乎是忠贞、执着等,在这些情爱叙事中都融合了民间的情爱伦理标准,这是对意识形态化的情爱的补充。 如在《红旗谱》中,春兰这一人物就是完全符合民间情爱理想的, 她的瓜园就是对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想象, 而她对爱情的态度也正是传统伦理文化所崇尚的:运涛被捕后,判了无期徒刑,周围的人让春兰嫁给大贵, 春兰哭喊着说:“不,俺不,俺就是不! 不管是谁,就是他长得瓷人儿似的,俺也不。 就是他家里使着金筷子银碗,俺也不! 我就是等着运涛,我等定了! ”春兰对运涛的痴心痴情是符合民间伦理对女性的要求的,但是,因为有了运涛作为革命者的身份的支撑, 它才具有了一种时代的意义, 才使民间性质的情爱在道德标准和时代标准之间获得了统一。
在“十七年”文学中,由外在的政治环境而形成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情爱叙事在认识上的一种主观感觉, 即情爱叙事是一种单纯被压抑的文学书写,但从上述分析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 如果完全把爱情看做是个体性的, 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革命与爱情的二元对立思维, 势必把革命叙事中的爱情处理成一种处处“委曲求全”的受压抑的对象,如果就此认为“十七年” 文学的情爱叙事在绝大多数时候已经远远偏离了情爱的个体生命本质, 成为政治叙事的一个装饰品,那么,是否存在完全纯粹的爱情? 以革命价值为爱情价值的爱情是否就不是爱情? 必须承认的是,爱情是个人的,但既然不存在完全纯粹的个人,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纯粹个人的爱情,爱情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同时,爱情并非完全被动地受时代制约,它会寻求与时代的合作以保护自身。 也就是说,从革命的立场来看,它是合法的,但这种合法并没有伤害爱情, 革命与爱情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因此, 考察作家面对政治化的文学主题时对个人情爱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为了展现“十七年”文学中人性在政治的压力下可怜的生存空间,而是希望以此探讨政治与文学、 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 尽管个人情爱并不存在与政治权力的平等的对话关系, 但个人情爱在压抑中显现出一种合作和逾越的可能。 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之下,情爱叙事的表达或循规蹈矩,或巧妙周旋,后者通过一些细节所表达的隐含之意, 及其在叙事中与主流话语所构成的张力,是不容忽视的。 这些说明,符合人性的情爱表达不是为了挑战秩序,而是在秩序中小心翼翼作些轻微探险,也因为如此,“十七年”小说仍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 同时,也必须看到,许多微小的细节、婉转的表达穿插在“十七年”小说中,它们生发出一种力量,在政治规范的限度内, 革命话语中的爱情叙事尽可以施展其本能,婉转曲折、迂回间接地表情达意,这样使革命文学更具有叙事上的张力和含蓄之美,也正是它们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的单一、透明的面貌。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小说中成为了一个缓解压力、释放人性的窗口。 不过,总地来说,作家只能小心翼翼、颇费心机地表达,即使是上述间接的方式也只能偶一为之,并不能改变“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基本格局。 并且,再“巧妙”也不会不暗藏危险,“革命读者和革命评论家发现了这种 ‘乔装打扮’的修饰夹带着非革命的‘私货’,群起而攻之”[11]。 最安全的办法仍然是无奈地延迟爱情的成熟时刻的到来,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个人欲望都能轻易地被革命叙事所轻易吸纳和消化, 这就形成了有论者所言的革命叙事中的情爱的无限的延宕的现象:“众多小说延宕爱情的结局, 暗示了那些‘低级’的元素———本能的、力比多的、身体的和女性的———不能完全或者轻易地被转变和提升到‘崇高’的、神圣的层面。 所以,那些不能被升化的就一定要被延宕或忘记, 因为它会对革命话语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12]情爱的“有始无终”,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症候, 表达了文学在政治压力下的狼狈处境。
参考文献:
[1] [奥]斯蒂芬·茨威格着,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4页。
[2]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9页。
[3]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29-230页。
[4]冯德英:《苦菜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83页。
[5]浩然:《艳阳天》(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07-208页。
[6]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7]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28页。
[8]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35页。
[9]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