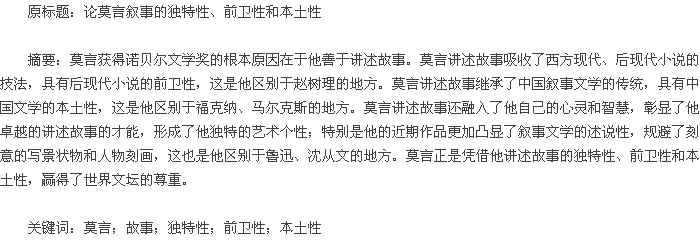
一、莫言在世界文学坐标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具有独特性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坊间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过不同版本的非议,诸如 “中国 GDP 影响说”、 “不同政见说”、 “马悦然关系说”等。中国的 GDP 增长影响了诺贝尔奖向中国作家倾斜———试问中国当代还有很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不授予其他作家呢?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因为莫言对时政持批判态度,那么,还有不少对时政颇有微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不授予其他作家呢?如果说莫言获奖是因为马悦然关系的缘故,那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国外的评奖,特别是诺贝尔之类的大奖仅仅靠请评委、拉关系、走后门是难以获胜的。当然,莫言获奖不排除有中国GDP 增长、莫言对时政持批判态度、马悦然关系等因素,但这些因素不是主要的因素。要探究莫言获奖的真正原因,还是应该从莫言作品自身的特点入手。
笔者认为,莫言获奖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他善于讲述故事。首先,莫言声明自己 “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感言时,就是以 “讲故事的人”为题。莫言 2 次说到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4 次说到自己是如何讲述故事,还讲述了自己一系列人生的和创作的故事。
其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颁奖词中说: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不通过这些故事,你很难进入一个人的声音被驴和猪的吵闹声淹没了的国度,在那里,爱和恶的呈现已经达到超自然的程度。”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着力描写的对象,是他的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他自己的精神家园。瓦斯特伯格说它“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这也正好说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所看中的是莫言讲述故事的艺术成就。
再次,就文本的品质而言,善于讲述故事是莫言作品区别于中外优秀小说的主要特色。莫言说过: “我觉得写这些小说目的就是为了讲故事给别人听。”①就是这样,莫言把讲述故事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之一。
莫言说: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非常明显,莫言受到过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巨大影响:福克纳虚构了一个杰弗逊镇,马尔克斯虚构了一个马孔多镇,莫言也营造了一个 “高密东北乡”。而且,马尔克斯和莫言都承续着福克纳心理独白的叙事传统,都将民间故事、民间话语融入了文本的叙述之中。在莫言的小说中还能找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叙述技法的影子,譬如莫言小说 《蛙》中对青蛙叫声的描写几乎就是对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中蚂蚁叫声的移植;万心喝醉了酒之后在狂风暴雨中奔跑,四周田野里蛙的叫声,使万心异常惊恐,她仿佛感觉到蛙在撕啃着她的肌肉,这几乎就是对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中长猪尾巴男孩被蚂蚁啃食的复制。但是,莫言讲述故事的神韵不同于福克纳的风格,也不同于马尔克斯的风格。福克纳深受美国南部地区风土人情的影响,在展示南部地区黑人和白人的矛盾时显露出的是一种美国南部地区特有的“边疆幽默”。马尔克斯则是对拉丁美洲历史、现状、生存环境和顽强生命力的展示,体现的是一种狭隘的、倔强的、孤独的、不乏自信的拉丁美洲精神。莫言尽管借鉴了福克纳、马尔克斯,以及此前的伍尔夫、马克·吐温的叙述技巧,但他讲述的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故事,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山东人的生活情趣和叙事风格。
在突出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上,莫言无疑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②,而且莫言本人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 “回归五四”的那一派;但是,莫言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鲁迅、郁达夫,不同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不同于全国解放之后的周立波、杨沫、欧阳山、浩然。鲁迅要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揭示民众的痛苦,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常常是通过生活的横截面表现的。茅盾展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图景,大多数作品是通过社会经济关系的纠葛揭示的。巴金描写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渴望与追求,主要的是通过青年与社会各种势力的矛盾和冲突书写的,而且书写的体式是用抒情的笔调。沈从文描写湘西生活则是用一个个的生活画面和一个个的生动细节来呈现的。赵树理讲述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故事,他是用中国山西特有的方言土语陈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小说家,如周立波、杨沫、欧阳山、浩然等,都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表现中国工厂、农村和知识分子生活圈的阶级斗争。莫言既继承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但他又没有拘泥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他和他同时代的小说家们通过借鉴日益发展起来的叙事理论与实践成果对中国现代叙事艺术实现了富于创造性的超越。
即或同样是隶属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回归五四”的中国作家,莫言的叙事也不同于陈忠实、李锐、张炜等。陈忠实、李锐的叙事偏重于对历史事件的图解,张炜的叙事偏重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刻画,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学院派习气。然而,莫言的文本则注重于讲述故事,他讲述他个人的故事,讲述他们家族的故事,讲述他周围人的故事。如果说莫言早期的 《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 《红蝗》还有一些现代小说注重于写景状物、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那么,他后来的 《檀香刑》、 《生死疲劳》、 《蛙》就更能体现出叙事文学的述说性了。
莫言自己说: “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
在小说这种原来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 《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③莫言就是这样 “撤退”和回归到了民间文学讲述故事的原点。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他显露出了叙事的艺术才能,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构筑了他不同于同时代小说家的精神高峰。这也诚如瓦斯特伯格所说: “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二、莫言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方略和技巧,具有前卫性
毫无疑问,莫言讲述故事吸收了 20 世纪的叙事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在叙事的方式上,莫言除了运用传统的插叙、倒叙等手法外,还运用了预叙事、元叙事等叙述手段。如:
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④这里的 “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就是对将要插入的我的爷爷余占鳌和我的奶奶戴凤莲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情节的预叙述。文本也作了适当的暗示,这种味道 “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红高粱》讲述的是高密县 1939 年农历八月的一场战争,那时我的父亲才 “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我爷爷奔向了战场。但是,文本的叙事却说他奔向了 “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墓碑”,而且我还牵着山羊在他的坟头放牧、撒尿、唱歌,这样就预先叙述了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小说 《蛙》中的 “我”反复强调, “我”是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 “我”最后创作了剧本《蛙》;而剧本 《蛙》只是小说 《蛙》中的一部分,小说 《蛙》是 “我”向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介绍我创作剧本 《蛙》的过程的叙述———这本身就是关于叙述的叙述。在小说 《蛙》中,元叙事的运用还有很多,如:
因为我一直准备以姑姑为素材写一部小说———现在自然是改写话剧了———这王小倜自然是重要人物。为这本书我已经准备了20年。我利用各种关系,采访了许多当事人。
这就是关于姑姑过去经历的叙事的叙事。 “预叙事”和 “元叙事” 在莫言小说中比比皆是,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叙事的技法上,莫言穿插了大量的联想和梦幻。如 《红高粱》写墨水河战斗,只有第 1 节写余占鳌带领部队奔赴胶平公路前线,第 4 节写余占鳌和部队驻守在胶平公路附近,第 6 节写父亲回家送信要奶奶为部队送饭,第 7 节写奶奶送饭到前线被敌人的机枪击中,第 9 节写余占鳌的部队击毙日军中岗尼高少将;而在第 2—5 节,和第 8 节中则采取回忆、联想的方式叙述了奶奶的家世、日本人修筑高平公路、罗汉大爷被剥皮、奶奶嫁到单家、奶奶告诉我父亲余占鳌是他的亲爹的情节。特别是在第 8 节中,还书写了奶奶在临死之前的各种奇异幻觉。小说 《蛙》中,万心喝了五粮液假酒之后在雨中奔跑,仿佛四周田野里的蛙声都是孩子的叫声,那些孩子仿佛就在撕啃她的身体,这里所描写的就是万心的幻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莫言借鉴意识流小说的叙事技巧,运用得非常圆通和自然,一点也不牵强和生硬。我奶奶的联想是我奶奶在弥留之际的联想,万心的幻觉是在万心喝醉了酒之后的幻觉,这样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
在叙事视角上,莫言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或几个独特的、新奇的角度,如 《红高梁》选择主人公孙子的视角,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其叙事视角大胆而反叛。 《蛙》选择主人公的侄子、剧作家为叙事的角度,讲述姑姑坎坷而富有个性的人生经历。作家本来是想将姑姑的一生写成剧本,而最后却写成了作为小说文本的 《蛙》,其叙事视角新颖而离奇。 《檀香刑》选择眉娘、赵甲、小甲、钱丁、孙丙等作为叙事的角度,展开多角度的叙事,其叙事视角变化多端而光怪陆离。叙事角度的诡谲别致,带来了莫言小说文体活泼新鲜的气息。除了在叙事的方式、技法和视角上向西方文学学习之外,莫言在创作中还引进了 “陌生化”的叙事方略,如:
那股小旋风,在母亲坟前盘旋一会儿,忽然转了方向,转向王仁美野草青翠的坟头。此时,黄鹂鸟在桃树枝头一声长叫,声音凄厉,犹如撕肝裂胆。 (《蛙》)一道道的闪电,刺目的蓝白的光,然后是震耳的雷声与倾盆大雨。四面八方都是响亮的水声,挟带着浓重土腥和腐烂水果气味的湿风从窗棂灌进洞房。红烛将残,抖抖颤颤,终于熄灭。我感到恐惧。 (《蛙》)汽车飞快地驶近,增大,车头前那两只马蹄大的眼睛射出一道道白光,轰轰的马达声像急雨前的风响,带着一种陌生的、压迫人心的激动。父亲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汽车,父亲猜想着这种怪物是吃草还是吃料,是喝水还是喝血,它们比我家那两头年轻力壮的细腰骡子跑得还要快。 (《红高粱》)文本对野外旋风和黄鹂鸟的描写,仿佛是叙述者第一次看到的事物,能够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
莫言经常用描写人或动物的词语 “垂头丧气”、“追上”来叙述旗帜和子弹,用述说动物轻微动作的 “舔”和 “吹”来描写熊和狼的啃咬和撕啮。这种语词的转换使用在文学理论领域叫作 “陌生化”现象,在语言学领域则叫作 “变异”现象。这也就难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对莫言的语言有如下的评价: “他的文字看似突兀,但却能让读者回味无穷、流连忘返,究其根由那便是莫言先生善于语言的调配、词语的组合,这种语言天赋与文字应用能力是一般作家不可企及的。”⑤在文学作品中,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⑥,即 “陌生化”的手法。莫言小说中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还有很多。譬如 《蛙》中有叙述小狮子分娩一节,其实小狮子并没有生孩子,只不过是让小狮子装着生孩子;而真正生孩子的是陈眉,可是,文本只叙述了小狮子 “生孩子”闹腾的过程,并没有叙述陈眉分娩的过程。如此有意识地模糊 “分娩”主体的界限,将本来熟悉的分娩主体变得陌生而含混,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和时间。
莫言对西方叙事成果的吸收与运用,已经为学术界所体察。莫言吸收 20 世纪叙事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创造性地构建了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在这一点上,莫言和赵树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树理的小说也讲故事,也运用了山西特有的方言、土语和民间故事,也很具有中国山西的本土特征,但是,由于时代、地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赵树理的小说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世界小说之间存在着一层明显的隔膜———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不仅在价值观上和西方叙事艺术尺度迥异,而且在叙事技术上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叙事文学。赵树理的小说仅仅用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策略讲述故事,远离了不断发展的现代叙事范式,不免带有一种低俗的土腥味。而莫言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位善于学习的作家。他向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学习,从现代、后现代小说中汲取叙事技法的营养,学习世界叙事艺术的前卫技巧,使自己的叙事作品保持了世界叙事艺术的前卫性。什克洛夫斯基说过: “谈到文学传统,我不认为它是一位作家抄袭另一位作家。我认为作家的传统,是他对文学规范的某种共同方式的依赖,这一方式如同发明者的传统一样,是由他那个时代技术条件的总和构成的。”不过,莫言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成果,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照搬,而是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美学理念,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这体现出莫言 “化”的功夫,也使莫言和其他先锋派作家区别开来。
三、莫言讲述的是中国 “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具有本土性
在吸收融化西方叙事技法的同时,莫言还十分机智地融入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本土经验,因而,莫言所讲述的故事,已经不是福克纳的美国故事、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故事、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故事、笛福的英国故事、大江健三郎的日本故事,而是一系列的中国故事、山东故事、高密东北乡故事。
在获奖感言中,莫言说: “在 《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 ‘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秋水》所营造的 “高密东北乡”本身就是一个神秘世界:
据说,爷爷年轻时,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成了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那时候,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方圆数十里,一片大涝洼,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棕兔子红狐狸,斑鸭子白鹭鸶,还有诸多不知名的动物充斥洼地,寻常难有人来。我爷爷带着那个姑娘来了。⑦“爷爷”和 “奶奶”在这里———“高密东北乡”落地生根,住下来了。不久, “我奶奶”怀上了 “我父亲”,在分娩的时候高密东北乡涨大水, “我奶奶”难产,从水上漂来的 “女护士”为 “我奶奶”接生,产下了 “我父亲”。从水上漂来的还有一个“黑衣男人”和一个 “白衣盲女”。这个故事真是太具有浪漫情结了———一个杂草丛生、无人居住的地方,来了一对为了爱情而逃离出来的年轻人,这能说不浪漫吗?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 “高密东北乡”,莫言讲了一系列的故事,讲了 30 多年的故事,而且还将继续讲述下去。
莫言所讲述的 “高密东北乡”的故事,首先是中国的故事。莫言的小说中, 《秋水》、 《檀香刑》讲述的是清朝末年的事情, 《红高粱》、 《丰乳肥臂》讲述的是抗日战争中的事情, 《透明的红萝卜》讲述的是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情,《红蝗》、 《蛙》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他的小说书写了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他叙述清朝末年的抗德运动,叙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抗日战争,叙述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叙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作,叙述中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莫言讲述中国故事,充分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叙述传统。中国是一个长于讲述故事的国度,早在宋代随着中小城镇的建立、市民社会的兴起,城镇的说书行业就成为擅长说书和讲述故事的人们谋生的手段,其说书的脚本,如 “三言”、“二拍”,就成为中国读者阅读的文献和叙事文学的文本。由说书脚本而衍生出来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等,无论学术界对它们的褒贬如何,它们讲述故事、穿插情节的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毛宗岗、李贽、金圣叹、脂胭斋对它们叙事技术的归纳与总结,亦堪称世界叙事理论的瑰宝。莫言的作品浸润着中国叙事文学的血脉,他有意识地向中国说书传统集结,凸显了叙事文学的述说性,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艺术风格。在莫言的小说,特别是后期小说中,几乎很难找到刻意的写景状物和人物描写———这方面也正是他区别于鲁迅、茅盾、沈从文,以及后来他的同时代小说家的所在。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时,莫言还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诸学派对宇宙、人生、生死的看法,张扬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浓郁的挥之不去的中国风情。
莫言所讲述的故事是中国山东的故事。山东是一个兼具儒家文化、巫术文化和匪徒习性的省份。儒家文化的鼻祖孔仲尼及其主要继承人孟轲都出生和生活在齐鲁大地。儒家学说的修身、养气、入世、进取的精神就贯穿在莫言的故事之中。莫言小说中最能体现儒家学说精神的人物要算 《蛙》中的“我的姑姑”———万心。万心美丽聪颖,父亲是革命烈士、民族英雄,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她进入卫生学校,学习过护士专业,在那个革命的年代理应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可是,她的未婚夫王小倜逃往台湾,她成了叛徒的恋人;她与县委书记有过接触,又被揭发成走资派的姘头。在受命运之神捉弄的时候,她忍辱负重,顽强地推进中国社会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着鲜明的儒家入世进取的思想观念。狐鬼妖怪的传说也浸淫着齐鲁大地的每一个血管。莫言说: “我老家那个地方,盛产鬼怪故事,上了年纪的人,脑子里都装满了这些东西。”⑧鬼怪的传说催生出了山东籍优秀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莫言十分崇敬蒲松龄,他的小说也不乏鬼神的描写,如 《檀香刑》中已经逝去的母亲的叫声即是典型的例子。山东还是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水泊的地方,在 《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身上就有李逵的影子。莫言所讲述的故事充分体现着中国山东人讲述故事的姿态、神韵和气派。
莫言所讲述的故事实质上是他自己的故事。莫言对西方前卫叙事理论的学习,对中国传统叙事技巧的吸收,对山东民间叙事作派的传承,都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融入了自己个人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情趣的再创造。莫言说: “我在小说 《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的影子。”莫言的小说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如 《蛙》中把青蛙用纸包着塞到姑姑手里将姑姑吓得昏死的男孩, 《透明的红萝卜》中在菊子“胖胖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的黑孩, 《红高粱》中光屁股在父亲墓碑上 “撒上一泡尿”的男孩等。莫言的小说还讲述他们家族的故事,讲述他周围人的故事。不过,在这个人物体系中,那个黑色男孩子是一个中心人物。莫言坦陈: “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莫言以这一个 “黑色男孩子”为中心,或者更直接地说,以自我为中心,充满激情和智慧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讲述了他们家族的故事,讲述了他周围人的故事。丹尼尔·贝尔说: “企业家和艺术家双方有着共同的冲动力,这就是那种要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骚动激情。”莫言用自己的寻觅、激情、骚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故事向世界文坛贡献了一个美丽而充满神秘感的 “高密东北乡”。当然,也不可否认,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感情是丰盈的,同时也是复杂的。
正是通过向世界讲述中国 “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世界文坛的尊重。莫言讲述故事的风格具有独特性,讲述故事的技巧具有前卫性,讲述故事的神韵具有本土性,讲述故事的基调具有述说性,莫言的作品释放出了他卓越的叙事才能。他为中国文坛再塑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为世界文坛平添了一束绚丽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