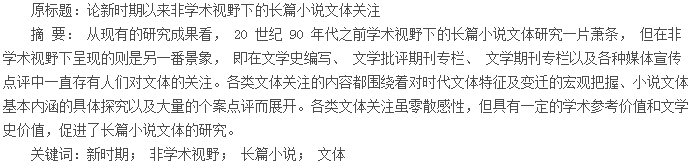
文体,又称“文学体式”,英语表述为“style”,中文释义为文体、风格、体裁、式样、类型等。对于文体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文体具有多重属性,对文体的理解也多从语言学、修辞学、审美学的角度入手。中国古代文体论者就指出了文体的多重属性。郭德英认为,古文体“义旨多端,或指体裁,或指风格,或指语体”。吴承学认为,古文体“内容相当丰富,既指文学体裁,也指不同体制、样式的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文学风貌”。
罗根泽认为,古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即文学的格,如元和体、西昆体。一是体类之体,即文学的类别,如诗体、赋体”。这里的语体、风格、类别等则包含了语言学、修辞学、审美学等多种属性。若只偏执于文体的某种属性,必然导致文体理解的混乱。如语言中心者认为,“文体是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
而修辞中心者认为,文体“关涉的是表达方式而不是所表达的思想”。
当前国内学界对文体的理解已趋全面。
在作家眼中,文体“通常是他与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在理论家眼中,文体“不是小说的一个局部,而是它的全部”。
结合各种理解,童庆炳给出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文体“是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弄清了“文体”的多重属性,再来界定“长篇小说的文体”就有章可循。长篇小说的文体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区别于诗歌、散文、戏剧、中短篇小说的一种体裁样式。但长篇小说广阔的社会场景、多义的主题揭示、复杂的情节设置、丰富的人物塑造以及多变的语言风格、多元的表达方式等决定了对其体式的考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体裁形式上,必然也要涉及语言学、修辞学、审美学等多重内涵。从语言学角度看,长篇小说的体式主要体现为对语言文字、标点符号、句式等的选择和运用上;从修辞学角度看,长篇小说的体式主要表现为小说的话语表达方式即叙事的特点,具体包括:叙事视角、叙述者类型、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内容;从审美学角度看,长篇小说的体式就是由小说的内容和创作方法所决定的。小说的结构方式或小说的内容、情感、情绪、创作方法等所构成的整体风格,与作家的气质、性格、思想倾向、审美趣味等息息相关。
当然,也有研究者将其内涵扩大到“心理学、社会学”。
这有点“泛化文体”的意味,塞进袋子的东西多了,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文体”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有过几次繁荣期。
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然后就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
新时期长篇小说处于式微期,故新时期以来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启动较晚。
1988年虽有《小说文体研究》问世,该书共选编新时期以来有关小说文体研究论文28篇,全方位反映了新时期小说创作文体新变趋势和小说文体批评新成果。
但该著只有极少篇章涉及长篇小说,故它的出现对于长篇小说文体的研究也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术视野下的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几乎空白,但在非学术视野下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即在文学史编写、文学批评期刊专栏、文学期刊专栏以及各种媒体宣传点评中一直存有人们对文体的关注,这些浮光掠影的文体关注从历史的高度还原了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流脉。
一、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点缀性掠影
所谓文学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文学活动的历史。但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已不复存在,唯一能直接把握的是文学活动的结果,而在所有结果中最接近文学活动本体的是文学作品”,此特点决定了文学史编写的滞后性。故根据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实况,在数以百计的当代文学史中选取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些代表史著进行分析,以管窥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在文学史编写中的地位与变迁轨迹。
(一)新时期后期文学史编写中时代文体特征及变迁趋势的宏观把握
1988年邱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略》已开始辟专章谈新时期的长篇小说,认为新时期以来的8年中,已有近千部长篇小说问世,但质量高、影响大的作品却很少,并归纳出长篇小说“侧重文化心理描写、淡化故事情节、突出民风民俗、追求结构与语言创新”的文体趋势。该著作开始提及“形式”二字,已是不小的进步。
但在分析作家作品时,还是落入“把作品分割成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先分析思想内容,后分析艺术特征”的窠臼。
并且,点缀性的艺术特征总结和长篇累牍的思想内容剖析在篇幅上明显不成比例,所以文学史就演变成主题思想史、人物形象史。
同年,李达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略》(1949-1989)肯定了新时期改革文学主体意识大张扬所带来的文体大解放,“一方面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是现代派小说的大量涌现,除写实小说之外,又有了写意、荒诞、变形、象征、魔幻等。
第三股潮流是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糅合产生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或现代现实主义”,并且该书在评价《李自成》时第一次饶有新意地提到了“杂糅众体”
的文体特征。
(二)后新时期文学史编写中独到的个案文体分析
1988年前后,文艺观念的深刻变革导致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文学的“向内转”以及“主体性”的讨论使新时期后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型,这点也体现在文学史的编写上。
20世纪90年代是当代文学史编写的高峰期,1990年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显著标志是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并分别从艺术结构、语言特色、叙述视角等方面总结了一些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在评论《李自成》时也指出作品“充分发挥古代各种文体的艺术作用,以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的文体融合特征,体现出编者一定的文体批评意识。1992年和1998年陈其光主编的两个版本文学史的风格和体例大致相似,在论及时代文体特征时无独到见解,缺乏一定的文体意识,但在评析《芙蓉镇》时则新颖地提出其“立人物小传的‘链条式’结构和‘融多种色彩成份为一体’的小说语言特征”。
1995年刘景荣主编的文学史在体例上有所创新,直接以作家论的形式来分章论述,在每个作家大篇幅的思想形象论述中再附上简短的艺术特征概括,不过这特征多是泛泛而谈,大而无当。当然也有让人眼睛一亮的发现,如在论及《黄河东流去》时,认为作品采用了“水浒传的链条式结构和古诗、民歌、谚语的开篇导入,适应了我国人民群众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的民族化艺术形式”。上述文体点评缺少一定的理论向度和深度,而同在1999年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较之以前具有稍强的文体意识,其中,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从新美学原则的崛起开谈,论述了西方现代意识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然后开专章论及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
虽也是选择个案分析来论述文学史的发展,但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文体特征,如贾平凹的“拟笔记体”、韩少功的“词典体”、马原的“元叙事”等。
朱栋霖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首次提及文学本体性,重点谈了先锋小说的文体特点、马原和莫言的文体特征以及新潮长篇小说在文体形态上的文学革命。
(三)21世纪以来文学史编写中关乎长篇小说文体本体的探究
进入21世纪,学者们编写文学史的热情并没减退,随着长篇小说成为时代第一文体,文学史中开始出现一些专题性文体探究,且评价内容越来越接近文体内核。
2003年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50-1990)》首次厘清了作品本体论、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并还分析了新时期以来的文体批评状况,即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大板块构成,前者包括了对文学形式的理论探讨和对文学形式演变的动态描述,后者包括了对具体的文学形式构成因素的研究,也包括了对某一具体作家作品的形式构成及特征的研究”[17]267。
2005年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提及了文学本体性的讨论,可是没有展开谈,但其开设了专章探讨新时期小说的文体特征,重点探讨了几个创作样式复杂的小说家的文体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1989-2000年长篇小说文体的特征。
在上述零散的文体掠影中,我们能看出文学史编写中文体成分的比例越来越大,编者的文体批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思想主题点缀艺术特征的固定模式也在一步步打破,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也在片段的掠影中得以彰显。
二、文学批评期刊专栏的经典化意图
进入21新世纪后,长篇小说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大文体。一些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期刊如《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分别策划了各种专栏,以期推动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的研究与发展。其中,《小说评论》于1999年开辟了“长篇小说笔记专栏”,此专栏特邀雷达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撰写了24篇文章,分为21期对新时期以来近百篇代表性长篇小说进行追踪式评论。
虽然其中不乏有一些关乎小说文体的精彩论述,但终究不是小说文体的专题研究。
不过,关于小说文体的专题研究专栏也有,早在1987年《文艺评论》连续发表了李国涛的4篇《缭乱的文体》评论文,为当时本已五彩缤纷的文体研究再添新彩,但依然不涉长篇小说文体,而真正对长篇小说文体进行专栏讨论的是《当代作家评论》。
(一)关乎长篇小说文体内部因素的第一次对谈
进入21世纪,《当代作家评论》曾两次举办大型长篇小说对谈会。
2001年该刊和《收获》在大连联合主办了“2001年长篇小说文体对谈会”。作家张炜、尤凤伟等和评论家陈思和、王一川等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在对谈会上,与会的作家、评论家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对长篇小说的文体、叙事、语言、结构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会后,该杂志在2001年第5期集中刊发了9篇评论文。
这9篇文章皆篇幅简短,随性率真,虽少了学术研究的厚重,但不乏真知灼见之火花。如学者型作家格非从宏观上论述了文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体与形式通常是作家与其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而在红柯的意识里,文章是没有文体之分的。作家们的言辞多具象可感,意象横生,而批评家们则是言辞犀利,一语中的。王一川拿出学术研究的姿态将长篇小说文体分成拟骚体、双体、跨体、索源体、反思对话体、拟说唱体等新类型,并归纳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正衰奇兴的新趋势;孙郁认为当下长篇写作在文体上出了问题,即在西方的宏大叙事理念里陷得太深,未能与民族语言艺术沟通起来;谢有顺认为更多的时候,文学的贫乏不是因为缺少文体的探索,而是因为文体的滥用。
(二)关于“如何写”长篇小说的第二次对谈
截止2005年,当代文坛长篇佳作迭出。2005年《当代作家评论》与渤海大学、《作家》、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了“2005年小说现状与可能性对话会”,作家莫言、贾平凹等与批评家王晓明、南帆等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相聚一堂,就长篇小说的写作展开了讨论,并于2006年第1、2期集中刊发了12篇评论文。
较之上次,作家的声音要多于评论家,所交流内容则重了创作实感,淡了文体探究。
莫言认为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小说文体的尊严;贾平凹认为生活给创作提供丰富的细节;阎连科则谦虚地坦承自己在写作中遇到了无力把握现实以及面对写作时出现新的重复的尴尬;东西则坦承写内心秘密、写人物和对生活的预测成了其写作的兴奋点;李锐认为中国小说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林白认为长篇小说无界限,它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态度的总和;艾伟则强调只有信服力、社会反思力、时代质疑力相结合才能写出令人信服的好小说。
而评论家们则显得言归正传,语重心长。
为防止长篇小说在语言、叙事、结构、精神书写上的粗制滥造,谢有顺呼吁要强化写作的难度,扩展经验的边界,增强叙事的说服力以获取长篇写作的尊严;洪治纲则认为作家须用超凡的文学想象和关键性的细节设置才能写出具有说服力的好作品;王晓明则认为在当下的图像时代,长篇小说写作应坚守文学的根本;王尧认为优秀的小说家要有自己的想法,要会在重新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之后找到观照和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李静认为艺术的创造力来自于作家对社会的独特洞察,但这必是一种将洞察力化为“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能力。
其实有这种想法与举措的还不止《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也曾在同期集中刊发过长篇小说专题论文,如在2009年第5期刊发吴义勤的《关于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热”的思考》、汪政的《多样化与长篇小说生态》、张福民的《长篇小说和它的历史观问题》,在2011年第6期刊发了张清华的《我们需要肯定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杨扬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问题》等。
当然,诸如此类同期刊发文章的情况颇多,在此只略举一二。这些评论性文字对小说文体的分析尚处于局部的、感性的层次,但它们的存在显示了文学批评期刊促进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经典化的意图,也表明了期刊关注长篇小说研究的决心与姿态。
三、文学期刊策划的“跨文体革命”闹剧
其实,在文学批评期刊积极策划专栏以推进长篇小说文体的革新与发展之前,各类文学期刊竟然同在1999年发起了文体革命,以推进小说文体的革新。
但这次革命不是作家群体的自发行为,而是先有各文学期刊的理念设想,后有作家们的创作实践。
其中,《大家》主编李巍指出,“凸凹文本是一个文学怪物,它就是要在文体上坏它一次,隔塞它一次,为难它一次,让人写小说时也能吸取散文的随意结构,诗歌的诗性语言,评论的理性思辨;同样让人写散文时也不回避吸纳小说的结构方式。
我们希望,在文体的表述方式上能以一种文体为主体,旁及其他文体的优长,陌生一切,破坏一切,混沌一切”。《莽原》主编张宇认为,“文体像牢笼一样局限和障碍着写作的自由,文体的繁复和腐朽伤害和围困着写作的激情和灵性。
于是,跨文体写作就像在自己的身上插上别人的翅膀一样,再也不是为了形式和形象,而是为了表现的实用,为了更自由地飞翔”。《中华文学选刊》则于2000年推出“无文体写作”,栏目主持人匡文立则认为:“‘凸凹文体’、‘跨文体’等旗号有‘意在笔先’之嫌,显示出来的是某种‘命名癖’。‘无文体写作’试图回避命名,只注视某种写作现实。
我们选择的标准也很简单:当一篇文字颇值得一读,却又无法妥帖地安放进任何现有的‘文体’,那就是我们张弓以待的‘大雁’了”。
从各杂志的创作实践来看,《大家》推出“凸凹文本”的代表作是李洱的《遗忘》,虽然李洱在极力实践主编的意图,把作品写成了一个既不像学术论文、又不像随笔散文、也不像小说的“四不像”文章,大家还是勉强将其归为小说。《莽原》的所谓“跨文体”最后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学术随笔或思想随笔。而《中华文学选刊》更是作茧自缚,其所提倡的“无文体”根本无法实践,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是随笔,要么是荒诞喜剧,要么是搞笑文章,要么是词语解释。最后难以为继,只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尾。
在各杂志主编极力鼓吹、各作家极力实验的合力下,“文体革命”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年多时间。
在闹剧上演的过程中,评论家们则表现出一贯的冷静与忧虑。一开始杂志主编们就将评论家定位为“革命”的助势者,在刊发各种实验文章时也刊发了评论家的评论文,但众评论家的观点几乎一致。
其中洪治纲认为“作为一种整合性的艺术实验,它失去了对某种主题的单纯表达,在一种后现代式的叙述行为中体现了作家对既定艺术规范的反叛。
但这种反叛并不具备明确的建构目标。”
吴义勤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凸凹文本这样一种包容性文体本身也是十分可疑的。
不能故弄玄虚,为文体而文体、为革命而革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这场文体革命闹剧虽已成为历史,但在现象背后遗留下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长篇小说文体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外在形式,它是作家内在精神情感外现的载体,它蕴含着作者在语言学、修辞学、审美学甚至社会学、文化观、哲学观乃至心理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如果要进行一种文体选择与创新,最起码的模式也应该是由作者本人从内心有了触动,再由内到外,由独特的个体到多个相似的个体的共同倡导,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体革新运动。
当众多文学期刊为了各种不可言说的利益而先入为主地邀请一些本身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运用尚未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青涩作家来推翻成熟文体时,事情本身就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其最终的不了了之也是必然的。
四、媒体宣传或评奖颁奖辞中的精彩点评
在长篇小说备受追捧的世纪之交,除了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期刊以专栏的方式探讨长篇小说文体,在相关的媒体如《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等也能见到一些散落的文体评论,这些评论或以文坛消息、年度总结,或以书评、短论等方式传达着当代长篇小说在文体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与信息。
(一)新的文体研究成果的及时报道
2000年《文艺报》的《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历史观照》对文体研究新成果《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作了及时性报道。2001年《辽宁日报》的《语言自觉文体创新》,以及《北京日报》的《文学界反思小说的文体》全面报道了由《当代作家评论》等主办的长篇小说文体对谈会的研讨成果。2003年《中国教育报》的《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体》及《文艺报》的《小说研究的新收获》全面报道了文体研究专著《新时期小说文体论》的研究成果。2006年《文艺报》的《小说文体研究的新成果》、2007年《文艺报》的《文体意识自觉与文体革命》皆评价了专著《新颖的“NOVEL”———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论》。
(二)经典作品的文体推荐及对时代文体的多维思考。
2000年《文学报》的《论王蒙的“狂欢体”写作》概括了王蒙“季节”系列小说的“狂欢体”文体特征。
2002年《文汇报》的《〈暗示〉: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指出:“《暗示》有文体的实验意识,但因为整个作品的构成元素不是叙事而是议论而导致基本上的失败。”
2003年《中国邮政报》的《一部等待了很久的小说》对新作《你在高原·西郊》的叙述、结构、语言作了充分的肯定。2002年《光明日报》的《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化》认为,90年代以来“陌生化”的文体追求带来审美表现方式和阅读的革命性变化,作家创作中哲学意识的强化使小说文体产生出寓言性、象征性表现结构。
2002年《文汇报》的《关注文艺的“新工具革命”》指出,文艺工具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超文体”现象上。
2002年《中国图书商报》的《呼唤文体独立的时代》指出,各文体之间是平等的,各文体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2003年《光明日报》的《纷繁的长篇小说文体》认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已从多方面展开,强大的冲击波正在改变着长篇固有的模式。
2007年《光明日报》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文体压力》认为,文体意识的强化不仅弱化部分作品的思想性,也使精神性和艺术性相割裂,使文学写作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异。2009年《文汇报》的《手机小说,创造另一种文体》指出手机小说对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的影响。
2012年《人民政协报》的《文体家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文体》盘点了当下小说家的文体意识状况。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新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文体类型》指出,新世纪文学写作呈现出以奇幻的形式重组历史记忆、以现实主义的策略重构现实整体性两种趋势;2013年《太原日报》的《长篇小说热与作家的文体意识》对当下长篇小说热以及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提出了自己的思考;2013年《北京日报》的《小说的长度与生存理由》指出,复调的种类与浓度是长篇小说存活的理由。
(三)各类文学颁奖辞中的神来之笔
除却各类报纸,还有部分关于个案文体评价的神来之笔镶嵌在各类文学颁奖辞或获奖作品简介中,如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国小说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等。
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为例,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认为,史铁生“一次次地突破语言和文体的边界,其写作已经成了文体变革和精神探索的象征”;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认为,格非的《人面桃花》“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有意以闲聊和回述的方式,让小说人物直接说话,把面对辽阔大地上的种种生命情状作为新的叙事伦理”;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认为,北村的小说“叙事果敢坚决,同时又不失隐忍和温情”、乔叶的小说“有着精微的叙事,细腻的感情,语言针脚准确而绵密”;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认为,“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有强大的叙事说服力”;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认为,方方的小说“叙事悠长而强悍,格局宽阔,气象磅礴”,而杨显惠的“叙事手法,也因着去修辞,赤诚,不夸饰,而有效恢复了文学与历史、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传统”。
这些评语虽只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而言,但都围绕文体的基本属性进行总结,比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显得精粹、到位,有些观点则直击命门,精彩无比。如指出了作品《人面桃花》的语言和审美属性、《妇女闲聊录》的修辞属性,同时对作家个人的文体风格也作出了精辟的总结。
五、各类文体关注的价值
(一)学术参考价值
在上述提及的文学史编写中,越来越重的文体成分已经表明编者的文体意识越来越强烈。而在文学史中留下的文体成分对于后来的文学史编撰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其对时代文体的特征及流变趋势的宏观把握,对后来者来说具有时代感和真实性。而由文学批评期刊、文学期刊所举办的文体关注专栏活动或所策划的文体革命活动,其所留下的各类文体批评文章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且活动本身皆为当代文体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事件。在媒体宣传或评奖颁奖辞中的零散式点评中,不仅准确报道文体研究新成果,还精辟道出文体研究的新动向,最终敏感传达出文体演变的某些动态。这些都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促进文体史的编写
当前的各类当代文学史都是思想流派史、人物形象史或文艺思潮史,几乎没有一部文学史将长篇小说文体的流变提高到和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艺术特征等相提并论的位置进行充分地论述。
但实际上任何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都不会放弃对文体的探索与追求,故一部全面权威的文学史也应该不会忽略对长篇小说文体的系统概述,尤其不会忽略那些有鲜明文体意识的长篇小说。
从目前的文学史编写现状来看,文学史中的文体成分越来越多,关注的内容也由之前的一笔带过转变为专章详论,这说明编者的文体意识越来越强烈,创作者的文体意识也越来越鲜明。
故现有的文学史编写中所含有的文体成分有利于后来学者依据其所提供的学术线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流变史的撰写。而此项工作的完成,则弥补了文学史编写的缺憾,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
(三)推动文体的发展
上述中由各文学批评期刊举办的专栏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争鸣论文的问世,在当时学界刮起了一股文体研究风,且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直接的。之后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如《暗示》《花腔》《桃之夭夭》《人面桃花》等文体意识鲜明的作品的问世,足见对谈会的召开对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切切实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由文学期刊发起的文体革命活动更具启示意义,更加引起人们对长篇小说文体的关注与思考,如长篇小说文体是否已发展到了束缚写作自由的程度何为跨文体它与文备众体、文体融合、文体互渗有什么区别无文体写作真的能成立吗大家都在期待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文体这些思考都有利于促进创作者的文体革新和理论者的文体研究。
而散落在媒体报纸或评奖颁奖辞中的精彩文体点评,更以媒介宣传的及时性、动态性、互动性、受众范围广、产生影响大的特点,报道了文体革新动向和文体研究新成果,营造了浓郁的文体关注氛围。在读者的文体期待心理、作者的文体求变心理以及研究者的文体研究兴趣的合力下,文体革新和文体研究会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郭德英.中国古代文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