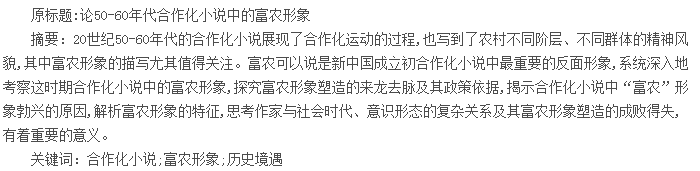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全国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地方到中央关于农村发展途径的设想和探索,它不仅给农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就反面形象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中,地主形象相对薄弱,与此相应,出现了大批富农形象,较为典型的有姚士杰、黄龙飞、马斋等,这些富农形象是此前土改小说中地主形象的延展,也是合作化小说中最重要的反面形象,在合作化小说中,他们代表着贫下中农的对立面,不仅使得小说中的种种矛盾冲突成为可能,也对地主形象形成补充。透过这些富农形象,我们也可以发现文学形象与时代历史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联、文学家在历史中的角色与作用。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合作化小说中的正面英雄形象和转变中的农民形象已有充分的研究,对地主形象也有一定关注,但对富农形象的研究却极为匮乏。
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为研究核心,探究富农形象的来龙去脉,考察富农形象塑造的文学史演变及其政策依据,揭示合作化小说中“富农”形象勃兴的原因,解析富农形象的特征,思考文学形象、作家与社会时代、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富农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
一、“富农”的概念界说、富农的历史境遇及其文学形象的前世今生
“富农”一词本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从俄国人那里援引过来的专门术语(俄语称为кулак)。在1920年代的俄国,虽然没有关于富农的确切定义,但一般根据农户占有耕地、耕畜的数量以及使用雇佣劳动、拥有非农业收入等情况来确定富农的成分。在中国,关于“富农”一词的界定,以毛泽东的说法影响较大,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从生产经营方式和剥削特征来定位富农:“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
毛泽东对富农概念的这一界说一直沿用到建国初期,其间虽然有一些删改补充,但基本内容没变。
在建国前后的中国,对富农的阶级属性的定性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俄国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农业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的问题。列宁要求通过农民自愿的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而斯大林在集体化过程中则实施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采取了强制性的剥夺和没收财产的手段消灭了富农阶级。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富农是“吸血者、蜘蛛和恶魔”,“是苏维埃的敌人”,所以在1920—1930年代,俄国联共(布)中央“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这些政策和做法也影响到中国,而“把苏联的这一做法搬到中国来,并非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做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1929年8月,中共中央推出了《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决议依照苏联的说法和做法,指出中国富农兼具“半地主半封建性”,并提出了“坚决地反对富农”的方针。虽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待地主与富农的政策有所不同,1946年的“五四指示”和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但由于富农具有“剥削”性,在土改时期,为了充分发动农民变革旧有的土地制度、巩固红色政权,不免把富农也归入打击对象之列,在土改后期,我国又把富农定位为“农村资产阶级”。
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我国逐渐将斗争目标对准了富农阶级,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政策,随着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来临,富农和富农经济最终走向被消灭的结局。
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伴随着现实中的集体化过程,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就出现了大量的集体化题材小说,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扎莫依斯基的《拉普基》、舒霍夫的《不共戴天》、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等,其中不少作品写到了富农形象,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关注土地革命和乡村生活现实的作家也注意到了富农这一特定的农民阶层。在1940年代解放区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富农形象开始出现,由于当时农村革命的对象是地主而不是富农,所以作家对富农的描写极为粗略,也显得温和,阶级论色彩较为淡薄,甚至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凸显了富农吃苦耐劳、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比如柳青的《种谷记》(1947)中的富农王存亮,虽然雇了三个长工,但他本人干活总是比长工还要重,他自己寒冬腊月连个帽子都舍不得戴,因此落了个“赤脑财主”的绰号;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富农顾涌勤劳本分,对土地有着本能的热爱,虽然家里有不少地,在农忙时也雇过工,但他勤勤恳恳,没干过什么坏事。由于农村土改现实中的一些过激做法也触动了富农的利益,一些反映土改的小说也写到富农对土改的惶恐和敏感,比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富农胡泰因为家里有多于其他人的田地和粮食以及大牲口,在土改工作组来了之后,成天睡不着觉,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在苏联集体化题材小说的影响下,也有作家开始用阶级论与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农村生活,去思考富农在乡村变革中的立场与作用,作家周立波就是如此。由于在1936年周立波翻译过肖洛霍夫描绘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这部作品展示了贫农、中农与富农、白军分子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它“对周后来的所有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对富农的描写(涉及没收富农财产,清算、驱逐富农,富农和反动分子的勾结等)也影响到周立波。有论者指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以‘阶级论’模式反映土改运动最早的小说之一”,《暴风骤雨》除了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农村典型人物”、展现新人的诞生和成长历程以外,也写到地主与富农。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富农阿斯托洛夫罗夫私藏反动军官,和反动的白卫军军官波罗夫则夫串通一气,煽动农民围攻集体农庄领导,抢劫集体农庄粮种,危害集体农庄的利益和事业。
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也把富农李振江写成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心腹和耳目,在土改斗争中,“他顽固地替地主说话,跟穷人对立”,李振江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作队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活动起了破坏作用,对元茂屯的土改起了阻碍作用。相比之下,在柳青眼中,富农则有好有坏,《种谷记》一方面写到了勤劳淳朴的富农王存亮,另一方面也写到做过地主狗腿子的富农王国雄在王家沟的变工种谷互助活动中所起的破坏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种谷记》中的人物关系已有了《创业史》的雏形:农会主任王家扶、富农王国雄对应着《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姚士杰,这使得《种谷记》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阶级斗争模式的雏形。
不过,在上述作品中,富农虽然比普通农民富裕、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或雇人干活或者像胡泰那样兼作生意,甚至喜欢和地主等有钱有势的人走动,但他们还说不上是农村革命的对立面,作家在描写这些富农形象时尚未刻意地丑化贬低富农或将其绝对化地设定为阶级敌人。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中,作家对富农形象的塑造明显受到阶级论的影响,富农几乎成了合作化小说中常见的反派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初的100多篇合作化小说中,如果说地主形象屈指可数的话,富农形象则随处可见。如《创业史》中的姚士杰,《艳阳天》中的马斋,杜鹏程《飞跃》中的李兴发、王汶石《新任队长彦三》中的彦子玉、胡正《汾水长流》中的赵玉昌、陈登科《风雷》中的黄龙飞、刘澍德《桥》中的吴林贵、秦兆阳《在田野上,前进!》中的郑洪兴、于逢《金沙洲》中的“老鼠福”等,都是作品中着笔较多的富农形象,这些富农形象无一例外的都是些否定性形象。
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0年代合作化小说中,富农之所以代替地主、成为主要的反面人物,有着复杂的原因,主要与农村阶级状况的变化、我党特定时期的阶级政策以及苏联文学的影响有关。从农村各阶层的情况来看,土改实施以后,“地主”群体的厄运就开始了,在土改运动中,各地地主由于抵制土改而大量遭到惩处甚至枪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使得地主数量锐减。经过建国前后的土改以后,地主阶级逐渐消亡,农村中作为阶级实体存在的主要是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层。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时期,“斗地主”的革命步骤已然完成,地主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或者已被镇压,或者已被打到,或者像秦兆阳《改造》一文中的地主王有德那样接受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由于地主阶级大势已去,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不再是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在合作化时期,富农阶级和贫雇农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在合作化小说中,作家一般不再把地主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富农形象上。比如赵树理在《三里湾》开头便对地主形象的缺席做了交代:地主刘老五早在1940年代就被枪毙了,他家的宅院现在已经成了三里湾村级党政组织的办公场所。这段介绍暗示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已被消灭,所以《三里湾》展示的不是地主和农民的争斗,而是合作化时期一幅正常的居家过日子的农村生活图景。而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吕二细鬼”和“杨大剥皮”两个地主也只是在小说的“题叙”里一笔带过,这两个地主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过去时代的“影子”或“符号”而存在,他们并未在合作化时期的生活中占有位置或与合作化运动发生什么关联。相比之下,《创业史》对富农姚士杰形象的着笔更为用力。
如果说土改是针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合作化运动则是针对农民小生产方式和私有观念的革命,革命对象的改变也造成了合作化小说中“地主”形象的式微和“富农”形象的勃兴。与此同时,由于富农阶级和贫雇农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富农成为合作化运动的阻碍力量,合作化小说也把富农作为主要敌对势力来加以阐释和描写,作家对富农也持鲜明的批判、憎恶态度,这使得富农接替从前在土改小说中被大写特写的地主,成为合作化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反派形象。
而从外来文学影响的角度和文学的纵向发展看,合作化小说对富农的否定性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苏联文学和1940年代周立波等人的土改小说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正是中国文学尊崇苏联文学的时代,也是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极大影响的时代,以至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被看作是新中国文学中“农业合作化叙事的经验之源”,成为合作化小说作家模仿借鉴的对象。如果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对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有着直接影响的话,它对中国合作化小说的间接影响则是通过本土作家周立波来完成的,“一方面,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翻译者,他(周立波)继承了苏联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农村题材中阶级论模式的始作俑者,他的创作对建国后的作者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合作化小说对富农的剥削性与反动性特征的言说
在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中,富农形象几乎随处可见。那么,作家在阐释新时代的农村革命时,是如何来言说、描写富农形象的?
考察合作化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特定阶级政策的影响之下,作家们常常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认识农村中的各个阶层,去表现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生活,他们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赞美歌颂合作化运动,并从人的经济地位去解释人的政治态度,按照官方的富农政策去描写富农形象。在作家看来,富农在农村经济地位较高,不免剥削人;由于合作化运动触及自身利益,加之和贫雇农阶级存在矛盾,富农不免反对合作化运动,进而走向反动;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并非仅仅是农民是否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的问题,也是进步农民与富农阶级的激烈斗争与较量的过程。
于是,富农形象的反面化、反革命化成为必然。
与1940年代土改小说对富农的温和描写不同,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基本上是把富农作为敌对分子来描写的,所以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虽然名为“富农”,却在言行表现与思想特征上和土改小说中的地主无甚差别,其突出特征是具有剥削性与反动性,其普遍表现是对贫雇农没有同情心,随时密谋破坏互助组与合作化等,富农的“地主性”特征使得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土改小说中的地主形象的延伸或翻版。
当然,在1950—1960年代,富农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阶级斗争被强调,富农形象越来越政治化与漫画化。
在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中,作家大多注重凸显富农的剥削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地主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富农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行为。毛泽东对富农的“剥削”方式有着更为具体的解说,他说,“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在合作化小说中,富农的剥削性被加以强调,比如《创业史》写富农姚士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剥削人的“根子”,他的爹是剥削人的“铁爪子”,姚士杰的“剥削人”的习性则跟他的父亲一脉相承,“姚士杰敦实的身体里循环的,就是这样气质的血型”。“剥削”使得富农被置于和地主相提并论的位置,所以柳青在《创业史》中借高增福之口说:“富农剥削人这一点和地主是一样可恶。”合作化小说也告诉读者:富农与贫农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表面上看,富农同贫苦农民一样有着发家致富的愿望,但他们发家的目的是想借此过上剥削阶级的风光体面的生活,比如姚士杰“平生的理想,是和下堡村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三足鼎立,平起平坐……”;《艳阳天》中的马斋,一直幻想着过上地主那种家大业大、有房有粮、有马车有长工的剥削阶级的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富农阶级成为斗争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也常常以“反动”面目出现,他们不仅和地主一样剥削人,而且仇视新社会和共产党,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
比如《创业史》中的富农姚士杰是“凶狠的阴谋家”和合作化运动的头号敌人,他仇恨共产党,仇恨新社会,“他在上黄堡集的路上,听见如果有人骂拥护新社会的任何人,他都感兴趣”,“他最喜愿听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的事情,发生什么问题。听见什么地方有了问题,他走路脚步也轻快了……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风雷》中的富农黄龙飞是“不甘心政治失败的反动富农”,他的阶级出身决定了他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新中国成立前他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富户,又是包揽诉讼的刀笔,是黄泥乡数一数二的乡绅老爷,土改后失去了土地财产和昔日的威风,合作化时期他兴风作浪、气焰嚣张。《艳阳天》中的富农马斋不仅仇视新社会,而且时刻梦想着“变天”,妄想新社会将来又变成地主富农的天下。
在合作化小说作家笔下,富农不仅外形丑陋(如黄龙飞长得“尖头细爪,獐眉鼠目”,姚士杰眼皮上有可怕的疤痕,马斋是生理畸形者———六指),他们也是合作化运动的反对者与破坏者。合作化小说对富农在合作化时期的反动立场及其破坏行为的描写,与我国当时的富农政策密切相关。在合作化时期,我国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1955年颁布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又进一步指出,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由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原来的地主、富农中的许多人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采取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警惕他们对于合作化运动破坏的严重性。”。这些对富农的认识判断和相关政策也必然影响到合作化小说对富农的描写,以致形成合作化小说有关富农的叙事惯例,即常常叙写富农在席卷全国的合作化潮流面前逆流而动,千方百计破坏合作化。考察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写到富农的破坏活动”。比如《创业史》写富农姚士杰阴险狡猾,在村里暗中使劲,竭力想促使贫富两极分化加速,不仅抵制活跃借贷的活动,还和互助组较劲比赛,企图降低互助组的影响,打击互助组员的积极性。
《风雷》写富农黄飞龙在合作化时期处心积虑,坏事做尽:伙同他人套购粮食,煽动群众围抢粮库,栽赃陷害试图搞臭党员干部,并试图颠覆黄泥乡的革命政权。《汾水长流》写农业社遇到灾害时,富农兼商人赵玉昌乘机伙同已被拉下水的刘元禄一起倒卖粮食,鼓动社员闹退社。不仅长篇小说如此,中短篇小说也不例外,一些以合作化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也大写特写富农的破坏活动,比如柳青《狠透铁》中的富农王以信采取非法手段盗窃农业社的粮食;《新任队长彦三》中的富农彦子玉一伙人操纵公社领导彦顺平,背着管区和公社党委,解散了公共食堂,又实行包产到户,使一些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大抬头;《春茶》中的富农黄厚福抵制合作社,一心搞单干;《运河的桨声》中的富农分子田贵拉拢富裕中农麻宝山搞单干,唆使富贵老头退社,勾结反动粮商王六密谋破坏活动,偷砍农业社用腐殖质培植的老玉米,破坏丰产实验地……富农对合作化的破坏活动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富农分子固然具有许多革命语义所规定的反革命特征,他们身上更有一种物质性,即他们的反革命行为与其说是反革命立场的选择,不如说是对物质占有、囤积的一种心理性行为表现,这些人被物质欲望所驱使去做了一些“反革命”的事情。
比如,刘绍棠的《夏天》中山楂村初级社的反动富农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结成联盟,他们之所以破坏合作社,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套购粮食而已。柳青《狠透铁》中的富农王以信的主要罪状也是盗窃、私吞粮食,“王以信勾结副队长王学礼和保管委员韩老六,盗窃了十二石麦子”,强烈的物质欲望驱使着这些富农走向合作化运动的对立面。
作家也常常把富农置于农村阶级关系、阶级情感中来加以表现。从阶级关系看,富农与贫下中农是对立关系。
如果说土改时期乡村社会中阶级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体现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上的话,在合作化时期,乡村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对立则表现在农民和富农的关系上。由于阶级差异和隔阂,贫农和富农阶级之间不仅存在着感情上的裂痕,生产生活上也缺乏相互协作与扶助,在合作化运动中,他们无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可避免地构成矛盾对立的两方。
阅读合作化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富农与贫农在感情上是不和谐的,一方面,富农为富不仁,对贫农没有同情心。譬如《创业史》中的姚士杰,当穷人向他告借之时,他每每“从缺粮人愁楚的脸上感到快乐,他把和告债的人谈话,当作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享受。”另一方面,贫农对富农有着天然的仇视心理,比如贫农高增福与富农姚士杰简直势不两立,他随时监视着姚士杰的动向,也怨恨哥哥丧失立场向富农借粮;出身贫农的欢喜听说婶子素芳要去富农姚士杰家伺候月子,他很是气愤,认为素芳“不要脸”,“简直是对于贫雇农立场的叛变!”;听说素芳要去姚家做事,高增福也气得脸色“煞白”。《艳阳天》中的积极分子焦振茂也绝不与富农为伍,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富农儿子谈恋爱,千方百计阻止马立本来追求女儿,在他看来,如果“自己跟富农六指马斋搭亲家,更是有损自己的人格”。
富农与贫农的紧张关系也让革命分子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富农分子,贫农阶级有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无论是在蛤蟆滩,还是在东山坞、山楂村,富农分子都时常处在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的全方位监控之下,正如《运河的桨声》所写的那样:“山楂村处处是眼睛,处处有耳朵”,监控着敌对分子的生活言行,农业社副主任春枝甚至拿着枪,晚上冒雨到村庄四周巡逻,并开枪打伤破坏堤坝的坏分子。
如果说富农与贫下中农总是处于对立关系的话,他们和地主或其他反动分子则打得火热,或有着这样那样的瓜葛,作品以此说明,富农跟地主等坏分子实际上是一丘之貉,所以在合作化小说中,富农跟地主总是同宗同族、同声合气,比如《艳阳天》中的富农马斋和地主马小辫是同族,《风雷》中的富农黄龙飞“是死洼湖里地主黄一夫的近族”。
在反对合作化的活动中,富农总是成为地主或其他坏分子的帮凶与工具,比如富农马斋和地主马小辫时时串联,干坏事时马斋也跟着跑龙套,敲边鼓;富农田贵被坏分子王六当枪使,在王六的驱使下去联络王六的同伙,破坏山楂村的堤坝和农业社的试验田。
总之,在现实政策、阶级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作家常常通过上述诸方面的描写来凸显富农的“坏”和“反动”的本质特性,在写作合作化小说时,作家对富农不再有同情,其笔下的富农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
当然,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除了有上述“共性”之外,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个性特征,比如姚士杰精明能干,被乡亲视为蛤蟆滩的一大“能人”;黄龙飞老奸巨猾,有着足智多谋的“师爷”特征;马斋老成而有城府……这些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富农形象的多样性。
三、合作化小说中富农形象描写的意义、局限及其思考
在20世纪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变革中,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镜像,而就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而言,其描写塑造不仅带有显著的时代性与政治性特征,体现了作家的立场选择,也有其利弊得失。
合作化小说不仅是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文学记忆,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矛盾,表现了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在合作化运动中不同的立场态度和心理,富农作为农村中的特定阶级与阶层,也得到作家的关注与描绘,这对于我们了解、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精神心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从文学角度看,合作化小说对富农形象的塑造,不仅使解放区土改小说中的富农形象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使得富农形象与地主、日本鬼子形象一起成为十七年文学中反面形象的典型代表,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透过合作化小说我们也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生态和作家角色的功能作用使得文学无法成为纯粹的审美产品,合作化小说的政治化、富农形象的符号化似乎不可避免,从某种意义上说,富农形象的塑造就是为合作化小说突出政治、深化主题服务的。有论者指出,“50-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中国’,政治被武装到了经济、文化和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当时的作家大多是以“社会的宣传员”的角色出现,是国家意识形态传输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作品水平的高低也就以能否给予人民以思想教育为标准,政治(甚而政策)内容加上文学的表达方式也就成了5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意义模式”。就合作化小说的创作而言,作家们普遍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政策,以为合作化运动宣传和造势的姿态来写作合作化小说,他们大多是在政治框架下和配合政策条文的前提下完成合作化的叙述的。这使得合作化小说中,乡村生活被革命和政治意识覆盖,宁静朴素的乡村成为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场所,作家常常围绕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矛盾冲突来编织情节,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则时常分类定性,图解人物。由于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对富农的政治定性和打击政策的实施,富农形象的塑造也必然成为政策的注解与政治化演绎的产物,而政治化的描写又使得面貌趋同或大同小异的富农形象充斥于合作化小说中,造成人物形象同质化的弊病。与此同时,由于合作化小说与现实贴得太紧,作家无法对现实中的富农形象展开各种想象,而大多对富农采用类似于地主的阐释描摹逻辑,所以在合作化小说中,富农在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土改小说中的地主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也使得富农形象与地主形象存在着明显的趋同化现象。
从人物描写的文学修辞策略看,富农形象的塑形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在1940年代的土改小说中,作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隐隐约约地写出了对富农的同情,而在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中,富农普遍地成为反面形象,作家对其只有憎恶与反感。从人物描写的修辞策略看,“政治道德化是50-70年代小说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修辞方式”,十七年小说对反面形象的一贯描写策略是在身体上进行丑化、在政治上进行否定、在道德人格上进行贬低。合作化小说也不例外,作家不仅通过种种情节细节言说富农在形体外貌上的丑陋性、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和对合作化的破坏性,还使用道德修辞,凸显富农分子的道德缺陷和人格污点,这主要体现在乱搞男女关系上。比如姚士杰虽是有妇之夫,却曾经和李翠娥及妻侄女素芳有染,不仅乱搞男女关系,还夹杂着乱伦;郑洪兴好女色,不仅和破鞋魏月英搞在一起,还对他的儿媳妇有邪念;黄厚福也和小姨子乱伦,还生下了私生子……总之,在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描写上,“人物阶级属性与道德品质……有对应关系”,这使得富农不仅是合作化的“敌人”,也成为道德败坏的典型代表,而千篇一律的道德化的富农形象进一步强化了富农形象的类型化阐释。
不仅如此,合作化小说还使用政治修辞和道德修辞来描写富农的家属,似乎是“近墨者黑”,抑或是与富农“同声合气”,富农的家属也大多表现出一些“坏人”的气质习性,比如富农姚士杰的老妈迷信伪善,他的婆娘风骚不正经,“三十几岁还娇滴滴”,他的妹子曾向高增福“骚情”,试图腐蚀革命干部;富农马斋的儿子马立本也子承父性,他贪污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手脚不干净,马立本表面上和父亲划清界限,实际上“还是跟富农一个肺叶搧扇子,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富农田贵的老婆狡猾反动,见到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俞山松时,“像一只狸猫似的,眼睛闪着磷光,隐藏着敌意,溜来溜去”,这个富农婆也是淫荡无耻的,不仅对反动粮商投怀送抱,夜里听到院子里俞山松的说话声,“田贵老婆出来了,不怕羞耻地穿了一件小衣”,“半裸体地站在那里不动”。富农及其品行不正的家属形象意在说明血缘、亲情关系中坏人习性的一致性,其修辞用意是从家庭伦理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否定贬低富农,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作家对人物所做的简单化理解和阶级泛化的处理。
文学形象应该丰富多彩,富有个性,作家不应该仅仅遵照政策指示来写作,还应该遵照自己的内心来写作,但在时代语境的制约下,在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作家不再有独立艺术个性的坚守和肆意表达的自由。在这种情形之下,合作化小说的创作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和个人行为,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治行为,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也因此成为单向度的、抽象概念化的反动人物,这不仅有损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和丰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生活真实。不过,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通过富农形象的描写塑造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譬如文学形象是如何与时代社会、现实政治发生关联的?文学形象的文学史脉络与演变潜藏着怎样的真相?文学家在文学形象的塑造描写中担负着何种角色与作用?
文学如何回归审美性?作家怎样保持主体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给予了我们启示与教训,而这些也许是考察观照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