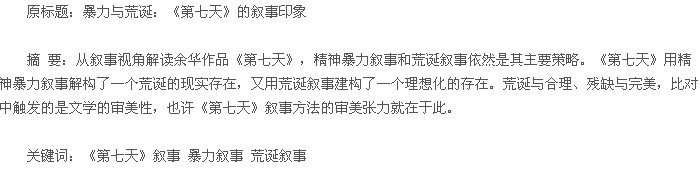
余华小说《第七天》讲述的是亡者杨飞从死后第一天到灵魂安息的第七天里所回忆和讲述的种种故事。这些故事似曾相识,或常见于报端、或频闻于广播电视,如强拆、豪华墓地、车祸、特权、卖肾等。 这些故事并无多少引人之处,更谈不上美感。 但读《第七天》还是感触颇多,一遍不够,两遍太少,其美妙还在于反复精读,好似玩家把玩玉石一般,集邮爱好者评品方寸邮票,细细琢磨后别有一番景象。 《第七天》的精彩之处不在于故事本身,或虚构、或夸大、或重述新闻,这也是《第七天》面世以来招致批评的主要原因,它的价值在于它为当下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做出一次很好的尝试,极力打造一个属于余华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一、用精神暴力叙事来解构荒诞的现实存在
精神暴力是一种软暴力、冷暴力,与叙事结合在一起, 主要是指文学创作的一种叙事技巧或叙事模式。
《第七天》中没有血腥场面,也没有打打杀杀,三个平凡人的爱情故事加上一连串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早已知晓或见怪不怪的事情,这些事情的确不怎么吸引人,但将这些事情汇集于一个文本中, 其给人们内心带来的压抑、沮丧、心痛、矛盾、想骂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强烈,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自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的人究竟怎么了?现在的社会究竟怎么了?……也许这正是《第七天》所要达到的目的。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余华选择的仍然是他最擅长的精神暴力叙事模式,或许余华已然认为这种叙事模式距离现实最近,最易触及人性的深处,或者最能表达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与物质二元分离所带来的痛楚。《第七天》中余华通过对小说人物杨金彪、杨飞、伍超三个普通人物爱情世界的残忍肢解和无情击碎,在叙述小说人物悲惨爱情世界的同时,敲打的却是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针砭抨击的是当下社会爱情的功利化、物质化和工具化倾向。
先来看一下杨金彪的故事。杨金彪是一个宅心仁厚的老实人,生活中的一次偶然,好心的他从铁轨上捡回并收养了从火车厕所下水道掉下来的婴儿———他的儿子杨飞,但从此爱情也就与他挥手拜拜了。 显然,杨金彪是余华笔下精神暴力叙事的对象,好人没有好报是残忍的道德故事,有悖常理,人们难以接受,难道社会道德与个人爱情不能兼而有之,难道道德之门打开,爱情之门就要被关上? 人们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来思考这个当下的道德难题。
与其父亲一样, 杨飞是一个坚守和忠实于爱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完美的,但家境很是一般。他的对象李青是一个外貌出众、 精明能干的事业型女人,李青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上充满美好,她相信爱情,不愿向功利化、工具化、物质化的爱情低头,她和杨飞就这样结合了。 但婚姻的发展并非喜剧,人们看到的是那个不愿向世俗低头的李青最终还是否定了自己,她与杨飞离婚后,嫁给了一位权高位重的官员,虽然李青在死后还没有从内心真正否定爱情不复存在,但纯粹的爱情在与世俗爱情的交手中败下阵来却是事实。杨飞和李青是余华笔下用精神暴力叙事的另一对小说人物,与杨金彪爱情故事叙述所不同的是,杨金彪的爱情故事还不是那么完整,最多是相亲、渴望爱情罢了,而杨飞的爱情故事却不同,他步入了婚姻殿堂,可见,在这则爱情故事里,余华采取了先建构、再解构,先喜剧、再悲喜剧的叙事安排,真是悲喜交加,人生难料,这样的安排对于读者心灵的冲击力也就自然不用多说了。
第三个爱情故事叙述的是伍超和鼠妹, 与杨飞、李青不同的是,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仔。 乡下人进城和进城的乡下人是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社会现象, 也是现实主义作家最喜欢的选题之一。 伍超和鼠妹身处繁华都市,却找不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处,他们住在防空洞,过着像老鼠一样的生活,鼠妹的别称代替了自己的名字刘梅,在城市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城市边缘人,现代科技文明同样吸引着他们,鼠妹想拥有一部漂亮的手机并不是她的错,伍超买不起正版苹果手机,给鼠妹买了一部山寨手机,也不是他的错,错在爱的评判标准被物质化了。
鼠妹知道伍超买给自己的手机是山寨的,并因此招致小姐妹的讥笑,她十分气愤,认为伍超用山寨手机搪塞自己,表明他并不爱自己,于是鼠妹从鹏飞大厦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为自己的爱情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当下社会物质已经成为检验爱情的唯一标准,爱她就要给她买宝马,爱她就要给她摘星星。伍超最终还是遵循了这个规则,将自己的肾卖了,买了一块墓地,或许他是要证明他是爱鼠妹的。 在伍超和鼠妹故事的叙事上, 余华选择了更加冷酷的方法,如果说杨金彪是代表小众,杨飞和李青代表的是城市青年,那么伍超和鼠妹则代表了浩浩荡荡的进城务工人群,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的精神生活无法实现农村与城市的跨越,进城务工人员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状况堪忧,他们陷入了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矛盾漩涡而无法自拔,让人读来颇感心酸和无奈,犹如伍超想到鼠妹的命运,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还是不出来好。 ”
三个爱情故事已经可以非常明显地让读者感觉到一个价值观扭曲、人文精神缺失的世界带给一群普通人的精神创痛是如此之大,“表面上看,余华的小说经历了从具有现代感的‘先锋小说’到温情的‘现实主义’的转型;就实质而言,余华将充满暴力感的生存真相作为小说主要元素的叙事策略并没有显着改变”,而在《第七天》的叙事中余华的策略依然如此。
二、用荒诞叙事来建构一个理想化的存在
存在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存在。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荒诞离奇之事按合理的逻辑本不该发生,但却发生了,合理的逻辑对这些荒诞离奇之事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依靠想象去解释。 想象的过程是不合理,甚至是荒诞的,鬼的世界不受人的世界的合理逻辑制约,因此,想象的翅膀就更加夸张了。 但想象的也并不是一定就不合理,荒诞的叙事在隐约中总可以让人触摸到那些合理的脉动。 《第七天》用精神暴力叙事的方法去解构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爱情逻辑,让人陷入了一个合情不合理、合理却不合情的怪圈。如何走出怪圈,接下来,余华借助荒诞叙事的方法建构了一个看似荒诞却是合情合理的存在,一种理想的存在,这种安排也符合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道理。在《第七天》中,这样的理想建构很多,下面仅列举两例加以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七天》中的“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被认为是对人最大的诅咒 ,与 “不得好死”差不多。 《第七天》却把它描绘成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理想化的世界应该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基督教宣传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曹禺笔下“那黄金铺地的地方”等,“死无葬身之地”与理想世界相提并论显得十分荒诞。如此这般余华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回顾漫长的人类发展史,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人们对幸福快乐和平等的追求就从未停息过,所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但生而不平等却是现实社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不平等带给一些人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痛苦,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楚,尊严和人格的不受尊重。 原来现实不是那么的完美,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即使是死后这个完美的平等能够实现也是快乐的事,于是就有了天堂等说法。 但当下的现实情况变得更糟了,生而平等做不到,死而平等也无法实现,特权、贫富已经延伸到殡仪馆和墓地,死后也有 “贵宾候烧区域和普通候烧区”、“一平米的墓地与一亩地以上的墓地”、“有墓地能安息与没有墓地的去死无葬身之地”之分。 当下人文空间不断被挤压,活着的现实世界充满荒诞,原本死后平等的世界也被现实的特权削去了一块,所剩的也只有“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块地方才有完美的平等了,“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 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用“死无葬身之地 ”建构了一个完美的平等世界 , 作者用诗词化语言来赞美它, 透露的是一种对荒诞现实存在的遗憾和无奈。 当下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已远超对精神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功利化了,爱便成了一种工具,亲情、爱情、友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一小再小。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天》中有关鼠妹前往“安息之地”的那段描写。几十个女性的骨骼为鼠妹净身,她们帮她缝制长裙,长裙精美得看上去像婚纱,她们用青草和野花为鼠妹覆盖身体,“于是我们看不见她的身体了,只看见青草在她身上生长,野花在她身上开放”。在鼠妹入殓时,那些在商场火灾中死亡的三十八个骨骼也来了,他们“一个个蹲下去用合拢双手的树叶之碗舀水后,又一个个站起来,依次走到鼠妹那里,依次将手中河水从头到脚洒向鼠妹身上的青草和野花”,入殓时的鼠妹闭上眼睛,平静得“像是进入睡梦般的安详”。
这段描写余华给了很多的笔墨,看似天方夜谭般的叙述却道出了人类道德的一个普世价值———爱是一个永恒主题。 爱有小爱和大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大爱,社会和谐是大爱,被物质和功利玷污了的爱已不再是爱,犹如苍老的骨骼所说:“那边的人知亲知疏,这里没有亲疏之分。 那边入殓时要由亲人净身,这里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每一个都要给她净身。 那边的人用碗舀水净身,我们这里双手合拢起来就是碗。 ”伍超将卖肾的钱为鼠妹买了墓地,于是鼠妹就有了安息之地,这是小爱,人类需要小爱,更需要大爱,这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孜孜追求的一首宏大的爱的交响曲,鼠妹听到了“夜莺般的歌声在四周盘旋,她在不知不觉里也哼唱起了婴儿们的歌声。鼠妹成为一个领唱者。她唱上一句,婴儿们跟上一句,她再唱上一句,婴儿们再跟上一句,领唱与合唱周而复始”。这段叙事在荒诞中透出的是普世真理,触发的是深深的反思, 当下社会处于变革的转型期,处于科技快速发展、 物质不断丰富的信息文明阶段,但物质正在侵蚀精神,亲情、友情和爱情倒退了,如果人们不再重视这些问题,这将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三、荒诞叙事与“真为美”的文学审美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创作方法的主线”,“真为美”也成为“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审视人生与社会现实”的写实主义创作思路和“人的文学”的文学审美观。
《第七天》是以荒诞叙事作为创作方法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似乎与“真为美”相距甚远。 这又如何理解呢? 《第七天》 封面上的一句话也许给出了答案:“与现实的荒诞相比, 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 ”言外之意就是说其实现实的存在本来就是荒诞离奇的,小说不过是用一种荒诞的写作方法把这种荒诞的现实存在再次呈现出来罢了。 因此,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荒诞叙事在本质上与“真为美”的文学审美观并非相悖,而是一致的,真如 1989 年余华所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
《第七天》沿袭余华一贯的小说个人主义创作方法,他似乎试图再次告诉人们,“荒诞的叙述,怪异的讲述才是接近真实的不二法门”。
伴随着文学价值观的转向,余华从先锋派创作转向现实主义创作,张新颖认为“从《兄弟》到《第七天》,其实是余华不断试探文学、文学传统、文学艺术与现实、个人之见的特别复杂的关系”,《第七天》可被视为余华对新写实文学的又一次有益的探索,《第七天》独特的叙事风格至少可以给人们以下三个启发。
一是荒诞与合理、残缺与完美是触发《第七天》文学审美性的两个开关。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荒诞变得更加荒诞,那也就成就了合理的更加合理;残缺变得俞是残缺,那也就塑造了完美的更加完美。 这种极左极右的叙事逻辑所触发的审美性也因极端的对比而显得愈加鲜明和愈加具有心灵的冲击力,平添了文学的感染力。 荒诞不经、不可思议、比拟、影射等都是暴力叙事和荒诞叙事常用的方法,也是实现以上审美逻辑的捷径,也许这也正是余华长期坚持如此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文学作品的张力源自小说情节、景物之外的“气、神、韵、境、味”,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是文学创作所要追求的意境和美感。 余华运用荒诞叙事方法,巧妙虚构、大胆想象、极尽扩张等,其所指在于增强《第七天》的文学感染力。
一部好的小说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犹如刘绪源所说,好文章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只有创作的内容与周围世界有所关联,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小说创作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 《第七天》在叙事技法上巧妙穿梭阴阳两界,交错融合现实与想象,文学的审美感由此产生,人们在小说中到了现实,但却不尽是现实,而是一种抽象;人们在小说中读到了虚幻,但却不尽是虚幻,而是一种心之向往。 《第七天》以亡者杨飞作为叙述者,回忆和呈现了一个个生前与死后的故事。杨飞犹如一位人类道德的审判者和发现者,唤醒的是深埋在人性深处的爱,无情抨击的是当下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无序和混乱,底层社会人群精神生活的缺失,那是一种生的痛、死的苦。《第七天》的文学审美价值就是在这种荒诞叙事的想象中,由心灵在瞬间自由实现了,“现实中人性的残缺在文学审美中得到了修复,现实中心灵的扭曲在文学审美中得到了匡正,现实中的麻木与冷漠在文学审美中得以复苏和温暖”。
社会转型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苦难人生在文学的审美中获得了片刻的心灵慰藉。
三是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当然也离不开精美的语言,虽然这是外在的,文本语言不仅要达意,而且要优美,这有助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以及文本与读者心灵的相互作用。 《第七天》文本语言甚是精美,这是余华创作的一贯风格。诗话般的遣词用语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如:开头“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结尾“他惊讶地向我转过身来,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向我询问。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再如“鼠妹在哭泣。哭声像是沥沥雨声,飘落在这里每一个的脸上和身上,仿佛是雨打芭蕉般的声音。鼠妹的哭声在二十七个婴儿夜莺般的歌声里跳跃出来……”“道路是广袤的原野, 望不到尽头的长, 望不到尽头的宽, 像我们头顶上的天空那样空旷”。语言精雕细琢,如诗如画,美妙至极,让人读之余情悠远,颇为享受。
参考文献
[1] 丁帆 . 中国新文学史 ( 下册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312,101.
[2] 何锡章,陈洁.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成因[J].天津社会科学,2010(5).
[3] 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
[4] 周明全.以荒诞击穿荒诞———评余华新作 “第七天 ”[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5] 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6] 童庆炳 . 文学理论新编 [M].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8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