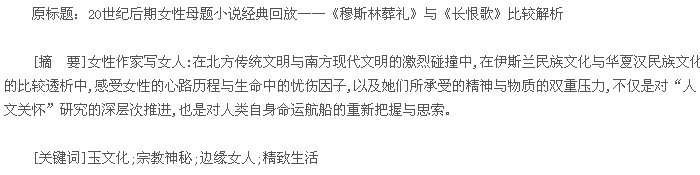
20世纪中后期,张洁、铁凝、舒亭、池莉、斯妤、韩小蕙、戴厚英、张抗抗等女性作家在女性母题的探索性写作过程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霍达、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凭借温婉如丝缠绵若水的语言和细腻似粉敏锐比针的情愫,非常精致地表现了对于女性母题的研究与关注。
一
霍达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高级编剧,她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葬礼》1987出版,1988年获“长篇小说顶尖级奖项”茅盾文学奖。一部作品面世之后,读者阅读文本之后产生的审美倾向肯定是多元的。而多元的审美倾向,恰恰是现代评论家对一部成功作品最起码也是最主要的肯定尺度。那么,霍达在这部小说中究竟抒写了怎样的人生境况和倾注了怎样的思想情绪呢?
尽管她说:“我无意在作品中阐发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我们仍然可以在字里行间阅读到作家对于伊斯兰民族生活的忧伤描绘和对于这种生活在心灵深处积淀的痛楚、神往与留恋。这也许就是作家要说的心里话中的一个主题。它是新时期文学,也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部成功地表现回族人民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具有其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此外,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对于“玉文化”的研究、对于宗教神性的探索、对于人伦理念的描绘等,从而构建了小说的多元性主题。这恐怕也是作家始料未及的。
尽管她说:“我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当中,它就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作家心灵之弦跳跃的脉痕。它宏观地回顾了中国境内穆斯林漫长而艰辛的跋涉足迹,深刻地揭示了回人在华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过程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人物在政治、宗教、商品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与追求,并展现了这个民族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世俗生活。小说具有52.7万字这样一个颇大篇幅,笔墨酣畅淋漓。
尽管她说:“我无意在作品中铺陈某一职业的特点,只是因为主人翁从事那样的职业,它就必然顽强地展示那些特点。”我们仍然不可避免的感受到“玉文化”的强大冲击力。“奇珍斋”斋主梁亦清,是第一代掌门人。这位掌门人,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玉器作坊的高级匠人。在雕琢玉器的行当中,他的技术出类拔萃。牢牢把握着玉质材料和玉器制作的精髓。
后来因为受到“汇远斋”斋主蒲寿昌的逼迫,不幸累死在制作精品玉器的条凳上,一口鲜血喷溅得四壁都是。韩子奇原名易扑拉欣,16岁时,随师傅吐罗耶定北上京城,与梁亦清一家巧遇。师傅走了,他却留了下来,是因为“玉文化”即玉器作坊对于这个少年的强烈吸引超越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宗教魅力。他被梁亦清夫妇收为养子,后来成为“奇珍斋”第二代掌门人。韩子奇在与蒲寿昌的接触中,认识了专做玉器生意的英国商人亨特。从亨特那里,他不仅知道买卖玉器作品可以赚取超过制作玉器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几千倍的高额利润,而且还熟悉了经营玉器生意的门径和具体的操作手段。在他手里,完成了从梁亦清时代的“制玉”到韩子奇时代的“贸玉”转变。他发了!
他不仅撑起了“奇珍斋”的家业,娶了梁亦清的大女儿梁君璧作老婆,而且,还收购了“博雅斋”斋主“玉魔老人”的全部珍藏。那里有北京城里许多玉器绝品。他,一跃成为“玉王”。他,因玉而对生命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他,因玉而对人生萌发了不可遏止的欲望;他,因玉而成名;他,因玉而步入了上流社会;他,因玉而流亡海外十年;他,因玉而使婚姻、爱情产生裂变;他,也因玉而被抄家被殴打被凌辱。他和他的一家似乎都是为了“玉”而活着。“玉文化”其实是中华大地精品文化之一。珍惜、保护、喜爱、研究它,其实就是在颂扬中华文明。对玉的赞歌,就是对我们民族性格中“竹可焚,不可改其节”、“玉可毁,不可改其洁”的优秀特征的真情表白与大力张扬。
尽管她说:“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儿‘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我们依然能够深切感受到从作品中渗透出来的宗教气息。韩子奇的师傅吐罗耶定对于伊斯兰教的深厚学养和无比执着的虔诚,曾经令梁亦清夫妇崇拜得五体投地。吐罗耶定从福建沿海北上中原进入京城之后,准备一步一步跨黄河,越祁连,穿吐鲁番,过大沙漠,经葱岭,抵中亚,达两河文明,万里跋涉,拜完世界闻名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的优秀经典。他宛若一位智者和预言家,洞察人生要义,对于生命具有独特的感悟。多么像乔治·桑笔下《莫普拉》中的乡村哲学家帕希昂斯、阿来笔下《尘埃落定》中藏传佛教的宣扬者翁波意西和陈忠实笔下《白鹿原》中的关中大儒朱先生。回人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中:“拉赫”即坟墓:穆斯林有试睡拉赫的隆重仪式,梁亦清去世由养子韩子奇试睡、韩新月离去由恋人楚雁潮和同父异母长兄韩天星两人试睡。那种神圣崇高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的做派,既表现了亲情的难舍,也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巨大魅力。没有丝毫杂念。灵魂升天,是多么伟大啊!作家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故事叙述中,给寻常读者带来的宗教神秘感,或多或少地也濡染上了些许“肉眼凡胎”难以辩识的“魔幻”意味,亦在情理之中。
尽管她说:“我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悬念’之类,只是因为这些人物一旦活起来,我就身不由己,我不干涉他们,只能按他们运行的轨迹前进。是他们主宰了我,而不是相反。必须真正理解“历史无情”四个字。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我们仍然能够轻易地在作品中寻找到“悬念”制作的痕迹。那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精巧运作,时时吸引着读者阅读的兴趣与好奇的探究。小说在叙述过程中设置了三大悬念,最后来了一个“文尾大揭秘”。一是韩新月生母之迷:为什么姑妈对于韩新月格外怜恤?为什么母亲梁君璧对于韩新月冰冷如霜?
为什么父亲韩子奇与母亲梁君璧十多年来分房而卧?这些都是因为韩子奇与梁冰玉流亡英国时期有过一段孽缘。而韩新月恰恰就是这段孽海情缘的结晶。1946年回国时,韩新月年方3岁,尚少不更事,以梁君璧为母。生母梁冰玉则只身返回英国,至1979年方才归来,那时,她已63岁;韩新月因风湿性心脏病(单纯二尖瓣狭窄伴有中等程度以上二尖瓣闭锁不全,不能手术治疗)已于16年前告别了人世,年仅20。阴阳阻隔,母女分离竟成永别。二是韩子奇民族身份之迷:梁君璧坚决阻止韩新月与楚雁潮恋爱关系的确定。最充分的理由就是两个人的民族不同。回人历来不与汉人结亲。无奈之际,韩子奇只得和盘托出自己的身世。他告诉梁君璧说,我本不是回人,却是个汉人。并问她,你可曾听我念过古兰经?你可曾见我做过祈祷?梁君璧如闻惊雷,歇斯底里地否认这一残酷现实。所谓的伊斯兰文化与华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恐怕没有比这对夫妻的特殊命运反映出来的事实更有说服力了。三是韩子奇耗尽毕生心血收藏的玉器珍品的结局之迷:躲过了20世纪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二次大战,却躲不过和平年代人为的破坏;炮火连天漂洋过海辗转异域都安然无恙,深藏密室却被“奇珍斋”原来的侯氏管家后代率人查抄罄尽。多少代多少人付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这是中华文明遭受浩劫的经典场景经典回放。
作家告诉读者:历史虽然残酷无情,然而历史必须真实。多元主题、民族色彩、职业特征、宗教神性和精巧构思,形成了这部小说的整体风格。
二
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30万字,1995年11月出版,2000年获“茅盾文学奖”。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王德威先生阅读文本之后认为:“王安忆细写一位女子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关系,历数十年而不悔,竟有一种神秘的悲剧气息。”
这是对小说的精确定位。
如果说《穆斯林葬礼》是“家”主题创作的又一次丰收,那么,《长恨歌》中的主人翁王琦瑶的“家”在哪里?王琦瑶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住到了同学蒋丽莉家中。作家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弱化主人翁“家”的概念。成年之后,王琦瑶先后与程先生、张秉良(李先生)、邬桥阿二、康明逊、萨莎、老克腊、长脚小沈等7个男人产生过情感纠葛,然而与每一个男人过招要么她的原因要么他的原因都没有家的感觉。居住在“爱丽丝公寓”享受十里洋场的繁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迅速荡尽。外婆故乡邬桥亦仅仅是人生的短暂过渡,目的是躲避政治风暴或阶级雷霆。“平安里”中的市井生涯,无论是遮蔽风雨的家还是寄售情感的家,都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况下,王琦瑶果然在这里不仅美人迟暮而且还“碧落黄泉”。显然,王安忆关注的不是“家”,而是“人”。一个女人。在一个“上海小姐”与一座城市的令人忧伤而叹息的哀惋故事中,写了一个悲剧结局的女人。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呢?
她的人生是一种“边缘人生”的经典展示——她是一个政治生活的局外人:她不属于任何党派,对于政治几乎是完完全全的“盲点”视角,任你如何洗头脑,唯我“独尊”王琦瑶。
她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夹缝中的小女人:从石库门弄堂的闺阁里袅袅婷婷走出来,18岁以后即凭借着上海姑娘特有的聪明与个性独立生存;生存很艰难,一点黄金、一块招牌(王琦瑶注射),是她的经济基础;她要应付意识形态方面给予她的不良定位,她要对付居家男女吵架时拿她开刷的利刃般的言辞,她还要周旋在母亲与女儿薇薇以及诸多男子的情感旋涡中,她更要面对并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现实世界,她真的很难。
她是一个没有爱情配偶的孤独女人:对于男人,程先生、阿二,她用情;萨莎,她用身;张秉良、康明逊、老克腊,她身心并用。然而,这六个男人没有一个始终伴在她的身边,更别说天长地久了。长脚小沈,她什么都没用,于是他就杀了她。就连唯一的女儿也随女婿小林到美利坚合众国陪读去了。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曲“长恨之歌”吗!
她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生存欲望,努力在现代都市中打拼属于自己那一块狭小领地作为生存空间的女人:一切都只能是指望自己。“王琦瑶注射”伴随她度过了后半生艰难岁月。她始终没有向生活屈服。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齐齐,典雅高贵,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喝下午茶、围炉夜话、四方大战、家庭舞会、过圣诞节等,都反映了王琦瑶的良好心态。生活中的审美取向,帮助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王琦瑶这个形象赐予读者的启示应该是:其一,对于生命的珍惜与坚持,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对于生命旅程中某些影响前程的偶然或必然情况的出现,要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努力承受,顺应时变,这是对一个人的人生定力的检验。其二,王琦瑶身上折射的上海文化精神的实质,应该具有的精确界定是:既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结合,也是东西方文明结合的现代都市的特殊文化蕴涵。这个精致的上海女人,在精致的上海过着精致的上海人的生活,最终却无可奈何地悄吟了一曲精致的上海生活走向没落的忧伤挽歌。其三,王琦瑶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却一层不变的神韵和气质,既是陈旧而典雅的传统,又是新鲜而俗气的时尚,在这个反映上海生活精髓的人物身上的结合;传统需要承接与涵养,时尚需要积淀与过滤。
既然王安忆被誉为海派文化的传人,既然《长恨歌》不为写家单为写人,那么我们阅读“王琦瑶”,就顺理成章地想到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曹七巧似乎有一个家,那是时隔久远早已淡忘了的关外少女时代的家。姜家,如丈夫姜季泽僵硬的躯体,冰冷;不是为了金钱,她一天也呆不下去。公婆丈夫死后分开单居的小家,也是没有爱情没有温暖,成日在毒品、麻将、死亡、争吵中苦熬岁月。因此,《金锁记》明是写家,实为写人。如同《长恨歌》一样,家是为人设置的。
王安忆写女性的温柔平和缠绵悱恻,是应该在冬日的阳台上捧着咖啡或红茶静静阅读,才能读出个中真味来的;张爱玲写女性的阴毒偏狭和冷酷贪吝,只配在盛夏的铁器作坊中扛着大榔头毛毛躁躁地瞅几眼也就可以了。
三
历史如长歌浩淼,家庭如音符呢喃,人生如诗篇悠扬,爱情如画卷璀璨,男女如日月行天,生活如江水缠绵,1945年出生的霍达与1954年出生的王安忆,在她们的作品中,对历史对生命对生活又是怎样描绘的呢?
其一,都是在历史变迁中塑造人物形象。将人物置于历史的剧烈动荡和社会的激烈矛盾中,完成性格铸造和命运的最后终结。《穆斯林葬礼》中的梁亦清、梁君璧、梁冰玉、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等主要人物,曾经先后经历了20世纪极为残酷的二次大战和建国前后风云动荡的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撕杀与呐喊;《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生活在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持续不停地进行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20世纪中后期。颠沛流离的游子生涯,突然变化的时代风云,陷于困顿的人生遭际,孜孜以求的生存状态,都显示了人物对于生命的坚韧与执着。
其二,都倾注了作家的人文主义关怀。在《穆斯林葬礼》和《长恨歌》的创作过程中,霍达和王安忆,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社会背景的直接而详尽的正面表述,坚持以人为本的写作思路。主人翁梁氏姐妹、韩氏父女与王琦瑶、蒋丽莉、吴佩珍的爱情、婚姻、家庭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韩子奇对于“玉文化”的守护与坚持,梁冰玉对于爱情的积极追求与一丝不苟的坚贞,韩新月对于理想人生与终身伴侣的向往,楚雁潮对于事业的磨砺与爱情的专一,王琦瑶对于生命航向的巧妙把握和超然姿态等,都是基于对生命的负责,基于对生命质量的努力探询。
其三,都是现代大都市中市井小人物生存状态的临摹。霍达和王安忆将淋漓的翰墨倾洒在都市的胡同或里弄中。寻常的百姓生活,平淡的世俗视角。
在吃、喝、拉、撒、睡当中揭示人物内心的爱恨情仇,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透露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结合,既是生活的奇遇,更是生活之必然。他们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从北平逃到英伦三岛。1936年到1946年,十年漂泊,十年孤寂。既有肉体原欲的本能饥渴,更有灵魂焦灼的急需慰藉。他们走到一起,是悲剧。然而,酿成悲剧的原因则是多元的。真的如“宝黛钗”一般,韩子奇与梁君璧只是婚姻,与梁冰玉却是真正的爱情?在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极为猛烈且政治气候极为严峻的形势下,王琦瑶、严师母、康明逊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萨莎四个人,却躲在挂着“王琦瑶注射”牌子的二楼小屋里,磨一点糯米珍珠丸、煎几块油榨麦面饼,烤几枚香甜焦黄红薯,还要在扁担长的俄式面包上切几片打打牙祭,然后再继续每天下午必修的娱乐活动:搓几圈象牙麻将牌。当然,门窗是必须关紧了的,桌子上是必须铺了厚毯子的,说话是必须悄悄的,抬臂举手打牌和牌是必须轻轻的。人生有许多种生存状态可供选择,大抵最常见者有两类:沉重如韩子奇父女们是一类,自得其乐如王琦瑶们是一类。短暂的生命究竟如何度过?霍、王两位女作家,凭借笔下的人物,似乎给了读者以某些有益的启示。
其四,都采用了平静简约的叙述方式。即便是夫妻别离,如梁君璧与韩子奇、王琦瑶与李先生;即便是情侣不再,如韩新月与楚雁潮、王琦瑶与康明逊;即便是繁华荡尽,如韩子奇作为一代“玉王”的落魄、王琦瑶从富人区“爱丽斯”公寓到穷人区“平安里”的角色转换;即便是生命永逝,如韩新月和李、程二先生等,虽则都是人类心灵难以承受却不得不承受的大起大落大苦大悲,然而,作家也是以纯客观的第三者的立场,平静地把故事叙述出来,简约而不赘疣,冷峻而不喜形于色,给读者以丰富的品位空间与想象余地,以及审美的多层次感觉。这是对读者阅读个性的尊重。
以上,我们从“历史背景”、“人文关怀”、“市井人物”、“叙述方式”等方面分别阐述了霍达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四个相同点,试图深入透析两位女性作家的意识流向与情感脉络。她们叙述了20世纪中国女性的生命里程。应该说,对于“女性母题”的关注与写作,才是她们最大的共同点,也正因如此,她们的文学创作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制高点。
[参 考 文 献]
霍达.穆斯林葬礼·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