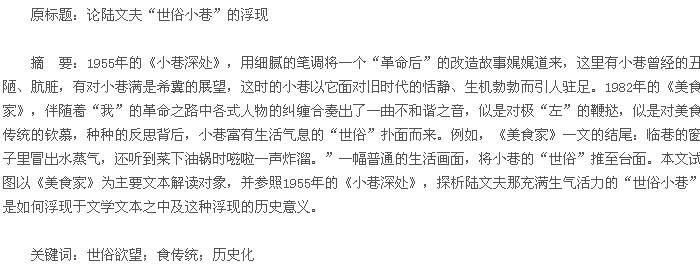
1 《美食家》中的多重叙事纠葛
陆文夫的作品倾向于采用多重对话结构,在矛盾纠葛中拎出问题《,美食家》亦不例外。阿二是朱自治的“包月”车夫,他的黄包车“有皮蓬,有喇叭,有脚踏的铜铃,冬春还有一条毡毯盖住坐车的膝头。漂亮的车子配漂亮的车夫,特别容易招揽生意。”
故阿二一家的生活还算是不错,除糟鹅和臭豆腐干外,老父亲还可以时不时地品口儿黄酒。作为车夫,阿二的最大愿望和最高理想是当司机,就算是拉着黄包车,也总是在停车的时候,摆出如“上海牌的小轿车戛然而止”的派头“,不减车速,而是突然夹紧车杠,上身向后一仰,嚓嚓掣动两步”。
对朱自治这个主顾偶尔的不满主要也停留在“那家伙坐车很挑剔,又要快,又怕颠。”上面。这是对生活容易满足的一批人,偶尔的抱怨只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正因为容易满足,生活也总是被凝缩在两道菜、几口黄酒、一家人、小巷、拉车这幅图景中“。我”为了“改造”朱自治而对车夫阿二开展了滔滔不绝的教育:苏联画报、汽车、拖拉机、洋房、沙发、收音机、伏特加。
这幅美丽的生活图景引导着阿二与主顾朱自治及顽固的老父亲的决裂,虽然有过物质的艰难,但生活亦为阿二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他自此之后摆脱了子承父业的黄包车夫的命运,而成了搬运站的基层工会的主席,“虽然没有当上司机,却也是司机的领导哩。”他的老父亲也自此对我刮目相看。虽然承诺依然遥远,阿二的父亲仍是那个坐在天井中喝黄酒的老头儿,但阿二的的确确相对于以前是“翻身”了。这是文本中关于阿二一家的叙述。
朱自治是旧时代的房屋资本家,没文化、没技术;不抽大烟不赌钱也不嫖。唯一的爱好便是吃。朱鸿兴的头汤面,阊门石路的茶楼,网罗苏州各种名小吃的晚饭。但他这一点却是让“我”由衷厌恶的,他对“我”的人生而言,是宛如幽灵般的存在。一方面缘于“我”这个“知道一点地理历史,自由平等,还读过三民主义”还懂一点尊严的人却是寄居于一个“馋痨坯”的篱下,还要承受他的各种使唤,穿梭于大街小巷去买各种下酒菜。霓虹灯下的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迫使我去参加革命;另一方面也缘于,新中国成立后不断的改造却始终未使朱自治改掉那个“贪吃”的毛病,甚至于他还是那活得最为潇洒的一群人,寻得了会做菜的孔碧霞,换着花样地享受各种美食,或者如“我”所言,闭居五十四号“,逃避改造”“。文革”后,百废待兴,古老的天堂,天堂里的苏州菜也等待着拯救。这个时候,朱自治被大家推到了台前,听他讲述关于苏州菜的绝技,但现实情况却是,朱自治始终只能是一个“清客”,他讲放盐的重要性,却不知放盐的绝技;他讲苏州菜的精致,却只能停留在今不如昔的感慨;甚至于在关于苏州菜的讲述中用了相当篇幅去描绘“姑娘唱小曲儿,卖白兰花,叫堂会等等”。对我来说,朱自治始终还是那个只会吃,只爱吃的“馋痨坯”。但“朱自治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个老专家,在十年浩劫中写了一本书,某某经历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小汽车接他去做报告,出两百块工资请他当顾问,他不去”各种巧妙的吹捧,使朱自治最终成了一个因“吃”成“家”的人——“美食家”。这是文本中关于朱自治的叙述。
这两套叙述的最后,阿二询问“我”这个曾经的引导者:“我家大男要结婚了,就在这个星期天。我想到你们店里订两桌酒席。”“我”自是用酒店的规矩拒绝了,但当领教过朱自治们吃的风采之后,回到阿二家,面对小外孙的选择巧克力而不要硬糖“,我”的情绪刹那崩溃“。我”似乎看到了无数了“美食家”正在“拔地而起”。文本于此结束,时间是1982年。
2 “食传统”对文本张力的弥合
文本中的“我”始终无法处理好人们对美好精致菜肴的渴求与“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像资本家那样唯利是图!”
之间的矛盾。正像我的老同学,“什么都懂”的丁大头所说的:“我只想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生理现象,那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资本家说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无产阶级尝了一口之后也跟着点头。他们有了钱以后,也想吃清炒虾仁了,可你却硬要把白菜炒肉丝塞在人家的嘴里,没有请你吃榔头总算是客气的!”
60年代的一些文本如《千万不要忘记》中,通过忆苦思甜和绘制美好蓝图的方式对世俗欲望进行引导,在“我”的推广大众菜的经历中,被证明是失去了效力。“我”甚至面临着“大众”们的唾骂,“说我们的饭店是名存实亡,饭菜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服务态度恶劣!”。
而与“我”推广“大众菜”的受挫相比,与此并行的是朱自治与孔碧霞的“鸳鸯双飞”。孔碧霞曾是一个国民党政客的姨太太,据说年轻时曾客串过《天女散花》“。孔碧霞数十年的风流生涯,都是在素手做羹汤中度过的。她丈夫的朋友都是政界、实业界、文化界的高雅得志之士……朱自治念念不忘的美食,在他们看起来仅仅是一种通俗食物而已。他们开创了苏州菜中的另一个体系,这体系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结晶,它把苏州名菜的丰富内容用一种极其淡雅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极尽雕琢之后使其反乎自然。”
而这种菜的另一面则是如杨中宝所忆“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苏州有一种堂子菜,是从高等妓院里兴起来的。做这种菜的全是聪敏漂亮的女人,连丑丫头都不许帮道,那做工细得像绣花似的。”
这是绵延于苏州这片天堂的“食传统”。
陆文夫面对前三十“吃的欲望”的被牵制所造成的混乱。
虽然在文本中直接表示“这吃的艺术怎么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呢,说得好听罢了,这发明权分明是属于朱自治和孔碧霞他们的。”但在文本中通过凸显了苏州的“食文化”去拯救并引导这种世俗欲望的安置,他提供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在这种折中下“,小巷子的上空难得有这么湛蓝,难得有白云成堆。
星期天来往的人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忙家务,家务之中吃为先,临巷的窗子里冒出水蒸气,还听到菜下油锅时嗞啦一声炸溜。”在略显抒情的笔调中,生活气息浓厚的“小巷深处”向我们款款走来。
3 “小巷深处”世俗的历史化探寻
回看1955年的《小巷深处》,这个文本较之1982年的《美食家》,显得相对和谐《。小巷深处》讲述的是关于“妓女改造”的故事“,妓女”重新被纳入新的国家秩序中去,徐文霞、张俊、朱国魂,各自的形象指向及作者的面对不同人物所持有的立场都较为鲜明。这个“小巷深处”的故事的相对和谐建立在对曾经的“小巷深处”的“传统”的挞伐上。那里“是秋雨湿漉的黄昏,是寒风凛冽的冬夜吧,阊门外那些旅馆旁的马路上、屋角边、弄堂口,游荡着一些妖艳的妇女。她们像幽灵似的移动,有的像喝醉酒似的依在电线木杆上,嘴角上随便地叼着烟卷,双手交叉在胸前,故意把乳房隆起。”
在创作于1982年的文本中《,美食家》选用的是“小巷深处”的另一种传统,孔碧霞与朱自治的幽灵般的传统。借用《1985:延伸与转折》在讲述“文化热”及寻根思潮时所说的一句话: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作用,以及来自于‘现代性’的复杂的需要,才会出现对于‘传统’的不同的虚构方式。”
如果说《小巷深处》对“小巷”曾经的黑暗的强调是为了结构徐文霞的“光明前景”;则陆文夫选择在《美食家》这个文本中凸显“食文化”这个老苏州传统,通过这个传统中的“食”的书写,引导着五六十年代诸多文学中被鞭挞的世俗欲望的安置,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动乱过后历史的重新书写。
陆文夫的创作曾被归为“市井小说”,而“市井小说”如汪曾祺所言:“‘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
‘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民’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
这个术语的启用,使我们看到在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及“文革”之后,异于50、60年代将人与一定的阶级相联系,文学开始将笔触转向悲喜交加的世俗生活,命运的无常,凡俗的人生百态。陆文夫的《美食家》等诸多作品通过这些饮食男女的书写打开着文学写作的世俗空间,在脱离十七年文学成规,建构新时代的新文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4 结语
浮现之后的困窘,如果说1955年的“小巷”更多地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了一种命运及政权的新生,则1982年的“小巷”则将我们的眼光引向了“小巷深处”庸常的岁月。选取某一对象作为文学的表达与作者的诉求,有着当时当地的现实背景。从1955年的“小巷”到1982年的“小巷”,历史的风云在此浓缩。同时,我们也无法忽视在《美食家》中,陆文夫有着对世俗欲望被打开的困窘,就如文本中“我”无法反驳的烦恼:那个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劳动”的朱自治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欲望,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其最大特性是永远追求满足。”
欲望被打开的同时,历史也面对着欲望的反噬。在这方面,陆文夫是清楚的,从十七年文学到80年代文学的转换中,这也是诸多作家纠结的难题。当世俗小巷被呈现纸面,当世俗空间不断地被开拓,在文学不断地被建构中,如何引导世俗的安置,始终会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陆文夫 . 小巷人物志(第一集)[M]. 北京:中国文艺联 合 出 版 社,1984:278,201,192,262,210,228,223,218,221,12。
[2]尹昌龙 .1985:延伸与转折[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39.
[3]杨德华 . 市井小说选·序[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4]程文超 . 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