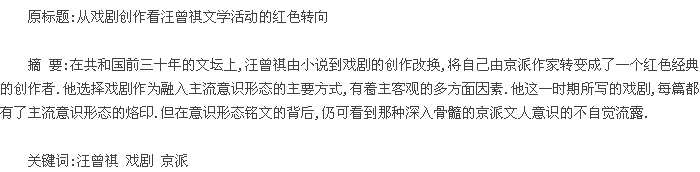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具个性的作家,汪曾祺向来以小说闻名.早在 1940 年代,他便发表过《鸡鸭名家》等小说,出版过短篇集《邂逅集》.1980 年代,他又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名篇.作为京派大师沈从文的"得意高足",他有"京派殿军"或"最后一个京派文人"的美誉.但小说名家的背后,汪曾祺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戏剧创作家.在 1949 年到 1979 年的近三十年间,汪曾祺的主要文学活动是戏剧而不是小说①.虽然公开发表且署名汪曾祺的戏剧只有《范进中举》(1955)、《小翠》(1963)、《雪花飘》(1966)和《沙家浜》(1970)四部,但作为北京京剧院的专职编剧,他一直在参与许多红色经典戏剧的创作,如《山城旭日》、《红岩》、《杜鹃山》、《决裂》等.他参与创作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曾风靡一时,并让他跻身当时为数不多的主流作家的行列.这就是说,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坛上,汪曾祺的创作由小说到戏剧的改换,将自己由非左翼的京派作家转变成了一个红色经典的创作者.这是一个跨度不小的转变,因为京派向来强调文学与政治的距离,而红色文学却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值得探讨的是:汪曾祺的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的转变在戏剧创作中又有哪些具体表现? 他是否真的完全弃绝了自己京派文人的风格?
一
1949 年 7 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这次大会,提出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文艺必须像解放区文学那样,坚持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确立了基本的意识形态规范.在此政治文化背景下,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负盛名,但又没有像胡适、梁实秋等人那样离开大陆,而是决意与左翼知识分子"一起走进新时代"的非左翼作家就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改变以往的创作风格,认可并接受新的文艺规范,积极写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要求的作品;要么主动搁笔,转行从事其它的工作.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作家选择了前者.如巴金、老舍、李劼人、曹禺等人,甚至连海派出身的张爱玲也曾试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写下了《小艾》、《色戒》等带有"革命"色彩的小说.后者以沈从文最为有名,他主动放下文笔,一头扎进文物研究,最后变成了一名着名的服饰史专家.
作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沈从文的"沉默"有着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着历史恩怨的纠葛.在1930、1940 年代,自视超然和独立的沈从文与"左"、"右"文坛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对他们都曾进行过批评.因此,在 1948 年郭沫若的《斥反动文人》中,沈从文被当做了反动文人的代表.全国解放后,沈从文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与新时代的距离,因而选择了搁笔.与沈从文不同,作为学生的汪曾祺虽然已小有名气,但"毕竟年纪轻、创作经历以及创作影响均与沈先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没有想到搁笔,但对自己不长的创作经历也作了认真的回顾.这使他朦朦胧胧地觉得,在未来的新时代,手中的笔不能放下,却也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写"[1](P80).汪曾祺明白,再不能写他以前所熟悉的生活,不能用小桥流水式的文笔吟诵他的田园牧歌了,如果要写,就必须按新的意识形态要求来写.但是,究竟该怎么写,汪曾祺显然也感到了困惑:"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又似乎不太符合新时代的需要.还有,他不愿意、也不擅长写那些符合政治中心要求、却无法体现创作个性的作品"[1](P80).
想改变却不知如何改变的困惑,一直纠结着汪曾祺.从 1949 年以来,他都处于这种纠结和徘徊之中,基本没有任何文学创作.1954 年,在当时《说说唱唱》编辑部领导的鼓励下,借着北京市纪念文化名人吴敬梓逝世 200 周年活动的契机,才改编了一部戏剧《范进中举》,1955 年发表于《剧本》.这是汪曾祺生平所写的第一个剧本,却意外获得 1956 年北京市戏剧调演剧本一等奖.自此以后,他似乎在戏剧创作中找到了摆脱困境的途径.然而受到主流话语认可不久,却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中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农村.1962 年,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进入北京京剧院任专职编剧,接手参与并主笔改编沪剧《芦荡火种》.1964 年,京剧《芦荡火种》公演获得巨大成功,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亲自提点.其间汪曾祺又改编《小翠》、《雪花飘》等剧本."文革"开始后,汪曾祺因为有右派"前科",在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再次被剥夺创作权利.一年以后,江青为了把持京剧创作战线,想起汪曾祺的才华,特批其"解放"并"控制使用".直到文革结束,汪曾祺一直在这种被控制的状态下参与红色经典戏剧的创作,其时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汪曾祺选择戏剧作为他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个人小说之路的受阻.汪曾祺擅长写旧社会的平凡生活和小人物,常常对即将逝去的某种文化表示淡淡的忧伤,但新的环境并不欢迎这种怀旧笔调,他必须寻找新的生活体验,改换新的写作方式.他曾想深入军旅生活,最终却"半途而废".而且,即便有新的小说素材,一旦落笔也很可能是自己早已习惯了的缓缓抒情的调子,根本写不出刚劲的文字.因此,最好放弃小说,从其他文类中去寻找方向.其次,戏剧是当时的强势文体.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戏剧因其受众面广、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一直受到重视.1942年 10 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亲自题词"推陈出新".在解放区,《兄妹开荒》、《白毛女》和《逼上梁山》等戏剧红极一时,对鼓舞工农兵士气起过重要作用.戏剧俨然成为最具政治动员能力,因而也是最为强势的文学体类.1949 年以后,戏剧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国家领导人一直十分重视戏剧工作,多次举行全国性的戏剧汇演活动,鼓励剧作家们的创作.在此背景下,自小受戏曲文化熏陶,喜爱看戏曲表演,并且曾经跟着父亲学唱过青衣、小生、须生,求学期间还亲自上台参演过话剧与昆曲的汪曾祺,走向戏剧创作之路并将其作为靠近主流话语的方式,也就自然而然了.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曾精辟地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2](P98 -110).纵观汪曾祺的戏剧创作之路,不难发现,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被意识形态"招募"的对象.当他放弃自己的小说写作,而致力于戏剧这种当时的强势文类创作时,他就由一个独立的个体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主体.
二
1949 年后的中国戏剧大体可分为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古代戏三种类型,"传统戏一般是指 1949年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编演流传的戏曲剧目……现代戏指当代作者创作的反映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以现实生活题材为内容的戏曲剧目.新编古代戏,则包括描写历史上的古代人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其他古代生活题材为内容的剧目"[3](P39 - 40).对新时代的现代戏,汪曾祺虽有兴趣,却一直没有充分的生活积累.因此,他的戏剧创作只能走改编的路子.《范进中举》改编自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节,《小翠》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雪花飘》是对浩然同名小说的改编,而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则是在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改编是在他人作品基础上的重新创造,不仅会打上改编者的个人印记,更会刻上改编者所处年代的意识形态"铭文"---即社会意识形态"'篆刻'/书写在每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化文本之中"的标记[4](P189).作为一种向主流意识形态自觉靠拢的话语实践,汪曾祺戏剧创作中的这种意识形态"铭文",也来得格外明显.
与小说原着相比,汪曾祺在戏剧《范进中举》中,新添了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一是范进的三个"同案":魏好古、卜修文和费学礼;二是范进的邻居---"关清"和"顾白"、饭店店家和摆渡的艄翁.前者是与范进同一类型的所谓"士",从名字中就可看出他们的可怜和可笑:"未好古"、"不修文"和"废学礼".
他们在剧中充当着范进的陪衬与补充,媚高耻低,丑态百出.这种设置让范进不再是所谓"士"中的个案,而成为整个"士"阶层的代表.与这个阶层相对立的是范进的邻居们,一些大字不识、靠自己力气过活的老百姓.在范进、魏好古这类虚伪、脱离实际的"士"面前,他们显得熠熠生辉."当听到胡屠训导范进不要与'这些种田的、拾粪的'平头百姓平起平坐时,他们便起身告辞,而且从那以后到出去参加乡试之前就没有踏进范家"[5],而得知范进没有路费时,他们却卖了自家过年的猪为其筹了一两二钱,还高歌"回家打扫空猪圈,不吃猪肉也过年".店家和艄翁也是热心肠之人:"半个窝窝,甭谢啦"、"都是喝一条河里的水的人,说什么肯与不肯".
不过,"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6].汪曾祺在范进身边添加的这两类人物,显然是按照剧本写作年代流行的阶级理论框架设置的.前者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后者则代表了劳动人民.汪曾祺写《范进中举》的 1955 年,正是新中国进行三大改造的关键年头,全国人民正以无限的热情参与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原理对各行各业以及各行各业中的人予以重新分类和重新组织的过程.知识分子"因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7],因此在运动中,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就此而言,对之展开一定程度的嘲讽和批判也就理所当然.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基于阶级原理而对知识分子软弱性、虚伪性的讽刺就已开始.作为从国统区出来的京派作家,汪曾祺一开始未必就熟悉这套做法,而此时他能按主流话语的要求,塑造范进们这类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展开批判,自然是努力自我改造的表现.批判的另一面是赞颂,他对范进邻居们的竭力刻画,显然是对普通劳动者的热情歌颂.与范进们的道貌岸然和手无缚鸡之力相比,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白发满头筋力健,只因平生未读书".这显然是汪曾祺按照时代要求而做出的"创造"---因为清朝的吴敬梓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这说明几年的纠结之后,作者已站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高度.于是这个剧本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获得了剧本一等奖.
汪曾祺喜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曾对其中几个经典故事进行改编.但抒情喜剧《小翠》是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用戏剧形式改编的.他删掉原着中替母报恩、五年夙缘等封建说教,而着眼于突出小翠的善良天真、知恩图报和智谋过人.尽管这部戏剧在政治上没有太多说教的东西,也未受到重视,而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排演,但他所采用的改编方式,却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打扫灰尘"、"去芜存精"、"脱胎换骨".而且,剧中情节的曲折,人物的机智勇敢等,和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英雄传奇也非常接近.这些显示出主流文艺规范对汪曾祺戏剧叙事的影响.《雪花飘》改编对象的选择本身便体现出汪曾祺时代意识的增强.剧作通过电话接线员陈大爷的故事,塑造了陈大爷、陈大妈、小红等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互帮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
如果说《范进中举》和《小翠》只是对古代小说的局部改编,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表达尚属委婉曲折,那《雪花飘》的改编则表现出对准现实题材,创造真正红色剧作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京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那里,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呈现.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了这部剧作,在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中,几易其稿."对于一部文本范例,重要的不是它讲述了什么,而是它如何讲述,以及它巧妙地有意识的省略"[8].剧本按照当时通行的规则,隐藏了人性中某些本我和小我的因素,如爱情以及家庭生活.剧中正面人物的家庭都是不完整的,春来茶馆只有智勇双全的老板娘阿庆嫂,阿庆却不知所踪,沙四龙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在"武装斗争必须领导地下斗争"的要求下,汪曾祺给代表武装斗争的新四军指导员和十八个伤病员增加大段唱词,而减少了代表地下斗争的阿庆嫂的部分唱词,并将故事结尾由阿庆嫂带着新四军趁乱大闹胡传魁婚礼,变成由郭建光带领新四军从正面攻打伪军.经过这些修改,《沙家浜》最终成为体现"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主题,以及"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的京剧样板,汪曾祺本人也由此真正完成了从京派小说家向红色经典创作者的身份转型.
有论者指出,"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9](P298)汪曾祺从《范进中举》到《小翠》,再到《雪花飘》和《沙家浜》的戏剧创作历程,就显现出这种由于时代发生变动而导致的作家"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这种转变在汪曾祺 1961 年底到 1962 年间曾昙花一现的小说写作过程中,亦体现得极为明显.这期间他一口气写了三个短篇:《羊舍一夕》、《看水》和《王全》,不仅改变了他以往小说的文风,而且以表达"个体进入集体秩序,成长为历史主体"[10](P115)为主题,连郭沫若都惊叹不已:"汪曾祺变了".
三
布封说,风格即人.作家的文学风格确实有如作家本人,一方面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显现出时代差异性,但另一方面,某些根本性的个性特征也仍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不难理解,由于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汪曾祺以戏剧作为最主要的文学活动,并尽力由京派风格向红色文学转向,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但同样不难理解的是,就在他有意识地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过程中,作为京派文人的那种个性和风格,也会不自觉或者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因为他以而立之年进入"新时代",此前已进行过近十年的文学创作,对世界的看法、人生的态度已经基本稳定,京派作家独有的那种文人情怀和审美意识也早已深入骨髓,不可能因外力的介入而彻底改变.
这种深入骨髓的京派文人情怀,首先表现在汪曾祺对政治所保持的那份欲迎还拒的心态上.虽然曾被江青特批"解放"而进入"样板团",甚至作为唯一一个文人身份的"革命文艺战士"(其他都是演员)上过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但汪曾祺从来都只是一个文人.他一直"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11].被打成过"右派"并在农村下放了四年,在"文革"中第一批被揪出来并关进小楼.所谓"解放"后也一直被"控制使用",就连"改编《沙家浜》这一事件,也充斥着地方政治利益的博弈"[12],让他苦不堪言."四人帮"倒台后还因为曾经的"辉煌"被审查了两年.也就是说,他的命运是随着新中国的各种运动而跌宕起伏的,而在这些运动中,他从来都是被动地接受,作为客体而在政治漩涡的边缘处求生.因此,尽管他写了一些红色文学剧本,但他并没有在心理上完全转变为惟政治是尚的红色作家,在内心深处,他是不愿和政治走得太近的.
在他这一时期所写的红色文学剧本中,也留下了其京派文人风格的印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汪曾祺对文学性始终有着执着的追求.即便在戏剧这种偏向于大众化的艺术门类里,他也强调:"决定一个剧种的兴衰的,首先是它的文学性,而不是唱念做打"[13](P179).他延续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注重抒情、诗情的路子,强调"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14](P206),并将之植入他的红色文学剧本中.
例如《范进中举》中,范进发疯后的那段唱词:"小河流水清悠悠.水中游鱼来了,小鱼儿摆尾水面皱,香饵空垂不上钩.一只蝴蝶飞来了,蝴蝶儿双双分前后,因风飞过树梢头,黄莺儿枝头来求友."虽然是疯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清悠悠的河水,微澜的水面,蝴蝶儿飞飞,黄莺儿欢鸣"这样的意境却也清新可爱、诗意盎然.这段话在演出时被演员(当时的四大须生之一---奚伯啸)改成了抨击封建科举制度的愤慨之语:"考得你昼夜把心血耗,考得你大好青春等闲,考得你不分苗和草,考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考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考得你弓背又驼腰,年年考来月月考,活活考死你命一条!"这个改变虽然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包袱"迭起,更能赢得观众的喝彩,却也失了汪本那种诗情画意.
京剧《沙家浜》中的《智斗》、《授计》几场,也都是汪曾祺独具匠心,发挥自己文人才华的成果.阿庆嫂那段着名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就化用了苏轼的《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唱词朗朗上口,还有浓郁的古典气息.《转移》一场中,郭建光的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也是汪曾祺尽显才华之处.尽管这段词是在迎合江青的政治意图(其时,要求由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必须突出郭建光的形象,增加其戏份)下添加的,却也添得自然而有富有诗意.朝霞、湖水,芦花飘扬、岸柳成行,苏南沙家浜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这里用的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用的即景抒情手法,通过眼前的美好风光,抒发个人抗敌救民、早上战场的急切心情.
此外,对古朴的人情美、自然美的回忆与美化,对理想的人性美的挖掘和表现,是汪曾祺等京派文人的一贯追求.而这也被汪曾祺成功地化用到了他的剧本写作之中:《范进中举中》的关清、顾白、艄翁和店家等,不计报酬地对邻居、落魄之人施以帮助.《小翠》中的狐仙小翠知恩图报,胜过人间的虚伪奸诈与以怨报德,王元丰虽然痴呆却保存了天然的真情与善良.《雪花飘》中的陈大爷、陈大妈和小红等互帮互爱、其乐融融.《沙家浜》里的军民一家亲、同舟共济.不管故事中有多少阶级化的投影,情节中有多少阶级矛盾的对立,以及主题上有多少政治概念的图解,但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却与汪曾祺 1949 年前的小说当然也是整个京派作家对美好人性的珍惜与赞美是一脉相承的.
从汪曾祺的一生来看,他的红色转向只是其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他很快便恢复了自己京派文人的底色,再次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京派风格的小说.他虽然还在京剧院做编剧,仍然坚持戏剧创作,且基本上还是从古代戏剧文学或历史中寻找灵感进行戏曲改编,他不必受意识形态的过多牵制,作品体现出了更多的个性.《一匹布》歌颂自由的爱情,《一捧雪》对我们自古以来的奴性心理进行了反思,《大劈棺》则深入知识分子内心、揭示人性欲望与超我道德之间的斗争与调和.1980 年代中期以后,汪曾祺在《裘盛戎》和《讲用》中,还分别从知识分子(戏剧界的精英)和普通人民两个角度对"文革"十年"左"的政策进行过批判与讽刺.这标志着汪曾祺在心理上对其红色剧作生涯的彻底告别,以及一个新的生命阶段的开始.
参考文献:
[1]陆建华. 汪曾祺是春夏秋冬[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路易·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 李迅译. 当代电影,1987(03) .
[3]王安葵、余从. 中国当代戏曲史[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4]戴锦华. 电影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柯玲. 梅开二度香飘千秋---谈汪曾祺对《范进中举》的改编[J]. 艺术百家,2003(03) .
[6]布里恩·安德森.《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J]. 戴锦华译. 当代电影,1990(03) .
[7]王素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变---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背景[J]中共党史研究,2008(04).
[8]戴锦华.《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J]. 当代电影,1990(03) .
[9]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0]杨红莉. 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汪朗. 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J]. 读书文摘,2012(10) .
[12]刘阳扬. 汪曾祺改编《沙家浜》的背后-透视当代文艺中地方权力的政治博弈[J]. 当代作家评论,2013(03).
[13]汪曾祺.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汪曾祺说戏[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14]汪曾祺. 小说笔谈[A]. 汪曾祺全集( 第 3 卷) [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