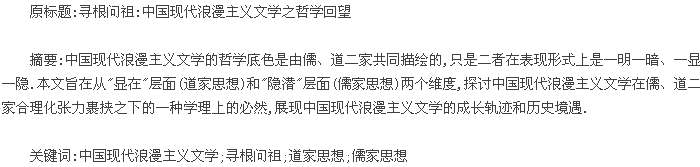
歌德曾在《浮士德》中感叹:
今天发生的一切
都无非是
祖先盛世的
凄凉的余响
这样的叹息难免令人伤感,而美国学者李维在《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中的说法,是以另一种客观姿态诠释了同样的感慨:"所有的文化,都是萦绕于对先前黄金时代的回忆. "[1]的确,远古历史时空中的原生态文明,无不凝结着人们对整个文化童年深情款款的记忆情结,它曾经真实而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遥远年代, 虽然智慧之鸿蒙未辟,却依然无法遏止后人的频频回望,它仿佛一个古老而安详的梦境,从更沉潜的人类学心理原型角度来看待,它更是一抹镌刻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深邃烙印,无法磨灭、不可或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沃土壤中,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交融碰撞,对中国文艺风尚和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铸就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 因此,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背景和哲学渊源,面向儒、道二家的"寻根问祖"将是一条难以回避的路径,但是儒、道二家在诸多价值观念上的迥异甚至相互抵牾,使得人们往往将之置于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模式之中. 但事实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底色是由儒、 道二家共同描绘的,只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是一明一暗、 一显一隐,本文旨在从"显在"层面(道家思想)和"隐潜"层面(儒家思想)两个维度,探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儒、道二家合理化张力裹挟之下的一种学理上的必然,展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历史境遇.
一、显在的嫡脉之源:道家思想观念
从浪漫主义诗学本体论和思想价值论角度考量,老庄道家的文化哲学显然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精神遗存:一方面是老子之"道"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另一方面是庄子之"道"作为一种带有主观倾向的心灵诗学[2],两方面的糅合与锤炼,构成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母题和基因底蕴.
1、个体自由的生命状态道家文化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是 "道",《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即世上万物万象都是由"道"而生,"道"是万物之根源. 老子认为,世界的一切运转都在冥冥之中有"道"支配,为此一切都要任其自由、顺其自然,任何人为的结果只会违反"道"的本原,这奠定了道家哲学本体论的基础. 而在庄子的笔下,"道"更多表现为对个体生命和心灵诗学的关注,成为一种至上的人生理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是天人合一、顺任自由、保持天性,自在逍遥于天地之间. 《逍遥游》的"游" 正是庄子对至高自由人格精神的寄托---"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在"无何有之乡"这个理想乌托邦中,个体因"无所待"而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自由和谐的精神家园.
这一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价值观,正是中国现代浪漫作家所崇尚的精神之一. "五四"文坛上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诸子,以"狂飙"式的浪漫风格受到瞩目,他们时常表现出对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亲睦契合. 郭沫若曾忆及少年时代时说,"我特别喜欢 《庄子》"[4]、"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 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5],道家文化精髓激发了郭沫若崇尚自由奔放的天性, 并为他后来哲思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点,随着郭沫若世界观的成熟,他逐渐将道家思想与斯宾诺莎学说相互参证、糅合、熔铸,最后建立了"泛神论"哲学体系,并强调"我在思想上向着泛神论,是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6]
在郭沫若的泛神论观念中,"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7],即自我便是神,自我能超越一切,这正是建立在道家追求"天人合一"、个体自由的思想基石之上. 在青年郭沫若笔下的《天狗》中,塑造了一个自我意识充塞宇宙天地、 迸发无穷情感、疾呼解放的天狗形象---"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面对大自然波澜壮阔的景观,发出了对自由生命真谛的呼号:"啊啊! /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在《凤凰涅盘》中,诗人借凤凰之口,质问黑暗恶俗的现实,批判压制个体自由的世俗世界---"啊啊! /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 宇宙,/ 我要努力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的屠场呀! /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 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 /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其实,郭沫若的独特并不在于他写就的一系列现代新诗,而在于他在继承道家思想前提下所开创的一种新精神---放任自由、 个性独立、身心解放---充溢着浪漫主义的现代性精髓.
2、抗争世俗的叛逆精神
庄子思想体系中对世俗人伦、 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批判和抵制,是道家文化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庄子认为,一切世俗权威都是对自由精神的禁锢、对生命本真的戕害,他对俗世伦常的否定、蔑视与鄙弃,一方面是通过"神人"、"圣人"、"真人"、"至人"的道家理想人格予以反面映衬,所谓"(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礡万物以为一, 世蕲乎乱, 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逍遥游》),"(圣人)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真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 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大宗师》),"(至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 另一方面则是正面抨击儒家传统道德和世俗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潜在摧残,庄子甚至直接向"仁义礼智"、尧、舜、禹、孔子等提出非议和挑战---"夫仁义憯然乃愦吾心, 乱莫大焉"(《天运》),"毁道德以为仁义, 圣人之过也"(《马蹄》)---足见庄子生命诗学中尊个体、非世俗、反权威意识的彻底性,而在"五四"时代应运而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又实现了这一文化灵魂的复活.
"五四" 是一个积极抗争世俗、 反叛传统儒教、高扬个人觉醒的时代,叛逆精神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尚,人们努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造就的蒙昧"(康德语)[8],更彻底地否定世俗纲常,更自觉地推崇自由解放和个性独立,处处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辉, 更流淌着道家精神的余温. "创造社"中坚人物郁达夫在早年《沉沦》时期的放浪率性和离经叛道,便熔铸着传统的道家精神和现代的浪漫情怀, 小说大胆表露的个体意识,连同狂热的欲望躁动、畸态的心灵感受和扭曲的情感意志,一并激烈地坦陈着对人性解放的渴望,虽然赤裸裸地书写个人的欲望、丑恶与罪孽,却并不因此卑微狎琐,反而获得了一种悲壮和崇高的美感,因为他在对人性隐秘世界的挖掘中揭露了世俗道德戒律的虚妄,凸显了人与世俗抗争的超拔勇气,这一可贵的叛逆精神为郁达夫赢得了"浪漫才子"的美誉. 另一方面,青年郁达夫在行为方式上更带有鲜明的"才子气",有一股与道家精神密切关联的"魏晋名士"之气,他曾写道:"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 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之列,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 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 "[9]魏晋名士的高洁、放浪和颓唐,陶渊明的隐逸率真之气,以及清代诗人黄仲则"野性束缚难为堪"的精神,都曾深深镌刻在郁达夫的情感、 生活和创作之中,无论是其"论才不让相如步"的卓绝才华,还是"二分轻薄一分狂"的狂狷性情,乃至他的嗜酒、狎艳和漂泊,无不传承着道家孤高狂放、愤世嫉俗和恃才傲物的风尚.
3、 对抗异化的自然人性
早在中国文明的发轫期,庄子便以一种先验的智慧审视着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他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反抗异化"思想的哲人[10].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分崩离析、淳朴民风沦丧殆尽,物质文明以一种急遽发展的姿态,遮蔽了人们的清醒和忧虑,它带来名利、财富和繁荣的同时,还裹挟着人性之恶---自私、享乐、贪欲、野心、侵掠等等---的膨胀, 庄子从人性本体思辨观出发, 犀利揭露人因物质功利而泯灭自然天性、丧失真实本性、扭曲生命价值的异化现象,大声疾呼"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丧己"、"不以物易性"(《齐物论》),呼吁人们摆脱人为物役、心为物役的困境,以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人间世》),倡导人重拾自然本性,重回精神家园.
历史总在轮回中前进. 庄子"反抗异化"的文明批判,在现代浪漫主义价值观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认和开掘, 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思维起点上,便非常重视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的反思批判,并引申出浪漫主义精神对个体乃至整体人类的精神救赎的意义.20 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 中揭示西方现代文明酿成的 "至伪偏至"、"性灵之光,愈益黯淡",即一方面是物欲的膨胀("物质也"),另一方面是个性的泯灭("众数也"),他高呼"精神界之战士",务求打破"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的失衡状态,这既是对西方现代浪漫主义精神的认同,更是对中国传统道家"反抗异化"观念的呼应. 但正如庄子在"人的异化"观念上的超前性,鲁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他一系列浪漫文论中的对现代文明和"人的异化"关系的探讨,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作家的普遍关注和创作上的呼应. 时至 20 世纪 40 年代,自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浪漫派"[11]的沈从文,对于人性、现代文明、个体生命的倾心关照和反思,才暗自契合了道家"反抗异化"的思想. 在沈从文的浪漫叙事中,无论是对"文明枷锁"束缚下都市人性的解剖嘲讽,还是对未经现代文明"侵蚀"的湘西边陲的礼赞,无不渗透出对健康人性的孜孜追求和对现代文明的灼灼焦虑. 在《八骏图》都市文化圈中, 沈从文勾勒出一群表面温文尔雅的学究人物,他们已在繁缛华丽的都市中迷失自我,被庸俗的名利、欲望和虚伪所控制,小说中的海滨公寓被讥讽为一个治疗病态心理的"天然疗养院".
而另一方面,沈从文却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湘西世界里,发现了一股尚未被文明"阉割"的原始天性和生命强力,《边城》 中的人们顺乎天然、悠然自适、性情皆善,满目是幽静灵秀、隽永明媚的自然风光,在翠翠、傩送和天保之间始终萦绕着一曲清新浪漫又略带感伤的爱情牧歌,沈从文将"人性"和"自然"二者纯粹化、浪漫化之后,成就了自己所言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2], 这不仅印照于现代浪漫主义的哲学背景之下,更植根于中国道家哲学的沃土之中.
4、回归自然的生命品格
自古以来,"崇尚自然"的观念在中国就相当发达,西方一位汉学家曾说:"在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中,便已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 "[13]老子最早谈及对"自然"的推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自然"一词,在《老子》中凡五见,主要指事物的本然、本初状态,即自然而然、自在自足、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如果说,老子的"自然"本体论尚且是个抽象的哲学概念, 那么在庄子的诗学体系中"自然"则被赋予了更丰富具象的内涵,一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二是生命个体的本真、自足、和谐状态. 庄子认为,"回归自然"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是人性消解一切虚妄意义之后复归的鲜活本原,正如《逍遥游》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生命个体惟有拥抱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相融相契,方能达到人生至境,获取人生至乐.
中国现代浪漫作家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展现着对"回归自然"文学母题的青睐. 郁达夫在后期创作中便有明显的风格变迁和主题转型,诚如他的自白---"想回到大自然的怀中, 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14]---《东梓关》、《迟桂花》 等后期代表作,是以一种恬淡沉静的风格更趋近了传统道家"回归自然"的母题,《沉沦》时期的浮躁凌厉、悲愤峻急和桀骜不驯消失了,完全被自然超脱的圆熟心境所取代,年届中年的郁达夫还在宁谧怡人的西湖之畔,搭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风雨茅庐",俨然一位现代隐士. 在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中,更构建了一个超凡脱俗、人境交融的现代桃花源,那里的人与自然格外和谐,正如沈从文所言:"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15],在无待、无碍、无累的自然状态中,个体得以重新返归心灵家园. 至于徐訏、无名氏所代表的"后期浪漫派",或许他们留给读者更多的直观印象是异域的旖旎风光、诡媚的情感意境甚至抽象的思辨,然而他们小说中所隐匿的皈依自然、 超脱尘俗和回归人性真我的精神力量,这一源自中国道家传统的东方智慧,往往会被遗漏和忽视. 在《荒谬的英法海峡》中,"我"无意间来到一个世外的孤岛上,那里杂居着黄、白、黑诸色人种,没有官僚,更没有阶级,小说借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大同世界,再现了一种返璞归真、淡泊平和、回归田园牧歌生活的美好意愿,实际上也暗含着与中国道家"回归自然"观念的投契.
二、潜在的价值渗透:儒家思想传统
中国的思想传统是一种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儒道互补的格局,这对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非常深远. 儒道二家始于"轴心时代"并在漫长发展中彼此融和、协调、对立统一,儒家思想以积极入世、关怀现实、仁民爱物的道义感与责任感,取得了中国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而道家思想则以无为而治、虚静贵柔和处下不争的风格态度,安守于中国思想传统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主一辅、一中心一边缘的稳定结构. 因此,儒家思想将是我们考量诸多问题时需要不断返回和驻足的一个重要原点. 不可否认,道家哲学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嫡脉,但在诸多深层价值观念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无法绕开儒家思想的潜在作用,即儒家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嵌入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理、意念和生命结构中,它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之间远非是抗拒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保持着某种合理化的胶着状态.
1、实用理性
李泽厚先生曾对儒家思想塑造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有过相当精辟和深入的研究论述,他认为"实用(践)理性"是"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16]. 所谓"实用(践)理性"是一种追求现实功利、目的和效用的理性精神, 它最早源于孔子对鬼神论、怀疑论等言论的反拨, 即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论语·八佾》),后逐渐发展为一套重视现实功用的儒家思维模式,它不重视在理念上抽象思辨地探讨哲学课题,而重视如何妥善处理解决现实问题,强调行动本身的实际效用[17]. 因此,"实用(践)理性"的儒家观念自一诞生,便沿着重功利、轻思辨、求务实、 趋实用的路径成长, 它与西方重抽象、思辨、和玄虚体验的思维模式,有本质的差异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自诞生之初,便在诗学、美学的理论准备上颇有欠缺,"五四"浪漫作家倾向于一种急功近利的创作方式,大多数"五四"浪漫小说只流于简单的情感宣泄,留下一些焦虑、苦闷的抽象概念.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言,它们 "没有像山姆·柯尔律治那样的人来指出想象力之重要;没有华兹华斯来向我们证实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 没有威廉·布莱克去探测人类心灵为善与为恶的无比能力"[18];鲁 迅亦批评 "五四 "浪漫小说"夸耀其颓唐"、"炫鬻其才绪"[19];梁 实秋更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对"五四 "浪漫文学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批驳[20]. 显然,"五四"一代的浪漫书写,并不是从浪漫主义美学诗学的理论逻辑出发,而是沉溺于一股模糊的启蒙价值和情感冲动之中,缺乏对浪漫主义精神价值的深入理解,而这一"逻辑前提的丧失也表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21]. 张灏先生指出,"五四"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五四"思想更是具备两歧性,"浪漫抒情"与"实用理性"这一对趋向相反的价值体系在彼此激荡、 盈虚消长中,形成了诡谲歧异的"五四"时代精神[22]. 换言之,"实用理性"这一儒家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植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生命肌体中,即使在那个极力反思、批判和解构儒家思想的"五四"时代,亦无法阻挠儒家思想的潜在渗透,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也是自"五四"开始,走上了一条在浪漫与现实、感性与理性、务虚与务实之间摇摆不定的宿命之途.
2、群体本位
"仁学"与"礼学"是儒家思想的两大核心,前者彰显"仁者爱人","仁学"带有鲜明的社会群体道德的色彩;后者则曰"克己复礼为仁",又曰"礼自外作","礼学"实际上是用以论证"仁学"中心的一种外在依据和方式,"礼"代表儒家群体秩序的外在规范,"克己复礼"是要克制和压抑个体需求以达到维护群体稳定的目的,儒家这一"群体本位"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记,它重在追求集体群体的和谐与协调,甚至以压抑个体精神生命为代价,这一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规约并引导着国人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和行为模式.
从哲学本体论上看,崇尚群体本位的儒家思想与追求个性意识的浪漫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但却恰好成就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国特色和历史境遇. 伴随"五四"文化启蒙思潮的兴起,高扬人的觉醒、肯定人的价值尊严、承认人的独立意志的"个体本位"主题,成为一股主流的言说趋向,"创造社"诸子凭借"自我表现"的浪漫主题,昂然走在"五四"的先锋潮头. 而自大革命溃败至"四·一二"政变发生,"五四"精神热潮逐渐消退冷却,当人们将思虑的触角伸向民族国家的历史纵深处时,很快感觉到了"个体"力量的有限性,而来自儒家"群体本位"的观念再度浮出历史地表,一度狂热追捧浪漫主义、高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家们,首先开始了对"自我表现"主题的全面否定,或许正因为他们当年曾是浪漫主义文学营垒中的主将,深谙浪漫主义的诗学主题和美学精神,因此他们的反戈一击更具颠覆性. 自 1925 年前后,创造社成员开始一反前期的文学主张,而以集体观念取代自我观念,将阶级意识无条件地置于个性意识之上,早期的个体抒情也迅速逆转为集体叙事. 1926 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毅然写道:"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23],不久又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大声疾呼:"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24]. 随后,郁达夫、郑伯奇、田汉、王独清等创造社同人纷纷投入到变革洪流之中. 1928 年,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接受日本左翼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后,重新创办《文化批判》一刊,并连同以蒋光慈等人为首的"太阳社",共同拉开了"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大幕. "普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政治与文艺的一次特殊联姻,在"革命+恋爱"的文学模式中强调"革命"与"恋爱"的糅合关系,即革命运动与浪漫爱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如同王德威所言---"革命与恋爱这两项观念, 获得了对等地位"[25],但随着"普罗文学"的日益炽盛,"革命"与"恋爱"逐渐成为无法兼容的选择对象,即"当恋爱与革命发生冲突的时候, 二者只能选择其一",而最终的选择往往是为"革命"而牺牲"恋爱", 革命的精神意志彻底取代了浪漫的个人情感. 因此,"普罗文学"在事实上改造了"浪漫主义"的某种性质,将原本崇尚"个体自我"的浪漫主义,改造为另一种充满宏大理想、英雄情结的浪漫主义,改造后的"浪漫"将"个体本位"彻底消融在"群体本位"中,改造后的"理想"也不再是个体小我的自发意愿,而是另一种符合人民大众的集体利益和群体理想, 正是儒家 "群体本位"意识,为这一观念逆转和思想置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它造就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一种独特、必然和有意味的历史境遇.
3、忧患意识"忧患意识" 一说最早是徐复观先生于 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予以阐释[26]. 事实上,"忧患意识"早在儒学经典文献《易经》中已初显端倪,据《易传·系辞下》记载:"《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王之事耶? "面对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事连年、夷夏纷争,孔子建构的儒家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对大时代的国族、社会和民生等问题有着深切思虑与忧患. 当然,面对时事沧桑和天下罹难,纾难解患成为"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诚如庄子所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庄子·骈拇》),但诸子各家所忧患的着眼点却不尽相同[27],徐复观先生亦曾说:"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虽然同是出于忧患,不过儒家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得到解脱"[28]. 因此,儒家的"忧患意识"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是因为它超越了对自我生命忧虑的浅层面, 而进入了一种忧国、忧世、忧民的思维深度,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其中的"道"在当时是指周礼和周公之治,随时代推移而演化为一种对国族、社会和民生问题的普遍关注.
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忧患"的主题意识、"感时忧国的精神"[29](夏志清语)始终没有中断,即使是在狂飙突进的"创造社"前期,浪漫才子郁达夫笔下哀怨凄楚的"零余人"所痛悼的也并不仅仅是自我个体的沉沦,而是整体国族的沉沦,迟至 1932 年,郁达夫在《达夫自选集·序》里明确对早期"自叙传"作品坦言道:"悲怀伤感, 决不是一个人的固有私情", 他忧心忡忡地说:"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30];青年郭沫若笔下吞食一切的"天狗"、在烈火中重生的"凤凰"、"开辟洪荒之大我", 一系列形象传达出的也不仅仅是个体自我的膨胀,更是整体国族意识的振奋,而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亡时刻的来临,敏感的郭沫若更是果断地带领创造社同人整体"向左转",急切呼唤"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31].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40 年代,中国历史进程已从"五四"思想革命中走出,在燃眉之急的 30、40 年代里,持续紧张的社会变革、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已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无暇旁顾,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政治变革的研究实践中去,即"已从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了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32]. 因此,无论是"革命文学"的论争,还是普罗文学"革命+恋爱"模式的兴起,以及之后的左翼文学思潮,无不代表着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强烈忧患和主动承担的精神,正是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和承担道义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成就了一条中国式浪漫主义文学的生命轨迹.
总之,在深邃广袤的思想时空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予以哲学式的寻根问祖,需要不断重返中国儒、 道两大思想体系之内进行深度审视,在儒道二家彼此碰撞、融合与盈虚消长的辨证关系中,方能展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真实风貌,它绝不同于西式浪漫主义那般"纯粹",而是在"儒家"与"道家"的两种观念体系之间徘徊、挣扎与矛盾,它一路波折,却又一直在倔强前行、义无返顾.
参考文献:
[1]〔美〕李 维 着 ,谭 震 球 译 :《现代 世界的 预 言 者 》第 1 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2]陈 鼓 应 :《老庄 新 论 》第 199 页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1992 年版.
[3] 此处及以下所引庄子言论均出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中下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4]郭沫若:《沫若文集(第 6 卷)·黑猫》第 2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 2 卷)·十批判书后记》第 464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6]郭沫若:《我的作 诗 经 过.质 文 》,1936 年 11 月 10日,第 2 卷第 2 期.
[7]郭 沫 若 :《沫 若文集 (第 10 卷 )·少 年维特 之 烦 恼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8] 见 H.B.Nisbet 翻 译 的 《康 德 政 论 文 集 》(Kant'sPolitical Writings),转引自〔美〕舒衡哲着,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 1 页,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
[9]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 3 卷)·骸骨迷恋者的独语》第 82 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 169 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1]沈 从 文 :《沈 从文文集 (第 10 卷 )·水 云 》第 294页,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
[12]沈 从 文 :《从文 小 说 习 作 选·代 序 》第 5 页 ,上 海书店出版社 1990 年版.
[13]〔德〕W. 顾彬着, 马树德译:《中国文人 的 自 然观》第 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14]郁 达 夫 :《郁 达 夫 小 说选 (下 )·忏 余 独 白 》,浙 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5]沈 从 文 :《沈 从文文集 (第 11 卷 )·断 虹 引 言 》,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
[16]李 泽 厚 :《中国 古 代 思想 史 论 》第 23 页 ,天 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17]李 泽 厚 :《中国 古 代 思想 史 论 》第 24 页 ,天 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18]夏 志 清 :《中国 现代 小 说史 》第 13 页 ,复旦 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9]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20]梁 实 秋 :《浪 漫 的与 古 典 的·文 学的 纪 律 》第 1-3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21]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于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第 44 页,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版.
[22]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于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第 5-9 页,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版.
[23]郭 沫 若 :《沫 若文集·革 命 与 文 学 》,人 民 文 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24] 郭沫若:《沫若文集 (第 10 卷)·留声机器的回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25]王 德 威 :《现代 中国 小 说十 讲 》第 73 页 ,复 旦 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6]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载于杨春梅编:《儒家文化思想研究》第 625 页,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27]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法各家都有忧患意识,不过所忧的对象、内容以及解决的方案都各有不同. 夏乃儒先生在《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语焉甚详,可参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2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 115 页,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29] 转 引 自 张 旭 春 :《政治 的 审 美 化 与 审 美 的 政治化---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 第 225 页,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30] 转 引 自 陈 国 恩 :《浪 漫 主义 与 二 十 世 纪 中国 文学》第 71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31]郭 沫 若 :《沫 若文集·我们 的 文 学 新 运 动 》,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32]钱 理 群 、温 儒 敏 、吴 福 辉 着 :《中国 现代文 学 三十年》第 20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