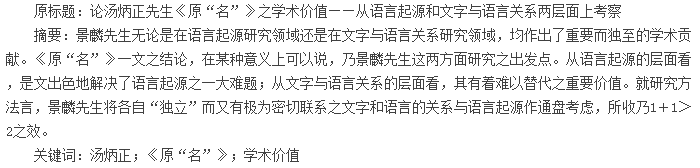
景麟(汤炳正)先生成稿于1947年的《原“名”》一文,着重探索的乃最初促成口头语言产生之客观条件。而由于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其与语言起源有着至为密切之关联,故是文所说不管是对探讨语言起源还是对研究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均有着即使今天看来仍独至之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用力去细而究之。下面,拟分别从语言起源的层面和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层面作一粗浅之研讨,以便我们对是文以至景麟先生之相关研究有更多之认识。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云。
一、从语言起源的层面看《原“名”》之学术价值
就语言起源的层面言,我们知道,摩尔根(1818-1881)在其《古代社会》第一编第三章的“现在再往上溯……最后还有手势语言”下有注云:……人类之发出声音最初是用来辅助手势的;等到这些声音逐渐具有固定的意义以后,便在这种意义范围内取代了手势语言,或者与手势语言结合在一起。这样也就促使发音器官的机能有所发展。我们假定,音节分明的语言从一开始起就有手势伴随着,这一点再也明白不过了。这两者至今仍然不可分离,正可以体现古代人心智活动习惯残余下来的痕迹。如果语言十分完备,还要再用手势来引申或加强语言的意义,那就会是一种错误。我们回溯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上推到较原始的形态时,就发现手势的成分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在表现方式上更为复杂,直到我们发现语言之依赖于手势乃至没有手势就根本无法理解其意义的程度。语言和手势均产生于蒙昧阶段,并肩发展,臻于兴盛,而在进入野蛮阶段很久以后,二者仍始终结合在一起,不过结合程度较轻而已。凡是急于想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的人,最好充分注意手势语言所能提供的启示。
然是说虽“极有意义而又嫌笼统”,而其所以“笼统”,乃因摩尔根并未涉及“在二者交替之际,如何过渡”这一语言起源之关键问题。景麟先生说:如先民之初,乃用口头语言“辅助”手势语言之不足,则首先应当注意下列事实:手势表意,只能用于白昼,昏夜即失其效力。如北美洲土著民族阿刺帕和人以及南非洲之布西曼人,除白昼以手势表意外,黑暗中相遇,即不能互相表达意志,是其例也。先民为“辅助”手势之所不逮,于是昏夜之际表达意志与说明事物,即不得不借助于口音。口头语言产生之客观条件,殆即与此有关。
这里,我们除了要“应当注意”“昏夜即失其效力”云云这一“事实”外,还须格外注意“先民为‘辅助’手势之所不逮”数语。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两者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景麟先生如此之说所以经得起推敲,乃缘其引证之坚实与考析之细密。要之,景麟先生于此将“口头语言”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辅助’手势语言”这一重要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就笔者目力所及,将这一问题说得如此透彻者,当以景麟先生所论为最。而此所谓“透彻”,乃缘识“肯綮”所在而中之,非引“北美洲土著民族阿刺帕和人以及南非洲之布西曼人”如何如何,便能造乎斯境。
先民何以“不得不借助于口音”?即“口头语言产生之客观条件”与什么有关?此乃关键中之关键。是文分“名——冥”“问——昏”“音——暗”三个部分,分别对“与语言有密切关系之‘名’‘问’‘音’等字所代表之原始意义”进行细致而具体的考察以究之。如在第一部分的开始,景麟先生便以《说文解字》“口”部之“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为例展开研讨。当然,我们知道,后人对叔重是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如宋元之际的戴侗之“《周官》‘中夏教苃舍,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莫夜则旌旗徽识不可辨,故必谨其号名以相壹,‘名’之文所以‘从夕’也”,段玉裁之“《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此许所本也。……其作器刻铭,亦谓称扬其先祖之德,著己名于下,皆只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许君于金部不录‘铭’字。从《周官》今书、《礼》今文也。许意凡经传‘铭’字皆当作‘名’矣”,李慈铭之“‘名’之‘从夕’,殊不可解。以‘冥’转训,亦甚迂晦。疑‘名’本从‘卩’,‘卩’者信也,亦制也。……”
张文虎之“窃谓‘名’字本从口,从令省,亦声。从令省者,从卪也,卪者信也。从口从卪者,所谓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篆文‘卪’与‘夕’形豪牦之误,附会为夕冥,其说甚陋,盖后人所妄窜,非许书也”等等,不一而足。然此中多或如李、张两氏的失之甚远,或如戴、段二家的未达一间。纵观古今各家之说,在我们看来,当以景麟先生所言最得“名”之所以为“名”之实,合《〈说文〉歧读考源》《古语“偏举”释例》所论观,看得更为清楚。而景麟先生之得,往往缘其解读文献之大智慧。如于此之将部分置于整体中作历时之考察,等等。用其《屈学答问·一一》的话说,即“做学问时,不能把一个问题孤立起来看,而必须把问题放在事物的整体规律当中,进行分析”。景麟先生又说:《说文》释“名”为“从夕口”,此实古义之仅存者;但又局限于“自命”“自名”,未能从泛指一切物名着眼,犹未达一间。……“名”字金文多作,甲骨文则作,仅就字形言之,其本义已灼然可见。
盖远古先民,于昼间皆以手势表事达意,逮日夕昏冥,视官失其功能,即不得不代以发诸口舌之语音,以乞灵于听觉。“冥不相见”而以口舌“自命”“自名”,特昏夕之中表事达意之一端耳。……“名”字从夕,许氏以为“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云云,可谓得其本义,并与“名”字所代表之语音,亦互相吻合。盖先民开始以口舌表意,乃出于日夕昏冥之际,故即以事物出现之时间特征“冥”音呼之;“冥”与“名”,一语之异文耳。推而广之,凡与“名”同纽之字,多表昏冥之义。
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致的考察,景麟先生得出如下结论:人类开始用语音表意,既在日夕昏冥之际,则其时白昼表意之工具,或仍为手势。此应属人类由手势表意到语音表意之过渡阶段,乃人类文明进化中所迈出最关键之一步。人类语言开始产生的环境与条件,可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昏夜降临,作为环境与条件之一,是否对语言的产生,曾起过促进作用,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景麟先生之说乃声音与手势二者“交替之际,如何过渡”这一语言起源之重要问题的种种研究中之最为出色者。我们知道,约翰·莱昂斯在其1986年于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一专门讲座——“语言的起源”中曾说:有一种关于语言的种系发生理论(原注:“我本人赞同的就是这种理论的一种修正形式。”)是认为语言并非起源于言语,而是起源于手势。这当然不是一种新理论。早在1746年,康迪拉克(Condillac)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这种看法,那多半是18世纪关于语言的起源或者各种起源的诸多讨论中最具独创性和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那以后,许多不同学科的代表人物,如泰勒(Tylor)、摩尔根(Morgan)、华莱士(Wallace)、冯特(Wundt)等许多学者,也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不过,现在又有了不少支持这种手势理论的新证据。有关证据只有一部分是来自语言学,大部分都是来自物理人类学、古生物学、心理学、个体生态学和神经生理学这些其它学科。
惜乎,当时约翰·莱昂斯氏无缘见到景麟先生此文(此文虽成于1947年,然1990年才问世)。当然,不止《原“名”》如此,《语言起源之商榷》《古语“偏举”释例》亦然。还有,是否看到景麟先生之文是一回事,看到了,能否看出其重要之价值又是一回事。借用鲁迅先生《叶紫作〈丰收〉序》的话说:“伟大也要有人懂。”
综上所述,从语言起源的层面看,景麟先生是文以《说文解字》“口”部之“名,自命也。从口夕。
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为例展开研讨,出色地解决了声音与手势“交替之际,如何过渡”这一语言起源之大难题。景麟先生正是以此与其在《语言起源之商榷》中所提出的“容态语”与“声感语”等崭新而极具深度之论,将语言起源中影响最大之“手势说”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的。
二、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层面看《原“名”》之学术价值
文字与语言之关系,乃语言文字学(文字学与语言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语言文字学家们为此聚讼不已。其所以如此,因为这一问题牵涉甚广而十分复杂,且不弄清楚它,许多相关的问题就难以讨论下去。而就这一关系言,我们知道最近百年间之主流观点,即如在成书于1912年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理论语言学诞生的一个标志之《国语学草创》中,胡以鲁(1888-1917)所说的“盖文字者,语言之徽识耳。……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语言主而文字宾也”,尤其是如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而影响特别大的《语言学概论》之“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说。
然而,这正如景麟先生在其《〈说文〉歧读考源:兼论初期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后引此文,略其副标题)一文中所说的:……当代国内外语言学界最权威之结论,似仍与中国清儒之成说相雷同。即认为:“文字不是和语言同时产生的,而是在语言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并在语言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是在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同时文字又是从属于语言的。”但是,吾人从文字发生和发展之某些客观的历史事实上看,似乎并非如此。简言之,即先民之初,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根据语言而创造。即使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然文字只是在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基础上产生出来,而不是在语言之基础上产生出来。语言者,乃以喉舌声音表达事物与思想;而文字者,则以图画形象表达事物与思想。语言由声音以达于耳;而文字则由形象以达于目。在文字产生初期阶段,语言与文字各效其用,各尽其能。因此,远古先民,实依据客观现实以造字,并非“依声以造字”;亦即文字并非“在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后来,来国龙在其《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和汉字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这一有反思意味之文中亦有类似的说法:文字和语言有密切的关联,但是,文字并不完全等同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回顾近百年发展起来的汉字起源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字起源论在理论上有所偏颇:这些研究往往只用“语言学眼光”来判断汉字的源头,把汉字起源的重点放在是否表音上,把汉字起源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的研究简化为只是对文字定义的争论,从而忽视了原始文字(proto-writing)和成熟文字体系在社会制度层面的连续性,割裂了前后发展的联系,看不到汉字产生的源头。
来先生之说,亦甚有见地。
然在我们看来,其撰是文时若能看到景麟先生的相关研究,当更有所进。如上所述,景麟先生在《原“名”》一文中,以《说文解字》“口”部之“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为例展开研讨,从而得出“人类开始用语音表意,既在日夕昏冥之际,则其时白昼表意之工具,或仍为手势。此应属人类由手势表意到语音表意之过渡阶段,乃人类文明进化中所迈出最关键之一步”这一殊具学术意义之结论。而这一结论,不仅对语言起源研究十分重要,对我们研究文字与语言之关系意义亦巨。当然客观地说,景麟先生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领域中所作之桀异贡献,主要的还是见于其名文《〈说文〉歧读考源》中,然《原“名”》这方面的价值,我们亦当珍之。否则,不仅语言起源之“发生学的问题”会极为含糊,文字与语言关系之“发生学的问题”亦难以说清楚。换言之,就文字与语言之关系言,《原“名”》所究乃“出发处”之去向。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文〉歧读考源》则正是从此处“出发”来展开具体而深入之研讨的,景麟先生在是文中说: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现象,不得不有赖于文字。然溯厥文字之初起,则既非谐声,又非拼音,只为一种极简单之事物形象符号。因此,古代文字与语言之结合关系及结合过程,必须加以探索。清代自顾亭林起,而古音之学大昌。乾嘉诸儒,递相发明,所得益精且宏,皆知根据声韵以抉语言文字之源。其中,对《说文解字》一书之整理,功绩尤伟。然考其所持之理论,莫不以为:“文字之始作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见段玉裁《说文解字》土部坤字注。)又云:“声之来也与天地同始。
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声,依声以造字,而声即寓于文字之内。”(见王筠《说文释例》卷三。)则是谓文字根据语音而创造,文字即为语音之符号,在文字产生之始,即与语音有互相凝结而不可分离之关系。此乃清儒以来一贯之理论。然清儒之治《说文》者,其成绩之所以能超越前代者固因此,而其犹有某些问题无法解决者,亦即因固守此说之所致。例如凡遇《说文》中具有两音以上之“歧读”字,既不能以“音近”解释,又不能以“音转”推演者,辄感迷离,其蔽可想而见。
“然清儒之治《说文》者”云云,见人之所未见,而十分深刻。景麟先生《〈说文〉歧读考源》一文着重探讨的,正是这些“无法解决者”之所以然。然如上所述,这正是以《原“名”》所说为出发点的——从发生学的层面说,无论若膺之“文字之始作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还是王氏之“声之来也与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声,依声以造字,而声即寓于文字之内”,均未尽然。既然“先民之初,乃用口头语言‘辅助’手势语言之不足”与“人类开始用语音表意,既在日夕昏冥之际,则其时白昼表意之工具,或仍为手势”,那么,“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与“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声,依声以造字”便未能尽其“始”。就段氏说言,其忽乎有“流动之形”(手势)而后有“静态之形”(图画之类),“流动之形”必先乎“静态之形”这一层;就王氏语观,其没有注意到“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形”(“手势”——“流动之形”),依“形”以造“字”一面。许叔重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说文字之制作是依仿客观事物的形状描摹而来,并且认为文字是“物象之本”。换言之,“初文”首先是描摹客观事物之符号,而非语言符号。不仅如此,景麟先生《原“名”》所说,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不管是初民之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前语言”),还是“结绳”“刻契”“图画”(“前文字”),两者都同样有一个自我逐渐“成熟”的过程;二,既然有“目治”之手势语言,自然就有同样是“目治”之“刻契”“图画”等——后者,当首先是前者之“延伸”,然后才与有声语言“走在一起”,即“文字”,正如景麟先生所说的,“并非‘在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蒋善国先生说:原始象形文字源于绘画,见画知义,因而见形知义,可以与语言联系起来,达到知音的程度。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是它专表形意,而与语音没有直接联系。同一符号可以代表两种语言里的同一个词,而有不同的读音,例如“目”这个词,埃及文作 ,克雷特文作 ,金文作 ,都画个眼睛形来表达,而读音不同。不论什么人看了,都知道是眼睛,都了解它的意义,都可以按自己的语言把它念出声来。在这种情况下,不通过语言,可以知道它所代表的概念,然后通过语言,了解它的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象形文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音读,也证实了表意文字与语音的联系不够。
据上所述可知,此近是矣。然蒋先生于此更要说明的是:“文字是表达语言的,特别是表达语音的。所谓‘依声以造字,而声即寓文字之内。’(王筠《说文释例》卷三)任何书写符号都不能避开语言,独自表示、表达概念,都是标记表示概念的单词,而不是仿佛不依靠词而存在的在词以外的概念本身,因此文字是通过语音来知义的,所谓‘以音载义’。”
即以《原“名”》所说例之,可知其同样似未免将后世发展已成熟之文字体系的特征加之于原始文字上之嫌。而此乃“清儒以来”,尤其是最近百年间,本研究领域极为普遍的做法。另外,关于汉字之起源,裘锡圭、沈培两先生撰写的《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之“汉字起源的研究”一节有说:“本世纪以来,一般文字学者都接受了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孙诒让、沈兼士、唐兰、蒋善国等人都曾明确指出象形文字与绘画的源流关系)。”又说:“七十年代末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汉字从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有些学者提出了‘原始文字’这一概念,以指称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文字。”
这是符合实际的。问题是,极少学者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景麟先生《原“名”》给予之深刻启示:一者,“……两者都同样有一个自我逐渐‘成熟’的过程”;二者,手势语言与同样是“目治”之“刻契”“图画”等的关系,厥初当更为密切。
综上所述,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层面看,景麟先生《原“名”》一文有着难以替代之重要价值。借用序波君在其一甚见功力之文中论景麟先生《语言起源之商榷》的话说,即其“迈向的是一个新的方向”。另外,景麟先生是文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由于“各方”都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故文字不可能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
余论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1860-1943)说:“由我提出并首先坚持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现代的语言一直追溯到历史与我们掌握的材料所容许的限度……如果靠着这种追溯的过程,我们最终能到达这样一种发音阶段:这些发音不再被称为真正的语言,而只是某种先于语言的东西——那么问题就会解决了。因为转化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无中生有,则是人类理智绝不能理解的。”
引自然,我们谁都无法回到“这样一种发音阶段”。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瑟夫·房德里耶斯(1875-1960)说:“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他们借助于已发现的最古文献来探溯这些语言的历史。但是在这历史中不论追溯到多么遥远,他们所碰到的始终只是一些已经高度发达的语言,这些语言的背后还有我们毫无所知的漫长的过去。”
不过,房氏于此未免太过于悲观(参后)。即“追溯”虽回到不了叶氏所期望之“这样一种发音阶段”,然亦未必如房氏所断言之总归“毫无所知”。而就“追溯”言,目力所及,当以景麟先生所至最为近之,以《原“名”》所说与相关之论比观,便不难明白。这一方面,缘于汉字“隐藏”着丰富而宝贵之“厥初”秘密。陈寅恪先生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杜学知先生说:“说到文字,现在全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都行用的是‘标音文字’,只有中国象形系统的汉字为例外。……轶出世界所有文字类型之外的汉字,独标一格,只此便富有研究的价值。”是均可谓得其大者矣。另一方面,则赖景麟先生之特识。
其于《原“名”》说:“时代杳远,记载缺乏,无由考其确实情况。为突破此一困难,本文所据之资料,并非历史所记载,而为古代文字结构中所表现者;且非尽为文字形体上所表现者,乃更着重于古代文字所代表之语音中所表现者。盖文字后起,不尽得事物之本义,而语音在产生之初,实即与事物结成不解之缘。因此,语音中所表现者,自当遗有语言发生时之社会事态。若能根据语音变迁之规律,上溯语音原始之形态;再据语音摹拟事物之原则,推究语音所描绘之社会事态。”此乃深知于关键处着力者之言也。而“上溯语音原始之形态”云云,未尝不包含有房德里耶斯所说的“漫长的过去”之某些“秘密”,尽管那“漫长的过去”之“秘密”,更多的恐将永远埋在人类智慧无法知之之所。
总之,与相关论著细加比观,便知景麟先生无论是在语言起源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字与语言关系研究领域,均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而《原“名”》一文之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几可以说,乃景麟先生这两方面研究之出发点。从研究方法之层面看,将各自“独立”而又有极为密切联系之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与语言起源作通盘考虑,其结果自然是1+1>2。景麟先生之学术研究,每多具方法之意义,以《原“名”》合之《〈说文〉歧读考源》与《语言起源之商榷》观,得其概矣。
参考文献:
〔1〕(美)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原“名”》,载氏著《语言之起源》,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
〔3〕戴侗.六书故: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二〔Z〕.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