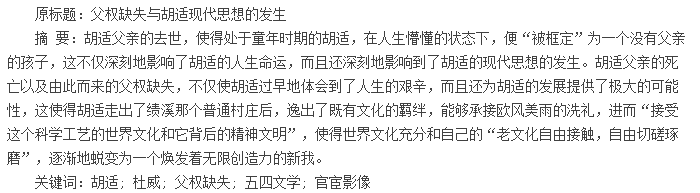
我们要考察五四文学的发生,就需要寻找那些隐藏在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背后的历史动因,尤其应到他们早期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追根溯源。胡适作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从徽州到上海,从上海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北京,在这样的空间转换中,胡适的传统思想逐渐地蜕变乃至升华为现代思想,这既渗透着大时代变迁的影子,更打上了家庭的烙印。
在家庭的诸多元素中,有些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少了这些元素,就没有后来的胡适,如胡适的母亲; 有些元素是可以缺失的,如果有了这些元素,就没有了后来的胡适,如胡适的父亲。
胡适父亲的去世,使得处于童年时期的胡适,在人生懵懂的状态下便“被框定”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胡适的人生命运,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五四文学的发生。这也许正是历史辩证法的诡异之处: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胡适父亲的过世以及由此而来的父权缺失,不仅使胡适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而且还为胡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使得胡适走出了绩溪那个普通村庄后,逸出了既有文化的羁绊,能够承接着欧风美雨的洗礼,进而“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使得世界文化充分和自己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逐渐地蜕变为一个焕发着无限创造力的新我。
一
胡适父亲的过世,对胡适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父亲的过世使得寄寓于父亲这个名分之上的父权,失却了存在的主体。在这样一个没有父亲教化和规训的社会中,胡适得以超越既有的思想疆域的羁绊,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胡适的父权缺失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胡适的父权缺失,使其人生疆域获得了无限拓展的可能性。胡适的父亲是通过“念书”得以走出绩溪成为了清朝的官宦,这在其思想深处自然就产生了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法则的皈依感。因此,胡适的父亲在临终前的遗嘱中,才会特别地要求胡适“认真念书”,才会要求胡适的兄长要供应“胡适念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推崇的“天地君亲师”的权力体系,以及由此体系而来的“孝悌”观念,是主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准则。这使得胡适父亲的遗嘱犹如其家庭中的“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基于对父命的恪守,胡适才得以与“念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胡适父亲遗嘱要求胡适“念书”,但是,对胡适要念什么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对象。在胡适父亲的心目中,所谓的“念书”并不是一个问题。在胡适父亲所认同的知识体系中,其所推崇的书自然不会超越其所接触的、被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事实也的确如此,胡适如果不是处于一个“五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其所念的书,并不会从根本上逸出其父所认同和推崇的典籍。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胡适的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了转变,缘此而涌现出了一大批与“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截然不同的“新书”,这些“新书”承载着“西学”的知识。由此说来,胡适在其父遗嘱中“念书”的制导下,逸出了其父所规范的“书”的藩篱,进入了无限广阔的阅读空间。
胡适在“念书”的过程中,逐渐地逸出了“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的疆域,开始接触大量的中国传统小说,这对其参与五四文学革命起到了奠基作用。从科举体系来看,科举时考什么,考生便准备什么,这是体制作用的必然结果。缘于科举并不会考小说,因此,考生如果读小说便会被看作“玩物丧志”,这在家长那里是严厉禁止的。幸运的是,当胡适因为偶然的机缘,阅读了中国传统小说并因此激发了“念书”兴趣时,他并没有受到抑制,反而获得了自由生长的空间: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 ‘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 ,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
《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的捧出来,我很高兴的捧回去。”“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五叔,守焕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
应该承认,胡适在此遇到五叔、守焕哥这样一些宽容而又仁爱的本家,还是非常幸运的,他们不但没有阻止其阅读小说的兴趣,反而还顺承着胡适的阅读欲望,积极帮助他满足自己的阅读欲望。当然,如果胡适在此所求助的不是本家,而是其父亲的话,那情形是否会像五叔、守焕哥那样,其阅读欲望还能得以满足呢? 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作为五叔、守焕哥等本家,对胡适不负有教化的责任,自然,玉成胡适小说阅读的欲望便是顺水人情的事。然而,如果是对儿子的人生负有教化使命的父亲,那情形自然就不同了: 他必然要从遵循体制的目的出发,把那些与科举毫无关联的书目置之度外,这也正是很多家长把孩子阅读小说当作“玩物丧志”的缘由所在。
如果说作为本家,对胡适的小说阅读欲望持有宽容态度,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代父行命”的兄长也对胡适的小说阅读采取了宽容态度,这对胡适思想的自由发展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胡适对此这样说过: “那时候正是废八股时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教我读书。”
这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转变,作为直接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二哥、三哥等这些左右着胡适命运的人,对胡适的读书有了更宽容的态度。自然,这也就逸出了胡适的父亲所认同的“书目”了。这说明,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兄长,比从科举中一路走过来的父辈要开放得多,这较之父辈的文化立场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位移。
然而,如果没有父权缺失,胡适及其兄长恐怕就只得在父权所划定的疆域内动弹不得,又怎么谈得上让胡适逸出父权所设定的疆域呢? 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和其兄长的遭遇,便很好地说明了父权是怎样深深地钳制着其人生疆域的: 接受了新思想影响的大哥,在和郭沫若闲聊时说:
“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放脚问题来。大哥又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小脚。我说: ‘我自然喜欢大脚了。’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 ‘好的,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西! ’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这真是晴天里一声霹雷。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对此,郭沫若感叹道: “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究是两个时代。单是对于‘野蛮’两个字的解释,轻重之间便有天渊的悬殊。”
由此可以想见,如果胡适的父亲在场的话,且不说胡适自己的命运了,单就其兄长的命运,便被父权先验地规定了。
如果我们深入探究胡适的思想发展,其所读书目逸出其父亲的规范固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但就其根本来说,还在于胡适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地建立起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学的“地图”,这使得其对五四文学的革命对象,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对此,胡适曾经这样说过: “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 30 多部小说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正是在这样广泛的小说阅读中,胡适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初步了解,并得以建立起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地图”,至于由此而来的语言训练,也为胡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如胡适所说的那样,“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
胡适的父权缺失,促成其思想逸出了父权疆域的羁绊,使其自我的主体性得到了确立和张扬,这为胡适在五四文学发生前反叛传统文学倡导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缘于父亲的死亡,胡适较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冷暖与艰辛,这不仅促成了其对社会和人生的敏锐的感知力,而且也促成了其自我主体性的确立。
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穷人的孩子,因为父辈无法为他们撑起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天空,诸多的人生决策需要依靠自我完成;与穷人的孩子相似的是,失去了父亲庇护的孩子,也就提早地进入了没有依靠的荒原。面对诸多的人生选项,没有了父亲的包办,一切只能任由自己做出抉择,这便为其主体性的确立和拓展奠定了无限的可能性; 至于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磨难,则砥砺了其对人生的认知深度和广度,为其思想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正是胡适的父权缺失,使胡适的思想成长迥异于父辈。正是胡适走出乡村的过程,也便是一个逐渐地确立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如果说,胡适在留学美国前因为其主体性还没有建构起来,表现出对其兄长意见的兼顾的话,那么,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胡适则逐渐地确立起了自我的主体性,甚至为了坚持自我的主体性,胡适和梅光迪作为“相交多年的知己,却因在提倡白话诗方面意见针锋相对,终于渐成陌路”。显然,在这样对抗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是胡适那种自我主体性得以张扬的表征。
其二,胡适的父权缺失,为其“西学”的知识谱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适成长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所阅读的那些“西学”图书。“西学”图书的印刷和发行,根源于晚清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如果没有晚清政府的允许乃至提倡,是断不会有西学图书的印刷和发行的,自然,胡适也就不会有阅读西学图书的机缘。胡适能够阅读西学图书,就根本来说,还是得力于新式教育,这使得胡适走出封闭的乡村,开始慢慢地走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可谓是儿子的第一导师,这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根据所在。但是,从胡适思想形成的源头来看,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和杜威。对此,胡适曾经这样说过: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 一是赫胥肯,一是杜威”,“杜威先生教我如何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胡适晚年回忆时也说,杜威“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胡适的这一自白,说明其现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完成的,而是从留学美国期间所接受的现代教育那里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胡适的父亲依然在场,那情形恐怕就大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如果胡适所接受的第一教育来自父亲,自然,其思想也就打上了父亲思想的烙印; 胡适父亲的死亡,使得胡适父亲对其思想的影响退居后台,而美国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美国所积累的体验,则使得胡适深受外国学人思想的影响,这促成了胡适思想与异域文化的对接。
新式教育大力倡导留学教育对胡适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来,家庭的败落使得胡适继续“念书”的愿望面临着破灭的可能,但是,留学教育所提供的充裕的物质保障,使得胡适得以维系即将中断的“念书”愿望。从“振兴家国”的目的出发,决定胡适命运的兄长期待着学习铁路、矿冶等实用之学,但由于胡适对路、矿都没什么兴趣,而又为避免兄长失望,他决定出国学农,以农救国。但是,走出了父权疆域羁绊的胡适,在走出了国门之后,是学铁路、学矿冶还是学农,不仅由不得胡适父亲的“遗嘱”,而且也由不得胡适兄长了。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当胡适留学归来,胡适已经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了。
胡适在出国留学初期是期望学成后报效家国的,因此,农学作为一个可以兼顾“家国”需要的专业,获得了胡适及其兄长的认同。在晚清留学的专业选择中,许多留学生都把科学当作报效家国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正是晚清以来的科学救国观念在时人文化心理深处的反映。
随着科举的式微,儒家文化典籍的支配作用已经衰减了。实际上,科举如果无法帮助时人晋升到上流社会体制中,并因此博得所谓的“功名利禄”,其被时人抛弃是必然的事情。与此相反,时人对科学的认同乃至崇拜则如异军突起,这恰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思想从那种务虚的“玄学”向着实用的“科学”转型的征兆。这样的一种转型,到了 1920 年代,便从当初的隐性矛盾跃升为显性矛盾,甚至还爆发了一场关于“玄学”和“科学”的论战。对于这场论战,我们如果从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来看,这样的矛盾实际上在他们留学期间便在其内在精神世界中发生了,其最终的结果是,科学把他们思想中的那些有关中国传统的“玄学”驱逐了出来。但是,就其思想的核心来看,胡适这批留学者,在其人生成长关键期,于耳濡目染之中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这使得他们深深地抱有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因此,他们在完成了对科学的认同和推崇之后,并没有继续从事科学的研究,而是利用这种科学的思维和实验的方法,对置身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进行了一番清理。
以胡适为代表的那批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 包括鲁迅和郭沫若等) ,在当初都把科学当作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展开形式,但到了后来,却又背离了科学研究,走到了从事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创建上来,这具有某种必然性。其一,从事科学研究,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并不是最为敏感的社会神经。科学救国对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以及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来说,并不是一个能立竿见影的“药方”。这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最为要紧的是如何能够挽救其生命不至于死亡———这个生命有机体只有继续存活才谈得上所谓的从根本上的救治。科学无疑正是这样一个可以从根本上救国之药方,但并不是最迫切、最有效的药方; 像医学尽管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但正如鲁迅所意识到的那样,救治再多的病人,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医治好了的病人,精神依然麻木,那对国家危机的纾解又有什么裨益呢?
胡适所从事的农学也是如此,农学可以促成科学种田,这对一个在精神上麻木的饥饿者来说,多打一点粮食和少打一点粮食,对国家的危难又有什么匡救呢? 所以,科学尽管很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和人的现代思想的确立相对接,那所谓的科学也就失却了存在的价值。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适等人放弃农学,对那些期待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来说,便成为历史的必然选项。其二,基于胡适等人建构现代国家的渴望,他们最终走到了文化和文学的前沿阵地,进而从根本上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改良”。胡适等人从科学出发,然后走到对人的精神启蒙上来,他们为什么会最终选择了文学作为他们思想的突破口呢? 不可否认,胡适和鲁迅等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包括并没有学习过现代自然科学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想从文学上“安身立命”,他们最终走向了文学,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文学对人的精神具有启蒙的功能。其实,这样的一种启蒙指向,早在晚清时期的梁启超那里便开始了。这正如梁启超所认同南海先生的话所言: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为此,梁启超把小说尊崇为“文学之最上乘”,到了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代文化先驱者那里,对文学的认同和推崇也是自然而然的。从学科上说,哲学这样玄而又玄的知识体系,自然是普通读者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现代政治学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松把握的; 在五四文学发生之前,便确立了新式教育,我们从学科体系上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但是,在这套教育体系中,我们给学生传授什么知识、帮助学生建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念,还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文学作为能够兼顾到诸多学科体系的知识谱系,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建构现代思想的“急先锋”,成为“引”人们到“光明”地方去的一个“桥梁”。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胡适作为文化启蒙者,并没有把文学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正是胡适为什么总是“但开风气”,而没有在“开风气”之后依然献身于文学的缘由所在。
尽管如此,胡适学习农学依然对其确立科学的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出于对农学的理解与把握,胡适对农学学科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农学作为西方现代科学之一翼,也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方法之上的。自然,胡适对这一学科知识的理解和皈依,也就意味着其对西学的现代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方法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与把握,并由此建构起了现代科学思维和实验方法。当胡适带着自己所确立起来的这种现代思维和科学实验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和文学时,便有了新的发现。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并不是那些专门从事近代文学的创建主体,而是一批建构起了现代知识谱系、接受了现代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方法的“客串者”。这恰说明了作为五四文学闯将的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半路杀出一条新文学的血路来,正是因为他们既有现代的科学知识作支撑、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作积淀,因此,当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方法来重新审视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时,才创建出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新文化和新文学。
其三,胡适的父权缺失反而凸显了其父亲的官宦影像,给胡适的人生带来了无法摆脱的政治情结。在胡适文化心理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胡适的母亲把胡适的父亲建构成了一个几乎可以堪称完美的形象: 不管是道德还是学问,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是胡适的母亲期待着胡适去追摹的对象。
这也难怪,从胡适母亲的角度来看,她和胡适的父亲结婚之后,胡适的父亲对她呵护有加,这自然促成她对丈夫的恩爱与感念。况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官宦人家讨小老婆者也不在少数,而胡适的父亲则是通过媒人正大光明地把她迎娶到家的。相对来说,胡适的母亲即便是身处苦难之中,缘于身边还有更多悲惨的参照系,难免会身在苦难之中而不知了。至于胡适的父亲死后,那随之而来的无所依傍的孤家寡人的切身感受,更会反转过来使她对亡夫充满了无限的思念之情。由此说来,胡适的父亲在其母亲的叙述中“完美化”便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胡适母亲所建构起来的这个近乎完美的父亲形象,对胡适的人生带来的潜在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胡适一生无法释怀的政治情结。
胡适父亲的官宦身份对胡适的政治情结的影响,我们如果和鲁迅进行对比的话,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鲁迅的祖父尽管也有着官宦身份,但是,他最终还是成了这个政治体制的“异己者”,这使得鲁迅一生对政治采取了一种疏离的人生取向; 而胡适则不然,胡适的父亲终其一生都身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之中,这使得胡适成为一个“人在江湖、心系社稷”的政治人物。胡适对政治所期待的,便是把自己所意识到的美国现代政治政体移植到中国社会现实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胡适会对国民党既亲近又疏远,并企图保持着政府的“诤友”身份的缘由所在。当然,胡适的这种政治情结,除了我们所叙及的胡适父亲的政治身份的影响之外,还与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入世”情怀有着极大的关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往往是身在民间心系庙堂的,如杜甫便希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此说来,文学在很多具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那里,便成为他们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种方式,这为他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洒出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此说来,胡适的这种政治情结,使得他在五四文学发生之后,又逐渐地远离了文学。对此,季羡林曾经说过: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 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应该承认,季羡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胡适作为一介书生,正是缘于其浓郁的政治情结,使得他无法安分守己、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纯粹的书生,而成为一个政治意气干云的“书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并不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书呆子”。对此,有学者针对胡适和陈独秀文学主张的态度差异指出: “陈独秀坚定地支持胡适‘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否定了胡适所坚持的‘自由讨论’的学术原则。过往的文学史评述常常以此为据,证明陈氏是真正的文学革命者而胡适充其量是软弱的文学改良者”。
其实,在“软弱”和“包容”等历史表象的背后,正深隐着胡适父亲的官宦影像———显然,这样的影像和那种“造反者”影像是截然不同的。
二
胡适的父权缺失,固然对他的现代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晚清时期,并不是所有与胡适遭际类似的人的思想都可以转化为现代思想,这就是说,父权缺失还给胡适的精神和情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具体来说,这种精神性创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的拮据几乎断送了胡适的求学之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占据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导地位,没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撑,“子”就失却了物质上的依托。与此相反,女性就没有被赋予社会性的事务,承担必要的社会职务,这就使得女性无法获得自我人生的社会价值实现,获得社会的回报。因此,作为孤儿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也就意味着他失却了为其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参天大树,甚至几乎断送了他未来的现代思想发展的可能性。
物质上的困窘对胡适前期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胡适就自己留学美国的动机便说过: “京中举行留学美国之考试。……且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
这说明了物质上的困窘的确对胡适人生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胡适物质上陷入困窘之际,如果没有晚清政府所提供的官费留学机会,胡适能否留学美国,便成为一个问题。自然,如果没有了留学美国的机缘,也就没有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胡适。
胡适留学美国归来之后,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教职,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经济的困窘,为其从事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胡适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 “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教者英文学、英文修词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 260 元,本月加至 280 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从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
由此可见,胡适在走出了家庭经济的困窘后,不仅显得意气风发,而且还重拾了复兴大家庭的信心。客观上说,胡适对传统的大家庭的中兴情结,恰是对其家庭因为其父亲死亡而带来的败落的痛惜使然。但值得肯定的是,当胡适在北京大学获得教职之后,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了其“先锋”地位之后,胡适即超越了“小我”的家庭情怀,升华为具有国家情怀的“大我”。
尽管胡适完成了这种自我超越,但在胡适的文化心理的深处,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成了自我的断裂和新生。实际上,在胡适的文化心理深处,还依然存活着这样的一种乡土情结,即胡适还是无法割断与自己的家庭、家族、乡土的脐带性关联,其文化之树还是盘根错节于绩溪那片土地中,在有些时候,还因此成为其无法超越自我的羁绊。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当胡适在“发乎情”时,总会因为“母亲”影像的出现,而最终“止乎礼”。
其二,胡适的父权缺失,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性格和情感,给其思想和情感带来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胡适的精神创伤对其性格和情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性格上的内方外圆,在阴柔与中庸之中不乏决绝与韧性。胡适人生成长的外在环境不是那种以阳刚之气为特点的环境,而是带有某种阴柔的特点。如胡适在阅读了传统小说之后,其所获得的认同更多地来自周边的女性推崇。对此,胡适说过: “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请我吃。”
与此相反,对胡适成长具有砥砺作用的男性则不是很多,在胡适的自述中,其所强调的是那位“族叔近仁”,“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
当然,就其根本来说,胡适的内方外圆性格深受母亲的影响。胡适的母亲,既有中国传统女性的阴柔之美,更有一种刚烈之性。这从胡适的母亲不顾家庭的反对而毅然决然地嫁给比自己年龄大了许多的胡适父亲这件事中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当胡适的母亲面对本家“泼污”时,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把其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清白”放在首位,并最终使本家赔礼道歉。这说明胡适的母亲在关乎自己名声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是逆来顺受的。与此同时,胡适的母亲还有一种内敛的性格,她把内心的刚烈性反抗转化为外在的柔性反抗。如胡适在自述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胡适母亲的如此方式,既是一种自我痛苦的释放与宣泄,又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策略,这样的一种策略,对胡适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作为政府“诤友”的胡适,在和政府不离不弃的过程中,又何尝没有这种策略的影子呢!
胡适那种内方外圆的性格深受其母亲的影响。对此,胡适曾经这样说过: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 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 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适尽管“能宽恕人,体谅人”,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所恪守的文化信仰,如对自由的信仰,对民主的信仰等,对现代中国的想象等,这些思想乃至信仰,都深深地植根于胡适的思想深处,与其生命相始终。然而,在一些非关重大操守的细枝末节上,胡适则采取变通的方式。如胡适对执政党的态度,并不是全部认同,但是,这样的不全部认同,在胡适看来,则仅仅是细枝末节,而不是关乎到人生之本的根本差异。也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胡适终其一生都对共产主义持有一种抵触态度,而没有像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其他先驱者那样,或者是向“左”转,或者直接地成为“共产主义者”。
其三,胡适因为父亲的死亡而失却了父爱,这既深刻地影响到了胡适的父亲观,又深刻地影响到了胡适之子的悲剧命运。胡适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对父亲并没有清晰的记忆,属于一种碎片化的记忆形式,这自然无法对其性格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此说来,胡适的父亲既没有对其暴力上的惩戒,也没有历历在目的“父子情深”。这样的人生体验自然对胡适的父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胡适的思想发展链条中,对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持有反叛的价值取向,这对胡适确立新思想来说,无疑是超前的。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胡适对传统父子关系的批判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胡适如何处理父子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发展和演进,是上一代向下一代进行文化“传”的过程,也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文化进行“承”的过程,具有鲜明的代际传承的特点。然而,胡适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宣称: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的这首诗,便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规范的父子关系,其所否定的是那种建立在“父父子子”等级体系中的依附关系,其所张扬的是父与子独立平等的人格,是“堂堂的人”。由此出发,至于儿子对父亲是否“孝顺”则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此一来,胡适就把“父为子纲”的传统价值体系彻底颠覆了。
胡适的这种“父子观”,对他如何做父亲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胡适正是在这种父子观的制导下,没有很好地担负起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致使他把培养儿子的义务更多地推卸给了妻子,这相对于中国传统所张扬的制衡体系来说,胡适所作所为正可谓“养不教”。这使得胡适在获得了自我人生的成功转型之后,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一个父亲的义务,没有把儿子的现代转型放到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体认,这结果之一便是部分地造成了儿子胡思杜的悲剧人生。当然,胡适作为父亲,也对子女充满了深情,如胡适在 1929 年写给大儿子胡祖望的信中说: “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 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然而,胡适如此不厌其烦的叮嘱,对一个年仅 10 岁的儿童来说,还是显得有些朦胧。
不管怎样,胡适在接受了现代思想后,未能较好地处理好文化的代际传承关系,确保文化的自然平稳演进,其所带来的警示作用还是非常强烈的。胡适之所以在文化的代际传承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除了与胡适早期没有体味到父爱有着关联之外,还与徽州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男性作为支撑家庭的“顶梁柱”,其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方式一般有两种: 其一,徽州人在十二三岁时,开始随着乡人到大都市去学徒,然后通过买卖来养家糊口。徽州一带属于山岭地带,盛产茶叶。茶叶是无法食用的植物,种植茶叶自然需要通过交换来获得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这就决定了与茶叶生产紧密相连的是茶叶交换。茶叶的交换,无法在本地区完成,只能到大都市才能实现茶叶流通和交换。因此,那些从事茶叶生意的徽州人,尽管人在外地,但其婚姻依然植根于徽州乡土之中,这就使得“一生夫妻三年半”。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培育下一代的任务,几乎全部落到了女性的身上,而父亲的直接承担则少得多。其二,徽州人注重“念书”在人的仕途中的作用。一般说来,那些具有相当财富积累的家庭,则注重通过“念书”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正是缘于这种文化导向,徽州具有了“东南邹鲁”的美称。胡适的父亲便是通过科举进入社会上层的。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的父亲才会在其“遗嘱”中特别地告诫胡适要认真“念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读书取得“功名”而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和其他人家通过“生意”而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就其本质来说是“殊途同归”。然而,在胡适的文化心理深处,他却把教育儿子的责任委之于其妻子江东秀。这使得胡适在儿子的教育中未能起到监护者的应有的作用。
父权缺失不仅对胡适的父子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了他的婚姻观。
在留学美国初期,胡适对中国的旧婚制非常推崇: “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悦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当配偶。人或疑此种婚姻必无爱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 Self - made) ,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 Duty - made) 。”
如此说来,胡适不仅没有意识到中国旧婚制的荒谬之处,反而对此大加赞赏,正标明了在胡适的思想深处,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实际上,就胡适本人来说,便是旧婚制的受害者。因此,胡适之妻江东秀并没有像其婆婆那样,顺理成章地承载起培育儿子的使命,相反,随着其对风流倜傥的胡适而带来的婚姻的担忧,江东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捆住”胡适上,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江东秀的如此煞费心机地扼守着婚姻的“喉咙”,胡适也许早就冲破包办婚姻的羁绊,展翅飞翔于“青山绿水”之间了。
当然,父亲的死亡,并不必然地促成胡适走上新文化运动的道路。实际上,在近代中国,缘于男性在社会中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再加上医疗条件的局限,男性的死亡率也就比较高。这就是说,在那种历史情景下,与胡适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像胡适那样,走上新文化新文学创建道路的人,却并不是很多。
由此说来,胡适留学美国,便是促成其完成自我蜕变乃至升华的关键点之所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留学美国,也就没有那个“暴得大名”的胡适,从这样的视点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横空出世,正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完成的。胡适也正是由此基点出发,开启了对“我们的老文化”进行“改良”的艰难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