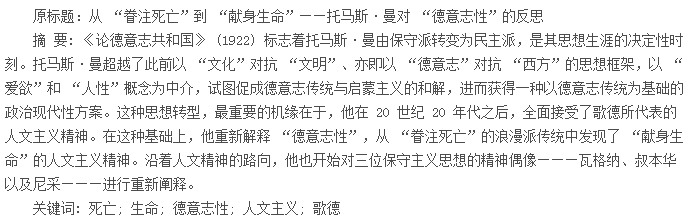
一、德意志与 “西方”: 托马斯·曼的政治时刻
置身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坎坷历史之中,托马斯·曼与其他文学家一样,都被裹胁到政治论争当中。
而他的政治情结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决断上,与亨利希·曼兄弟阋墙。与前方的硝烟连天相映,后方的文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笔仗不休。托马斯·曼在民族主义的激情中讴歌战争,在与民主人士的论战中写出了德国保守主义的经典着作 《一个非政治者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1918,简称 《反思》) 。与其他同时代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一样,托马斯·曼的反思图式,本质上就是后来由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所系统表述出来的 “文化”(Kultur) 对抗“文明”(Zivilisation) 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图式中,所谓 “政治的”,就是 “西方的”,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降的工具理性所产生的 “文明”。而 “文明”所代表的世界观,就是以精神或理念评判生命和社会,并意图使后者服从于前者。在托马斯·曼看来,所谓 “非政治”(unpolitisch) ,即不相信政治,不相信 “进步”,是以保守的姿态、以审美的姿态、以反讽的姿态对工具理性发出的抗议。一言以蔽之,这种保守主义图式,其精神实质乃是以德意志的 “文化”抵制西方的 “文明”。亨利希·曼这些民主派,因而成为浅薄的 “文明作家”(Zivilisationsschriftsteller) 。这一时期的托马斯·曼,其政治决断仍是明快的: 在这种 “文化”观中作出的政治决断也极为明快,那就是: 民主、共和之类的西方文明果实,不应该、也不可能移植入德国的文化土壤当中。
1. 德意志共和国: 传统民族和现代国家的综合体
1919 年,德国在战败的废墟中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由于魏玛共和国根基不稳,政局动荡不安,诸如革命、暗杀之类的政治事件如同走马灯般上演。而托马斯·曼的政治思想也悄然转变。1921 年,他提出了一个冲击着整个魏玛时代的概念——— “保守主义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 。而这个概念的初衷,在于试图实现 “德意志”与 “西方”,亦即保守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和解策略,本质上不同于以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为首的 “保守主义革命”理论者的构想[1]。这种和解的努力,最终定型于 1922 年的 《论德意志共和国》(Von deutscher Republik,《共和国》) 。促使其民主思想成形的一个关键事件是: 当年 6 月,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托马斯·曼义愤填膺,决定为这新生的共和国正名,遂于 1922 年 10 月 13 日在柏林的贝多芬大厅公开发表演讲,以图将青年们争取到扞卫共和国的阵地中来。从 《反思》到 《共和国》,托马斯·曼的政治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扭转,演讲一发表,便引起了剧烈的争议。这位曾被人当作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来倚赖的人,现在被指认为 “落水者”、“变节者”。而在今天的评价中,这篇演讲甚至获得了比 《反思》更为重要的思想地位,被认为是 “在托马斯·曼的政治着作全集中的一个关键文本”[2]。
托马斯·曼所理解的 “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 Republik) ,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专有名词。
在这里,“德意志”作为 “共和国”的形容词,其真正所指是一种限定,是对作为政治制度 “共和国”的文化界定。因而,“德意志共和国”具有双重维度,它是传统的民族 (Volk) 和现代的国家 (Staat)的综合体。在他看来,“将民族的生命与国家的生命剥离开来,乃是病态的……民族的生命远比公法的条文 (Buchstabe) 或制度安排 (positive Form) 更有力,更能塑造生活……真正的民族生命,不论何时何地,都远高于任何方面。”[3]所以,与德国的民主相匹配的,除了 “德意志民族”,别无其他。他所理解的共和国并非诞生于 1918,而是 1914。[3]344———在思想史上,这是整个德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体发出“1914 观念”(Ideen von 1914) 这一民族主义最强音的时刻。虽然时过境迁,但托马斯·曼作为 “1914观念”的匿名支持者,并未曾放弃他的民族理解。对他来说,共和国与其是一种政治上的既存现实,毋宁是一种理念; 而共和国的理念绝非启蒙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架基于合理性的法则、放之四海而运作自如的机器,而一个扎根于德意志传统的政治有机体。就此而言,一种以德意志文化为本位的“观察”方式,比起 《一个非政治者的反思》,不曾有丝毫改变。[4]但此时托马斯·曼的问题式已变为: 如何在政治现代性的范畴内重构德意志性?
由于思想使命的更新,托马斯·曼的论述策略也随之更新。相对于 《一个非政治者的反思》中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论德意志共和国》使用了典型的浪漫派范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引入一个 “第三因素”,使原先对立命题获得和解。在政治浪漫派的天主教理解中,世俗的各种权力无法通过自身而获得平衡,而只有通过教会这一同时具有世俗性与超世俗性的 “第三因素”,才能达成一个任务。而在这里,政治浪漫派所眷注的教会,已被托马斯·曼赓续为共和国。共和国的政治所指无疑是 “民主”,而 “德国的民主”,或曰 “德意志共和国”如何建构出来呢? 也就是说,一个能够综合了 “社会性与内在性,人性与贵族性,踞于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神话与理性之间的美好而庄严的……德意志的中间地带”[3]144-145何以可能? 托马斯·曼寻找到的 “第三因素”,便是 “人性”(Humanit?t) 。
2. 第三因素: “人性”
这幅政治构图的灵感触发点,则是惠特曼诗歌。通过惠特曼,他领悟到: “惠特曼所说的 ‘民主’,就是我们古代风尚中所惯用的 ‘人性’。”[5]或者说,“民主只是较古老的、经典的人性概念的现代政治名谓。”[6]作为民主派、同时也是浪漫派,惠特曼将民主主义的政治蓝图渲染成浪漫主义的美学图景。
在他看来,现代民主制度绝不只是一套关于立法与选举的制度设计,而是与人们的心灵、情感与信念紧密相关的价值系统,而这恰恰是民主的 “本质性的魅力”(wesentlicher Zauber) 。[3]146也就是说,民主的核心最终是宗教因素。这幅政治-美学图景也恰恰为托马斯·曼提供了重构政治浪漫派的参照系。
而重构政治浪漫派则相当于重构德意志精神,亦即德国人的民族概念。在 《论德意志共和国》里,他左手援引惠特曼,右手援引诺瓦利斯,让两人互证互训,指向了这一核心观念: 德国浪漫派蕴藉着民主、共和的因素。[3]150与此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同,在这里,他建立的是一系列的恒等式: 德国浪漫主义 = 民主 = 人性 = 爱。这种思想倾向的动因,一方面是试图将当时社会上充满戾气的战争文化转化为充满生气的和平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人性”概念下调和个体与国家、传统与革命、死欲与爱欲等等矛盾,从而实现德意志精神与现代政治体制的和解。
个人主义显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伦理基础。虽然集体、顺从和团结等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的传统伦理观,但托马斯·曼并不认为,德意志传统便因而缺乏个体观念。而关于个体的价值,诺瓦利斯与惠特曼有着惊人的共鸣。惠特曼说: “完善的个体主义理念,事实上就是在最深层次上赋予共同体理念以特征和色彩。”而诺瓦利斯说: “个体为普通之物赋色,是浪漫主义的要素。” (Das individuelle Koloritdes Universellen ist sein romantisches Elemment. )[3]148-149而他们关于个体与整体之关系的理解也同气相求,都将个体与整个理解为有机的统一体。在其中,个体乃是整个的器官,而整体又是个体的器官。个体与个体之间,遵循的是多元主义的原则。或者说用浪漫派常用的表述方式来说,国家作为诗 (Posie) ,而非散文 (Prosa) 。[3]151这就是诺瓦利斯的共和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事实上是将国家建构视为教化的过程。这在托马斯·曼看来,就是 “政治的人性”,即 “人作为一个文明 (gebildet) 国家中的一员被教化”。[3]145-146而这也恰恰是德意志精神———在诺瓦利斯看来,德意志性的理想便是 “真正的人民性”(echte Popularit?t)[3]128。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曼论断道: “德意志人,或者说,泛日耳曼人,拥有致力于建构国家的个体本能,拥有基于每个个体成员之间互相承认的共同体理念,拥有人性的理念,这种人性理念既综合了内在人性和国家,又综合了贵族制和社会性,既迥异于斯拉夫性的政治神话,又迥异于西方的无政府的极端个人主义———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统一,这种 “真正的和谐”,一言以遮之,就是共和国。”[3]149
传统与革命的紧张也是托马斯·曼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固守传统是德意志性的显着特征,因而保守主义一直是德国思想史的主流,而迄至 20 世纪,浪漫派仍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而作为 “保守主义革命”的命名者,此时的托马斯·曼强调,其保守主义的思想使命,不是为过去和反动服务,而是为未来服务。他也不将传统理解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按照诺瓦利斯的思路,将其理解为不应为时代激变所分解、而又可以产生新的结晶的根基和核心。[3]143
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浪漫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席勒将浪漫的诗视为伤感的诗而与古代的素朴的诗区分开来,梅列日柯夫斯基在论及俄罗斯文学时提出的 “创造性批判”,都指明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矢向,那就是现代性。因而,浪漫派的 “保守”,未尝不是 “进步”。而诺瓦利斯更将基督教史的核心解释为 “绝对的抽象,泯灭现时,神化未来”; 在托马斯·曼看来,这位 “浪漫主义的雅各宾派” (romantisches Jacobinertum)[3]147所构想的“进步的乌托邦主义” (Fortschrittsutopismus) ,乃是人类的完善。[3]153-154
而与此同时,这种精神气质与世俗的现代商业精神也毫无矛盾。可以说,在托马斯·曼的理解中,浪漫派本身就是传统与革命的综合体。
总之,在托马斯·曼眼中,浪漫派不乏 “自由人性” (freie Humanit?t) 的理念,而其核心则是“爱”。这里的 “爱”,不是基督意义上的那种苍白而贫血的悲悯,而是审美主义意义上的情欲。托马斯·曼的英文传记作者注意到: “当惠特曼复兴了情欲、从而造就了民主的时候,德国诗人却誓言献身死亡。”[7]的确,德国浪漫派整体地沉湎于死亡崇拜的氛围当中。而这不仅是文化心理问题,而且是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死亡就是虚无和毁灭。浪漫派的死亡崇拜深刻地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心理,并集中地体现为尼采的xuwuzhuyi。在二战的硝烟中,列奥·斯特劳斯极其深刻地将尼采的xuwuzhuyi定义为 “德意志xuwuzhuyi”: 它不是要毁灭一切,而是意图摧毁那种 “人性的、太人性的”西方文明。[8]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阐释浪漫派的死亡崇拜,对托马斯·曼而言,成为至关重要的思想使命。
他的答案也极具创造力。死欲与爱欲这对弗洛伊德心理学上的对立概念,被他巧妙地转化成互补概念。早在福柯之前,他已从歌德的 《威廉·迈斯特》中洞见到: 迈斯特的成长史已形象地演绎出生命、死亡与人文主义的内在逻辑。迈斯特作为一个戏剧演员而又热衷于解剖学,已经表明剧院这样一个淫靡的空间,已在为医学———一种人本主义学科———作准备。因而,对身体、疾病、乃至死亡的关切,本身就是崇高的人文主义主题。而浪漫派、特别是诺瓦利斯的作品 (如 《夜颂》) 更是交织着各种疾病、死亡与欲望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却又深刻地缔造于 “婚床” (Brautbett) 意象。托马斯·曼认为,关切于疾病与死亡,关切于颓废与病态,只是关切于生命、关切于人的表达,这已被医学这门人本主义科学所证明。也就是说: “谁关切有机体,关切生命,谁也特别关切死。一部成长小说无妨展现这样的主题: 死亡的体验终归是生命的体验,一种通往人的体验。”或者说: “对美的爱,对完善的爱,无非是对死的爱……如果你愿意的话,所有诗都是病态的; 因为所有的诗、每一首诗在根本上就是与爱、美和死的理念无从剥离地、不可救药地缔结在一起。”[3]164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此时正处于创作过程的 《魔山》也试图在文学表达上改写 “眷注死亡”的精神底蕴———用托马斯·曼的话说, “开始于眷注死亡 (Sympathie mit dem Tod) ,结束于决心献身生命 (Lebensdienst) ,对我们而言,没有哪种精神形变比这更熟悉了”。[3]165
从 “眷注死亡”到 “献身生命”,借助惠特曼那原始的、强健的诗歌,托马斯·曼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形变,也试图促进时代精神的形变[9]———从以死欲为核心的战争文化转变为以爱欲为核心的和平文化。他论断道: “厄洛斯作为政治家,甚至作为国家的缔造者,自古以来这就是一种确信的观念。
在我们的时代,最近又被巧妙地再次宣传。但企图把它的本质与政治问题说成是复辟君主制,则完全是胡闹。毋宁说,它的本质是共和制———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种国家与文化的统一体。”[3]160面对日渐强烈的 “第三帝国”的呼声,托马斯·曼也试图将此 “第三帝国”加上 “人性”的拱顶石,使之成为 “具有宗教意味的人性之第三帝国”[3]160。
在浪漫主义、人性、民主与爱欲的思想演绎中,托马斯·曼展示一次调和启蒙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努力,也向他的德意志同胞展示一种建构一个 “德意志中间地带”的政治图景。在其中,现代性的各种矛盾,如神话与理性,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国家,审美的孤立主义与伦理的普遍主义,道德的理性与世俗的合理性,都应当在 “人性”的理念中合目的地聚合起来。虽然这幅图景并不清晰,有时候更显得草率或凌乱,以至他的儿子戈罗·曼有过这样一番不恭的评论: “就像他曾经给战争发明了一个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的意义一样,当他为共和制作思想论证的时候,他也只是巧妙构思,只是拿古老的德国文学加以拼凑; 那是文学,不是现实。”[10]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思想敏锐性,以及他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政治反思和政治建构的文化-政治视角。发表 《共和国》演讲,是托马斯·曼思想生涯中的决定性时刻,这一时刻深切地关涉于其文学创作与文论思考。
二、“德意志性”的人文主义路向
写作 《一个非政治者的反思》时的托马斯·曼便对 “德意志性”(Deutschtum) 兹兹以求。在 “德意志性”的视角下,滥殇于赫尔曼战役的德意志历史,始终是反抗罗马精神和启蒙精神的 “非文明”的历史; 而德意志文化则执着于内向度化的心灵世界,而不涉外向度的社会政治。而艺术作为最强大的、最保守的精神力量,成为 “德意志性”的最重要的载体。叔本华-瓦格纳-尼采,作为德意志精神苍穹的璀灿星辰,联结成托马斯·曼文化视野中的稳恒的三角形星丛。[11]而当他从 “眷注死亡”转向“献身生命”时,歌德的人性观如同一颗启明星般闪现出最耀眼的光芒。在其披照之下,叔本华-瓦格纳-尼采星丛转而焕发出人本主义之光。这是因为,托马斯·曼的理智将歌德拣选为主星,并在其定位下,重新构拟了 “德意志性”的精神星丛。
1. 歌德的 “人性” 概念: 德意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 “中间地带”
思想转向之前的托马斯·曼亲近于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而歌德对他而言只是一尊高山仰止的精神偶像,虽然他已意识到歌德所代表的健康明朗的生命活力乃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但他的内心仍然同情于 (精神生物学意义上) 病态的席勒。在其早期小说 《沉重的时刻》中,面对难以为继的 《华伦斯坦》手稿的席勒,在焦虑与沮丧中遥想起 “那个光辉的、好动的、感性的、跟天神一样不反思的人,想到那边那个人,那个住在魏玛的人,那个让他爱恨交加的人”[12]。这位病态的席勒事实上就是托马斯·曼自己的心灵投影,而后者的思想旨趣并未出离于浪漫主义的 “眷注死亡”。然而,一个机缘促发了他由 “眷注死亡”向 “献身生命”的思想转变。托马斯·曼后来反复提及这个机缘: 年轻的他在《席勒 〈钟〉后记》接触到歌德所自铸的伟词——— “无愧于生活”(lebenswürdig) 。歌德说: “死亡应该俘获无愧于生命的人(Den Lebenswürdigen soll der Tod erbeuten! ) ”。这句话即刻震惊了曾深深浸淫于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托马斯·曼,完全扰乱了他此前基于艺术家病态心理学的艺术观和价值观。[13-14]他由此洞悉到歌德式的 “倔强的生命乐观主义”(ein trotziger Lebenspositivismus) ,“超越悲观主义的生命肯定”(ein überpessimistischer Lebensbejahung) ; 而这在他看来,就构成了市民性的最高和最普遍的形式,即 “生命的市民性”(Lebensbürgerlichkeit) 。
此时,他对歌德的敬仰,就不是仅仅基于歌德的作品,而是歌德这个人,这个人的生活态度有丰沛的文化蕴含。汉斯·迈尔(Hans Mayer) 对托马斯·曼的思想转型总结道: “我们体验到的,不是一条伴随歌德的道路,而是一条通往歌德的道路。”
托马斯·曼认同于歌德,乃是因为他的思想主导动机———以 “人性”概念作为融汇德意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 “中间地带”———在歌德身上找了一个理想原型。他在发表于 1921 年的讲演 《歌德与托尔斯泰》中,把歌德称为 “天生热爱有机物的自然之子”,歌德那种艺术地再现物质世界的天才,比起席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 “精神之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完美的精神统一体。发表于 1932 年的讲演《歌德作为市民时代的代表》一方面将歌德呈现为一幅典型的市民肖像: 他心境平和,笃信秩序,谦恭有礼,不问政治,坚持不懈,肯定生活。另一方面则是一幅冷眼旁观、喜怒无常、悲观主义的艺术家肖像。应该说,对歌德的两重性的理解,托马斯·曼并非着人先鞭,亦非独辟蹊径,但他将歌像的肖像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文化符号,却仍是具有独擅的理解。他认为歌德的天性包含两个方面: “德意志的与地中海的-古典的,欧洲的与民族的。这种统一本质上就是天才与理性的统一、神秘与澄明的统一、低沉的重音与洗练的词语的统一、抒情诗与心理学的统一。他是那位最伟大者,因为他以最为愉悦的方式、以一种兴许倘若非如此便不会出现的方式,把魔性与教养 (D?monie und Urbanit?t) 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正是这种魔性与教养的综合,使他成为人类之骄子。”
歌德于是成为一面澄明的人性之镜,《歌德作为市民社会的代表》,通过把歌德视为 “我们所谓市民时代、即始于 15 世纪迄于 19 世纪之间五百年的代表”[13]309,则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德意志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完美统一。
歌德的作品折射的正是市民时代的精神光谱。《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塑造了一个超前于时代的教育者,他预见了新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亲和力》中直觉的人性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的精神状态,通往思想与情感的更幽暗、更深层的世界的道路。《浮士德》不仅展现出歌德作为市民之子与艺术天才的神魔二重性,诗作的第二部事实上是对技术进步、文明与交往的讴歌,并且做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梦,对于素来独尊 “文化”的德意志文化而言, “对于这一时一味寻求审美精神的哲学趣向而言,不啻于一次故意的冒犯! ”[13]340的确,歌德的创作引起了浪漫派的讥讽。诺瓦利斯将歌德指认为“完全讲求实效的诗人 (praktischer Dichter) ”,将 《威廉·迈斯特》指认为 “极端缺乏诗意”,无论它在表现上有多么诗意,而事实上对诗、对宗教的嘲弄: “它讲了寻常的人间事务,把自然和神秘主义遗忘了。它是部分诗化了的市民的、家庭的故事。其中第一部表明,低价的、日常的关切,如果饰之以简朴、文雅而流畅的语言,并以适当的节奏讲述出来,也会中听。” “他 [指歌德] 之于其作品,正如英国人之于其商品: 非常简朴、整齐,舒适,耐用……就像英国人一样,他拥有一种天生的讲究实效的趣味,一种通过知性而获得的合式的鉴赏力。”[13]320-321而托马斯·曼把这些讥讽当作有力的把手,更深切地把握到歌德的市民性。歌德不仅认为最好的文化只能来自于市民,而且他也能天才地把自由经济原则转化为精神生活。[13]337歌德走出了一条把诗性市民化、把市民性诗化的中间道路,“它具有一种韵律般的魅力,塑造出厄洛斯与逻各斯的最为纯粹的混合体,让我们欢快地、毫无抵制地接受它的诱惑。”[13]321-322这种诱惑毋宁说是理智上的选择,因为歌德以其艺术姿态、连同其生活姿态,展现出一种克服 “文化”与 “文明”的辩证法。
2. “叔本华—瓦格纳—尼采” 星丛的人本主义之光
在 《歌德作为市民时代的代表》临近结尾处,托马斯·曼讲述了一段佚事: 在一个晚会上,歌德旁若无人地走向叔本华,祝贺他写出了 《充分理由律的四重根》。这个场景对他而言是充满象征性的:歌德握住了那只正在写作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手,也就握住了瓦格纳和尼采的手,握住了代表着 19 世纪市民文化之另一侧面的悲观主义。而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也意味着歌德式的人本主义已暗中传递给了叔本华-瓦格纳-尼采,就像米开朗基罗的 《创世记》中上帝把精神灌注给了亚当。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由此在托马斯·曼的理解中散发出人本主义的气息,作于 1938 年的论文 《叔本华》便是对叔本华的人本主义阐释。叔本华哲学的死亡气息弥漫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精神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深刻地缔结于德意志音乐———尼采曾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发现了同叔本华哲学一样的愉快: “伦理的空气,浮士德式的气息,十字架,死亡与坟墓。”托马斯·曼的小说事实上也从属于这种氛围。而现在,托马斯·曼则力图将这种死亡气息生命化,从而作出了这样一番夫子自道: 《魔山》已经表达出这种观念: 谁关切生命,谁就特别关切死亡; 而他在 《布登勃洛克一家》设置了托马斯·布登勃洛克阅读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情节,事实上源于他年轻时的经验,而目的就是把叔本华缔结于市民精神。他把叔本华融进叙事,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在死亡中发现生命,让他从烦忧的个体主义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叔本华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写青年人而写的,因为青年人比老年人更懂得爱,因而也更懂得死亡。他由此认为: “耽溺于死 (Todes-Erotik) ,作为一种音乐的逻辑的思想体系,产生于精神与感性之间巨大张力———这种张力所迸发出的火花,恰恰是情欲: 这也恰是具有类似体验的青年遇到这种哲学时的结果,对于这种哲学,他不以道德的方式来理解,只能以生命的方式、个人的方式来理解……”[17]
而叔本华的历史效果,在这一生命之维远逊于死亡之维。这在托马斯·曼看来,是因为后来的艺术家们误用了叔本华,他们作为叔本华的 “背叛者”,必定 “有愧”于叔本华。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就是他的人本主义。他作为悲观主义者乃是因为他是意志的哲学家。意志作为消极的满足的对立面,本质上是痛苦的。它永无止息,追寻着某种东西。它是匮乏、热望、贪婪、要求。因而一个意志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而叔本华对意志的研究,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研究。“心理学本质上就是要揭露,就是以尖锐的、反讽的、自然主义的洞察力揭开理性与本能之间的迷惑性关系。”[17]301
所以,叔本华开辟了一个深广的人本主义探寻领域,而弗洛伊德便是叔本华的 20 世纪的学生,因而也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只是人们未能洞悉叔本华的用意,因而叔本华那种对痛苦真理的智性认识转变成对精神本身的蔑视。叔本华哲学本身不可能导致20 世纪前30 年代这个各种恶劣本质的繁荣时代。在托马斯·曼意图以 “人性”骄正非理性主义的文化格局中,叔本华仍葆有强大的现代意义,因为他指引了一条更为通达的现代性之路——— “他那智性的感性,他那化为生命的学说: 认知、思想、哲学不单是头脑的事情,而且关涉到整个人,关涉到心灵与感官,身体与灵魂。或者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存在,能催生出一种新的人性,一种超越了偏枯的理性与本能崇拜的人性。”[17]303
瓦格纳曾说他是通过叔本华才找到自己的。托马斯·曼甚至将瓦格纳获知叔本华当作其一生的伟大事件。托马斯·曼曾将德意志精神理解为一种音乐精神,这是因为他从叔本华那里获知: 其他艺术只展现了现象的图像,而音乐所展现的,则是意志的图像。他从叔本华那里所获致的生命哲学,也倾注到对瓦格纳的理解中。一些瓦格纳专家认为,《特里斯坦》,只是爱情戏剧,包含着对生存意志的最强烈的肯定,因而与悲观主义的叔本华无关。他认为,这种观点严重缺乏洞察力。因为叔本华认为只有审美状态才能超离令人痛苦的意志,这只是对意志的智性否定,这种否定只是派生性的。而叔本华将性欲作为意志的核心,事实上表达出一种普遍性的爱欲,而 《特里斯坦》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才得获得深刻的理解。他的这番辩驳,无疑是想把瓦格纳音乐视为 “意志的图像”,视为 “德意志性”的典型代表,视为歌德与叔本华的 “人性”的传承。
其时,纳粹的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瓦格纳音乐的民族主义精神。所以,写于 1933 年的 《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与伟大》便面临着双重任务: 就不仅要保护瓦格纳的 “德意志性”,又要反抗那种加诸其身的民族主义。而托马斯·曼的解决方式也极为巧妙。他正本清源地分析出瓦格纳歌剧中所徘徊着的浪漫派幽灵: 小施莱格尔、诺瓦利斯、霍夫曼、阿尔尼姆等等。瓦格纳禀性中的浪漫主义之维,塑造了他的艺术家姿态: “应该意识到,艺术家即便置身于最为庄严的艺术领域,也绝非严肃的人; 寻求影响和消遣乃是他的行规,悲剧也与喜剧同根同源。换一个角度,两者就颠倒: 喜剧是隐秘的悲剧,悲剧———说到底———是崇高的玩笑。”[18]
“对艺术家而言,新的 ‘真理’经验就是新的游戏刺激和表现的可能性,除此无它……他对艺术的严肃,其本性是绝对的,那就是 ‘游戏中的严肃’。而他对精神的严肃不是绝对的,因为他的严肃目的在于游戏。”[18]42
这种浪漫主义姿态,表明了非政治姿态。以瓦格纳的诗句——— “即便神圣罗马帝国沦为尘埃,而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幸存下来。”———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无非就是通过玷污它们的 “浪漫主义纯粹性”而误用了它们。对于托马斯·曼而言,只要 “德意志艺术”幸存下来,这些诗句描述的只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对国家的冷漠。
对瓦格纳的文化身份加以辨识,事实上也包含一种 “文化”与 “文明”的辩证法。歌德在预言“世界文学时代”时说道: “为了影响世界,德国人不应该将自己限制起来,相反地,必须将世界装入自身。”[13]336这在托马斯·曼看来,不啻为解决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而这种思想方式在瓦格纳那里获得了完美的展现。瓦格纳艺术固然是 “德意志性”的 “最为感性的自我展现和自我批判”,而同时也能 “使德意志对一个哪怕只有最平庸的智商的外国人都显得有趣”。[18]69尼采曾认为瓦格纳的欧洲特性过多而将他指认为浪漫主义的堕落者。而托马斯·曼认为尼采错了,因为瓦格纳的“德意志性”强大而纯正。瓦格纳正是通过这种 “德意志性”而实现了与世界主义的伟大统一与互动,而这正是 《威廉·迈斯特》早就决定了的方向。
在以歌德为主星的德意志精神星丛中,尼采也受到托马斯·曼最多的批评。这是因为尼采对于 20世纪泛滥成灾的非理性主义真的难辞其咎。1947 年,托马斯·曼发表了 《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
“我们的体验”,最大的体验便是两场世界大战了。纳粹主义通过战争与屠杀,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尼采也被捆绑上德意志战车驰向不义之战的前线。托马斯·曼的思想努力便是将尼采从这架战车上解救出来。这篇论文的主旨便是给尼采正名,或者说拯救那种被纳粹主义所玷污的尼采哲学。
托马斯·曼的策略无它,还是将人本主义的的阐释策略贯彻到尼采哲学中。但这一次则多出了许多批判性。对尼采的批判,正如写作 《浮士德博士》一样,本质上是德意志的自我批判,但这种批判,从另一角度看,则是对 “德意志性”及其可能性的理智扞卫。
在托马斯·曼看来,作为叔本华的追随者与反叛者,尼采一生的思想主导动机便是疯狂地珍视着“文化”。“文化”概念意指着生活、艺术和本能。生活的本质就是建立在假象、艺术、错觉、前景和幻象之上的,因而 “文化”的天敌就是意识、知识、科学,还有道德。尼采用以狄奥尼索斯这位酒神为代表的审美主义向以苏格拉底这位 “理论人”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发起了反攻,从而让德意志精神、德意志音乐和德意志哲学得到复活。然而,尼采激烈的非道德主义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并必都是立得脚的。
首先,尼采指认出道德认识所诉求的真理性,事实上是建立在 “兴趣” (Interesse) 之上,就此而言,只有审美比道德更接近真理,而生活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有存在的理由。但托马斯·曼却看到,非道德的尼采,其禀性恰恰是清心寡欲和道德主义的,而其真理概念也是苦行主义的,因为尼采不认可愉悦的真理,认为真理是令人痛苦的。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只能证明那种建立于真实性之上的道德的僭妄,但这不能成为扼杀道德的理由,相反地,他是让道德从自己的真实性中自我扬弃出来。而从 “我们的体验”而来,尼采的非道德主义也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上犯下了 “不啻灾难的错误”。
其一,尼采颠倒了本能与理智之间的力量对比,好像理智成为危险的主宰,而本能则亟需抢救。但只需看看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人们便会即刻醒悟: “似乎最微不足道的危险就是人世间可能有朝一日太重精神! ”“生活被人的精神毁灭还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才可能呢。”[19]
其二,尼采错误地将生活置于道德的对立面,而事实上,生活与道德乃是休戚相关的统一体,真正与道德对立的是审美。然而,膜拜审美的希腊人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尊崇伦理的犹太人在失去了国家之后绵延了数千年。
在托马斯·曼看来,尼采的这种错误恰恰在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精神导师。尼采的审美主义鄙视商业精神,而帝国主义是工业化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联盟,他们以赚钱的精神发动战争 (在这里,托马斯·曼悄然地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又怎么可能为尼采所接受呢? 诚然,尼采是将战争视为保存文化活力的方式,但托马斯·曼认为,自 1870 年后,尼采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平静的市民时代,平庸的商业主义氛围促使尼采想像战争的伟大作用,这说到底乃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市民之子的幻想。事实上,连康德这样的和平主义者都认为长期的和平会导向庸俗的商业精神,无怪乎尼采这位呼唤超人的思想家为何渴望血与火的洗礼了。托马斯·曼颠覆了尼采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图式:“我不信是尼采铸就了法西斯,相反,是法西斯塑造了尼采,我想说,尼采实际上是不问政治的,是无辜和精神的……”
[19]178,这种正本清源的论述策略与辨析瓦格纳的民族主义问题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尼采哲学的精神本质是非政治的审美主义。在托马斯·曼看来,审美主义的确为开创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作出了贡献,但与王尔德对恶加以浪漫化一样,尼采的审美主义与野蛮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无法真正地对应 20 世纪上半叶的人类浩动。所以,应该重申道德主义。因为通过贬抑理性来扞卫道德只能是一时的修正,而要真正地扞卫生活只能通过精神或道德。由于尼采认为一切判断只是以兴趣为基点,因而在生活之外别无什么道德的法庭。但托马斯·曼并不认同这一论断。他认为,即便真的不存在道德的法庭,但也确乎存在一个精神的法庭,而其中的仲裁者便是 “人的精神,与判词相联系的、作为批判、讽刺和自由的人性本身。”——— “这精神就是生活的自我批判。”[19]172精神作为生活的自我批判,这一言简意赅的论断,的确指出了尼采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而生活的自我批判的可能性,便是人性的可能性,也就是重建精神、道德、理性、乃至于新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一视角下,托马斯·曼认为,尼采 “上帝死了”的预言,在恰恰预示了一种无神论的人性论: “他倡言的超乎一切教派之上的宗教信仰只能是和人的观念相联系的,只能是一种以宗教为基石的、带宗教色彩的人本主义,只能是一种饱经沧桑、阅尽世事、将一切关于低贱和魔邪的知识纳入它对人类奥秘的尊崇中的人本主义。”[19]187
三、结束语
早期的托马斯·曼,以德意志精神苍穹的璀灿星辰———叔本华-瓦格纳-尼采的艺术思想作为自己文化视野中的主要星丛。而当他从 “眷注死亡”转向 “献身生命”时,即在人文主义转向之际,歌德的人性观如同一颗启明星绽放出最为耀眼的光芒。在其思想披照下,叔本华-瓦格纳-尼采星丛转而焕发出人本主义之光。这种人本主义,是在 “德意性”的文化土地上、并以 “人性”的拱顶石而屹立着的精神建筑。这并不是高超而细密的思想建筑术,而只一幅粗略而又意味深长的建筑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