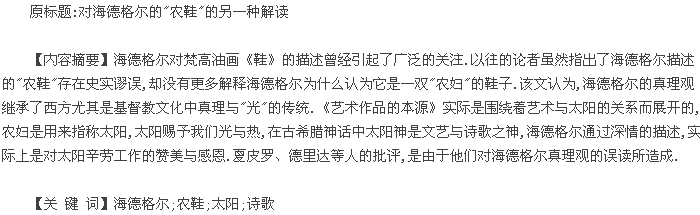
荷兰画家梵高在1886年画了一幅题为《鞋》的作品,现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里.这幅并不出名的画,由于海德格尔在1935-1936年间的讲座《艺术作品的本源》(以下简称《本源》)以及《形而上学导论》中的深情描述而广为人知,并成为现象学描述的范例,并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辩.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两次引用时态度并不一致,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用的是农夫的鞋,而在《本源》中则为农妇的鞋.这就成为德里达驳难之处.夏皮罗在《描绘个人物品的静物画:关于海德格尔和凡·高的札记》一文中指出,这鞋根本不是什么"农鞋",而是凡·高自己的"城鞋"[1].并由此对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观提出质疑.一个是早期受过神学训练、惯长哲学幽思的思想家,一个是受过英美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的艺术史家,海德格尔的阐释与夏皮罗的指缪,实际显示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夏皮罗指缪后,海德格尔的文本并没有丝毫更正,之后,雅各·德里达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也围绕这幅画进行了讨论.德里达在《绘画中的真实》一文中,将论述引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从解构思想出发,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甚至对画面是否是双鞋都产生怀疑,并不认为这双鞋是一双,而且都是左脚的[2].他认为海德格尔对这幅画的描述是既可笑又可悲的.譬如"图解"时一本正经的学术态度和言之凿凿的轻率语调;急匆匆地消费绘画再现中的内容;描述中事无巨细的复杂化;究竟是在谈论画、"真实的"鞋,还是外在于画的而且还是想象的鞋……杰姆逊则在这幅画中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以为,以上论者存在对海德格尔原意的重大误解.为了分析,我们有必要把两个文本中关于农鞋的描述进行比较:

其一,《形而上学导论》:海德格尔在开篇提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问题后,在众多的举例中提到凡·高《鞋》的油画的:
梵高的那幅油画:一双坚实的农鞋,别无其他.这幅画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出.但你立即就单独与在此的东西一起在,就好像一个暮秋的傍晚,当最后一星烤土豆的火光熄灭,你跩着疲惫的步履,从田间向家里走去.什么东西在此在着呢?是亚麻画布呢?还是画面上的线条?抑或是那斑斑油彩?
其二,《本源》:在谈到器具的器具性时,他提到了这幅鞋的油画:
从梵高的画上,我们甚至无法辩论这双鞋是放在什么地方的.除了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外,这双农鞋的用处和所属只能归于无.鞋子上甚至连地里的土块或田陌上的泥浆也没有粘带一点,这些东西本可以多少为我们暗示它们的用途的.只是一双农鞋,再无别的.然而--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
然而,我们也许只有在这幅画中才会注意到所有这一切.而农妇只是穿这双鞋而已.要是这种径直穿着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夜阑人静,农妇在滞重而又健康的疲惫中脱下它;朝霞初泛,她又把手伸向它;在节日里才把它置于一旁.这一切对农妇来说是太寻常了,她从不留心,从不思……[3]两段话的表述大相径庭.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举例的目的是追问存在,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存在者,而没有存在,也认为这鞋只是农夫鞋(Bauernschuhe).
这双鞋既然什么也没有说出,那就是说出了"无",也就是存在.而到了《本源》中,农 夫 鞋 迅 速 地 变 为"农 妇 鞋"(B uerinschuhe),这段充满想象又诗意盎然的描述简直将农鞋提到了至高的地位,却又显得过度阐释,而真正值得思索的问题是:第一,关于农鞋的画作绝不仅仅只有梵高才有,海德格尔为什么偏偏选择梵高的画进行反复描述?第二,为什么海德格尔将农夫鞋改为农妇的鞋,并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深情地描述?第三,为什么单单要选择鞋子,而不是其他物品,比如手在生存论上更为重要,为什么不选择一幅关于"手"的绘画,难道不是更能表达生存的艰辛?
一、为什么选择梵高的画?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海德格尔为什么选择梵高的画.梵高出生于基督教牧师家庭,基督教信仰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画作表现的是北欧民族基督教文化现实中个体与整体关联的内在激情.梵高回归到一种本真原始生命的冲击力,选择了基督文化的精神内核:光,作为神性的艺术化身,太阳隐喻成神的艺术语言,而用以"向日葵"为核心意象.
在具体绘画创作中,光线具有重要的作用.1885年9月,梵高在圣雷米给弟弟提奥的信就直言:"我多么渴望见到强烈的阳光,因为我认为一个人不了解光线就无从理解德拉克洛瓦作品的基本手法和技巧的要点.在北方,我感受到的色彩是遮掩在雾霭中的.这儿的一切是非常真实的."[4]
关于梵高的画,另一位被海德格尔称为"法国最爱思考的头脑"的思想家乔治·巴塔耶也进行过分析,他在写于1930年的《献祭的损毁与文森特被切除的耳朵》一文中,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本质上,艺术是艺术家的一种献祭活动,其献祭的对象就是普照大地的太阳,它赐予我们光和热,使万物得以生长,并赋予我们的生命以基本的意义,而艺术就是我们向太阳献祭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
巴塔耶指出,梵高的这种向太阳献祭的活动不仅表现在切割耳朵这样在现代人看起来比较极端、残酷和非正常的行为,其实,向太阳献祭始终是他的作品中一个异常重要的主题,其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非常集中的对于太阳的描绘.
梵高有许多幅关于太阳的画,巴塔耶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理解凡·高绘画中的太阳,或者,为了能够理解而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画家的个性,甚或是本人的一种病态的表现,其原因即在于没能理解梵高的绘画实际上是向太阳的一种献祭所致[5].他最着名的画并不是农鞋,而是《向日葵》,这是他向太阳献祭的一种变形.在法语中,向日葵和太阳是同一个词Soleil,在英文与德文中则为Sunflower 与Sonnenblume,也是"太阳花"的意思,并且,它不仅形态像太阳,它本身就是对太阳献祭的产物,正因为它始终是面向太阳的这个特点,我们汉语也习惯将其称为"向日葵".
在《逻辑学:真理问题》一书中,在谈到绘画的描绘时,海德格尔谈到了梵高的《向日葵》:"然而,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描绘了什么呢?如果这画没有经受苦难,就不会损坏,考虑到这位艺术家出发去描绘凋零和损坏的向日葵,他将通过并不是制作了一幅损坏的画,而是通过制作一个完美的作品,他描绘了他所意指的:凋零的花,从而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当我们接近或自然地理解这幅画,我们就能看到他描绘了什么."[6]
对海德格尔而言,艺术作品就是一种揭示活动,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说:"诗无非是基本的付诸言词,即发现作为在世存在的生存,随着(诗的)说出,先前盲目的他人才得以首次看见世界."[7]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不是流俗的"符合论"的真理观,他认为在"真理"的古希腊文" λ θεια"(alethetia)中,否定前缀"α"包含褫夺、遮蔽的含义,而"λ θεια"则表示显露、解蔽的含义,因此真理" λ θεια"是对遮蔽的解蔽,是显现与遮蔽(隐藏)的不断"争执"(Streit)的动态的发生过程.
什么是遮蔽呢?在《无蔽》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对希腊人来说,"遮蔽"意味着太阳沉到云层下,在云层背后消失.那么"解蔽"就意味着太阳浮出云层、显现出来、发光.
他终生关注人类生存与时间的关系,他的真理观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尤其是基督教认为真理是"光"的传统,这"光"来自太阳,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的不断显现与隐匿的周期性轮回就形成了人们基本的时空意识.由于太阳对人类生存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太阳在海德格尔诗学中也具有中心地位.
二、Ereignis 与太阳
在《本源》后记中,海德格尔说:"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作为精神的显现,艺术归属于Ereignis(笔者暂译为"事件"),而'存在的意义'(参看《存在与时间》)唯有从事件而来才能得到规定."[8]"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集中到探讨的根本位置(eigentlichen Ort)上,我们在那里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语言的本质和诗的本质……一个从外部很自然地与本文不期而遇的读者,首先并且一味地,势必不是从有待思的东西的缄默无声的源泉领域出发来设想和解说事情真相.这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深感迫切困难的是,要在道路的不同阶段上始终以恰到好处的语言来说话."[9]
为了正确读解《本源》,我们必须先来理解"Ereignis"."Ereignis"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中心词语,在早期,海德格尔通过它强调前反思、前理论的非主客二分的原发境域,是在实际生命体验中相互关联的整体意蕴世界,是纯粹认识,也如黑格尔所说这纯粹认识就是光,是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给予者.海德格尔是依此在生存的有限性(也即时间性)对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进行分析.日夜交替形成了我们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时间意识.对海德格尔而言,时间的意义就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时机,即做某事的正确的时刻.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其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切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10]日出之时,我们要对我们新一天的生活做出决断,这日出就是生存论上的"Ereignis"(事件).必须指出,"Ereignis"本是个日常德语,但在基督教中却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指的是耶稣的出生、死亡、复活、再临的根本"事件".在天主教中,太阳升起代表复活[11].三重复活是指:耶稣的复活、大自然每天黎明的复活以及我们内心醒悟的复活(也就是我们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因此海德格尔将"Ereignis"和"Dasein"写为"Er-eignis"和"Da-sein"来表示去主体性之意).因此"Ereignis"既是生存论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也有"使成已""破晓""生成"等诸多含义,它又归属于"自然",它与"自然"是同义的.它的丰富意蕴确实是不可翻译,但又始终是一个语言问题.这也是他对保罗书信中的基督再临的时刻做了生存论读解的结果,正如保罗在致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并没有回答基督何时到来的问题,而是将时间与帖撒罗尼迦人的具体生存联系起来:"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帖前》5:1-3)也就是说,时间的意义在于基督徒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决断自身.
太阳落山后,月光、星光作为对太阳光的折射,如同镜子一般,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乃是"镜象游戏"(Spiegel-Spiel).是月光带给我们太阳的消息,指引着黑暗中的人们走向归家之路.日月交替形成我们基本的时间意识.他认为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这曾在者就是指太阳的离去与复归.日月交替所形成的时间观在他的思想中具有核心的地位,这从他将康德的时间观解释为"天时",将尼采的思想归纳为太阳、月亮交替的"永恒轮回"学说,在他对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等人诗歌的解读之中处处可以见出.在作于1966/67年的《赫拉克利特研讨》一书中,海德格尔和芬克(Eugen Fink)探讨了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永恒的活火",并指出,这"永恒的活火"就是尺度,就是带上前来 的 东 西(bring-force-to-appearance).
而"过 去""现 在""将 来"的 三 维 时 间("was""is""will be")就来自于常在、永恒[12],因此,"永恒的活火"使得三维的时间成为"四维"时间,而本真的时间就是四维的.这也为我们理解"Ereignis"提供了参考,海德格尔在1962年的演讲《时间与存在》后的讨论班上,认为Es gibt(它给予)的"Es"就是"Ereignis",就是将三维时间带上前来的东西,那么"Ereignis"就是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永恒的活火",正如他们后续讨论所认为的,从根本上就是指太阳,是太阳提供了我们最基本的时间--空间意识,提供光和热使得生命得以生长持存,因此,作诗与思想(Gedanke)确实就是一种感恩(Danken).
对太阳的崇拜活动普遍存在于原始时代的人们之中,这从一些原始壁画与艺术作品中都可以充分看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同时也是文艺之神.
在一首《Ereignis》中,海德格尔写道:
火焰在燃烧
热和光产生
心和目光
靠近
在一起
存有
冒出火花
和谐的本已的火,
一个火炉
非凡的
年岁的延续[13]
从这首诗我们明显可以看出Ereignis 与太阳的紧密关联.
三、农妇与太阳
为什么海德格尔独断地说这是双农妇的鞋?以往的论者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农妇是如此辛劳,朝霞初泛时就穿起它劳作,直到夜阑人静时才脱下它.从常识上看,她难道中间不吃饭?她没有孩子?
为什么只有在节日里才脱下它?这里是描述真正的农妇吗?笔者认为,只有从整体上了解海德格尔诗学,才能真正理解这段话.在德语中,太阳(Sonnen)为阴性,而在海德格尔的诗学体系中,农妇(B uerin)往往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尤其体现在海德格尔对黑贝尔方言诗的解读中.在《语言与家乡》一文中,海德格尔在阐释黑贝尔的诗歌《夏日傍晚》时说:"诗的第一段把太阳这位疲惫的妇人的返乡带入视野,特别是太阳的落山,沉落到隐身地守护着的静寂……同样,在《夏日傍晚》这首诗的第二段中,呈示出了劳作的间域,在居家,在田野,在山林,在峡谷,太阳无处不操持地劳作着.因为当此之时,来自四面八方的万事万物无不期盼太阳的赐予,渴望着太阳赐予丰满的生长和丰满的收成."[14]
而太阳落山时,天幕垂下一道绚烂的晚霞,告别着的太阳发出最后的致意.诗的第八段第一行写道:"看哪,她疲惫地依坐在山巅!"海德格尔阐释道:"这是刚干完活准备回家的农妇,在田边地头的小路上一屁股坐下来休息时凝视到的景象."[15]"粗略地说,《夏日傍晚》这首诗游动在一种太阳与黑森林农妇的比拟中,在那首名为《哈伯穆斯》(Das Habermus)(《阿尔特维克》Altwegg,第1卷,第104页下)的诗中,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现在我们阐释的这首《夏日傍晚》互为唱和,黑贝尔在那首诗中这样说太阳:多么浪的女人,却又如此善良而宜人!……还有人会否认,在这里,如同在《夏日傍晚》一样,太阳被比作慈母般的农妇?"[16]海德格尔在《黑贝尔》一文中也谈到了农妇与太阳:
自然之自然性物是太阳、月亮、星星的那种升与沉,此一升与沉径直吁请着居着的人,由此一吁请而将世界之秘密向居着的人娓娓道来.尽管在对世界之筑居的科学启蒙中把太阳思索为哥白尼式的,然而,这个太阳也同时保留在自然性的自然之内,这在黑贝尔的两首诗中表现出来:一首是《尤物女人》,从她的身上"散发着光与热的源泉""吁请着万物的惠允";另一首是《多么的亲善与合宜》.(《哈伯穆斯1》,第104页下;《夏日傍晚1》,第78页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认为鞋子的主人是农妇而不是农夫,太阳赐予光与热,具有着孕育万物的力量,使得万物得以成长.
四、为什么选择鞋子?
梵高的代表作是《向日葵》,为什么海德格尔却选择《鞋》进行论述?正如德里达所说,这关涉到脚,但不是如他说的是海德格尔或夏皮罗的脚,而是太阳的脚.太阳怎么会有脚呢?这必须了解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海德格尔终生强调向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思想学习,赫拉克利特对他有着重大的影响.必须指出,《艺术作品的本源》
隐匿地贯穿着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如文中在提到大地与世界的"争执"时,专门提到了赫拉克利特的残篇B53(战争是一切之父,一切之王.他使有的成神,有的为人;他让有的沦为奴隶,有的获得自由).太阳在赫拉克利特思想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提供尺度,区分四季的界限.他的残篇第3说道:"太阳的广度为人脚之宽."在《赫拉克利特研讨》中,海德格尔与欧根·芬克(Eugen Fink)专门对残篇3进行了探讨,芬克说:"作为一个现象,太阳具有人脚一样的宽度."海德格尔说:"当你说到'现象',你的意思是它在自身中展现,并且不是'现象学的'."芬克说:"残篇3同样以寓言的方式来表达的.
它开头是这样说的,拥有自己的光亮的太阳作为光源所占的位置是很小甚至微不足道的,太阳的打开力在整个被照亮的空间所占的位置很小,这种打开的力量隐藏在被它所打开的事物中,作为光源,她被她所照亮的事物包围.在这种程度上太阳在天空的出现以人脚的宽度显现,上升、下落并且消失,她每天都是新的,如残篇6所说的:太阳不仅如赫拉克利特所言,每天都是新的,而且会永远常新.""赫拉克利特没有给出科学的规定如何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每天的新与她每天都是同一的并不矛盾.她是相同的,但总是新的.
我们必须保持在这个思想,关于作为永恒的活火的形式的太阳,它永久在(is),但是--如残篇30所说--作为按比例点燃和熄灭,在持续的更新中表现自身.当我们看到残篇30,尺度的概念将允许自身更精确的决定."[17]
从我们人类的视角来看,相对于天空的辽阔,太阳所占位置很小,移动又非常缓慢,所以赫拉克利特说太阳的广度为人脚之宽.海德格尔通过深情地讴歌一双农妇的鞋子,实际是描述太阳从日出到日落辛勤的照耀.太阳按节奏地升与落所形成的昼与夜的交互变换,是形成海德格尔《本源》中"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思想基础.世界的敞亮与大地的隐匿就相对于白昼与黑夜."农妇"为什么只有在节日时才把鞋子置于一旁呢?节日是休息的时间,笔者以为"节日"相对于"日食",当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时,太阳的光度被完全或部分遮挡,就会发生"日食",也就是太阳"休息"的时间.
如果我们以上的解释仍显得牵强,我们可以再来分析海德格尔后面所举的例子,C·F·Meyer 的诗歌《罗马喷泉》(Derr mische Brunnen)与希腊神庙.那么多首诗歌,海德格尔却偏偏引用《罗马喷泉》,显得奇怪而突兀,他实质上并不是在说喷泉,他在这里实际是强调喷泉"Brunnen"与燃烧"brennen"之间的词形关联.太阳给予我们光与热,是万物生长的源泉,这首诗就是在描述太阳对万物无声的永不消歇的无私赐予.我们再来分析希腊神庙:
"岩石的璀璨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得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显露出来."[18]
"在建立作品时,神圣(Heilige)作为神圣开启出来,神被召唤入其现身在场的敞开之中;在此意义上,奉献就是神圣之献祭.赞美属于奉献,它是对神的尊严和光辉的颂扬.尊严和光辉并非神之外和神之后的特性,不如说,神就在尊严中,在光辉中现身在场."[19]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什么是神?答案正如他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诗歌所言: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如苍天般昭然?
我宁愿信奉后者.
神就是天空之物,而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时,海德格尔分析道:"'在光明之上'的至高之物,乃是光芒照耀的敞空(Lichtung)本身.按照我们母语的一个较为古老的词语,我们也把这个纯粹的敞空者,也即首先为每一'空间'和每一'时间''设置(在此即提供)'敞开域的敞空者,称为'明朗者',它是三合一,既是明澈,又是高超,又是欢悦,一切纯净之物都沉浸于明澈之光华中,一切高空之物都矗立于高超之威严中,一切自由之物都回荡于欢悦之运作中."[20]我们就此可以看出,这作为"明朗者"的神,除了太阳外,不会再有别的.
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引用了另一位诗人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
歌声飘扬于变化之上,
更遥远更自由.
还有你的序曲歌唱不息,
带着七弦琴的神.
作为这首诗的中心的是"带着七弦琴的神"(Gott mit der Leier),它究竟何指呢?这里明显在指太阳神阿波罗.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音乐之神的是太阳神阿波罗,他善谈七弦琴(Lyre),下辖七位缪斯女神,所以音乐也叫μουσικ (英文music,德文Musik).而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所用的乐器则为复笛(Aulos).
海德格尔对梵高农鞋的阐释,是借助于作品来阐发他自己的生存论思想,夏皮罗等人的指缪也显示了这种"六经注我"式的阐释可能与具体艺术史实并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背离,这也体现在海德格尔将特拉克尔诗歌中的"妹妹"解读为月亮,以及对荷尔德林诗歌的一系列误读之中,如《还乡--致亲人》,这里并不是在讲诗人荷尔德林的还乡,而依然是描述太阳不断轮回的运动以及对它所爱着的人类("亲人",verwandten)无私的赐予光与热的活动.太阳在我们看来是"东升西落",但它始终在运行着,始终"在途中",因此"返乡"永远不能到达"故乡".
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对于伟大作品而言,作者只是一个通道.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作者的个性消失于作品背后,因此,是作品本身在"说话".海德格尔依时间性对此在生存论结构进行分析,日月交替所形成的时间观是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进行解读的主要出发点.
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人类操劳着的生存活动就是在这时间性中展开的,海德格尔讴歌太阳辛勤的劳作,实际是讴歌人们生存活动的艰辛.也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你伟大的天体啊!你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你有何幸福可言哩!十年来,你向我的山洞这里升起:如果没有我,没有我的鹰和我的蛇,你会对你的光和行程感到厌倦吧.可是,我们每天早晨恭候你,接受你的充沛的光,并为此向你感恩."[21]
结语
太阳是对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一个天体,太阳赐予万物光和热,使得万物得以成长.在古代先民中存在着普遍的太阳崇拜,表现于各民族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古希腊传统中,太阳与文艺密切相关.太阳神是文艺、音乐、诗歌的保护神,又是预言之神、航海之神.在德尔斐(Delphi),太阳神阿波罗的神谕由他的女祭司皮提亚(Pythia) 发布,再由"宣告者"(Prophetes)编排成诗体向请求者宣告.做诗首先就是倾听阿波罗神的话语而跟随着道说.正如巴塔耶所说,艺术从本质上就是向太阳的献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出日落形成了人类最基本的时空意识,海德格尔对艺术的论述是围绕着太阳而展开的,正如他后期在《语言与家乡》一文中对诗的本质的论述:"在诗的话语中,不重现任何被给定的东西,而是在场地向着太阳夏日一天的劳作而诗,因为此诗的言说才把这整日的劳作赋予我们.这丝毫不是诉说有关太阳的事;反倒是,太阳教我们说,并向我们说,我们因之才有了说这回事,前提是,我们倾听到诗着地言说."[22]
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以为,虽然确实有违艺术史实,但海德格尔对农鞋的描述是大有深意的.他的本意并不单是描述农妇或农鞋,而是通过农鞋来展现"农妇--太阳"辛勤的劳作,是对太阳的讴歌.《本源》中的文本隐匿地围绕着太阳而展开,他表达得如此晦涩,并不是海德格尔故弄玄虚,而是他为了保持所说之物的神秘性,以唤起人们的敬畏与感恩.只有从整体上理解了海德格尔诗学思想,才能对他对农鞋的描述做出正确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