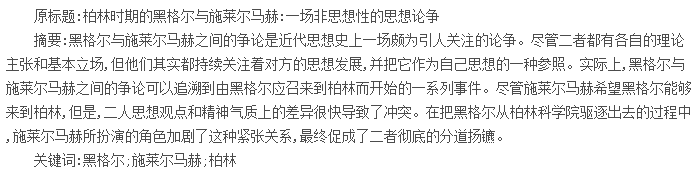
要弄清楚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历史性争论,通常都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对于一个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的阐释者来说,所遭遇到的第一个层面的困难就是他们各自思想的复杂性。时至今日,关于二人基本著作的阐释仍然没有在学界达成定论。第二个方面的困难是文献和文本方面的困难。两位思想家都在相当多的文献中就某些相关主题表达过自己的思想。黑格尔著作的丰富程度自不必说,施莱尔马赫著作的数量也不少。
这里面既有整部的著作,如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基督教信仰》,也有通过讲演、笔记的形式形成的大量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演录》、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而且,这些主要著作都有多次修订和再版,大量文献和文本的出现无疑为理解和阐释这两位大思想家的思想增添了极大的困难,更不用说有关二者的对比性研究了。第三个也是更进一步的困难在于,二者思想所涉及的主题领域有所不同。黑格尔偏重于哲学,而施莱尔马赫更多关注宗教,尽管二者分别在宗教领域和哲学领域内都有涉足和研究。这一点就导致了对二人间差异、对立和冲突进行具体阐释和评价的立场和角度上的偏差。从宗教哲学家们的立场来看,无疑会对施莱尔马赫更抱有同情与好感,然而从哲学家的角度去分析,又会更多偏向于黑格尔,而对施莱尔马赫持更多的批评意见。例如,通常的看法会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缺乏有关宗教体验和宗教经验的成分,而施莱尔马赫则在系统性和辩证逻辑上有所欠缺。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在对二人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或对二人间的差异性进行阐释的时候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局面。带着这一系列的困难和困惑,本文试图还原到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真实境况,来追溯和探寻这两位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发生的历史真相。
一、早期的相遇以及差异的前兆
作为准同事,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都曾卷入德意志理智重估的浪潮中,这一浪潮紧跟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欧洲,其中心问题就是有关宗教信仰的地位问题,以及宗教哲学与传统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曾经撰写过青年黑格尔和青年施莱尔马赫传记的思想家,威廉·狄尔泰坚持认为,在1800年前后的那段时期中,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思想分歧。
狄尔泰要求人们关注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所发表的《1800年的体系片段》。其中黑格尔就认为宗教“并没有要求成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这说明他承认存在有并非是由理性范畴所形成的宗教维度。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似乎与青年施莱尔马赫相一致。但事实上,黑格尔同时也认为,尽管宗教就其自身而言可能“并没有要求成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但对于哲学来说,站在宗教的立场上作出这种声明本身就是很愚蠢的。通过论断“无限者被有限者所感受到的神圣情感,只有通过把反思附加其上并对它加以支配的事实才是完整的”,黑格尔预示了他成熟时期的观点。通过断言宗教不仅仅植根于非理性基础之上,并且为了对其加以最充分的表达,还必须把反思和理性附加其上,黑格尔指向并预示了他后来对施莱尔马赫的一系列批判。尽管如此,狄尔泰认为这两位思想家在早期具有许多相一致的地方。例如,他们二人都试图对宗教、哲学、政治学以及伦理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论和研究,都在给贵族家庭做家庭教师期间度过了相当长的学徒生涯。
在早期的神学论文中,黑格尔在寻找一种有关宗教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宗教看作是群体性生命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在近代把一种政治共同体联合起来,正如古希腊的城邦受到古希腊神话的塑造一样。因此,在其第一部哲学著作中,他对《论宗教》的作者给予了评价。尽管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一书是匿名发表的,然而作者的身份实际上广为人知。黑格尔对《论宗教》一书的看法,简要地出现在他于1801年在耶拿所撰写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论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别》的序言部分:“诸如《论宗教》之类的现象并不可能与思辨的需要直接相关。然而它们及其被接受表明了对哲学的需要,这种哲学能够为自然在康德和费希特体系中所遭受到的粗暴对待加以补偿,并且使理性自身与自然相和谐,并非是通过理性放弃自我,或者变成自然的一个索然无味的模仿者,而是凭借理性出自其自身的内在力量把自己投射到自然当中。”
严格来说,这种评价其实并不是一种批评,相反,黑格尔把施莱尔马赫青年时代的作品看作是有关那个时代所追求的对宗教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充分理解、一次重要表达。黑格尔也同样意识到,施莱尔马赫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论宗教》受到同时代人们的广泛欢迎和接受,然而,黑格尔还是认为《论宗教》确证了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并暗示出他自己的哲学的必要性。可见,此时的黑格尔对于施莱尔马赫并没有公开的敌意。
然而即便是在这最早的时期,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仍然有分歧。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黑格尔对《论宗教》给予了某种更具批判性的解读,在1802年的《信仰与知识》中,他对《论宗教》的评论变得更加谨慎。在批判雅可比直观哲学的一段文字结尾处,对于施莱尔马赫过分依赖于直观以及具有这些直观能力的个体,黑格尔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认为施莱尔马赫有关宗教的观念植根于某种主观经验,面临着永远不可能获得一种充分的客观显现的危险。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如同艺术家一样拥有自己的灵魂,但却未能客观展现在艺术作品当中,而文化不仅仅要求具有灵魂,也同样要求有作为其客观化显现的艺术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讲,黑格尔对《论宗教》的阐释是合理的,并且有某些文本上的依据,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就是施莱尔马赫事实上是把讲道活动看作是基督教艺术形式的具体体现。对施莱尔马赫来说,一个好的讲道本身就是宗教艺术作品,除此之外,教会也是宗教艺术的一种公共展现。对于《论宗教》中的施莱尔马赫来说,社会的和公共的维度是第二讲演与第五讲演之间联系的桥梁。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有关宗教团体的看法的深层次差异。
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教会作为真实存在的宗教团体具有其自身作为人类救赎组织的存在理由,并且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教会应该独立于政府。而与之相对照,黑格尔则更加强调在政府教育和道德生活背景下宗教的公共服务功能。因此,在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论宗教》的早期反馈中,能够瞥见二者最早的差异和不同,这些差异将会在日后二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不断放大。
二、柏林大学的同事与二人间的政治分歧
1814年在纽伦堡的时候,黑格尔希望他能够很快获得一个固定的大学职位,他的朋友,也是他在图宾根的早期学生海因里希·保鲁斯,写信告诉他柏林大学哲学教席的空缺,以及柏林方面在任命费希特的继任者问题上的分歧。保鲁斯同时也向黑格尔报告,施莱尔马赫的一个很受欢迎的同事,教授解经学和历史神学的德维特支持他的老师弗莱来担任这一职位。而除了弗莱,这个哲学教席的其他主要竞争者就是黑格尔。在当时,凭借《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这两部著作,黑格尔的学术声望已经确立。
在争取这一任命的过程中,德维特写信给他的老师弗莱,告知他有关他的神学同事菲利普·马尔海内克试图邀请黑格尔作为费希特的继任者的情况。与此同时,施莱尔马赫的助理教授和未来的继任者奥古斯特·特温斯特恩写信给施莱尔马赫,抱怨黑格尔的《小逻辑》晦涩难懂。施莱尔马赫回复说,尽管他还没有亲自读过这部著作,但是依据相关评论来判断,他也有类似的印象。
1815年在考虑黑格尔是否适合作为未来同事的时候,施莱尔马赫有充足理由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自己的思维模式构成了一种挑战。尽管有黑格尔对《论宗教》一书的批评在先,尽管在1811年被正式接纳进入柏林科学院时施莱尔马赫在演讲中对黑格尔的哲学表示过深深的怀疑,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施莱尔马赫对黑格尔曾产生过彻底的质疑,并希望阻止他进入柏林大学。因此,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思想分歧,冒着有可能会得罪他的朋友和同事德维特的危险,施莱尔马赫还是投票支持黑格尔就任柏林大学哲学教席。学术委员会于1816年1月4日批准黑格尔担任费希特的继任者,但是迟至10月这一任命还没有获得官方批准。施莱尔马赫甚至颇有微词地抱怨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大学将会变成什么,如果它一直缺乏哲学家的话。”
最终这一任命在种种催促和质疑声中获得官方批准,黑格尔在1818年应召来到柏林大学,与施莱尔马赫成为了大学同事。
在当时的柏林,施莱尔马赫的学术影响很大,但是,随着1821年《权利哲学》的出版,黑格尔早期有关《论宗教》的看法中所预示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一下就被扩大化了,政治哲学也因此成为他们之间第一次公开决裂的契机。两位思想家早年虽然都有相似的经历,年轻的时候都曾经亲眼见证过法国大革命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而且他们曾经短暂任教过的大学(1806年的哈勒大学和耶拿大学)都曾由于拿破仑的占领而被迫关闭,也都深知革命给他们那个时代所带来的种种骚乱,都感受到民族文化和德意志统一的缺乏,并且终其一生都试图把教学和著述活动同服务德意志文化联系起来,但是,这种相似的经历却并没有导致二人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
早在反映其所受虔敬派影响的早期著作中,施莱尔马赫就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生活必须在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其个人信仰从属于改革宗,但施莱尔马赫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教导,有时却更接近于马丁·路德有关两个国家的教义。施莱尔马赫坚持宗教生活和宗教团体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尽管它与国家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然而它却并非从属于国家。这一论点不仅出现在施莱尔马赫早期作品中,也贯穿其一生。相比施莱尔马赫,黑格尔有关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以及它对宗教生活的影响的看法显得更加保守。黑格尔认为宗教生活应该与国家和政府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宗教生活实际上从属于国家的内在教化和精神指导的领域。很显然,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信仰和教会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个位置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国家和政府。
三、柏林科学院事件
相比二者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而言,在把黑格尔从柏林科学院排除出去的过程中,施莱尔马赫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激起了黑格尔对他的敌意。
把黑格尔从这一组织中除名并不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事件,它的影响非常深远,并且进一步冷冻了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早已充满问题的关系。早在1811年施莱尔马赫在他被接纳为柏林科学院成员的演讲中,已经正式把自己与思辨哲学划清界线,并且建议,只有那种通过历史批判的方法所得到的哲学,才是唯一适合在科学院中提交的哲学,当黑格尔到达柏林的时候,这一敏感话题又进一步尖锐化。施莱尔马赫在传统文学领域内有影响的同事奥古斯特·博克,明确提出了反对思辨哲学的两条根据:思辨哲学的性质相比于其他学科更具自我封闭性,而不需要集体性的研究工作,而培养集体协作研究的精神正是成立科学院的基本宗旨和主要目的;凡思辨哲学应该加以表述的地方,在文学和历史学领域内都已经表述过了。
在有关柏林科学院历史事件的记载中,阿道夫·冯·哈那克坚持认为,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敌对直到黑格尔来到柏林之后才发生。哈那克相信,施莱尔马赫之所以反对黑格尔成为柏林科学院成员,更多地是基于有关科学院成员资格先前已颁布的政策规定,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敌意。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施莱尔马赫同时也终止了自己在哲学分部的成员资格,而只在历史和文学分部提交自己的论文。依照哈那克的说法,“施莱尔马赫担忧黑格尔哲学的独裁专制,起码能够使科学院摆脱它的控制”。从黑格尔对大学的影响力以及他接下来在学生中的影响来看,这一事件对黑格尔本人来说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学术团体,并出版了专门的学术期刊,大有与柏林科学院分庭抗礼之势。这个新的学术团体与柏林科学院有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它是在文化部而不是在大学的领导之下;其次,它试图在推进有关重要学术问题的学术性研究方面比科学院更加积极。到1828年1月的时候,这个学术团体的成员已经包括了威尔海姆·冯·洪堡、A.W.施莱格尔、歌德以及黑格尔以前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神话学家F.W.科洪策。由于这个学术团体与大学并不相关,因此,其团体成员并不仅限于柏林。当施莱尔马赫被提名为该学术团体成员的时候,黑格尔威胁,如果施莱尔马赫被获准加入的话,他将主动退出该团体。基于施莱尔马赫先前坚决要将黑格尔排除出柏林科学院的做法,黑格尔的这一回应并不出人意料。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学术团体就这样构成了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学术壁垒。
四、余论
作为柏林大学的同事,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之间的冲突和争论无疑为理解两个人的学术处境和思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线索,至少添加了不少饶有兴味的思想佐料。然而,其中让人感到些许遗憾的是,从这两位举世瞩目的柏林大学同事之间的相互争论和冲突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纯粹思想的争鸣与碰撞,从表面上看,它反而揭示出某些人性的狭隘和局限。其实归根结底,两人之间思想抵牾的最根本原因并非性格上的冲突,而在于二者作为当时在各自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正统学术观点的捍卫者,并且承担着那个时代所必需的对传统基督宗教进行合理阐释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一历史定位下,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才会产生这种既爱又恨的论争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