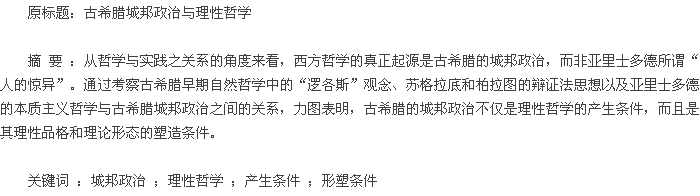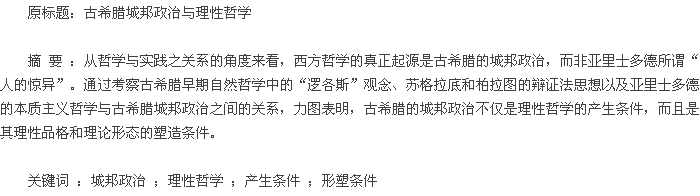
城邦政治和理性哲学被公认为古希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成就,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复杂的。最可引证这种复杂关系的莫过于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法庭判处死刑这一历史事件。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现行城邦制度看作败坏哲学本性的根本原因,并致力于探求适合哲学本性的理想城邦。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城邦政治和教育环境下,即使是那些最具哲学天赋的年轻人,其中也只有极少数“受神力保佑者”才有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哲学家。通过把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把“真理”的探究和“行动”的探究明确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似乎也就把哲学理论与城邦政治完全分离开来了。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从哲学家们的专门论述以及从对哲学文本的阅读中所得到的答案似乎都是 :一方面,人类的政治生活必须接受哲学的评判,尤其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哲学的指导下才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超越政治生活的,真正的哲学只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在本文中,笔者力图表明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理性哲学之间的肯定的相关性,即城邦政治不仅是理性哲学的产生条件,而且是其理性品格和理论形态的塑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在本性上就是政治性的。
一、作为理性哲学产生条件的城邦政治
作为有机统一体的城邦本身、城邦内部的公共空间以及普适法律,这些都是理性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为了证明这个论点,让我们首先引述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演讲辞中的如下段落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 ;但是在国家事务中,我们遵从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上的人,我们服从 ;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耻辱的法律。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 :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 :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 ;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是没有矛盾的 ;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是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事故的人。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曾经说过 :“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活层次 :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与公共的东西。”韦尔南则认为 :“只有当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这里的公共领域是两个意义上的,它们既相异又相关 :一是指涉及公共利益的、与私人事务相对的部门,二是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与密教仪式相对的公开活动。”
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领域的典型体现是公民大会和“公众集会广场”(agora)。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有同等的资格和机会成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有关城邦公共利益的议题都要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开、自由和平等的讨论。在公民大会上,话语是人们可以使用的唯一合法和有效的工具,话语的基本形式不是单向度起作用的格言警句,而是交互的论辩,话语的力量不是来自话语之外,比如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或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而是来自话语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我们知道,围绕话语本身的“说服力”而在智者和理性哲学家之间展开的论战正是理性哲学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二是普适法律。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像伯里克利所说的那样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一定是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即普适法律。韦尔南说 :“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图景,被伊奥尼亚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他认为,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使得城邦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心的圆形“宇宙”,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们所建立的世界模式就其几何框架而言是与此一致的。笔者认为,普适法律的出现在哲学上更为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逻各斯”思想产生的政治生活基础。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三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城邦本身。当伯利克里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时,那就意味着,没有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就没有作为公民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整体优先于并且在基本性质方面规定了公民个体。城邦的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城邦的共同善是城邦的最高价值,城邦若要存在,就必须维护这种价值。正是维护城邦的生存及其价值的政治需要促成了理性哲学的诞生。
二、话语政治 :修辞术与辩证法
正是城邦政治使得“话语”成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可以合法使用的唯一有效的权力工具,并催生了智者及其修辞术,进而导致了理性哲学的产生。“可以说,没有智者的思潮,就不能产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没有对智者的批判也就不能建立苏格拉底的哲学。”智者与哲学家之争,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实质上都是政治争论,最终是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公民个体与城邦整体之间关系的争论。在城邦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一种是智者的个人主义立场,即将城邦看作个人的汇集之所,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满足和促进个人利益 ;另一种是理性哲学家的共同体主义立场,即认为城邦是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足整体,个人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具有了公民身份并且有可能获得作为公民所应有的品格。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城邦就是把个人、家庭和村落等都作为部分包含在内的、以最高善为目标的政治共同体。所谓最高善就是城邦的公共善,它既超越个人私利,也超越家庭和部落利益,唯有以它为目标,城邦才能成为真正的有机整体(统一体)。“要真正配得上城邦这一名称而非徒有其名,就必须关心德性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 ;否则城邦共同体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联盟。”作为自足的整体,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人,这就类似于作为有机整体的人的身体优先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身体器官,一旦脱离身体,身体器官就将丧失其原有的功能,从而变成徒有其名的东西。个人依赖于城邦,并非仅仅因为每个人都在城邦中获得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更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能获得诸如公正和善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说 :“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本质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恶人,要么就是超人,他就像荷马所说的那种无族、无法、无情无义的人。
这种被逐出城邦的人立即就成为好战分子,他可以被比作一个在棋盘上被孤立起来的棋子。”只有在城邦生活中,人才有可能成为理性动物,也就是说,人首先必须是“政治动物”,然后才有可能成为“理性动物”。修辞术是一种“说服人的技艺”,在这一点上,理性哲学家与智者并无分歧,但他们对于修辞术的本质和根本目的的理解却完全不同。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高尔吉亚说,修辞术就是“用你的逻各斯使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或其他公民集会中的民众信服你的能力。只要具备这种能力,你就能使医生、教练成为你的奴隶,使商人弄钱不为自己而为他人,因为你能演说并说服多数人”。
可见,智者的修辞术仅仅为了帮助演讲者利用听众的弱点来说服他们,从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而不管演讲的内容是否真实,是知识还是意见,也不管在道德方面会对听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苏格拉底指出,智者的修辞术只是一种讨好听众的庸俗手段,是一种冒牌而非真正的政治技艺。作为一种政治技艺的修辞术应当致力于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以知识和教养,使他们过上以善为目标的理性生活。苏格拉底所说的作为真正政治技艺的修辞术就是他所创立并终身实践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最终目标就是对于善理念的认识,即是对于城邦最高善即公共善的认识。柏拉图说过 :“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才是有用和有益的。”认识城邦的公共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作为共同体的城邦本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所以反对智者的修辞术,就是因为这种修辞术的使用最终只能导致个人的道德沦丧和城邦的分崩离析。
三、城邦的法律与宇宙的逻各斯
赵汀阳先生在《城邦、民众和广场》一文中说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在城邦环境中产生的,尽管哲学所讨论的并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至于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的那些被后世追认为‘自然哲学’的思考,其实都只是对于世界的美学想象。”
这里,赵汀阳先生无疑正确指出了古希腊哲学的政治性,但他又认为,只有苏格拉底“道德哲学转向”后的哲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换言之,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因此,并不具有政治性。笔者认为,无论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是否可以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如果认为它不是城邦政治的产物,如果认为它只是少数人间怪杰对于世界的“美学想象”,那就是误导性的。关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和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是韦尔南说得中肯 :“在政治伦理思考和自然哲学这两个方面,某些论题是类似的,并且是同步提出的,如法则、秩序、平等。”
他认为,在雅典立法者梭伦(Solon)和米利都学派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的思想之间就存在某些类似性。事实上,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也有其特殊的城邦政治背景。首先,如果不考虑自然哲学产生的神话背景,则“本原”探究本身就是难以理解的。正如康福德(F.M.Cornford)对于不顾及神话背景的哲学史研究所抱怨的 :“就好像泰勒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仿佛他碰了一下大地,就崩出来‘水是万物的本原’。”
韦尔南指出,尽管赫西俄德讲述神谱,自然哲学家描述自然,但他们的整体思想结构仍是相同的。另外,荷马笔下神国的等级森严和迈锡尼王国等级制度的相似性也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前者正是人们凭借想象力把后者投射到自然之上的产物。在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中,最明显地反映自然哲学和城邦政治之间密切关联性的或许莫过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思想。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有多方面的含义,但在如下段落中显然意指宇宙的普遍规律 :“如果要理智地说话,就得将我们的力量依靠在这个人人共同的东西上,正像城邦依靠法律一样,甚至还要更强一些 :因为所有的人类法律都是由一个神圣的法律所哺育的,只有它才能要怎样治理就怎样治理,才能满足一切,还能有所超越。”
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普遍认为,这里所谓“人人共同的东西”指的就是逻各斯,即宇宙的普遍规律。现在的问题是,赫拉克利特究竟是如何认识到这个普遍规律的?如果我们在形而上学方面坚持朴素的外在实在论立场,在认识论方面坚持个体主义的反映论立场,即认为逻各斯本身是一种客观实在,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和思想的“逻各斯”是人对它的主观反映,并且企图借助哲学家的理智直观或者其他神秘的认识能力来论证这个概念或者思想的真理性,即它与逻各斯本身的一致性,那我们就不得不假定我们人类能够拥有普特南所说的“上帝的观点”。笔者认为,关于“逻各斯”思想的形成机制,上述引文给予我们的暗示恰恰是 :它是类比思维的产物,也就是哲学家把现实的城邦法律在意识中模式化后再投射到外部世界的产物。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是,仅仅凭借经验观察,人永远无法获得对于外部世界之必然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以必然性为基本特征的“逻各斯”的观念或者思想,并非源于人对外部世界的直观观察,而是源于人类创造性的社会化生活本身。人类首先创造出普遍必然的法律来规定自己的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必然性的意识。当人把这种意识模式化并进一步投射到外部世界时,就形成了对于外部世界之规律的认识。如果笔者是对的,那么,这就正是赫拉克利特的那段文字透露给我们的有关自然哲学认识的基本秘密。
四、《形而上学》与城邦政治
没有人会否认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城邦政治的密切关系,但如果我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与城邦政治有内在的关联性,甚至说它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人们或许就会感到疑惑。让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中介来说明他的《形而上学》与城邦政治之间的关联性。首先,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城邦政治背景是十分明显的。对此,韦尔南指出 :“历史地讲,正是修辞学和论辩术,通过对演说形式这种在公民大会和法庭斗争中克敌制胜武器的分析,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亚里士多德不仅确立了说理的技巧,还确立了论证的规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真的逻辑……”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正如陈康先生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本体论的逻辑”;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为逻辑公理的确定无疑性提供了终极的理性辩护。在城邦内部,无论是解决个人之间的利益纠纷问题,还是处理公共政策议题,都离不开公开辩论。城邦若要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政治共同体,而不是原子式个人的汇集之地,公正和公共善就应当成为解决个人利益纠纷和讨论公共政策议题的真正目标。这样,政治和法律论辩的真正目标就是人人共同的真理,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私利。以真理为目标的论辩若要能够有效进行,辩论参与者就必须始终遵循一些最为基本的话语规范。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亚里士多德为无矛盾律和排中律等逻辑公理提供了一种“否定”形式的先验论证。也就是说,通过否定性地证明,违反逻辑公理将使得一切论辩都成为不可能的,从而论证逻辑公理是论辩活动的可能性条件。“所有这类辩论的起点并不是这样的要求,即我们的对手应当说某物要么是要么不是(因为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样做是在窃取论证),而是他应当说出某种对于他自己和另一个人都有意义的话 ;因为,如果他确实想要说出什么东西,这就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他没有意指任何东西,那么,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他人,他都无法说理。”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逻辑公理不成立,人们就无法在论辩中确定地谈论任何东西,并把它们彼此区分开来。例如,如果无矛盾律不成立,即如果“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既是又不是”,则所有的东西都将被混为一谈。因为,如果“人是人”和“人不是人”(或“人是非人”)同时都是真的,则“人是船、墙、马等等”和“人不是船、墙、马等等”也都同时是真的,这样,人、船、墙、马等就都将是一样的东西。还有,如果“一个东西既是人又不是人”是真的,则“这个东西既不是人,又不是非人”也是真的,这样,当人们在言谈中使用一个语词时,这个语词就不是具有一个意义,而是具有无限多的意义。“这就显然不会有言谈了 ;因为,没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而当语词没有意义时,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谈话以及实际上与他自己的谈话就都消灭了,因为,一个并未思考某种东西的人是不可能思考任何东西的。”
亚里士多德当然清楚,人们无法给出对于逻辑公理的肯定证明,所以,他把他的论证称为否定性的。实际上,当亚里士多德论证逻辑公理是人们确定地思考和谈论事物的可能性条件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违反逻辑公理,人们之间任何形式的话语交流都将成为不可能,而是以真理为目标的论辩即理智对话将成为不可能,这同时意味着城邦的基本政治生活将成为不可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于逻辑公理的研究与对于“存在本身”的研究同属形而上学,对于逻辑公理的辩护自然导向对于本质主义的辩护。简单来说,亚里士多德对于本质主义的辩护是这样的 :如果事物只有偶然属性而没有本体和本质,则逻辑公理就不能成立,因此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那些后果。亚里士多德指出,逻辑公理的反对者们,诸如普罗泰戈拉、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拉、德谟克利特等,尽管导致他们立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从存在论上看,他们都废除了事物的本体和本质。
笔者还想指出,城邦政治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哲学的产生条件,而且是其形态塑造条件。如果说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实际上是基于与城邦政治结构(即城邦的三个阶层及其关系)的明确类比来阐明个人的灵魂结构(即灵魂的三个部分及其关系),那么在《形而上学》中,城邦政治结构则是亚里士多德思考事物的本质和定义形式的隐性类比基础。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一再把具有自足统一性的城邦共同体与松散的军事联盟加以对比。一方面,与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结成的军事联盟不同,城邦是为了某种公共善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所有的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起来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既然所有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则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即所谓城邦或者政治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
另一方面,军事联盟仅靠数量起作用,而“城邦不仅由众多个人组成,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的。种类相同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城邦”。我们可以说,城邦共同体所追求的最高善不过就是“城邦的本质”,即由不同种类的个人合理分工而形成的功能统一体。我们认为,当亚里士多德把事物的本质一般性地公式表示为“种+属差”时,他就使得事物的本质与城邦的本质具有了结构上的类似性。正如城邦共同体的本质合理地决定了城邦内部不同种类的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一样,事物的本质作为一个统一体(即“种+属差”)也合理地决定了最初的种和所有种内属差之间的关系结构。
如果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政治论辩是城邦共同体的存在和繁荣所必需的,如果对真理的追求过程就是对存在的探究过程,则以“存在本身”为研究主题的《形而上学》就为城邦政治提供了最为基础性的理性根据。最后,让我们用韦尔南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希腊人发明的不是‘理性’这个唯一的、普遍的范畴,而是‘一种理性’,一种以语言为工具,可以用来制约人而不是用来改造自然的理性,一种政治的理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理性”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谢德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2]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6.
[4]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2)[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5]Aristotle. Politics[M].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6]Plato. Complete works[M]. Edited by John M. 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
[7]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J].世界哲学,2007,(2).
[8]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1)[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9]陈康.论希腊哲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10]Aristotle. Metaphysics[M].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