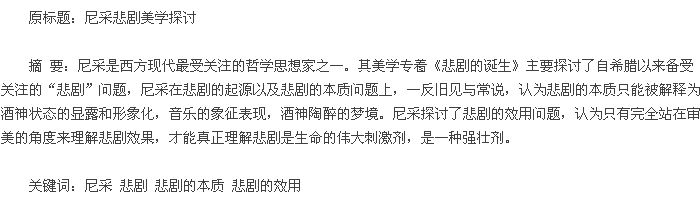
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异化”的时代,表现在文学方面诸如: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加缪笔下的“自我”变成了“局外人”,卡夫卡书写的主人公永远进不去眼前的“城堡”,福克纳发出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等等。表现在哲学思想领域:马克思论述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被“异化”,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一个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单摆”.在众多观点中,尼采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惊骇之语,要“重估一切价值”,独树一帜的尼采被世人称为现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出版的第一部专着,也是他的哲学奠基之作。在此书中,尼采主要探讨了自希腊以来备受关注的“悲剧”问题,他一反旧见与常说,就悲剧的起源、悲剧的本质、悲剧的效用等提出了独到而又自圆其说的观点。尼采的美学观念并非从该学科的理论上探讨,而是立足于美学对人生之意义,即美学对审美人生的作用这一角度来论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与文学艺术联系密切,文学艺术家对此尤为热衷,至今还没有哪一部美学名着能与之媲美。
一、悲剧的起源与本质
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家都会涉及到悲剧理论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特里西诺、高乃依、莱辛、席勒、叔本华等。哲学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生的痛苦,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冲突。与上述哲学家不同,尼采从文学艺术角度入手,创作了《悲剧的诞生》并以此论述悲剧问题。对尼采影响颇深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曾说:“在这黑暗的人生中,在如此之多的危险中;只要此生还在延续,就是这样、这样度过!”[1](P428)这几句诗引自路克内兹《物性论》,很显然,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痛苦的、无聊的,而尼采则与之大相径庭,他用现实的悲剧来肯定人生,他认为悲剧对人生起着“形而上的慰藉”作用。
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悲剧诗人将古希腊悲剧推向了繁盛,与此同时,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理论着作,即亚里斯多德《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2](P63)这是亚里斯多德给悲剧下的定义,他认为悲剧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里亚里斯多德说的现实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它不同于柏拉图所言,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虽然说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乃至所有的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是他没有更深一层论述。尼采则具体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文学艺术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悲剧亦然,“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一个慰藉异常清楚地体现为萨提儿歌队,体现为自然生灵的歌队,这些自然生灵简直是不可消灭地生活在一切文明的背后,尽管世代更替,民族历史变迁,它们却永远存在。”[3](P112)尼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这一个问题做了更深层的论述。
马克思曾言:“希腊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是一个健康的儿童。”悲剧源于古希腊,这一时期就像人类的童年,拥有一种健全、生机勃勃、昂扬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希腊人对自然社会、人类的苦难、命运的沉浮有敏锐的洞察力。尼采认为,希腊人是一个独具敏感力,并能用各种艺术形式将其表达出来的民族。比如西勒诺斯的神话:“弥达斯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寻猎酒神的伴护,聪明的西勒诺斯,却没有寻到……‘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要好的东西--立刻就死。’”[3](P96)西勒诺斯的神话很典型地把这种敏感力给表达出来,西勒诺斯对弥达斯国王所说的关于人最好不要降生的那段话,说明了希腊人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性。但希腊人并没有立刻死掉,而是积极乐观地面对着人生的悲剧性,并给它们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企图用这个艺术世界来给人生一个缓冲,同时又给人提供了承受苦难、战胜苦难的可能性。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提到了悲剧的起源。在这一问题上,尼采延用了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观念,即:悲剧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歌队的酒神颂,并由祭祀时的悲剧歌队演变而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在《诗学》以及后来有关悲剧理论着作中,都涉及到了悲剧诞生的过程:比如阿瑞翁为酒神节创作赞美诗,忒斯庇斯创作演员角色,引进开场白和台词等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很少论及悲剧的起源,他所关心的是悲剧的本质问题。他在《悲剧的诞生》第八节里说到:“魔变是一切戏剧艺术的前提。在这种魔变状态中,酒神的醉心者把自己看成萨提儿,而作为萨提儿他又看见了神,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变化中看到一个身外的新幻象,它是他的状况的日神式的完成。戏剧随着这一幻象而产生了。”[3](P116)尼采认为悲剧的本质是通过魔变这种方式实现的。
二、悲剧的效用
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悲剧理论源远流长。集大成者当属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在此书中,亚里斯多德给悲剧下了定义,该段论述也包含了悲剧的效用问题:“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4](P36)文中“陶冶”一词,朱光潜先生译为“净化”,无论是“陶冶”还是“净化”,说的都是悲剧的效用。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九章,重点阐述了悲剧所引起的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引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之情)……”[4](P46)我们用古希腊代表性的悲剧作品来说明这种观点。比如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其主人公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高大无比、心地善良的形象,他心系下界的人类,不顾宙斯的反对,给人类送来了希望的火种,而自己则遭受着每天被秃鹰叼食肝脏的痛苦。再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一个聪明、贤能的人,他解开了人类困惑已久的难题--斯芬克斯之谜。在他当上国王后,他贤明执政,但却无法逃出命运的安排:弑父娶母。最终在真相大白后,他挖去双目,流落至孤独荒岛。种种迹象表明:冥冥之中似乎有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的命运,无论你如何地努力挣扎,最后还是挣脱不了,逃不出早已被这种神秘力量安排好的命运。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曾言:“近代西方悲剧在基本精神上来源于欧里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它从探讨宇宙间的大问题转而探讨人的内心。
爱情、嫉妒、野心、荣誉、愤怒、复仇、内心冲突和社会问题--这些就是像莎士比亚、拉辛或易卜生这类戏剧家作品中的动力。”[5](P103)用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来解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是,尼采在哲学上要“重估一切价值”,在悲剧理论的问题上,更是一反传统,他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形象来概括其悲剧理论: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并用日神与酒神的关系来解释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以及悲剧从欧里庇得斯之后开始走向灭亡。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中提到:“最近我还在《偶像的黄昏》中表明,我如何借此而找到了‘悲剧的’这个概念,找到了关于何为悲剧心里的终极知识。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里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斯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3](P434)尼采这里说的通过悲剧所达到的生成之永恒喜悦(这种喜悦包含自身的喜悦和自身毁灭的喜悦),就是一种悲剧的快感,但是这种悲剧快感同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有关悲剧理论家所提倡的悲剧快感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这种悲剧快感表现为悲剧引起人们的恐惧与同情,以此带给人们净化灵魂的作用;而尼采所强调的悲剧快感则是超越悲剧给自身带来的永恒喜悦之上,超越了悲剧给你带来的恐惧与怜悯,悲剧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在鼓舞人、感召人。
尼采关于悲剧的理论与传统的悲剧理论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传统的悲剧理论一般都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尼采认为如果悲剧同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那么悲剧将会延缓生命力的进化与生成。尼采认为只有完全站在审美角度来理解悲剧效果,才能真正理解到悲剧是生命的伟大刺激剂,是一种强壮剂。“自亚里斯多德以来,对于悲剧效果还从未提出过一种解释,听众可以由之推断艺术境界和审美事实。时而由严肃剧情引起的怜悯和恐惧应当导致一种缓解的宣泄,时而我们应当由善良高尚原则的胜利,由英雄为一种道德世界观作出的献身,而感觉自己得到提高和鼓舞。我确实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悲剧的效果正在于此并且仅在于此……”[3](P174-175)尼采表明了自己悲剧美学与一般悲剧理论的不同,他的悲剧观念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能让人感受到和谐、生机勃勃、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尼采悲剧美学的关键所在。
注释: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现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4]转引自罗念生:《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后文所引亚里士多德《诗学》皆出自本集,故不再标注。
[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