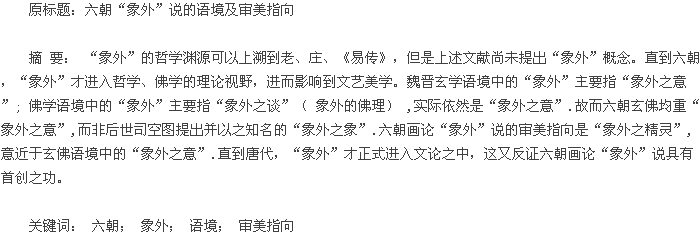
先秦典籍对于“象”颇多论述,但“象外”一词,晚至三国时期才出现。在六朝玄学及佛学的影响下,“象外”成了重要的新兴文艺美学范畴。“象外”主要用于六朝画论之中,至唐代才用于文学评论,这体现出画论重神轻形的审美趣味对文论审美趣味的正面迁移。
一、“象外”的含义及渊源
要讲清“象外”的概念,先要明确何谓“象”.许慎《说文解字》释“象”为“南越大兽”.但从殷墟遗物及卜辞来看,殷商时期北方仍有象。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认为: “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1]445《吕氏春秋·古乐》记载: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罗振玉、王国维都认为这是殷代有象的确证。1973 年,在甘肃省出土了“黄河象”化石,经考证此象是生活在距今 250 万年左右的剑齿象。
这一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北方在很古的时候是有象存在的,不过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象主要生存在南方。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分析了甲骨文“象”字的字形特征后指出: “据考古发掘知殷商时代河南地区气候尚暖,颇适于兕象之生存,其后气候转寒,兕象遂渐南迁矣。”
[1]446至于战国时期,北方已经很难见到活象。所以《韩非子·解老》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可见,韩非子之时,北方已经很难看到活象,但仍可见到象骨象牙,以及象骨、象牙做成的器皿和饰物。《左传》、《国语》中的“牺象”即是象骨雕成的酒器。《战国策》中有“象床”,《韩非子》中有“象箸”.《荀子·正论》讲豪奢者“犀象以为树”; 《韩非子·喻老》讲宋人以象牙制作楮叶; 《管子·轻重》讲吴越以“珠象”作为贡币。这些都证明,象牙象骨在古代北方是常见之物。“常见象骨而见不到活的象,于是一般人只能根据眼前的象骨、象牙来揣摩、意想活象的样子,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大概是因为那时候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象牙、象骨,而活象又太难见到,所以揣摩活象的样子也就成了人们经常发生的一种普遍心理活动。久而久之,人们也就把任何经过意想作用而呈现于主观之中的观念形象称之为象.”[2]316《易·系辞上》: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可知古人对“象”和“形”有不同的界定,“形”是客观的外在形体,而“象”则是外物经过视觉而呈现在眼中的主观感觉,这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哲学上的“象外”理论,受到老、庄思想的直接影响。“象外”类似于老子所说“大象无形”( 《老子》四十一章) 之“大象”.王弼《老子指略》说: “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无形的大象,属于“象外”的范畴。《老子》十四章: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里“无物之象”是“惚恍”,而惚恍正是道的特点,《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也证明了这一点。故而“无物之象”指向的应是“象外”之道。《庄子·秋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象注: “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 夫言意者,有也; 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庄子所谓的言、意不能到的就是“象外”指向的“无”的境界。《庄子·天运》: “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
故有焱氏为之颂曰: 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乐无声无形却又无所不在,天乐令人无言而心悦,而“象外”给予人的也是这种审美愉悦。比如,陶渊明看到夕阳西落、飞鸟还巢,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 ,这种难以言辨的真意,存在于“象外”.陶渊明对于象外的感受,达到了庄子所说的“无言而心说”的境界。“象外”也类似于庄子所谓的“象罔”.《庄子·天地》记载“象罔得珠”一事: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 “异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黄帝所遗的玄珠象征“道”,而“知”、“离朱”、“吃诟”、“象罔”象征四种求道的方式。“知”即“智”,指智者。“离朱”即明,指善视者。“吃诟”,指聪明善言者①.“象罔”,即象无。《尔雅·释言》: “罔,无也。”象无,即是象外。四种求道方式,只有“象罔”得到了“道”.此即证象罔( 象外) 通于道。
“象”是《易传》中的核心范畴。《易·系辞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颖达解释说: “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故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者,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 《周易正义》卷八) 《易》的卦象是对万物之形的模拟和抽象,相对于万物之形来说,《易》的卦形是象。所以《易·系辞上》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比如,晋卦的卦形是坤下离上,即地在下,火在上,卦象模拟的是太阳从大地升起之形,用于表现上升。晋卦的卦辞说: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意谓: “康侯出征异国,俘马甚多,以献于王。其战也,一日三胜。”
[3]237这是由卦象上升之意,喻指人事。孔颖达指出: “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 《周易正义》卷一) 亦明此旨。《易传》没有提出“象外”的概念,但认为“言不尽意”的解决途径是“立象以尽意”.
正如《易·系辞上》所说: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相对于卦象而言,卦辞中描述的人事,往往是对卦象所作的引申和附会,而这属于“象外”的范畴。
综上,“象外”的哲学渊源可以上溯到老、庄、《易传》,但是上述文献尚未提出“象外”的概念。直到六朝,“象外”才进入哲学、佛学的理论视野,并进而影响到文艺美学。
二、玄佛语境中的“象外”
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中,存在“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两派观点。“言尽意”这一派不承认有“象外”.欧阳建《言尽意论》指出: “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无不尽。”( 《全晋文》卷一百九) 既然“无不尽”,一切都可言尽,那么也就不存在“象外”了。“言不尽意”这一派则相反,他们把“象外”视为“意”的最终归宿,提出了“象外之意”的命题。
三国魏玄学家荀粲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象外者也; “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何劭《荀粲传》,《全晋文》卷十八)荀粲认为言不尽意,象也不尽意,故而有“象外之意”的说法。显然,所谓“象外之意”,是对《易传》“立象以尽意”的否定,是荀粲用老、庄思想解释易学的结果。
王弼倾向于“言不尽意”派,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在王弼看来,“象”不过是存“意”之具,得意即可忘象,所以他说: “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显然“象”本身并不是“意”,要得“意”,必须沿着“象”的象征之处探寻,即“寻象以观意”,这必然是在“象外”得“意”.王弼认为,解《易》不应拘泥于“象”,寻求“象外之意”,才能领悟易象所蕴含的深奥道理,所以他说: “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忘象”就是不主张于象内求意,从这个层面讲,“忘象”通向的必然是“象外”.王弼的这种观点,是他借庄子以解《易》的结果,比如前引的鱼兔筌蹄之喻,明显出自庄子。
六朝佛教中也有“象外”学说。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 “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文选》李善注: “象外谓道也。……无生谓释典也。”( 《文选》卷十一) 孙绰所说的“象外之说”与“无生之篇”是互文见义的,均指佛理而言。翻检文献可证,当时僧人多以“象外之谈”指称佛理。比如僧肇《涅盘无名论》称赞涅盘学说: “斯乃穷微言之美,极象外之谈者也。”( 《全晋文》卷一六五) 僧肇《般若无知论》: “《成具》云: 不为而过为。《宝积》曰: 无心无识,无不觉知。斯则穷心尽智,极象外之谈也。”( 《全晋文》卷一六四) 这是以“象外之谈”称颂《成具光明定意经》、《宝积经》所载佛理。释法瑗应宋文帝之诏,讲竺道生的顿悟思想,何尚之闻而叹曰: “常谓生公没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其文也。”( 慧皎《高僧传》卷八) 这也是以“象外之谈”指称佛理。
释僧卫《十住经合注序》“抚玄节于希声,畅微言于像外”( 《全晋文》卷一六五) ,是对翻译《十住经》的鸠摩罗什的赞语,“像外”是指称鸠摩罗什所谈的佛理。佛教认为色、相俱空,故不主张执着于“象”,而应向“象外”寻佛理,正如竺道生所说: “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 释惠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庆》序引,《全宋文》卷六十三) 所以,东晋袁宏认为佛教: “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 《后汉纪》卷十) “佛教关于真谛的领悟,本质上是追求一种象外的境界。佛教徒所理想的涅盘,也是超言绝象的境界。”
[4]77南朝梁代释慧皎《高僧传论》阐释了佛教立象而不依象的道理:夫至理无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言语路绝,则有言伤其旨; 心行处断,故作意失其真。所以净名杜口于方丈,释迦缄嘿于双树。将知理致渊寂,故圣为无言,但悠悠梦境,去理殊隔; 蠢蠢之徒,非教孰启。
是以圣人资灵妙以应物,体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像以传真。故曰: 兵者不祥之器,不获已而用之; 言者不真之物,不获已而陈之。
……将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则废指,得兔则忘蹄。经云“依义莫依语”,此之谓也。( 《全梁文》卷七十三)佛教“托形像以传真”是不得不为,明知形象并不是佛理本身,为了教化众生,却不得不用,这好比兵器是不祥之器,为了保家卫国却不得不使用。“托形像以传真”指向的是象外的佛理。故而佛教对待“象”的态度是得意忘象,这就是佛经讲的“依义莫依语”之意。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曾经组织了一次对“神灭论”的大讨伐,他颁示《敇旨垂答臣下审神灭论》,诸臣作答,其中司农卿马元和答曰: “伏惟至尊先天制物,体道裁化,理绝言初,思包象外,攻塞异端,阐导归一,万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沧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灭之论,宜所未安。”( 僧佑《弘明集》卷十) 马元和称颂佛教至尊“思包象外”,“象外”指的即是精妙的佛理。
综上,六朝玄学语境中的“象外”主要指“象外之意”; 佛学语境中的“象外”主要指“象外之谈”( 象外的佛理) ,实际依然是“象外之意”.故而六朝玄佛均重“象外之意”,与后世司空图提出并以之知名的“象外之象”并不相同。
三、“象外”的审美指向
魏晋以来玄佛语境中的“象外”概念,逐渐影响到文艺美学领域。南北朝时期,“象外”开始用于画论。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评张墨、荀勖: “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物体,则未见精粹; 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 《全齐文》卷二十五) 谢赫认为绘画有两种取象方式,一是“拘以物体”,拘束于外物之形,绘画求形似,即以形写形; 一是“取之象外”,不拘泥于外物之形,取象外之神( “精灵”) ,即绘画求神似,这类似于东晋顾恺之所谓的“以形写神”.谢赫《古画品录》提出了绘画“六法”: “六法者何? 一,气韵生动是也; 二,骨法用笔是也; 三,应物象形是也; 四,随类赋彩是也; 五,经营位置是也; 六,传移模写是也。”( 《全齐文》卷二十五) “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它代表了谢赫对于绘画的审美理想。骨法用笔,是用笔问题,属于技巧层面; 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则是绘画的过程。谢赫讲“应物象形”、“传移模写”,并不是主张绘画追求形似,他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绘画创作的不同阶段。
谢赫对于形似之画多有批评。比如《古画品录》评刘绍祖: “善于传写,不闲其思,至于雀鼠,笔迹历落,往往出群。时人为之语,号曰移画。然述而不作,非画所先。”( 《全齐文》卷二十五) 刘绍祖善于传写( 即传移模写) ,长于模仿事物外形( 即应物象形) ,故号为“移画”.谢赫认为这是“述而不作”,即只模仿外物之形,缺乏对外物之形的艺术加工,这是“非画所先”的。可见,谢赫反对“移画”式的形似之作,而主张对外物之形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气韵生动。又比如《古画品录》评毛惠远: “泥滞于体,颇有拙也。”( 《全齐文》卷二十五) 这也是对绘画拘泥于形似的批评。另一方面,谢赫对超越形似而有气韵的绘画多有称赞。
比如《古画品录》评晋明帝: “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 《全齐文》卷二十五) 晋明帝的绘画虽然在形色上不足,但有神气,故得谢赫好评。
又比如《古画品录》评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象”,评陆绥“体韵遒举,风彩飘然”( 《全齐文》卷二十五) ,都是对绘画有气韵的赞扬。
可见,谢赫所谓“取之象外”,是与“拘以物体”( 即取之象内) 相对的取象方式,他主张绘画取象不拘泥于外物之形,而应取象外之“精灵”,以达到绘画气韵生动的目的。故而谢赫所谓“象外”的审美指向是“象外之精灵”,其意近于玄佛语境中的“象外之意”.谢赫的“象外”说受到魏晋以来玄学、佛学“象外”理论的影响,是哲学、宗教“象外”理论在画论中的延伸和发展。朱良志对“象外”作了很好的概念界定,他指出: “取之象外正是强调不为外物所拘,超越对象的外在形体,去掘取其深层意韵。
如其评陆探微的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即能尽取之象外之妙。谢赫论画重象外之妙,这和他以气韵生动为绘画最高准则有关。但谢赫认为象内象外要处理好,其间的斟酌十分重要,体现了画家的微妙用心。”[5]279朱良志认为谢赫所谓“象外”,指的是与一味模拟物态相对的象外之妙、象外之意韵。
此论契合谢赫原义,与笔者前文所论含义相近。
谢赫的“象外”理论对唐代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司空图提出了着名的“象外之象”说。根据“象外之象”说,学界反过来又对谢赫的“象外”理论有所阐释,甚至认为,六朝文艺美学“象外”理论指向的是“象外之象”,而不是“象外之意”.比如敏泽论述六朝“象外”范畴时,指出“象外”即“象外之象”:“艺术所表现的总是具体的象,但它应该具有二重性:既是具体的象,又非具体之象,不能执着于所表现之象本身,而应该通过具体的象,反映和显示具有普遍性或无限性之理,即象外之象。”
[6]485敏泽认为宗教和哲学追求的是“象外之理”,不是“象”本身; 而艺术表现的总是具体的“象”,因此文艺美学中的“象外”,应该是“象外之象”.从文艺美学的一般规律而言,此说可通,但具体到以谢赫“象外”说为代表的六朝文艺美学“象外”理论时,则未必符合事实。
叶朗也认为,六朝文艺美学语境中的“象外”是指“象外之象”.他说: “谢赫所说的象外是对有限的象的突破,但并不是完全摆脱象.象外也还是象,是象外之象.”
[7]269叶朗认为六朝佛教理论家讲的“象外”实质是“象外之意”,而谢赫所说的“象外”指的是“象外之象”.的确,宗教的“象外”理论不同于文艺美学的“象外”理论,二者的理论旨趣不同,这是无疑义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思路,宗教“象外”理论对文艺美学“象外”理论产生潜在影响则又是可能的。比如刘宋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 “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 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求于书策之内。”他在画论中谈到的“象外”问题,就明显受到佛教“象外”说的影响,因为宗炳本就是佛学家,师从慧远,曾作《明佛论》,他所讲的“象外”就是“象外之意”.叶朗并未论证为何谢赫所谓“象外”就是“象外之象”,其依据反而似乎是司空图“象外之象”说。司空图“象外之象”是否义同于谢赫所说的“象外”,这是值得探讨的。祖保泉解释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两句,认为“象外之象”的第一个“象”是作品描绘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形象”、“景象”; 第二个“象”从创作来讲是有“蕴藉之美”,从鉴赏来讲是要挖掘第一个象的“含蓄所在”[8]58.这实际上是说“象外之象”即是“象外之意”.叶朗则认为: “有人说,象外之象的第一个象指作品具体描绘的象,第二个象则指第一个象在读者脑中引发联想而产生的意象、意境。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
[7]269根据前文所引,叶朗认为“象外之象”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象”.司空图“象外之象”究竟何指,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探讨六朝文艺美学“象外”的含义,不能依据唐代“象外之象”来逆推,而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寻找答案。前文分析谢赫《古画品录》得出的结论是: 谢赫“象外”说的审美指向是“象外之精灵”,意近于玄佛语境中的“象外之意”.
四、余论
六朝文论虽然没有使用“象外”一词,但实际上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陆机对于“玄览”、刘勰对于“隐”的探讨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了“象外”的获得方式、内涵等问题。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实际探讨了获取“象外之意”的途径。“玄览”即《淮南子》中说的“览冥”,是道家一派观察宇宙人生的方法。叶兢耕《释“象外”》指出: “作者观察山川万物,必须能静观之而求得其蕴而不出的象外言意.
作者要能玄览,才能求得象外之意.在陆氏看来当是补救意不称物的修养工夫。这里可以看出思想上的一个线索: 要求象外之意就感到意不称物的困难,乃提出一玄览的一个重要方法。象外之意的极致是忘象忘言的境界。”
[9]95南朝刘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指出“文患其事尽于形”( 《宋书·范晔传》) ,反对作文记事只求形似而缺少内涵,他以文章“尽于形”为患,其旨趣当然是追求形外的余意,这与刘勰“文外曲致”( 《文心雕龙·神思》) 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刘勰又说: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 《文心雕龙·隐秀》) 可知,“文外重旨”、“文外曲致”即是“隐”,其理论内涵近于“象外”,这与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 《与李生论诗书》) 相近。
陆机、刘勰的探讨与画论“象外”说处于同一理论层次,甚至更为深刻详尽。但当时的文论“却不曾明确地提出象外这一美学范畴。诗文评和画论中所出现的这种差异,是值得研究的”.[6]486直到唐代,“象外”才正式进入文论之中,比如皎然“采奇于象外”( 《诗议》) ,刘禹锡“境生于象外”( 《董氏武陵集纪》) ,司空图“象外之象”( 《与极浦书》) ,“超以象外”( 《二十四诗品》) ,等等。至此,作为文论的“象外”范畴才真正形成。这又反证六朝画论“象外”说具有首创之功。
参考文献:
[1] 李圃。 古文字诂林: 第 8 册[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李壮鹰。 逸园丛录[M]. 济南: 齐鲁书社,2005.
[3] 高亨。 周易大传今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 曾祖荫。 中国美学范畴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 鲁枢元,等。 文艺心理学大辞典[Z].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6] 敏泽。 中国美学思想史: 上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
[7]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 祖保泉。 司空图诗文研究[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9] 张国风。 清华学者论文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