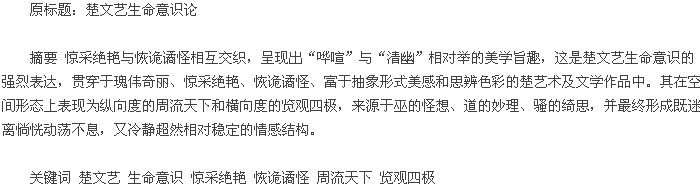
作为先秦时代中华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予以观照和言说。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还不能很好地阐释楚文艺中貌似两极对峙的“哗喧”与“清幽”美学旨趣的共存现象,对楚文艺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的统一性路径的探讨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有效阐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回归作为民族精神呈现和民族心理秘史的楚文艺作品本身,通过文化“还原”①理解、阐释作为整体性的楚文艺的独特创造价值,藉此才能再现楚文艺生命意识的真相和本质。
一、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生命意识的神秘性
对生命的理解及其态度,构成人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首先表现为个体性的对于生命的体认,包括生存意识、安全意识和死亡意识等。族群生命意识由个体生命意识构成,个体生命意识在选择向度上的“不约而同”,形成族群生命意识的共同趋向。
本文所说的楚文艺生命意识,正是这种融入族群内在心理层面、呈现于艺术作品之中的楚民族的生命认知。
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相互交织,呈现出“哗喧”与“清幽”相对举的美学旨趣,这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强烈表达。无论是惊采绝艳,还是恢诡谲怪,都是对常态化、一般性的突破和超越,因此在观众或读者看来,难免会感到突兀、震撼,甚至神秘。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年代,距离楚国灭亡不过才一百二三十年的时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继楚人项羽灭掉秦朝之后,楚人刘邦建立了汉朝。西汉初年,楚风弥漫。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都是典型的楚歌楚调。按照常理,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司马迁都不应该对“近在咫尺”的楚文化感到神秘和陌生。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偏偏写道: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上述对于荆楚民情风俗的文字描述,语涉讥讽,背后潜隐的其实还是太史公对于楚文化的情感隔膜。因为缺乏理解,也就不会有“理解的同情”;因为缺乏理解,才会有“他者”视域中的神秘和陌生。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楚文化惊采绝艳的美学呈现,主要表现在楚辞和其他传世文献中。这种超乎寻常的炫彩夺目的美,往往会令读者目眩神迷,流连忘返;巫山神女朝云暮雨的美丽传说,让人陡生无限的惆怅;而特立独行的楚人风标,则更让千载以下的中国人发出“身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深长感喟。《文心雕龙·辨骚》称赞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楚人所钟爱的惊采绝艳的美,是一种繁富、鲜明、艳丽、强烈的美,这种强烈的炫目的美,远远超出北方儒家所推崇的“绘事后素”的审美规范。正是这种超越,造成了审美的距离,而距离更加突显美感,也更加突显出楚文艺的神秘感。“山奔海立不足以喻其壮,鬼使神差不足以喻其怪,国色天香不足以喻其美”①,荆楚辞赋惊采绝艳的美学呈现和丰富繁盛的绚丽色彩,营造出楚文化神秘美学的高堂邃宇。《高唐赋》、《神女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千百年来,颠倒众生,引发无限神秘的遐思。后世文学由此衍生出“云雨”、“楚梦”、“峡云”、“高唐十二峰”、“巫山一段云”等神秘意象,在无数骚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寄托情感表达理想的重要载体。
荆楚大地多特立独行之士,以至于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名词“楚狂”,专门用来指称楚国的特异之士。在常人看来,“楚狂”无一不是神秘的。《庄子》记载:“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论语》记载孔子到楚国游说楚王,途中听到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楚狂洒脱不羁的风采,令千载以下的盛唐大诗人李白心折不已,其《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荆楚大地上不仅民间狂人极多,而且在位居高堂的君王和重臣中,也多有狂人。《左传》记载楚庄王听到宋人杀死楚国外交使臣申舟的消息后,“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于此不难想见楚庄王的狂傲和冲动!而三闾大夫屈原,一生狂放孤傲,愤激忧思,是骚人之狂的典型代表。《天问》中诗人昂首青天执着地一连发出一百七十多个诘问,这是在大自然面前,在精神上从来没有雌伏过的楚人之狂。这种人格独立之狂,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荆楚文物的相继出土,楚国文艺的神秘美学得以“实物”的具象方式呈现,甫一面世,即征服了当代观众。楚国漆器、玉器和丝绸上流变着的兽面纹、龙凤纹、云雷纹等,是一种抽象艺术,是楚人活跃的生命机能的尽情发挥,充满着运动和力量的美。在色彩搭配上,多以黑、红、黄为主,辅以绛、褐、白、蓝等其他颜色,并以金粉勾勒局部,整体效果显得金碧辉煌,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这是楚文艺特有的不碍于物,不滞于心,无拘无束,无所挂碍的“流观”审美意识的具体表达,体现了荆楚人民富于艺术想象,饱含生命激情,发扬踔厉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精神。《韩非子》有一则“买椟还珠”的寓言,说的是楚人“为木兰之柜,薰桂椒之椟,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用这种美丽绚烂的漆盒盛了珠宝,前往郑国去卖,结果“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这从侧面证明了楚人善于制造美丽的漆器,在当时诸侯列国中颇负盛名。楚地出土的漆棺上,绘画内容更为诡异,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是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南方神话传统的视觉呈现。各种龙、凤、怪兽造型,布满棺面,恢诡谲怪,神秘莫测。从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可以看出,楚国奇异繁丽、玲珑剔透的镂空装饰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种种攀附兽造型,既生动地表现了紧张、活泼的生命力量,又显得奇诡怪异,富含神秘的巫风色彩。江陵望山出土的木雕座屏,透雕着51个动物形象,刀法圆熟精细,形象逼真传神。善恶相争的主题表达,则透露出神秘的南方巫术文化背景。木雕辟邪用树根雕成,虎头,龙身,四足,卷尾。四足细长,雕为竹节形状,右侧前腿上雕一蛇蜿蜒而行,右侧后腿上雕一长蛇追赶一青蛙,左侧前腿上雕一蜥蜴正在吃一雀,左侧后腿上雕一蝉。这件辟邪,被视为最富有“现代派风格”之作,的确予人怪异莫名之感,给人难以言传的审美惊奇。
在仔细观看了有如夏夜星空一般繁丽闪烁的楚文艺精品之后,英国艺术史家苏立文感慨道:“如果纪元前223年的战争,胜利者不是西方野蛮的秦国,而是有高度文化与自由思想的楚国,那么中国文化又将是何种面目?”①这一问,可算是对中国文化史的“天问”。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天问”没有答案!
二、周流天下与览观四极:生命意识的空间感
贯注于楚文艺之中的充沛的生命意识,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纵向度的周流天下和横向度的览观四极。周流天下与览观四极是楚人生命意识的自觉流露和实现方式。如《离骚》云:“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远游》云:“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哀郢》云:“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刘纲纪将“周流天下”与“览观四极”视为楚文艺美学的“流观”意识,并认为这种“流观”意识“是与屡见于《楚辞》中那种企图超越人世的污浊、黑暗、痛苦而求得人生的解脱、自由以至永恒的存在相关的”②。这无疑是对楚文艺审美意识的深刻洞察。“流观”是一种动态的审美观照方式,《左传》中记载的“观鱼”,《庄子》中记载的庄子与惠施“观鱼于濠梁之上”,《东君》中记载的“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澹兮忘归”等,都是一种归结于视觉愉悦感受的审美体验。
楚文艺惊采绝艳的呈现方式,就是以浓墨重彩的画面震撼观者的观感,以饱满炽烈的激情点燃观者的情感。“目观”之美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征。在楚人的生命意识中,燃烧、激情、自由、狂放、浪漫、理想、不羁、炽烈,是永恒的主旋律。楚文艺“目观”之美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向空间延伸,高台累榭是其典型。《国语·楚语》记载楚灵王与伍举的对话,伍举说:“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望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由此可见,伍举是坚决反对“目观”之美的,他是将善等同于美,不善则不美。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伍举的观念可以说是以道德判断来代替审美判断,固然不足为训,但从中亦可反证出,楚文艺传统是很重视“目观”之美的。因为楚人生命意识中永远有不甘于平庸的成分躁动不息。
与中原相比,楚国的出土器物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修长挺拔、向上伸展的趋势。考古学家将楚式升鼎、于鼎、小口罐形鼎的出现,及其独特审美趣味的呈现,视为楚式鼎真正成熟的标志。楚式鼎束腰收腹,平底,有极度夸张的外撇耳,予人凌空飞翔之感。如河南淅川下寺2号春秋楚墓出土的“王子午升鼎”一共7件,堪称春秋时代楚式鼎的代表之作。
这组升鼎铸造十分精良,造型特出,“器表饰繁缛华丽的浮雕夔龙纹、窃曲纹和云纹,鼎耳、口沿及鼎腹的腰带都饰有浅浮雕花瓣纹,器腹周围攀附六只形似夔龙的怪兽。攀附兽造型奇诡,兽口咬住鼎的口沿,兽足抓住鼎腹的腰箍,两角铸作两只盘绕的夔龙,尾部又作成一兽头形状,背部也构成一饕餮形的兽面,这种象中有象,超越模拟的组合构成手法,造成令人目不暇接的艺术效果”③。生气流注,活灵活现,这是楚人热爱生活、长于幻想的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
细长、拔高的器物造型,抽象、繁复的龙凤纹饰,将楚文艺导向浩瀚无边的星空和神秘的宇宙之中,这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强烈表达,是楚人开拓进取浪漫多情的精神呈现。楚文物中常见的立鹤、镇墓兽、虎座立凤、虎座鸟架鼓等,莫不头插鹿角,或者凤身修长、昂首天外,在视觉样式上创造出游目骋怀的审美对象,有一种“仿佛离开大地般的超脱感和升腾感”④。楚丝绸艺术中常见的飞凤和蟠龙图案,无疑更是楚人飞扬灵动自由奔放的生命意识的具象显现。曾侯乙墓漆箱以衣箱的拱形盖面象征圆形的天穹,以衣箱的长方形底象征大地,盖面上绘有北斗,环绕北斗的是二十八星宿,还有方位神青龙、白虎等。楚人关注天象,超脱世俗的生命趣味,于此件作为日用实用性的衣箱的漆绘图案中,亦可见一斑。
如同“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埃及人所有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存在于金字塔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很久”①,如何看待死亡也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主要内容。楚人如何看待死亡?闻一多说:“道家是重视灵魂的,以为活时生命暂寓于形骸中,一旦形骸死去,灵魂便被解放出来,而得到这种绝对自由的存在,那才是真的生命。”②既然死亡是自由的实现,是真正生命的开端,那么,楚文艺表达死亡的情感趋向就是一片欣悦安和,幸福吉祥。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帛画”和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是楚人死亡观念的生动呈现。
“人物驭龙帛画”中的男子腰佩长剑,驾驭着一条昂首飞行的长龙,凌虚遨游于天宇之中;“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子拱手胸前,头顶上有龙翔凤舞,导引着她向上升腾。帛画中随处可见的龙、凤、鹤、鲤鱼等吉祥之物,则大大强化了灵魂飞升的愉悦感。
诉诸空间的升腾感和自由感,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主要特征。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经常不断地思考它们,它们就愈是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永远新鲜和更加强烈的惊叹和敬畏,这两种东西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③楚文艺明显地更加关注我们头顶的星空,而中原艺术更加关注的则明显是脚下的黄土地,更多地指向内心的道德法则。览观四极在《庄子》中有更加出人意料的表现。
《庄子·逍遥游》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山木》写道:“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这无疑是先秦时代最伤感最深情的送别文字。庄子肯定到过海边,见过大海,要不然绝对写不出“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等类文字。庄子以览观四极的方式,实现了主体精神的自由无羁,他“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人间天地,绝对不是限制楚人主体自由精神的牢笼。穷极四海,周流天下,览观四极,主体张扬,这便是表现于楚文艺作品之中的楚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
三、地理环境与人文精神:生命意识的源和流
楚文艺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瑰伟奇丽、情感炽烈、惊采绝艳、恢诡谲怪、富于抽象形式美感和思辨色彩的艺术及文学作品之中。这种独具特色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既得益于灵秀无匹的荆山楚水的养育,也得益于楚人“人神交融”的南方式巫术思维。
同时,楚民族生命意识相对稳定的成型,还源于楚人情感中近似于太极两仪的“冷”与“热”之间的张力。
这是楚民族达观的生命态度、深湛的艺术智慧、超常的艺术想象的具体表现,饱含着楚人对于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眷怀,对于神秘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于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
《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着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④可见地理环境、自然气候都是影响艺术创造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地域内某种艺术类型的生命意识取向最早的决定性因素。
楚文艺生发于先秦时代的荆楚大地,此地有崇山峻岭、大江长河、平原沃野、静流深泽,地形复杂,地貌多样,物产丰富,四季分明。富于变化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环境,促生了荆楚文学雄奇秀丽、玄思妙想的独特品格。难怪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会发出如下感叹:“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荆楚地理的最大特色是土薄水广,这一点与北方地理相比,特色尤着。荆楚大地水势汪洋,既能润泽万物,又能为荆楚先民提供鱼虾蠃蛤之惠。水在荆楚人民看来,是衣食父母,是美与善的统一体,“上善若水”。《左传》哀公六年记载荆楚先民的祭典:
“三代命祀,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荆楚人祭河川,而不祭名山。江河湖泊的特点是深,是动,是灵活多变而激荡跳跃,颇具传统文化中“智者”的风范①。
楚人智慧的具体表现就是不拘一格的艺术创新。楚文艺的创新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即使是在生活器皿的制造上,也是如此。如楚式鬲的产生和形成,就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夏变夷,以中原华夏先民创造的鬲为样本,进行仿造性制作;第二阶段是用夷变夏,即采用荆楚传统罐形鼎的形制,改变了中原鬲的形态,推陈出新为萌芽形态的楚式鬲;第三阶段则是熔夷夏为一体,对华夏和蛮夷的鬲,融会贯通,创造出了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成熟形态的楚式鬲。再如青铜冶铸,荆楚先民成功地融合了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至楚成王以后,楚国的青铜铸造工艺青胜于蓝,创造了失蜡法或漏铅法,以及镶嵌黑漆等铸造工艺。楚人的准则主要不是模仿,而是创造。楚人所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
“于是,显然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出现了,楚国的青铜器卓然自成一家了。这样的成就,是长于铸造的诸夏和长于冶炼的扬越都不能企及的。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青铜器发展的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②。
在政治制度和军事管理方面,荆楚先民也体现出鲜明的夷夏结合特色,如楚官多称尹,形成一套独特的体系;列鼎呈偶数;所有封邑传承不过三世;兵制上设莫敖、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以“广”为作战单位……凡此种种,可以看出荆楚先民往往会有意显示出亦夏亦夷或者非夷非夏的民族个性来,那种强烈的自尊心和积极的独创性,于此可见一斑。
对楚文艺生命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人文精神传统,无疑还有楚人的“积强”观念和独特的“无”的观念。楚人鬻熊说过:“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
观其所积,以知祝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③以柔克刚,转弱为强,充满了辩证的光芒;这种转变也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积”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柔为常胜之道,正是荆楚人的兴国之道,熊绎跋涉山川以事天下,熊渠得江汉间民和,都是从柔弱中“积强”的准备阶段,到楚庄王时才会有一飞冲天问鼎天下的壮举。
楚艺术的哲学思想来源于老子和庄子。老子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第一次提出了“道”的本体论,而且在于他第一次用否定性概念来描述宇宙本体,充满了鲜明的辩证理性色彩。在西方,只有阿那克西曼德“无限”的概念可与之媲美。庄子将这种否定性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即不仅否定了肯定性,而且否定了否定性;如果说肯定、肯定性都是“有”,否定、否定性就是“无”,否定了肯定性是“无有”,否定了否定性则是“无无”,这是一种绝对的否定性。
庄子在《逍遥游》中追求绝对的自由,在《齐物论》中追求绝对的平等,认识到了人的意见、语言和理性都具有局限性,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楚民族的创造才能,丰富了楚文艺的表现形态,拓展了楚文艺的表达空间。
尚玄自适则是楚文化精神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与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相比较,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师法自然、贵己为我的思想主张具有极大的突破性和超越性价值。冯友兰说过:“先秦道家虽然有许多派别,但是也有一个一贯的中心思想:‘为我’。‘我’的主要东西,就是‘我’的生命。”④道家对于“类”并非不重视,即使是从哲学对立范畴而言,离弃“群”、“类”的“个”、“独”也不存在。但是,道家思想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还是其个人主义的思想主张。《老子》全书五千言,“我”字十七见,“吾”字二十二见,“自”字二十见,“己”字二见。《老子》的个人学说虽然是构建在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等二元性对立范畴基础之上,但又超越了此轸彼域的狭隘意识。在庄子看来,人的生命由“天”“赋予”,要保障个体生命,“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就要“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而人是处于社会、群体之中的,所以要尽个人生命的“天年”,就应该“因其固然”,“依乎天理”,与世无争,否则,生命历程中充满着“大轭”与“肯綮”,稍不注意就会丧命①。庄子对个体的关注,主要不在于对个体社会价值的阐发,而在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人要“存我”、“全生”,就要反对一切不义的、人为的战争对生命的残害,就要反对统治者借集体、家国的名义而加害天下的一切做法。道家文化此后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些爱好自由、张扬个性、维护自我权益、追求自我实现的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文艺家的精神源头。
楚文艺炽烈燃烧、无限投入或者超然飘逸、法天齐物的生命意识的起源则是楚巫。《国语·楚语》记载观射父之言:“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男觋女巫,统称巫师。在楚国,大巫都是社会精英。史载楚昭王时大夫孙圉论楚国之宝,首推观射父,次举倚相,第三才是物产丰饶的云梦泽。前面两位都是楚国大巫。大巫能够交通天人。楚文艺浓烈如火、上天入地的自由生命意志的实现和表达,显然其来有自。春秋晚期楚文化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巫学也开始分流:“其因袭罔替者仍为巫学,其理性化者转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为骚学”;“道家站在楚文化鼎盛期的起点上,冷眼看世界,尚能聊以卒岁。
骚人则站在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点上,热心向世界,就不免蹉跌和愁苦了”②。如此看来,楚文艺的生命意识是“一源二流”,一源即是巫,二流即是道与骚。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足鼎立,才形成楚文艺生命意识既迷离惝恍跳荡不息,又冷静超然相对稳定的情感结构。
深邃幽昧的大地,澹远苍茫的长天,惊涛骇浪的海洋,广漠大野的瓠樗,无一不是楚文艺的关注对象,其间贯注着楚人一往情深的生命意识。楚人热爱生命,热爱自由。“热心向世界”的屈原,固然为国事蜩螗和贤良见弃而“蹉跌和愁苦”,情发于衷,不能自已;就是“冷眼看世界”的庄子,也饱含一颗燃烧的心灵,对“人间世”充满了伟大的同情———虽然庄子一向是以消解情感的姿态展示于人前的。还是同为楚人和诗人的闻一多,最能够“同情地理解”庄子。
闻一多在《庄子》中反复称扬庄子:“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庄子的着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③。推而言之,创造了楚文艺的楚人,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情种”?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世界文化、历史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以后人类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④。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以对古希腊文明的回望,而实现了对中世纪神学摧枯拉朽的扫荡,从而获得了近代文艺的全面新生。楚文艺正好处在“轴心时代”,楚文艺炽烈的生命意识,一定可以为我们实现“新的飞跃”而“重燃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