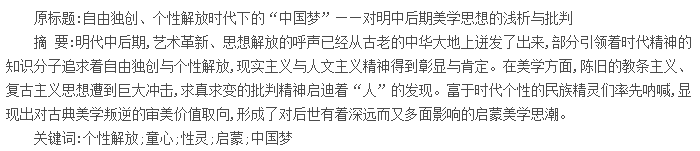
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中的艺术思想与审美理想是当时背景下民族理想、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处于明中后期的中国在艺术上与思想上也正经历着艺术革新、思想解放的碰撞、荡涤与变革。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的自我批判总是在其自身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的条件下进行的。
这一时期美学思想带有时代气息的启蒙正意味着这样一种自我批判及对古典美学的反叛。
当时,传统的经济、文化模式失范,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矛盾加剧,内忧外患的局面开始显现。这些都导致了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巨大冲击,新的文化因素开始律动。追求自由独创和个性解放成为当时整个民族在艺术上最高亢嘹亮的呼声。部分开明、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敏锐地从审美主体与传统意识对峙的新维度吹响古典美学自我批判的号角,在普天皇土上留下一脉异音。正是这一脉异音奏响了时代个性、人文精神洋溢的“中国梦”的新声。
一、千古“异端”李卓吾及其“童心说”
李贽(号卓吾)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工商业发达、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东南沿海地区,有着世代为商的家族背景,这使他对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近代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有更深的体察与同情,在抨击传统偏见时担当起新兴市民的思想、情感的代言人。
李贽的哲学是程朱理学的异端哲学。早年他也曾钻研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进得去”,也“出得来”,能以批判的眼光辩证看待传统儒教、理学。他认为宋明理学泯灭人的真性情,忽视人独立存在的价值。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主张人人效法孔子。
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他认为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不必依附于个人之外的权威。他尤其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套理学家的说教,力图冲破封建伦理束缚,肯定人们合理的生活愿望。这在当时有着唤醒人心、启蒙思想的作用。
由此李贽提出了童心说。童心,“真心、赤子之心”,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若后天学习了太多的儒家经典,童心就会丧失,那样就会造成人、事、文皆假的后果。他认为人的个性不同、阅历不同,只有从这些条件出发才能做出好文章。李贽要求文学作品表现“童心”,但又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要肯定和表现人欲,以人性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他肯定《西厢记》《水浒传》及当时的民歌,都直接根源于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李贽所说的童心,并非仅指人生来就有的纯真之心,最重要的还指对社会、现实真实的感受。李贽追问“人的存在”,重在批判虚假地存在于世的现象。所以,他认为艺术家要挣脱世俗传统观念束缚,把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表现出来。这才是童心说的实质。正如他那流传最广的评说“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李贽的“童心说”直接开启、引导了晚明美学与文学的繁荣蓬勃景象,有着积极的影响。他在封建伦理道德日益僵化的背景下向天下喊出了自己的“中国梦”:敢于求真,敢于突破世俗观念束缚,尊重个性,人的合理欲望应得到满足,并打破权威。李贽就是希望他所身处的中国能变成这样一个每人都能表达自我真实想法、个性自由得到尊重、合理愿望诉求得到满足的国度。
二、“情决生死”的汤显祖及其“情至说”
在晚明启蒙美学思潮中,如果说李贽是开拓前驱的话,那么汤显祖就是推波助澜的主将。李贽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自上而下地确立美学的主体性,而汤显祖则是自下而上地深化这一课题。作为明代大戏剧家,他的美学思想、艺术追求还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创作实践,其代表作《牡丹亭》可谓家喻户晓。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古典美学中,理想与现实是和谐统一的,美的理想就存在于现实之中,人们无须在现实之外寻求美的理想,理想的美就是现实中分散的美的集中概括。启蒙美学则以矛盾冲突为本质,同时包含理想现实的尖锐对立。汤显祖的创作实践便是去追寻现实之外的理想。他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情”,都由情产生,它们之所以感人,也因有情。结合汤显祖生活的时代来看,他讲的“情”有着更新的内涵。首先,他将“理”作为对立面,将矛头直指宋明理学及其中的封建伦理规范,反对“以理相格”,即反对用理否情。其次,“情”又与“法”相对立“,法”就是明代的封建政治法制。他将天下分为“有情之天下”“有法之天下”,对当今之世抱有批判性的态度。这虽值得肯定,但也存有对古代理想化的缺陷。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在《牡丹亭》中塑造了一个含“情”至深的艺术典型———杜丽娘。他借此人物来反对封建伦理、礼法,并在此基础上显露了他追求个性解放、自由的精神。当杜丽娘对柳梦梅相思成疾时,她竟死去;再度与柳梦梅相会时,又活了过来“。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乎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
于此,情已达到了可决生死的境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他已将情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为了情能够用热烈、奔放的幻想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现实无法实现的,汤显祖便将美好的愿望寄寓“梦”中,“因情成梦”。梦中的才是“有情之天下”,有情人方能终成眷属;这样的梦想又以“戏”的形式表达出来,把理想化成艺术形象,这便是“因梦成戏”。
该剧以变幻明灭的梦境、曲折离奇的情节及以情胜理的结局凸显了汤显祖的“情至说”,为“真情”“至情”唱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理想之歌,表达了他独具时代特色的“中国梦”:情是人生的真谛,情有独立的权利,应该从理束缚下解放出来。从理想主义、唯情主义的美学观出发,追求个性解放、情感自由,呼唤“有情之天下”,并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汤显祖这种美的理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同时又太富于理想化,也并未提出它的实现途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就继承了汤显祖追求“情”解放的审美理想,引领后人在“情”的世界里继续探索。
三、“公安三袁”及其“性灵说”
湖北公安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提出文艺应“独抒性灵,不拘客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性灵”指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欲望,为每人所独有,是每个人的本色。“性灵说”正如“情至说”一样,都是在艺术领域对“童心说”的呼应。三袁还强调“真人、真声、真文”“。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性灵”除了“真性情”之义外,还有“灵”的内涵。“灵”是汤显祖曾说的“心灵”,也是袁氏所指的“慧”、“慧黠之气”,即才气。
而“慧黠之气”的流动又产生了“趣”。“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因才气流动而趣味横生。趣,就是一事物给人的美感、审美趣味。故要有“趣”,则就要淋漓尽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欲与聪明才智。由此审美感受与追求个性解放的关系得以打通,对美的追求上升到了追求个性自由、人性完善的高度。
在美学、文学思想上三袁坚定地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倡导艺术的自由独创,倡导“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即时代变化决定艺术的变化,文学是社会实践产物。在此思想的基础上,三袁又提出了“胆”这一概念,以敢于自由创造、敢于因时变革,才有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
袁宏道在《与徐汉明》一文中说“不为禅亦不为儒,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人也”。他提倡不入世也不出世,不求主体合于社会或自然,而任一己之情,行欲行之事,不受清规戒律、仁义道德的羁绊,以追求主体意志的自由独立。比之魏晋名士韬晦以保全真性的佯狂,他们颠迷狂放并非力求消解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而遁入隐逸式的空间,作为时代先知、文化精英却因社会的黑暗现实及其普遍压抑力而被视为异端。继而他们将对此的苦闷与忧愤以癫狂的审美情感表现出来,达到与“适世”同形同构的自舒无拘、非道德非规范化的状态。但是,袁氏兄弟却没有说明性灵、适世和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他们在耽于山水、物欲中反抗社会,把主体情感欲望提升到本体地位,围绕人的自然天性对“性灵”和“适世”展开论述,因此带有一种脱离后天社会生活、实践的倾向。这也呼应了“最天下不要紧人”与“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的“山林之人”,为这类人率性、甚至放荡生活方式提供依据。故性灵说有脱离现实的消极因素和庸俗低等的趣味。这在清代的袁枚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明确地感受到三袁对那个时代寄托的强烈愿望,希望世人皆以自己真性情生活,以“才气”肯定自身存在的价值,获得美的享受,呼唤变革,尊重人的自由性与创造性。这是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期盼。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陈述,可见在明代中后期,文艺、美学思想上都反映了当时的士人对个性解放、自由创造的渴望。尤其是呼唤“真性情”,反映了当时人的存在价值意识的觉醒,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可看成是中国近代以前关于“人的发现”的端倪初见。而对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人格价值建构的反叛,也正是对追求欢乐情欲、高扬人自由主体意识的时代气息的积极回应。封建制度日益衰落并走向反动腐朽,儒家“温柔敦厚”“中和贵仁”的教条已成为统治者镇压、束缚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部分先进士人就是凭借对“人”概念的敏锐觉察力,发出了时代先声,这种“中国梦”的进步意义应充分肯定。
不过,我们也应理性看到,这些进步思想家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发出的上述“中国梦”也有一定的思想、历史局限。他们的学说立足于人性的完善健全和时代的进步,但都未找到可实现的现实途径,有着理想化、片面化色彩,没有与社会实践真正结合。这些,也值得我们深思和批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109.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56.
[3]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9.
[4]李贽.焚书和续焚书[M]. 张建业,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38.
[5]李贽. 焚书和续焚书[M]. 张建业,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298.
[6]李贽. 焚书和续焚书[M]. 张建业,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156.
[7]汤显祖.玉茗堂文之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96:38.
[8]汤显祖.玉茗堂文之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96:63.
[9]汤显祖.玉茗堂尺牍之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96:91.
[10]袁宏道.袁中郎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