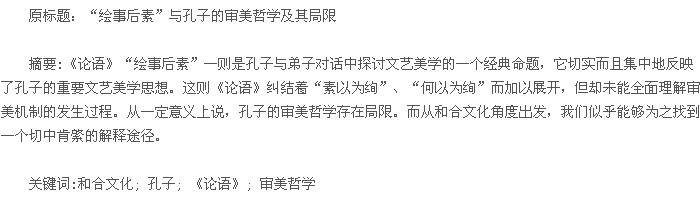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 “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
《论语》中的这则内容主要由师生讨论《诗经》而生发,触及儒学要义,并及绘画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先秦典籍的大量缺失,在流传下来的有关文献里,关于色彩与绘画理论方面的着述并不多,目前可见的,“绘事后素”就应该是最早的了。另外,《论语》本身里面专门涉及绘画理论方面的内容也不多见,“绘事后素”大概是唯一的一则了。因此,“绘事后素”一则虽然文字不多,人们却将之视若珍宝,并赋予其为微言大义的典范,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一直以来持续地关注它、研究它。
一、“素”喻关系及其含义。。
“绘事后素”,即“绘事后( 于) 素”,指“绘事”须在“素事”之后进行。“绘事后素”作为一般的工序说明没有太多值得我们深究的意义,但一旦放到了孔子与学生对话的现实语境中则别具深意与新意。这里孔子以“绘事”中的“素”接子夏的话头,喻子夏所云美人之“素”。与此对应的,孔子的“绘事”则是喻子夏所说的“倩盼”。如此,“绘事”、“倩盼”还好理解,孔子、子夏所云之“素”却一个本体、一个喻体,又具体分别何指、分别是何意呢?
“素”本义是生帛,白而细密的生帛,是一种未经漂煮加工和上色的丝织品,也正因为“素”的本身特性,后又以“素”来指称白色。《诗·召南·羔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毛传: “素,白也。”
《诗经·桧风·素冠》: “庶见素冠兮? 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庶见素衣兮? 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庶见素韠兮? 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逸周书·克殷》: “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尔雅·释鸟》: “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翚; 江淮而南,青质五采皆备成章曰鹞。”
元戴良《赠别祝彦明》诗: “此时悲送君,安能发不素?”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具体到“绘事后素”中,其“素”则指“素事”,即织素、打底的工作。因为是为“绘事”而准备的,这个“素事”当不仅仅指织素的一般性工作,还应该包括方便绘事进行的其他相关内容,总体上而言就是打“白底子”。这个“白底子”,重在其“纯粹之质”的涵义。《管子·水地》: “素也者,五色之质也。”尹知章注: “无色谓之素。”《伐檀》毛传曰: “素,空也。”《礼记·杂记下》: “纯以素,紃以五采。”
①刘熙《释名·释采帛》: “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巧饰也。又物不加饰皆自谓之素,此色然也。”孔子曰: “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 质有余,不受饰也。”这里的“素”,指事物之“纯粹”、“无”、“空”等“本来之质”的方面,即“白底子”。
事物的“本质( 底子) ”既可以是劣质,亦可能是美质; “绘事后素”之素当然是指“白底子”,指一种天生之美质; “素”之“白底子”的含义以纯净美白为主要方面,又常常引申和扩大用来指称某事物独有的根本美质,比如“纯”之清白、“素”之白净、“丹漆”之红润、“白玉”之通透、“宝珠”之光华等。人们在形容女子之绝美时,往往就要用到“素”之“美质”的概念。唐代着名的《敦煌变文集·欢喜国王缘》有云: “盈盈素质,灼灼娇姿。”女子素质与娇姿相互辉映,光华绝代,“娇姿”因“素质”盈盈而分外灼人,“素质”为“娇姿”灼灼提供支持。“素质”应指女子白皙的容色,女子之白皙,即其美质的主要方面。
清珠泉居士《雪鸿小记》: “融酥作骨,抟粉为肌,素质艳光,虽玉蕊琼英,未足方喻。”女子肌骨酥粉,冰清玉洁,光华四射,魅力照人: 如此的美艳,让人感叹世界上没有再好的词语能将之形容殆尽! 素质在此不专指容色之白皙,还有骨态之轻柔。虽仅仅素质而不论其美饰,但却已经是艳光无限,灼人双目了,道理何在呢? 这种疑问其实由来以久,不仅仅是清人有,抑或唐人有,早在春秋时候的子夏先生就已经有了: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你看,她嫣然一笑动人心呵,秋波一转摄人魂,天生丽质于是变得绚美灿烂、令人目炫神迷呵! 诗讲的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讲) 啊?
稍加考察,我们发现子夏引诗并未涉及“素”字,关于“素”的内容其实还在前面。《诗经》对孔子师生而言那是耳熟能详的,仅列举三句诗,是要言不繁之义。子夏引诗出自《诗经·卫风·硕人》,全文如下: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②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子夏所言美人之“素”是指这里的 6 个比喻句,即“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意思是,她的双手那样鲜嫩柔软,就像初春的草芽; 她的皮肤那样细腻光滑,就像凝结的脂肪; 她的脖颈那样细长白净,就像天牛的幼虫; 她的牙齿那样洁白整齐,就像葫芦的籽儿; 她的前额方正润泽,就像蝉儿的头面; 她的秀眉细软弯曲,就像蛾子的长须。诗人用“柔荑”、“凝脂”、“蝤蛴”、“瓠犀”、“螓首”、“蛾眉”等 6 种自然事物,来分别比喻、形容硕人庄姜双手之鲜嫩、皮肤之滑腻、颈项之白净、牙齿之整齐、前额之方正和眉毛之轻细,本体与喻体之间十分相似的特征是成此博喻的出发点,即鲜嫩、滑腻、白净、整齐、方正和轻细,这些就是硕人与生俱来的诸多美质,即“素”也。
二、“绚”美境界与文质之层次
“素以为绚兮”,即“素以( 之) 为绚兮”,“之”当代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人们为硕人之美所诱惑而目眩神迷、感动不已,但一时又找不到内心之所以被感动的原因,疑问也就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了。这是《诗经》即情与景的一般艺术手法。应该说,“素以为绚”是一个典型的审美过程,这种审美体验真切而生动,只是究竟存在一个怎样的审美规律或审美机制,审美主体一时间弄不清楚而已。
“绚”,即绚丽灿烂之意。《说文》里没有用其他字来互训或解释,就只单单引“诗云‘素以为绚兮’”而已。绚丽灿烂是一种美的客观面貌,结合到人的审美体验那就是目眩神迷了,美得让人目眩神迷。这可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美得要命”的意思。晋葛洪《抱朴子·畅玄》: “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寡欲》亦云: “其视秀惠温柔,不啻伐命之斧、鸠毒之杯。”伐命,即要命也。绝色美女不仅让人目眩神迷,而且可以美得让人送掉性命! 这样的审美体验确实够得上惊心动魄。
由此我们以为,子夏“素以为绚”之“素”与孔子“绘事后素”之“素”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特指女子鲜嫩、滑腻、白净、整齐、方正、轻细等诸多天生丽质。硕人既有诸多美质,再有“倩盼”一类华采文饰的表现,互辉互映,于是绚然而丽,光彩照人。
这里,其美质因“倩盼”而生动,“倩盼”助美质焕发光华。我们说,人人都可以巧笑逗人,人人都可以流盼传情,这些都可以轻易做到,但只有美人的“倩盼”才可以产生绚丽灿烂的审美效果,丑女不识好歹去巧笑逗人、流盼传情,则只能倒人胃口,徒取其辱而已。
“素以为绚”的含义,清初姚际恒的理解最为到位。其《好古堂家藏书画记·续记》云: “陆包山‘牡丹折枝’,根叶作绿色,花以墨圈,露纸地为白色。吴人画花卉,每用此狡狯,殆得素以为绚之意。上题诗云: 东风拂面花饶笑,浥浥轻韶沁玉肌。绰态玲珑那得似,水晶宫里月明时。”
①在陆包山的笔下,“根叶作绿色,花以墨圈”,此为画之文;而“露纸地为白色”则是充分利用纸白之质,寥寥数笔,素底纸质自成艳白花瓣矣。这样的折枝双花,无论花姿还是花色都在素朴中呈现一种淡雅的韵致,让人观赏的时候颇得一份雅思,即便灿烂夺目,也无张扬之弊。
关于“礼后”的理解,这里同样涉及这个“后”字的字义问题。因为《论语》以言简意赅为基本特色,所以省略处随处可见,这类禅偈式的问答客观上也造成人们正确理解文意的麻烦,这就需要读者认真联系上下文来体会原文本意。我们以为,子夏发“礼后”之问是建立在其已经理解清楚孔子“绘事后素”的回答基础上的。即,硕人既有柔美的手指、白净的皮肤、整洁的牙齿等诸多美质( 孔子“素”之喻) ,再有“倩盼”一类行为表现( 孔子“绘事”之喻) ,就一定会绚丽迷人吗? 不一定,还要符合“礼”。可见,“礼”是一个比“美质”更大的统摄性前提,不仅要有“美质”,更要有“礼”,如此才能通过“倩盼”一类行为表现获得“绚”的审美效应。子夏对自己的这种理解不是十分有把握,于是向老师求证。孔子开始并未想得如此之深,经子夏一点拨,顿时觉得与自己的礼乐思想瞿然贯通,豁然开朗,“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的感叹也就由衷而发。应该说,这是一个师生互相启发、教学相长的典型案例。
由上所述,“绚”的审美效应是通过“倩盼”来实现的,“倩盼”是饰,或可称文; 对“倩盼”而言,与生俱来的“美质”与“礼”都是质,是质的两个方面,且这两个方面都要先于“倩盼”而存在; 对“质”而言,其本身的这两个方面却不分先后,也都很重要。另外,相对而言,我们说“素”与“礼”还构成另外一个意义层次上的文质关系,即“素”为文而“礼”为质,“素”是既有的看得见的文的范畴,“礼”则是既有的却看不见的质的范畴。这些文与质的关系,再宽泛一点而言,就是形与神的关系,就是外与内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对于文质关系,孔子说得好: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相称才是最好的,才是最美的。
宋人黄裳云: “诗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美目之文见于容貌之间,无素而徒致其文,则趋于乱而已。有诚心之所乐,然后有倩兮之笑; 有诚心之所向,然后有盼兮之视。是则素以为绚者也。此庄姜所以贤乎?”①“容貌之间”,“素”也; “诚心之贤”,“礼”也。先有“容貌之间”、“诚心之贤”,然后有“倩兮之笑”、“盼兮之视”,则绚然而美。同样,针对子夏“礼后”之问,顾炎武亦说得简明扼要: “‘素以为绚’,‘礼’后之意也。”②就是讲“倩盼”不仅要在“素”之后更要在“礼”之后进行,以此达致“绚”美之境界。
三、和合概念对孔子审美哲学之补充
本文讨论的《论语·八佾》章短短数语是透视孔子审美哲学非常难得的文献资料,其审美探讨的中心则是一“绚”字,即“美”的研讨; 而何以为“绚”? 又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从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圆满的解决。何以为“绚”? 其实答案已然在《诗经》之中,即“素以为绚”也。不过,对这一答案如何去理解,却让人颇费踌躇; 也正是对这一答案的不解,才引起了孔子与学生这场关于美学的对话。
孔子试图以“绘事后素”来解释“绚”美境界形成的原因,但很明显没有能彻底解除子夏心头之惑,这也同时说明孔子对此审美现象的形成机制尚无清晰的思考,于是乎方有子夏“礼后”的再次征问。
那么,是不是“绘事”后于“素事”、“倩盼”后于“礼”与“美质”,“绚”美就可以发生呢? 好像还不能这么说。因为再怎么厘定清楚其先后次序,如果只是相互之间的独立存在,彼此不产生接触关系,仍然不会有“绚”美之可能。有了“白底子”,也有了绘画之人、绘画的笔与色料,人却不去使用笔与色料,是不可能有画作出现的; 同此,美人有了“美质”,也自有“礼”份,还能作出“倩盼”之举,但如果不相合一,仍然是不可能产生“绚”美之境界的。
苏轼《琴诗》云: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乐曲的产生单靠一把琴不行,单靠人的手指头也不行,还要靠二者切实地发生关系。再如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 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诗人对水、石之间发生关系的疑惑,其实与苏轼之于琴、指,思理相同。
佛教教义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之间正因发生了联系,才得以成为某种存在。
《圆觉经》: “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 “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楞严经》则更说得明白: “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 妙 指,终 不能发。”
事物之间的联系,往往相辅相成、和谐相契,以达致和合混一。水击青石,水本无声,石亦静物,但当风吹水动,水击岸石,才会訇然作响; 风从窗外经过,树叶发出了声音,空气本无声,树叶本无声,但是风吹树叶,却发出诸般大自然的妙音;再如秋风乍起,层林尽染,那种种颜色的名称恐怕也只有天书方能写尽。天道循环,生生不息。老子《道德经》开篇云“道可道,非常道”。“道”可以说,但讲出来就不是我们想说的“道”了。“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三家审美理想、审美哲学与和合文化有着难分难解的契合与呼应关系,和合概念更多时候对三家的审美哲学能有所补全,体现出一份独有的中国诗性智慧。
回到《论语·八佾》,有必要做一番“道可道”的事情,以从和合概念出发,相对彻底地阐释一下究竟“何以为绚”: 即“绚”美境界之发生,除了要先有“礼”与“美质”,次有“倩盼”之举外,根本上还要各因素彼此间相互和合统一,也就是说,《论语·八佾》应该续写两句,方臻大善。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 “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再曰: “和乎?”子曰: “合也已! 善! ”
聊为可惜的是,孔子是儒学宗师,非释门中人,如此用和合概念来解释这种美的发生机制,可谓强为之作解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