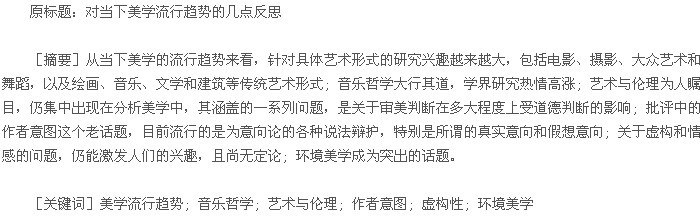
我将从一个美学期刊编辑的视角,对美学的某些流行趋势谈几点看法,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这可以看成是我 2000 年发表的题为《英国美学杂志: 40 年回顾》(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Forty Years On”,BJA,40,2000 年 1 月,第 1 期) 的那篇综述的补充。在那篇文章里,我回顾了 40 年来美学发展的趋势。
一
一个清楚而显着的趋势,是针对一些具体艺术形式的兴趣越来越大,包括电影、摄影、大众艺术和舞蹈,以及绘画、音乐、文学和建筑这些传统艺术形式。在最近出版的《劳特利奇美学指南》( Routledge Companionto Aesthetics,2001) 、《牛津美学手册》(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2003) 、《布莱克韦尔美学指南》( BlackwellGuide to Aesthetics,2004) 三本文集中,都有一些单独的章节,专门讨论那些具体的艺术形式,这并非偶然。而20 年前的美学综述,还不会是这样。举例说,在心灵哲学领域中,任何称职的研究者都不会忽视吉尔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 在 20 世纪中期做的经验心理学研究。在科学哲学中,门类清楚的分支( 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 得到了发展,正如在道德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得到了发展,甚至法律体系也涵盖了一些特别的用途。
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关注,既有利于美学接近实际的批评实践,又能促进美学与各学科( 如音乐学、电影研究、文艺理论和艺术史) 方面的专家之间的联系。这也给美学的那些宏大规划以有益的约束,特别是对建立高高在上、无所不包的艺术理论的美学规划企图的约束。但是,这也有些危险,如,美学变得狭隘了,更受文化的局限。英语为母语的哲学家谈起音乐、电影或文学,涉及的作品在范围上很窄,这都成套路了———写文章的人不可避免地谈论他们知道的那些作品,那十有八九是西方传统中的经典之作。对这些作品及其特点的概括,并不总能适用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品。当然,夸大这种担心,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西方艺术传统毕竟是巨大而重要的。如果哲学家们能够阐明它,那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美学会因此失去哲学的那个伟大的抱负; 无论会受到什么讥嘲,哲学的抱负是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是要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好像确实是共存的。换句话说,论题越抽象,发现的东西就越可能具有普遍性; 与对印象派绘画、前卫电影或现实主义小说的讨论相比,对真理、意义、本体论、符号或虚构的分析,天生就较少受文化的限制。
由此担心又引发另一种紧张感,即: 在讨论某一特殊艺术形式的细节时,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不可否认,莱文森( Levinson) 和基维( Kivy) 等哲学家能把相当抽象的哲学分析与关于具体音乐作品的那种言之有物的讨论结合在一起; 努斯鲍姆( Nussbaum) 讨论文学,或者卡罗尔( Carroll) 谈论电影时,也基本如此。但是,这种担心是: 美学的论题越抽象,争论所用的那些套话越具有分析性,美学就越能在更大的哲学圈子里赢得尊重。这种抽象研究能和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融洽,并能达到某种普遍性。然而,赢得尊重的同时,却付出了代价,因为它失去了作为一个自治的哲学领域的独特之处; 因而也面临一种危险,即失去了对它试图分析的那些艺术形式的接触,失去了与从事这些艺术形式的那些人的接触。另一方面,美学埋头于对具体艺术的研究,因此倒可能会扩大它的吸引力,美学看上去就可能不那么像是体面的哲学,却更拘泥于某种文化的狭隘眼界。我认为这些说法指出了目前美学真正的窘境。
二
在过去的 5 年间,《英国美学杂志》最受欢迎、也是提交论文最多的单一领域,可能就是音乐哲学了。对此,我没有现成解释,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国内外知名美学家,如: 罗杰·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 、彼得·基维( Peter Kivy) 、斯蒂芬·戴维斯( Stephen Davies) 、马尔克姆·布德( Malcolm Budd) 等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音乐美学书籍,以此为音乐美学搭起了戏台。实际上,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论题,如演奏的本真性和音乐的表现性,被陆陆续续地提出来。我将简略地回顾其中一个方面: 音乐哲学或称音乐的本体论。在过去的三四年间,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热情高涨。音乐哲学既是美学作为分析哲学分支的一个典型例子,也证明学界对特殊艺术形式的专注。朱利安·多德( Julian Dodd) 的论文《作为永恒类型的音乐作品》( “MusicalWorks as Eternal Types”,BJA,40,2000 年 10 月,第 4 期) 和罗伯特·豪威尔( Robert Howell) 的回应《类型: 原创类型和指示类型》( “Types,Initiated and Indicated”,BJA,42,2002 年 4 月,第 2 期) 这两篇文章再次激活了20 年前杰拉德·莱文森和彼得·基维之间的论争。多德站在基维一方攻击莱文森 1980 年的 《音乐作品是什么》( “What a Musical Work Is”) 一文,文中莱文森试图展示“尽管音乐作品是某种抽象的结构,但是它们仍然是可以被创作的”。
一般说来,音乐作品不等于某一次演奏,也不等于一系列物理声音———毕竟,在每一次具体的演奏结束之后,那个作品似乎仍然存在。作品也不等于纸面上的乐谱,因为乐谱可能会丢失或损坏,而音乐作品不会损坏。音乐作品好像是某种抽象的声音结构,很接近于数学结构。但是,种类和共性,这种抽象实体,通常被认为不受时间影响,是永恒的。圆形和三角形的属性不是人类创造的,正如我们说数学家“发现”了抽象定理而不是创造了它们。因此,站在多德一方的哲学家认为,严格说来,作曲家只能“发现”而不是创作了被认为是纯结构的音乐作品。但对莱文森来说( 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也一样) ,那种结论太过荒谬,是无法接受的,作曲家当然必须创作他们的作品。为此,莱文森还引进了“指示结构”这个说法,以与“纯结构”相对照,他还引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类别“原创类型”。确实,指示结构和原创类型( 音乐作品是原创类型的例子) ,会在某一特定时刻,因为某个人类行为的指示或者始创而出现。然而,多德正是对后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原创类型确实是类型,类型在本体论上又与共性一样,而且如果共性无关乎时间,那么原创类型也必须是永恒的; 因此,莱文森的创造论则不攻自破。
尽管我仍然支持莱文森的观点( 豪威尔也维护莱文森) ,但多德的结论———不管多么有悖直觉———却很难反驳。莱文森观点的推论之一,即: 作为指示结构,音乐作品从本质上来说永远属于作曲家( 尽管我并不赞同此观点) 。按照莱文森的观点,从哲学上看,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其他人完成。即使别的某个作曲家碰巧想出了一模一样的同一系列音符,那也不可能与《第五交响曲》完全一样。我同意莱文森的假设,认为不同的认定条件适用于难以识别的客体或结构。如果与《第五交响曲》碰巧完全相同的声音系列( 与贝多芬没有任何联系) 在 20 世纪末真的曾经被创作出来的话,那么,该音乐作品要么看似过时,或者是拙劣的摹仿,要么就是刻意复古。但是,这一切绝不会是贝多芬作品的特点。因为拥有不同的特点,20 世纪的这个作品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都必定是独特的,即使它们的结构是相同的。在莱文森看来,上述两个作品,是相同的纯结构,却是不同的“指示结构”。但是,接受那个结论并不足以迫使我们接受莱文森关于音乐作品起源的那个必然性的一般说法。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看问题有失偏颇。《第五交响曲》在本质上确实属于贝多芬,但那部分地是因为这个作品有偶像地位。不考虑作品创作时的独特情势,就不能把作品的核心特点说得那么清楚。对于没有偶像地位的作品而言,作品的核心特点干脆就说不清楚了。关于作品的确认条件,关键是它们必须能够保存价值。要让两个结构算是同一个作品,它们就必须能提供同样的美学价值( 共有同样的美学品质) 。对于有偶像地位的作品来说,美学价值部分地归属于原创者; 但是,对于所有音乐作品而言,就不是这样了———同样的价值和旨趣倒是也能保住,不管作曲家是谁。我们没必要否定自己以证实某一个作品可以由在相同的艺术环境中工作的任何一个作曲家所谱写。
三
最近几年,另一个为人瞩目的主要领域是艺术与伦理,仍然集中出现在分析美学中。这个领域涵盖的一系列问题( 问题本身并不新鲜) ,是关于审美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道德判断的影响。引发最近期刊论争的动因是诺埃尔·卡罗尔( Noёl Carroll) 的《适度道德主义》( “Moderate Moralism”,BJA,1996) 和波利·高特( Berys Gaut) 发表在莱文森 1997 卷《艺术与伦理》( Art and Ethics) 上的《艺术伦理批评》( “The Ethical Criticism of Art”) 这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引发了关于这个话题的小规模论争。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自己是在攻击某种唯美主义或者形式主义,都试图将道德判断引入审美价值之中。在卡罗尔的核心论证中,有一个关于叙事和叙事结构的构想; 叙事和叙事结构基本上涉及读者或受众的反应方式。卡罗尔认为没有受众的想象力补充的叙事是不完整的。若无受众想象力的补充,叙事作品就是不完整的; 从这一无可争议的前提开始,卡罗尔论证说: 有时候这种必要的补充是一种道德类型的补充,如在邀请受众对叙事内容采取赞同或反对的道德立场的时候,如果受众确实不能接受作品所要求的道德立场的话( 这可能是因为那与他自己的道德情感立场相去太远) ,那么叙事目标就没能实现,而这种失败是艺术上的失败,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失败。
这一论断很有独创性,但最终我却认为道德主义( 无论多么适度) ,并未得到充分论证。卡罗尔期望我们为我们的直觉鼓劲儿,手段是诉诸那个随时可用的备份: 希特勒。无疑,他认为我们都会赞同: 一幅将希特勒塑造成悲剧人物的、让人同情的肖像画,绝不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当然,永远不会有人同情希特勒; 因此,以同情为目的的一幅作品将成为艺术上的败笔。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情况是不成立的,虽然在实践中很难想象出一幅如上所述的、有价值的作品。从理论上看,把最极端的人间邪恶描绘成( 比方说) 一种有缺陷的人类状况,这状况有些可怜,不是没有可能。弥尔顿不曾提供给我们一个令人同情的撒旦形象吗? 莎士比亚不曾描绘过麦克白吗? 麻烦的是,一旦与宣传搅在一起,问题就变得混乱不堪。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居然会起劲地宣扬纳粹主义,我确实感到这不可思议; 它是纳粹的宣传品,则另当别论。但是,这里的毛病,不仅仅是得到宣扬的纳粹主义,而是艺术宣传的任何观点。任何艺术作品,如果其主要目的是宣扬某种意识形态或道德观,那它作为艺术就存在潜在的缺陷。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Hard Times)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证。正是因为它竭力宣扬社会正义,也就夸大并扭曲了某些主要人物。葛擂挭的实用主义跌入自嘲; 企业家庞德贝先生罪孽深重无以解脱; 无可挑剔的工人史提芬·布莱克普,则完美得让人疑虑重重。这些都是艺术缺陷,但我们很难挑出其道德内容上的毛病。
我们必须把作品中的道德内容与道德反应、道德见解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并非相生相随。大多数艺术作品都有道德内容,关于人,他们的动机、欲望以及选择,都可以用道德的说法来描述。卡罗尔在这点上是正确的: 正如他所说,在反思道德内容时,读者需要“激活他们自己的道德力量”,并且去填补不曾明言的细节。
有时,需要读者去想象( 并用想象来补充) 的东西,几乎是他们无法做到的。若是如此,读者就无法进入作品的世界。有时,想象上的这种失败与在道德上的别扭有关。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去想象某种与我们的道德设想相去甚远的东西,我们就无法想象。这看起来像是艺术上的失败,而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度道德主义者认为道德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极少适用于所有内容。假如某一作品要求我们去想象一种家具,但对大部分受众来说那干脆无法想象: 设计太古怪、太不像家具,而且太缺乏实用功能等; 那么,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除非在极小程度上) 家具价值就显然与美学价值相融和; 如果承认道德主义,我们也必须连带着承认家具主义。实际上,道德也罢,家具也好,同样的审美上的失败出现在这两种情形之中: 那是连贯性的失败,是想象性的失败,是那个作品强人所难。作品要求我们沉浸在它们自己的世界里。但是,我们有时候无法遵命: 作品太乏味、太异想天开、太叫人厌恶、太让人费神。然而,道德内容在表现上的弱点,与任何其他内容上的弱点,在种类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谁另作他想,我相信,那才是道德上有毛病呢。
四
我要讲的第三个样本话题,是批评中的作者意图这个老主题。目前有很多人以此为题给《英国美学杂志》投稿。关于这个题目,你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有分量的新东西; 但是,目前却很流行为意向论的各种说法辩护,特别是所谓的真实意向和假想意向。前者由诺埃尔·卡罗尔和嘉瑞·艾斯明格( Gary Iseminger) 提出; 后者的支持者是杰拉德·莱文森和威廉·托赫斯( William Tolhurst) 。
我个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假。首先,我认为真实意图其实陷在了假想意图中。用莱文森的话说,根据“作品中的证据,以及具备合适的背景知识”来形成关于作者意图的假说———不这样做,支持真实意图的那些人还有其他办法吗? 其次,我认为参考“作品意义”是完全误导的。像小说或戏剧那样的作品具有意义,在方式上不同于句子或者词具有意义。没有一个哲学家会问“休谟的《人性论》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假定那个问题用在《哈姆雷特》和《战争与和平》上就有道理? 其三,与上文相关,参考说话者的意思或者话语的意思———不同之处是要抓住真实意图与假想意图间的差别———也是不合适的。从言语行为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作品是一种话语,因为与话语语境相关的那个恰当的想法不见了。最后,我坚信卡罗尔在文学作品与对话之间所做的关键类比是不可信的。想想看,在对话语境中谈什么阐释,那该有多么奇怪吧。如果会话话语需要阐释,那也只能出现在会话结束/破裂的时候,这是唯一例外。在谈话中,只有某一句评论性的话才可能需要解释,那还是在谈话中断的时候才发生的。在谈话交流中,也没有作品中的那一整套对文学至关重要的把戏; 谈话中不存在有待于引出的主题,不存在有待于识别的象征,不存在有待于找出的联系,不存在有待于注意的互文性。这正是与文学阐释相关的那些事儿; 但是,在寻常的谈话中却毫不相干。目前,持意向论观点的文论之争所缺乏的东西,正是在我看来把论争搞得索然无味的关键: 即关于文学批评的意义、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特别兴趣或者价值的见解。寻找类似于谈话的那种意义,这种勾当太陈腐乏味了,难以恰如其分地开始文学所要求的那种欣赏。实际上,意图论者的论争劳而无功,其原因不是因为其论点质量差( 即便质量确实是差) ,而更是因为那种论争坐落在不同的文学概念之间的断层上: 文学是对永恒真理的客观“模仿”( 古典主义) ; 文学是个人情感表现的工具( 浪漫主义) ; 文学是纯粹的语言制品( 现代主义) 。这些观念仍然都很活跃。
五
关于其他话题,我说得更简短些。在我的编辑邮袋中,几乎总有关于虚构性的稿件。关于虚构和情感的那个老掉牙的问题仍然激发人们的兴趣。但请注意,就落在纸面上的全部东西而言,我认为那个问题尚无定论。品尝一番新话题,可能会有帮助———关于恐怖电影,沃尔顿( Walton) 的“为自己害怕”( 而不是更常见的“为别人害怕”) 的晦涩用法,对论争有歪曲作用。艺术的历史定义,本来是莱文森提出的,是另一个受欢迎的话题,有稳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那个想法是这样的: 有一个一般被认作艺术品的作品体系,以此为出发点,任何东西,要想被看作那个作品体系的成员,它本身就是艺术品。在这个定义中,有一个不错的递归因素,刚好能避开循环论证。卡罗尔通过引进一个观念改良了这个定义,那就是与艺术有关的一些故事。这些论述的难点在于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确立一种正确的关系———既坚持延续性,又为激进的新创作留下空间。但是,如果那些使艺术史联在一起的叙事,既允许摒弃过去,又支持延续过去以求发展,那么,任何要求成为艺术品的作品,又怎么可能不会成为艺术。对我来说,那太宽容了些。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也是在目前的潮流中很突出的话题,就是自然美学或称环境美学。对美学来说,眼光要超越艺术哲学,是一种积极的举措,尽管这仍然令人想起这个现代论题的根源是在康德那里。追溯到 20年前,哲学家们多半想当然地认为: 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从本质上看,与康德的思路一致,那是建立在对自由美的判断之上的,事关孤立对象的形式特征,大致与概念无关。人们普遍认为,对自然的欣赏与对艺术的欣赏截然不同; 因为对自然的欣赏,没有惯例或规范,也不拘泥于任何既定的批评术语或传统。但是,阿兰·卡尔松( Allen Carlson) 改变了一切,提出了一种认知观点; 按照这个观点,对自然的审美欣赏,要想严肃而恰当,那就必须了解自然科学的背景知识,特别是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知识。要想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和环境,我们就必须充分明白它是如何变成如今那样子的。卡尔松的观点与肯德·沃尔顿( Kendall Walton) 的看法是一致的,沃尔顿坚信: 只有把作品放在合适的类别中来感知,对艺术的审美欣赏才是可能的。为什么风景看起来是那个样子? 是什么赋予一道山脉与众不同的外貌? 要解释我们对外貌的反应方式,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外貌之下。卡尔松观点的优点是: 它把美学与环境规划的实用而有理据的决策联系了起来,它与生态保护的伦理关怀联系在一起; 它还使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更加接近( 在艺术那里,人们认为背景知识是必需的) 。同样有意义的是,它首次把哲学中的分析方法引入环境美学领域,使环境美学走出了纯主观或者流于印象的境地。
因此,对美学目前状态的最终评估是什么呢? 有相当多言之有据的论争,说美学迷了路,说美学断了气,没有道理; 一种目的上的严肃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高质量的论文不断发表,还不仅仅在美学期刊上发表; 出版商兴趣浓厚( 看看一系列选集、百科全书、伴书、手册、指南,还有学生导读等出版物) ; 美学家( 至少是对那些称职而且灵活的美学家来说) 有不错的就业前景; 在许多方面,明显有研究机构的支持; 美学是一门融汇到哲学课程表中的课程; 在学术界,重要任务受尊重; 新话题,以及关于旧话题的新想法不断涌现; 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研究生越来越多,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说明美学健康发展的状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