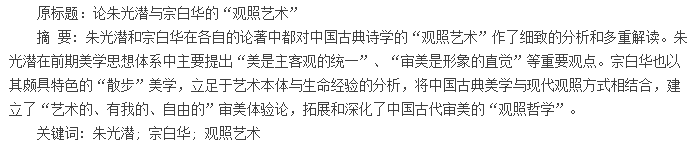
“学者风范”的朱光潜与“诗人气质”的宗白华在各自的论著中对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的“观照艺术”都颇有见解。“观照”一词来源于佛家,《佛学光大辞典》解为: “以智慧观事,理诸法,而照见明了之意。”它要求主体以般若智慧直观事物,直接洞见事物的本质。即指一种不借助理性解析的直观体验。
“审美观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殊范畴,它不仅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的起点,更贯穿于整个审美活动过程中。“观照艺术”作为动词可理解为审美认知论,作为名词则可看作是审美创作论。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所独特的韵味与意境,皆与“观照艺术”密切相关。对于“绝对美的观照能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的审美“观照哲学”,也能清晰地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美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
一、“聆听暝色赴春愁”: “情”与“趣”的修养
宇宙自然中“声音的大小、旋律的长短”自可用耳聆听,“光线的明暗、线条的流转”自可由目见出,而“距离的远近、空间的转换、气韵的流动、生命的律动”更是可观、可感。对“生命节奏”的把握离不开对艺术实体的重视,也离不开审美体验的积累,更离不开审美主体“观照艺术”的修养提高。朱光潜主张以“读诗”来培养个人纯正的趣味。在他看来,“诗是文学的精华,真正的文学都必有诗的特质,”所谓“诗”,包含了一切纯文学,“非诗”就包含了一切无文学价值的文字。
朱光潜眼里的“故事”就是小说与戏剧中最粗浅的部分,而“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扶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
这些弥散着香气的“葛藤花卉”就是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每个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自然无往而不美的真正原因在于宇宙自然无时无刻不在“人情化”、“理想化”。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情趣深浅成正比,艺术趣味的高低决定是否能够冷静地“见”出形象的美。
宗白华同样重视艺术家的自身情趣修养,他在谈及“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时,十分赞同普罗廷诺斯的观点: “你若想要观照神与美,先要你自己似神而美。”倘若你的心灵是美的,那么宇宙“真、美”的音乐将直接“赴”向你的心灵。这一“赴”字用得巧妙,盛唐诗人皇甫冉的《归渡洛水》中有一佳句: “暝色赴春愁,归人南渡头”。古来暝色易触人深情,徒生忧思,描写暮色、黄昏与愁绪的诗句数不胜数。只有深入到自然中观悟,方能坐拥“倚枕自歌,能移我情”的审美情致。“诗人气质”的宗白华恰也能够化愁为美,有诗作《春与光》为证:你想了解春么? 你的心情可有那蝴蝶翅的翩翩情致?你的歌曲可有那黄莺儿的千啭不穷? 你的呼吸可有那玫瑰粉的一缕温馨?你想了解光么? 你可曾同那疎林透射的斜阳共舞? 你可曾同那黄昏初现的冷月齐颤? 你可曾同那蓝天闪闪的星光合奏?诗人宗白华善把玩这宇宙黄昏时刻的点滴妙悟,集“斜阳、冷月和星光”,化作杯中的滴滴美酒,皆“赴”了这永恒的春愁,同宇宙共“饮”了这杯春光美。视觉的观感仅作为生理刺激与官能满足的条件,至高的美不是感官所能感觉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宇宙的音乐“赴”向心灵,自然的暝色“赴”了春愁,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审美佳境,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取生命的同情。
二、“流观静照忘所求”: “真”与“诚”的坚持
与朱光潜“文学到了最后都必定是诗”的观点不同,宗白华认为“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艺术是生命的审美延伸,由于音乐是生命状态的直接表现形式,音乐的节奏与和谐具有强烈的感染性,因此,作为生命表现的不同形态的艺术不能不是趋向于音乐的。中国古代所谓“乐”,并非纯粹的音乐,而是舞蹈、歌唱、表演的综合。无论是中国诗、画、书法、建筑等艺术皆融于“舞”,富有音乐的情趣和节奏,音乐的节律与和谐。然而,他又更为强调“一切艺术虽是趋向音乐,止于至美,然而它最深最后的基础仍是在‘真’与‘诚’”。“真”和“诚”皆出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是我国古典诗学的传统原则。“真”字最早见于《老子》第二十一章: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对“真”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形象化地解读: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庄子·渔父》)庄子在这里阐扬“保真”的思想的同时也提到了“诚”,强调情感的表里一致,内外如一,方能动人。《易传》中所提出“修辞立其诚”的命题,引发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诗品、人品的讨论。作为“观照艺术”中的审美态度时,“真”与“诚”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方能成就真切动人的美。宗白华认定“真”与“诚”为艺术最深最后的基础,是有感于现实中的“伪”与“欺”,眼前所见所闻的一切是不真、不诚。像圣人那样入凡尘乱世而坚持“真”、“诚”,做到不“伪”不“欺”,不拘于俗,并非易事,而宗白华身体践行,用优美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留给我们一个亲切而温暖的背影。当代美学家汝信在《宗白华评传 o 序》中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他以歌德为人格的理想和人类精神文化的代表,从歌德那里接受了对生活价值的肯定态度,以‘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倾情追求人生的审美化、艺术化,学术界因此称赞他‘出淤泥而不染’,有晋人风度、陶渊明风格和哲学家的风范。”
与朱光潜在《谈美》和《文艺心理学》等论著中回答了“什么叫做美”的问题不同,宗白华对美的本质没有做过多的追问,而是以“美从何处寻”为目标,对“唯美的、艺术的”人生展开了艺境的探索。宗白华在他的“散步”美学中,把“诗与春”当作美的化身,诗为艺术的代表,艺术的审美正通过意象的塑造来满足人们的美感需求。春乃自然,“移我情”的生命体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由此可见,其重视艺术本体和生命体验,将自然、艺术与人生三者紧密联系的研究特点。
宗白华的“自然”是流动而充满活力的。自然是宇宙生命的纯真体现,是审美观照的首选对象,也是美和艺术的创作源泉。取法自然、师法自然方能酿就艺术的永久生命。他在《怎么样使我们生活丰富》一文中说:黄昏片刻之间,对于社会人生的片段,作了许多有趣的观察,心中充满了乐意,慢慢走回家中,细细玩味我这丰富生活的一段。追溯到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论艺术本质所讨论的“模仿自然”: 柏拉图认为人类感官所接触的自然乃是“观念世界”的幻影,亚里士多德与之意见不同,他认为自然界现象不是幻影,而是真实的生命实体。对虚幻世界进行形而上的探索,就是“真”; 将真实的情感表里如一诚实不欺的表达出来,就是“诚”。“真”与“诚”正是宗白华对“自然”的观照态度,而情感是推动逻辑语言成为音乐语言的要素。这种微妙境界的实现,端赖于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
翻开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历史,庄子眼里的自然不仅是“活”的,还有“丑”的一面,正如宗白华对庄子的描述: “他好像整天在山野里散步,观看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 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禅宗也不避讳谈丑,正视现实人生的种种丑恶与苦难,执着的贪欲是人痛苦的根源,寻求超越世俗痛苦的办法。然而,自然美与人格美渐渐统一,到了魏晋玄学便不太提“丑”了。从此,自然总是那么美轮美奂,可以令“人情开涤”,把人超升为“风尘外物”。故而,宗白华艺术理论中的“自然”大多经过“自然原则的人格化”处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就带有浓厚的人格唯美主义色彩,可谓艺术人生化的代表。人生、艺术、自然确实构成了他诗性宇宙的整体轮廓,而这三者之间之所以能和谐共融,就在于它们都以生命的自由展示回应着整个宇宙的生命律动。
艺术作品中不仅有诗人的真实情感,还应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精神,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获得较为永久的生命力,点滴渗透进艺术的人生。
三、“游心移情缓入境”: “回”与“旋”的艺术
审美主体运用什么样的观照方式去体验世界,这不仅作为“观照艺术”的核心,其观照方式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朱光潜在论“诗的境界”时,认为“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且“诗在任何境界中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他在论著中的“观照”或是康德“无所为而为的玩索”: 受康德“先验直观的纯形式”和“合目的性逻辑表象”等理论的影响,朱光潜的“观照艺术”大多也建立在该方法的综合上,即以“直觉、距离与移情”三方面对美感经验做出解释,强调审美主体的非功利性与无所求,以见出“没有道德目的而合道德目的”的文艺为最佳; 或是尼采“阿波罗式的观照”: 阿波罗本身即为“诗神”,“诗神”的观照是“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或是一种“聚精会神”的观照: 在凝神的境界里,忘记了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观照对象与周围的关系,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朱光潜提出建构“节奏模型”的概念,他认为: 诗与音乐的节奏常有一种模型,在变化中有整齐,流动生展却常回旋到出发点。这模型印到心里也就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模型,我们不知不觉地准备着照这个模型去适应,去花费心力,去调节注意力的张弛与筋肉的收缩。有规律的节奏都必能在生理、心理中印为模型,都必能产生预期。
为了把握这“流动生展而回旋于初”的节奏模型,要求以“回旋”的观照哲学与之相适应,从有限到无限的统一,从诗境到心境的升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审美境界。与朱光潜的“节奏模型”概念相比较而言,宗白华更加向往于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所描绘的“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的审美情致,他认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两元。”并推崇俯仰宇宙的观照法,“俯仰往还,远近取去,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诗与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
他在《宇宙的诗》中如此说道: “宇宙的诗,他歌了千百万年,只是自己听着。”透露出诗人所体验的宇宙是无边孤寂的。他在《宇宙的灵魂》一诗中说道: “宇宙的灵魂,我知道你了,昨夜蓝空的星梦,今朝眼底的万花”。将宇宙的体会活泼地呈现目前。或是在《雪莱的诗》里激动地呐喊: “雪莱,我听到你的诗了! ”
从这几首小诗里,我们看到诗人的赤心与激情和他难以抑制的喜悦,迫不及待想去寻求诗人的所见所观,迫不及待想去体验诗人的所悟所感,迫不及待想去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这样的艺术心灵恰恰包含着审美静照与同情,在创作中妙悟宇宙的“生生节奏”。生命有形式的表达,而形式在生命之中,从中获得启示抵达形而上的宇宙,体悟人生的最深至境。
这“暝色赴春愁”自主的审美选择与“无所为而为”游心的审美观照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 宗白华在《美从何处寻》一文中指出: “这里我所说‘移情’应当是我们审美的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条件,而美学家所说的‘心理距离’、‘静观’,则构成审美的消极条件。”
“静观”是一切艺术及审美活动的起点,“移情”是主体心理的积极选择,是心物流转而循环往复的审美观照,主体在进入宁静的观照时,其积极运思的过程,即建立了主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眼不可见的事物,以心灵去体悟世界是中国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宗白华在主张“静观”的同时,还提出“活静”与“审美同情”的观点,重视心灵对于宇宙的生命体验,强调反省内倾的形而上的观照哲学。一个艺术品,没有欣赏者的想象力的活跃,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中国哲学如《易经》以“动”说明宇宙人生,正与中国艺术精神相表里。
“流观”的本质在于强调审美主体在静观的同时,将人生的哲理沉思注入到审美的情感体验,而得情景交融的情致和虚实相生的境界。艺术的有机体对外是一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尽管是实用世界的回光返照,却没有实用世界的牵绊,它是独立自足而别无依赖的。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以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身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
无论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和“以静观动”、庄子的“游心体物”和“无为复朴,体性抱神”,还是禅宗代表著作《坛经》中所言的“识心见佛,自成佛道”的“顿悟见道”说,其思维方式均是将外界自然人化,指向人的自身,强调人自身的能动性,在主体的自我体验与自我反思中,穷尽人和万物的一切道理。中国人不是向无边空间向外作无限制的追求,而是向内在心灵做回旋的往复,构成独特的宇宙观。
不难看出,“观照艺术”最终指向于“创造”,回归到艺术与生命,而节奏与和谐恰能体现生命深处的旋律与情趣。艺术意境归根结底诞生于人的性灵中,要求我们不仅要以“同情的态度”来“玩味生活”、“妙悟人生”,通过“观照艺术”渐入艺境,还要按照心中“美的理想”来创作出“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的人生。
参考文献:
[1]慈怡. 佛光大辞典( 2 -7) [M]. 台湾: 佛光出版社,1988.
[2]张锡坤. 周易经传美学通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 第 5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4]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 第 6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5]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 第 2 卷)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7]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 第 3 卷)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8]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释[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9]王德胜. 宗白华评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10]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 第 1 卷)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