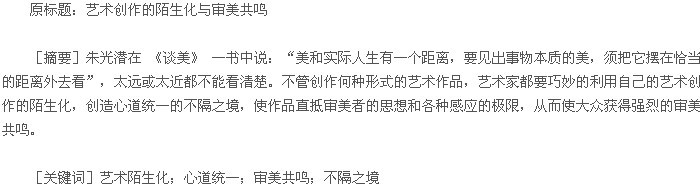
惊鸿一瞥、过目不忘与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是一对相背的词语,前者是在大众惯有的审美习惯中从未有的令人惊异又充满感动和美好的视觉印象,后者则反之。艺术作品最怕的是后者,对太过熟悉或太过陌生的事情,审美者常常报之以麻木或抗拒。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就是这个意思。朱自清先生说:“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描写,使你与平常身历之境,也含有惊异之感。”艺术创作要避免和别人雷同,这个容易做到。
但要注意自己描写的角落,一定要拨动很多人的心弦,做到独特又与大多数人达成心灵的共鸣才是艺术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探索。
一、艺术创作的陌生化
艺术作品的“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它是要在艺术创作中将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物按照一种超出常规的形式表现却又被人的情感完全接受的表达,审美者不仅不感到别扭难受,相反会感到它挑战了自己的审美经验,并在审美愉悦中同步得到了经验和情感的升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技巧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势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艺术创作的陌生化从来就不是单指形式感的陌生,它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陌生。但这个陌生对大众来说不是完全不识,而是情感上愿意靠近并无限接近它的陌生。
(一)舞蹈的陌生化语言以杨丽萍为例
舞蹈是用肢体语言传情达意的艺术样式,但在视觉艺术浅表化的当下,舞蹈的处境愈发尴尬和落寞。它或是充当舞台的背景,或是沦落为吃青春饭的肢体运动,纵观舞蹈界,能单枪匹马杀出重围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杨丽萍是个例外,她的出现像是茫茫人海中的惊鸿一瞥,看过就再也无法忘怀,而你的精神会自觉的选择和她一起浪迹天涯与海角。欣赏她的舞蹈,无论是《孔雀》,还是《月光》《两棵树》《松竹梅》,无不被她创造的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所深深打动,在她的表演中,仿佛看到一粒种子在静谧的时空里茁壮成长并孕育着勃勃的生命迹象,那是令人无比欣喜、感动和向往的生命状态。无疑,杨丽萍是天然的,它的天然不仅仅是她从小就徜徉于云南洱源那片神秘宁静的旷野之上,更是她的灵性与天地万物交相呼应的问答中感悟出生命本源的力量。
除了杨丽萍的独舞和双人舞,由她编排完成的大型歌舞集《云南映象》《藏迷》《云南的响声》同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力量。舞者都是她在少数民族寻找来的擅长原生态歌舞的农民,他们每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绝技,而这种绝技是他们出色的艺术天赋在一代代的歌舞传承者中创造演变出来的。将舞蹈艺术回归到充满泥泞的乡间小路、回归到带着草香的泥土里恰恰是杨丽萍对舞蹈艺术最具人文关怀和生命本质的追寻。然而,她是不会只满足于发现并推荐的,因为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充满生命力的歌舞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有着太遥远的距离。杨丽萍要做的是把这些瑰丽的珍珠一颗颗小心的捡起来并用特别的线绳串起来,这就是艺术构成的方式吧。如果我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来形容看过的感受,你一定懂得那是怎样的惊艳和惊心动魄,那颗早就被压抑和麻木了许久的心真想跟着舞台上的舞者一起肆无忌惮地撒撒欢,大声地吆喝上两嗓子,而舞台的灯光、色彩、舞美、化妆、道具、音乐无不和谐紧密的透露出人类在探求世界过程中的生命呐喊和无穷力量。在杨丽萍的大型歌舞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单纯的肢体运动,而是在舞者强大精神驱动下呈现出的充满幸福憧憬与蓬勃张力的肢体语言。
正如在漫天飞土的黄土高原上打着腰鼓的汉子,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强烈的表达愿望使其身体与灵魂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融合。而一个没有信仰和精神世界的人是不会呈现出如此强悍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吧?!所以,他们是把舞蹈当做自己的宗教,并在日渐丑陋和荒诞的世界中将自己一步步救赎而出。每当看到这样的作品就会不由自主的流泪,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我知道,那是对人类正在不断丧失的生活热忱、真诚、激情、憧憬和信念的无限感伤,更是内心对这个世界越来越稀有的一种品质所做的倔强挽留。杨丽萍对原生态歌舞的挖掘和关注是她爱舞蹈爱艺术的生命轨迹,但在我看来,它同时也是对那些在“现代文明”的过度追寻中不断丧失心力的现代人精神的致命撞击。它展现的不仅是艺术表现手法的透彻之美,更是每一个有力量的生命个体对美好生命的不断追问。作品中气定神闲的正能量表现的越纯粹,我们麻木的灵魂感受痛苦和幸福的能力就越细腻。它瞬间唤醒的是审美者对更纯粹的自我、更透彻的生活以及更广大精神的深沉爱恋和怀念。
(二)文学的陌生化语言———以木心为例
陈丹青形容木心是“一个叛徒和与世隔绝的人”。他不仅在“文字”上从不讲我们习以为常但又让人心领神会的语言,而且戴礼帽,拿手杖,从不穿中山装,他既不是文艺圈里的大多数人,也决不从众。陈村在读到木心的《上海赋》时说自己“如遭雷击”,于是撰文宣告:“不告诉读书人木心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何立伟在《意外之人,意外之文》中形容木心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感情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小宝在《古来圣贤皆寂寞》中写木心“写文章像巫师作法,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出妙手,让你惊艳。”来读一读木心可爱的文句吧。“浅浅的知识比无知更使人栗六不安,深深的知识使人安定,我们无非是落在这一片深深浅浅之中。“”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平时,画沉睡着,有善意的人注视它时:醒了。借旁人的眼看自己的画,倏然陌生了,便能适意于自己作品的分离。”“活在自然美景中,人就懒,懒就善。”
木心的文字我从未一遍就看明白,总是似懂非懂,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迅速进入第二遍的阅读,继而第三遍乐此不疲。好的艺术作品总会和阅读者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和陌生感,让人在俗世的生活中感觉到强烈的讶异和独立的美感。木心文学的美感基于他文字的简洁和语言组织的奇特。似乎从未有这样的形式表达,但又感觉如此的和谐和融洽;似乎省略了太多的话语,却又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引领着缓缓潜入心灵深处,无知的羞愧和有知带来的喜悦交叉进行,情感和智慧的闸门瞬间被打开。“艺术是知识的源泉之一,正如科学和哲学,如果人们只是搬弄一些已经程式化、或已经现成的概念,那么,人类为了使自己对于现实的感知不断变的敏锐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人类在这场斗争中将获得崇高和自由———将不会有什么结果。陈旧的形式不能为新的观念服务。当形式不能向社会挑战,不能搅动社会,不能激发社会去思考、不能去揭露社会落后的时候,或者说当形式没有决裂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在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面前,观者应感到一种必须进行反省和修正自己概念的需要。艺术家应该给观赏者揭示出他所处在那个世界的局限性,并给他开拓新的视野。”
现代社会,当我们被越来越多的感官世界狂轰乱炸到无处可藏时,文学艺术的呈现大多已堕落为一种浅薄的表象,看亦或是不看都是麻木。而真正的艺术不止是外部感官的愉悦,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满足了人类一种深层次的心理需要。一个人的快乐是他的心智在对外部世界的不断开启中慢慢开出花朵,而木心的文学恰恰是在人的完整性方面做了有价值的探索。此时此刻,你一眼我一语,一个深层次的心理对话在目光与文字之间悄然展开。
作家刘春在《妙像庄严》一文中说道:“先锋派作家玩元叙事,木心玩的是‘元感觉’。他创造日常经验,再以白描手法将它们制成一块块文字琥珀”。“元感觉”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是人们看到事物后最初的反应和想象。而木心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恋爱的方式穷尽生命的第一义。
(三)绘画的陌生化语言———以八大山人为例
八大山人以绘画着称于世,而花鸟画是他绘画中最华彩的乐章。在他的花鸟世界中,无论是山雀、画眉、翠鸟,还是鹌鹑、白头翁等,更多的不是表达双宿双飞的美好,而是独来独往的孤独和寂静。他们或高傲的仰着头,或愤怒的翻着眼,或平静的低着头,画面中看不到红尘的繁华与热闹,有的只是苦闷和寂寞的格调。而正是这样一种格调让人惊奇并产生深深的共鸣,从而使他成为中国花鸟画新趣味、新风格的开创者。八大山人在艺术中苦苦追求“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鬼骂神之谈,无古无今之画”。而他这种无古无今在孤独中的内省和修养使其像一朵盛开的奇葩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绘画是将大自然中活的生命用静止的方式固定在二维空间的画面中,而审美者却是要在这个看似静止的画面中感受到生动而鲜活的生命力。如果创作者用一种冷静的理性和熟练的技巧表达自然,审美者就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换言之,创作者如果不能将自我鲜艳的生命活力和充沛的情感有效的转移到所描绘的自然物上就完全不具备审美价值。庄子提倡的艺术创作是凭感情、凭冲动、凭灵感的生命运动。欣赏八大的作品,他孤傲、寂静、愤世嫉俗的个性和气质跃然纸上。马总霍在《书林纪事》中描述八大山人“性孤介,嗜酒,爱其笔墨者,多置酒招之,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於座右,醉后见之,则欣然攘臂握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从这些文字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八大山人狂呼大叫,挥毫泼墨,汪洋恣肆的身影,他的创作是他情感冲动和生命之火在画面上燃烧出来的痕迹。画面中的山水、花鸟、鱼虫无不是八大个性的写照,禅宗中所说的物我两忘就是指的这种境界吧。
谭天着在《非哭非笑的的悲剧》中说:“八大山人画中寂寞的境界带来的孤独感是贯穿始终的,前期是一种孤怨,中期是一种孤愤,后期是一种孤傲。”当我们回溯八大传奇的一生时才发现,正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气质。从显赫的明室贵族后裔到国破家亡隐姓埋名的躲过清兵杀戮;从落难的金枝玉叶到遁入空门的疯和尚;从潜心修佛到由佛转道并最终在禅宗的独立悟道中回归于诗意的自然,回归于人生的大自在。八大的一生是在对“有为”的悲愤追求中黯然转化与自然相亲而内心世界不断摆脱羁绊的“无为”心境,然而,历史终会给这些清静无为的文人以公正的评价。多年后,多少帝王将相的面目已模糊不清,而八大山人画中苍翠的生命力仍旧鲜活的盛开在人们的心中。
人无论怎样强大,在艺术创作中都不能逆自然规律而成长,以上列举的三位艺术家无不是在与天地万物的精神往来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正如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倡画家必须懂得“一画之法”,何为一?《老子》云:“一,数之始而物之级也。”可见,“一”即是“道”,它是万物的本源。画家要在心灵深处确立“一画之法”,掌握宇宙万物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形态,从而使自己的主观精神与宇宙万物之内在规律相统一、相融合,从而达到“心道统一”的审美境界。而一旦达到此种境界,艺术家对于“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距度”,皆可以“深入其理”而“曲尽其态”。
二、审美共鸣的产生
(一)人格化的风格是永不凋谢的花蕊
每个人都悲喜交加的活在这个令前人始料未及又令今人沮丧麻木的世界中,然而,站在精神的荒原,如何能保持自我对文明与尊严的忠诚却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要终身清醒面对的誓言。艺术家的风格是在天地万物的滋养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受日月之精华的洗礼,物质和精神都是松散而闲适的,所以人格即风格。现代社会,对感官世界的无度追求,直接导致了大众感官的麻痹。与人格无关的风格太多,所谓的艺术家已经被自己矫揉造作到忘记了本性和初性。博眼球、搏出位是现代词汇,它一方面证明了“艺术家”正在用越来越惊世骇俗、标新立异的形式赢得大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不无遗憾的标明了内涵已被放在了潮流时尚的最低端。然而,放弃人格的塑造而盲目追求所谓的风格终究是滑稽可笑的。只有将所有的目的、观念、欲望回归为零,从个体自然的天性、兴趣、个性、感悟出发才有望回归艺术的本质。因为艺术终究是精神产品,它必然要靠有力量的精神打动世界和不同的心灵。
(二)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决定了艺术的深度
艺术家的创作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计和对名利的追逐,它是艺术家对艺术执着的爱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想当年,司马迁在遭受了严酷的宫刑后,在狱中完成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曹雪芹在饥寒交迫中批阅十载终于完成《石头记》;而屈原在流放途中完成了着名的《离骚》;木心在狱中用写检查材料克扣下的66张纸的正反两面写了65万字,完成了他的《狱中笔记》。我们可以设想,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他们居然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身体的病疼而拼死保护自己作家的身份以完成老天赋予他的使命———保护和照顾好葡萄藤(出自《圣经》)。试想,如果他们是为了名利,曹雪芹十年才磨一剑,他早就饿死了。所以,对艺术的赤子之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度,而爱与责任是前提。杨丽萍有句名言:“别人跳的是舞,我跳的是命。”“每当我伸展双臂起舞时,我感觉到我的灵魂在无限延伸,与天地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美妙的感觉让我整个身心都得了最清静的安抚。”对她而言,舞蹈不是谋生或谋利的手段,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与天地沟通的方式。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爱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追寻,不计较名利,不计较得失,更不计较后果,只在过程中享受与艺术冲突和交融带来的惊喜与反思。人从来就分很多种,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要的只是那“满院子的月光”啊。
(三)雅俗共赏是审美的基础
“雅俗共赏”出自明代孙人儒《东郭记·绵驹》:“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原意是形容某些文艺作品即优美,又通俗,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朱自清先生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说:雅俗共赏体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雅俗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求同存异,在矛盾的同时又相互交融。在我看来,俗本就是生活最真实的面目,而雅却是在俗世中要有所坚持。如果从来没有在生活中透彻的体验过俗的真正含义也就无法做到真正的雅。
雅不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更不是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真正的雅是雅在骨子里的。着名的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在清华演讲的时候说道:“中国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其实蕴涵着深刻的为人处世哲理。人生在世,面对打击磨砺,至刚则易折,必须灵活应对,这是外圆的处世技巧。但做人必须有坚守的准则,信念、尊严、骨气等这些底线永远不能丢,这是内方的做人之本。古语‘智欲圆,行欲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俗共赏与外圆内方在本质上是不谋而合的。强调的都是要深谙俗世生活的真相,做到即心性通达、顺应自然,又在保存自己个性气质的同时与周围达到天然和谐。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味的追求所谓的雅太造作,一味的表现俗又太烂熟。只有将自己还原到真实的生活里,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才有望于表达出即让老百姓熟悉和感同身受的人生故事,又让他们感到有别于俗世生活的惊异和美好。从这个角度讲,俗表达的是真实的生活,而雅则是艺术家要在大众熟悉的俗世生活中用智慧提炼出有别于常人的审美视角和组织形式,并在这种独特的表达形式中渗透自己坚守的人生态度。
真正有力量的人生是雅俗共赏的人,真正有价值的创作是雅俗共赏的创作。正如我们熟悉的世界经典电影形象:阿甘、简爱、卡西莫多还有银行家安迪,他们无一例外的表达了俗世的爱情、挣扎、坚持、贫困、丑陋和温暖。然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执着的表达了大多数人正在丧失而他们却依旧在坚守并乐在其中的人生品质,这就是雅的部分吧。其实,看似最容易的事其实是最难做到的,貌似说的慷慨激昂的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们的可贵之处恰恰是把寻常的事化作生活的细节,把对别人的说教变成自我的救赎。像从小身患残疾且不断被同伴取笑智商不足75分的阿甘,因为他始终坚信“人生就像各种各样的朱古力,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块属于你”的信条,一步一个脚印的从特殊学校,到橄榄球健将,到越战英雄,到虾船船长,到跑遍美国,用强大的意志力塑造了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轨迹;而《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因被诬陷而终身监禁于肖申克监狱的银行家安迪,在面对黑暗、毒打、侮辱以及失去自由的痛苦时没有丧失对尊严和文明的追求,靠着顽强的毅力和智慧用19年的时间凿开了一条通往自由和光明的道路;相貌平平、身材矮小又过着寄人篱下、被人欺凌的简爱,从不放弃对圣洁、光明、美好以及有尊严生活的向往,她追求平等、独立、自由的爱情,在得知他深爱的罗切斯特对她婚姻的欺骗时,她说:“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她毅然选择放弃而开始再一次的漫漫旅程,结尾的光明处,罗切斯特家毁人残,而简爱在得知这一切后又重回罗切斯特的身边,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尊严;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塑造的最纯洁善良的形象是美丽的吉普赛女郎艾丝梅拉达,而最感人至深、永生难忘的形象却是那个又陀又瞎又聋又瘸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这个曾一度受命于卑鄙阴险的副主教克洛德的忠实奴仆,在亲眼见证了一个纯洁善良爱恨分明的美丽吉普赛女郎的无情遭遇后,他以不掺一丝杂质的纯真爱情守护着心中的女神,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使她远离伤害。最终他用死亡拥抱着心爱的爱斯美拉达一起魂归心中那片美丽的圣地。在那些貌似优雅英俊而内心阴险、丑恶的副主教和卫队长面前,丑陋的卡西莫多却以善良、勇敢、正义及对光明世界的无畏追求使他永远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人活着终极的价值是追寻生命的自在,而真正的自在跟生命本身与生俱来的喜悦、憧憬、吉祥、美好是和谐共存的。只是有的人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将自己抛离轴心越来越远,以至于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要么是有名有利后故作姿态的附庸风雅,要么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恶俗。雅俗共赏本就是更接近生命本质的一种生活和创造啊!
(四)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艺术作品永恒的本质要素
真善美是艺术创作的终及目标。每个艺术家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真实、善良和美的境界。“真”指的是做人做事要真实、真诚、不虚伪、不睁着眼睛说瞎话。从艺术的角度讲,就是要有诚意的对待创作,尊重艺术的创作规律,尊重每一个形象的生命轨迹,不为了任何理由而在细节上妥协或放弃求真的创作原则。在以造假成为时尚的娱乐圈,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真诚的创作,而是大量虚构的故事加上高科技制造的塑料美女,它给大众营造的是越来越虚无和冷漠的生存空间———暴力、色情、拜金及各种窝里斗充斥人们的生活,这也推波助澜的强化了生活中的假、恶、丑。真诚是创作的基础,但真诚的人未必能创作符合生命真实和大众期待的艺术作品,因为“真相”往往有很多种,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大众嘴里津津乐道的所谓真相与事实的真相未必相同。而艺术家需要的是在社会大熔炉中通过各种体验和顿悟找到更接近事实真相和有说服力的答案,并用艺术的手法有力地呈现出来才有望于和大众达成心灵的共鸣。从大众的角度讲,艺术作品替大多数人表达了他们想说又不敢说,或想说又不知如何去表达的心里话。
木心先生说“伟大的艺术常是裸体的。”艺术家是具有血肉之躯的人,他的艺术必须和大众坦诚相见。创作者不是要通过作品告诉大众一个虚假美好的结果,而是把对生命真相的各种思考完整的呈现给大众。或者,真相是残酷的,然而它却会让被假象麻痹了的大众瞬间开始反思,并借以激起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探寻。正如鲁迅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让人在感受愚昧的同时又看见愚昧背后人们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或者,我们都曾因阿Q的愚昧麻木而感到可笑和可怜,可是笑过之后却又陷入深深的悲凉,因为你会忽然发现我们自己身上也有着阿Q那令人可笑又可怜的性格特点,只不过是表现强弱的差别罢了。台湾女作家龙应台说:“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人看见愚昧,而伟大的作家使你在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现出最深刻的悲悯。”
善指的是善良,有道德,是一种爱的力量。与人为善是一种胸怀和美德。伪善是一种功利思想,他是建立在有更大利益的前提条件下。而真正的善是干净的,他不图回报,只享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喜悦。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的就是人在不同的阶段对善的要求。其实穷达本是身外物,但道义却是根本的。从小爱到大爱,从爱自身到爱周围的人,我们看到无数有道德有爱心的艺术家在做慈善。功夫巨星李连杰、画家范增、影星奥黛丽赫本……他们都在爱与关怀的传递中完成了对更广大人群善意的辐射。而善呈现在艺术中,它是一种正能量,是一种对美好和光明的无限追寻和崇敬。如:已故香港歌手黄家驹根据南非总统曼德拉光辉而跌宕起伏的一生创作的歌曲《光辉岁月》曾经打动了无数人的灵魂;而被喻为“世界上最动听的歌曲”的《拯救世界》是一首呼唤世界和平、关注生存环境的歌曲,是杰克逊为了配合自己的同名慈善组织所作,它展现了艺术家对我们生存空间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的爱的力量。
美兼具人的外表与心灵。外表是老天给的,而是否美丽却是一个人一生的修为。长相好坏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美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和修养在脸上荡漾出的光彩。心灵的美与正义、善良、勇气不可分离,而气质的美则是对自我灿烂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做的无穷追问。木心先生说“在脸上,能接替美貌,再光荣一番,这样的可能有没有?有———智慧。唯有极高的智慧,才可以取代美貌。”所以,有的人越老越有味道,有的艺术作品时间越久越绽放出奇异的光彩。其实,真善美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在艺术中呈现了真善美也就具备了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不断追求和信赖的人生品质。这就是审美共鸣产生的基础吧。
艺术创作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精神需要而产生。但能否让大众产生审美共鸣却是艺术家追问一生的结果。无论是古代的八大山还是现代的杨丽萍,他们作品的深入人心皆出自于深邃的意境,而意境的产生则是他们和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心道合一、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这也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之境。何为不隔?能将心中之情与目中之景自然的运用艺术语言达到水乳交融的状态即为不隔。而如何创造不隔的艺术境界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诗人要“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针对所有艺术家的创作原则,“入”是要深入宇宙人生去获得更多的经验、知识、阅历、理解,而“出”则是站在一个高点上客观地看待现实人生,做出更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与评价。史铁生说:“我即在眺望,也常常看见自己在眺望”说的就是此意。每一个忠实的艺术追随者都要在慢慢天涯路的上下求索中体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妙与感动。
参考文献:
[1]安塔比亚斯.艺术实践[M].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13.
[2]吴泽顺.郑板桥全集[M].长沙:岳麓书院,2002:349.
[3]石涛.石涛画语录[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