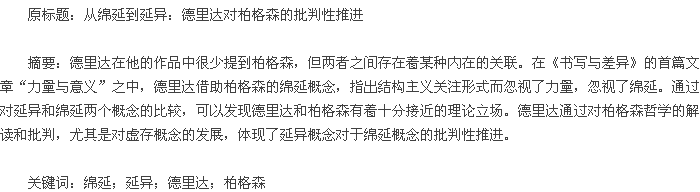
德里达的许多哲学文本,都建立在对西方思想史重要人物的解读和解构的基础上,引用率最高的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等人。奇怪的是,翻阅一下德里达的着作,发现极少提到柏格森的名字,然而柏格森却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对萨特影响很大。求学时期的德里达颇为崇拜萨特,因为萨特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德里达年轻时也曾讲授过关于柏格森哲学的课程,但在他后来发表的着作中极少提到柏格森。①而德里达早期频繁使用的延异概念,显然有着柏格森绵延概念的影响。国外学者从现象学的角度,曾论述过德里达和柏格森二者间的关系。②实际上,在德里达早期的文本之中,也曾有好几处引用柏格森的思想,当然,他同时也与柏格森拉开了距离。柏格森被归结为简单的形而上的对立,正如德里达所说:“在此,我们并不是通过某种简单的钟摆运动、平衡运动、反转运动,来将绵延与空间、质与量、力量与形式对立起来,将意义或者价值的深度与形象的表面对立起来。相反,反对这种简单的二项选择,反对在诸系列之中对这个或者那个选项进行简单的选择,我们认为,必须寻找新的概念和新的模式,一种避开这种形而上的对立的体系的某种经济学。”
这段引文来自于《书写与差异》中的首篇文章“力量与意义”(Force et signification)。显然,在上述引用的文字之中,绵延与空间、质与量、深度与表面、力量与形式,这些术语所影射的显然就是柏格森。而且,笔者还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之中,德里达正是借助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来批判在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结构主义。接下来,通过对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柏格森的绵延概念的比较,我们认为,尽管德里达极少引用柏格森,但他的延异概念与绵延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既对绵延概念有所继承,又是对绵延概念的批判性推进。
一、柏格森的绵延概念
在讨论《力量与意义》一文之前,我们先看看德里达所说的这些形而上学对立,在柏格森那里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些对立并非德里达所谓的只是一种“抽象主义”,而勿宁是梅洛-庞蒂式的一种“重新观看世界的方式”,[2]一种想要通过“绵延的思”(pensée en durée)来把握实在的具体运动和世界意义的原初生成的一种努力。
柏格森在其第一部着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①中,首次提出了“绵延”(durée)的观念,这是柏格森哲学的起点。在这本书中,通过关于多样性(multiplicité)概念的探讨,引出绵延概念。柏格森区分了物质对象的多样性和意识状态的多样性:前者是某种空间之中的多个对象的并置,其数目是可计算的。而计算这一行为已经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种均匀、单质的空间,从而陈列多个位置各异的对象。两个不同的对象,不能占据空间的同一个点,而是互不渗透的。在物质多样性观念中,人们倾向于用几何的、数量的方式来呈现物质对象,而忽视其时间的、质的方面。与之相反,意识状态呈现出另一种多样性,与物质对象截然不同。意识状态总是彼此相续、互相渗透、彼此交融,每个当下的状态,既饱含着过去,亦包含着未来。各个意识状态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性”(totalitéorganique),[3]也就是某种绵延。
绵延概念也意味着重新理解时间概念。在柏格森看来,近现代的哲学中,无论是牛顿的绝对时间,还是康德作为先天感性形式的时间,都只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而非真正的时间。空间化时间的关键在于把时间设想为某种“空虚而均匀单一的场所”(un milieu vide et homogène)。[4]
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之中,物质多样性得以可能,对物质的计量成为可能。空间是与绵延相对立的概念。空间的诞生,在于通过某种意识行动将所有的对象都并列地安放在“某种空虚的、同质的场域”.[5]法国学者沃姆斯就此写道:“因此,空间就是纯粹的、同质的表象(再现),我们支配并立的对象,并且区分它们、分离它们。”[6]借助这种空间观念,我们可以尝试把意识的内在状态解释为在一个同质空间中的许多个点,于是就可以把质显现为量。
与空间概念相反,在绵延中,所有的状态都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不可能从中抽离出任何一个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子状态。仅仅是通过理智的后天努力,才有可能从人的意识之中分离出过去、现在、未来,才有可能从中分析出一个又一个互相孤立、彼此分离的意识状态。因此,纯粹的绵延,是一种互相渗透的质的多样性(une multiplicitéqualitative et pénétrante)、一种 无 外 在 性 的 延 续 (une succession sans extérioritéréciproque)、一 种 有 机 的 进 展 (undéveloppement organique)、一种纯粹的异质性(une hétérogénéitépure)。它不断延续又不断差异,每一瞬间都有异于此前的瞬间,却又保持其自身。
但是,纯粹绵延的概念、绵延-时间的概念,常常为我们所忽视。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用空间代替时间。“要呈现纯粹的、原始的绵延,我们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种困难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外部事物的角度来思考,习惯于在空间中思维。空间思维有助于认识外在的事物,有助于人们对外物采取行动,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人们一旦习惯于在空间中思维,就容易忽视时间和绵延,从而无法深入地把握到生命、精神、自由。因此,不应满足于只考虑那些在空间之中的“现成”(déjàfaites)的事物,不应停留在空间化的语言、符号的表象之中,而是应该扭转思维的天然倾向,重新把握运动和变化着的实在本身,“在绵延中思”(penser《en durée》),直接把握那“生成着”的事物(ce qui est《se faisant》)。为此,我们需要通过长期与对象建立一种亲密而熟悉的关系,从而最终实现我们自身与事物本身的某种同情(sympathie)。同情意味着通过某种思的努力,把握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本身,并且使自身与对象融合为一。在柏格森看来,当我们达到这种同情时,我们就获得了对事物本身的某种哲学直观。
二、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评
概述了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德里达。《力量与意义》一文,于1963年出版在《批判》(Critique)杂志上,后来收入到1967年出版的文集《书写与差异》之中。在这篇文章之中,德里达的主旨在于反思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结构主义,揭示出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形而上学前提,进而加以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还写过不少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类似的工作。当时,德里达对新兴的结构主义充满兴趣,但他也对结构主义感到失望,认为结构主义错失了某些在德里达看来关键的东西。对此,德里达晚年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在那时候,有着人们所说的结构主义,代表者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对于在结构主义中所发生的东西,我既有所同感,也深怀兴趣,同时,我也感觉到,让我倍感兴趣的书写概念对于这些伟大的论述仍然是未知的、被忽视的。”
在另一篇文章《在人文学科论述之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La structure,le signe et le jeudans le discours des sciences humaines)①的开头,德里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结构主义,指责结构主义仍然是一种关于中心的思想(une pensée du centre)。在德里达看来,结构总是与某种中心、某个在场的点、某个固定的源头联系在一起。结构主义所做的,只不过建立一系列的替换,用一个中心替换另一个中心。“母体形式(forme matricielle)将是把存在的规定性规定为对于这个词的一切意义中都保持在场。”
于是,在一定意义上,结构主义重复着在场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看来,必须进行去中心化的思考,为此需要借助一些解构的思想家,如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德里达所寻找的不是某种源头、某种中心,相反,他主张某种游戏,即某种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从而超越结构主义和传统的人道主义。
让我们返回到《力量与意义》一文,看看德里达如何批判结构主义。此文批评的对象是瑞士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让·卢瑟(Jean Rousset)②,德里达视之为结构主义的典型。当时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只是刚刚兴起,但德里达就已经对其开始进行冷静的解剖和无情的批判,指出“结构主义现象值得受到观念历史学家的考察”.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要对结构主义盖棺定论为时过早:“正如我们生活在结构主义的繁荣期,要鞭打我们的梦是太早了。”
在文章中,德里达批评的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结构主义,但他的批评最终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德里达重点考察了卢瑟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部重要着作---《形式与意义:论从高乃依到克洛岱尔的各种文学结构》(Forme et signification:
essai sur les structures littéraires de CorneilleàClaudel)。显然,德里达文章名“力量与意义”本身就已经构成对卢瑟书名的某种回应与批评。不是“形式与意义”,而是“力量与意义”.他用“力量”来反对卢瑟的“形式”,言下之意:“意义”在于力量而非形式。德里达写道:“也许,明天,会有人把[结构主义]诠释为对于力量的注意力的某种放松,如果不是某种缺失的话,而这种注意力正是力量的强化。当人们不再有力量在力量的内部来理解力量时,形式就开始使人着迷。也就是说创造。因此,文学批评,就其本质而言,在一切时代,命定地就是结构主义的。”
德里达还指出,结构主义的意识“是一种作为对过去的思想,我想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对于已经完成的、已经建构的、已经建成的事物的一种反思”.
这样,结构主义就被视作一种仅仅只考虑既成事实的思想。如果推到极致,就意味着某种基于已然存在的因素所进行的建构,一切都简化为某种特定的结构或者某种图式。这将是某种没有历史性的结构,某种无需深度的广度。“借助于某种图式化或者某种空间化,我们就在平面上浏览,以及更自由的,完全没有力量的场域(lechamps désertéde ses forces)。”德里达指控结构主义的意识已经是一种“灾难性的意识,既是被摧毁的、又是具有摧毁力的,是解构的(déstructurante)”.[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