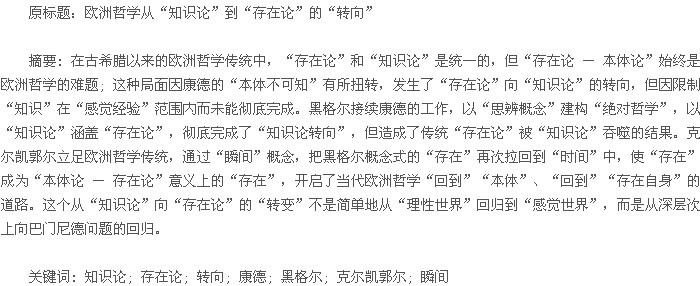
欧洲哲学自古代希腊以来的传统,“存在论”与“知识论”经常是“统一”在一起的,“存在”为“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对于”“存在”的“知识”。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不是很单纯的,而是“矛盾 - 对立”的,古代的“辩证法”由此而凸现出来,从而有经过巴门尼德“存在论”到柏拉图“理念论”,又进而为亚里士多德的“真知识”、“存在之存在”,以求二者在“理论”上之“统一”。
古代希腊早期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早期“理念论”以“辩证法”之“否定 - 消极 - 批判”精神,揭示了对于“存在 - 事物本身 - 本体”的“知识”之困难,如果不是巴门尼德对苏格拉底的一番教训,这条思路,已经是走在了“不可知论”的道路上。然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和柏拉图从积极方面建构的“理念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存在”,都难以使哲学“存在论- 本体论”真正摆脱自身的困境,以至于基督教神学还要为自己的“神”的“存在”作出“理论”上的“证明”。
欧洲哲学这种“存在论 - 知识论”的“纠结”到了近代康德有了一个“明快”的“了断”:“存在 - 本体”“不可知”,“存在 - 本体”不是“知识”的“对象”,“存在 - 本体”被“括了起来( 搁置) ”,“知识”只是以“感觉经验”所能及的“世界 - 经验世界 - 现象界”为“对象”。康德的哲学工作长期以来被称作“知识论转向”,康德将“知识论”和“存在论 - 本体论”严格划开了“界限”,“知识”进入“存在 - 本体”则被斥之为“知性之僭越”。
关于康德的哲学,已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足资参考,这里试图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寻求他的“知识论转向”的一种意义。
“存在 - 本体 - 事物自身”的“不可知”,不等于“感觉经验”的“存在者”“不可知”,我们人类面对的“经验世界 - 生活世界”是“可知的”,我们有可能 - 有权力“把握”它们的“规律”,我们有权力“拥有”“科学知识”,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事物自身”,而是提供给我们“感官”可以“接纳”的“经验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感性存在”,不是“理性存在”。
在这个领域,用得上巴克莱主教的那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
然则,“存在 - 感性存在者”如果单纯是我们的“感官”的“对象”而对于“感官”没有一个“界定”,则这个“存在”作为“知识”的“对象”就会是很不可靠的。康德在“知识论”上的工作首先要为“感觉”作出一个普遍性的“界定”,为“感觉”“给出”“规定性”,以避免依赖感官自然结构的主观的随意性。康德以“时间 - 空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出现,以“保证”“感官”作为“知识”的“感性器官”的“普遍有效性”。
人们常说,康德的“时空观”,深受牛顿“绝对时空”的影响,这话是确实的,当然康德把牛顿的“客观绝对时空”转变成“主观绝对时空”以完成他的哥白尼的“革命( 转向) ”,其“绝对性”意义是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时间空间”是一个“主观”的“接收器 - 观测器”,“事物 - 自然”通过这个“接收器 - 观测器”“给予”我们,就必定要受这个( 或两个) “器具”的“影响”,因而所“接受”的已经不是“事物自身- 本体”,而是“经受”“接受器 - 观测器”“影响”了的“对象”,康德叫做“现象”,“现象”不是“本质 - 本体”。“本体 - 本质 - 事物自身”因“不接受 - 或通不过”“时空”这两个“接收器- 观测器”,因而不为我们“感官”提供任何材料,从而它们“不可知”,不是“知识 - 科学”的“对象”。
“时间 - 空间”这两个“接收器 - 观测器”是“先天的”,它们在“绝对性”的基础上和“概念”有统一的可能性,因为在“概念”中,“先天”的“概念”———“范畴”,是无需通过“经验”形成的,这样,“直观 - 时空”和“概念”的“先天性 - 绝对性”,就“保证”了“知识”在根基里有一种“先天绝对 - 必然”的“可能性”,而不必“等待”“穷尽”一切“经验”就“允许 - 有权”“推论”“普遍必然”的“规律”。也就是说,“时空”和“范畴”的“先天性 - 绝对性”提供了“经验知识 - 科学知识”有“普遍必然”的“可能性”,“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得到了肯定的阐述。也就是说,“感官”“接受”的“杂多材料”得到了“规定性”。
然而,“可能性”不等于说凡“经验知识”就“一定”是“普遍必然”的,因此,康德的“知识论”并不“替代”“经验科学”,而是为“经验科学”自身“可能”具有的“普遍必然性”求出“根据”,作出“阐述”。
就康德那个时代来说,牛顿的时空绝对性的巨大影响,提供了康德“知识论”以“普遍必然”的“根基”。但“经验知识”的“获得”显然还需要不同于“绝对时空”的“非先天 - 非绝对”的“接收器 - 观测器 - 感官”,它们对于“被接受 - 被观测”“对象”的“影响”,“迫使”“经验知识”在“存在者 - 非存在者”二者之间,“不可能”作出“绝对 - 先天”的“判断”,“经验知识 - 经验科学”不仅依靠“推理”,而且要依靠“实验”,而多次“实验”的“归纳( 综合) ”,仍然对一个“进一步”的“实验 - 归纳”保留“开放”的“未来”,这就是康德推崇“实验 - 归纳之父”“培根”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接收器 - 观测器”“限制”了我们的“知识”。
又是在某种意义上,在“知识”领域,康德接续了古代希腊智者学派和少年苏格拉底的传统,严格阐明“事物自身 - 本体 - 本质”是“不可知的”,其理由也正在于一旦“知识 - 知性”“妄图 - 僭越地”要“认识”“事物自身”,必定要陷于“自相矛盾”而“自行解体”,康德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事物自身”的“不可知”的“理论”上的根据。
我们“认识”“事物”的“接收器 - 观测器”“独立”于“事物”之外,而“事物自身”乃是“绝对”,我们因缺乏与其“相对”“独立”的“工具”,因而对于“事物自身 - 绝对”则“认知”无门———无法通过。
于是,我们看到,就康德来说,只有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 - 允许以消极 -否定 - 批判的态度谈论“事物自身 - 绝对 - 本体”,而并无“德本体 - 情本体”一说。康德的“道德”不问“时空条件”,以“形式”的“自由”为根基,而其“审美”与“目的”并无“客观”的“建构性”,乃是一个“反思判断”,它们都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为客体立法”,只是在“至善”的第二层意义上,“道德”与“知识 - 经验 -幸福”才达到“同一”,达到“绝对”,不过这已不是“本体 - 事物自身”的“知识”问题,而是“信仰”问题。就这方面来说,康德的“知识论”的“转向”,并不是很彻底的,“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使这个“转向”“半途而废”。
真正“完成”这个“知识论”“转向”的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 - 科学体系”拆除了康德“批判哲学”所设置的各种“界限 - 限制”,使“哲学”不仅是“批判”,而且是“学说”,是一个“科学体系 - 知识体系”。
黑格尔能够把“哲学”“推进”到这一步,有其深厚的欧洲哲学的传承; 同时或许我们可以说,跟他“改造”了“知识”的“接收器 - 观测器”也有关系。在康德那里的只适用于经验世界的“纯粹概念 - 范畴”被“改造”为“本体 - 事物自身 - 绝对”的“思辨概念”,这个“思辨概念”也“吸收 - 扬弃”了康德的“时空”“先天直观形式”,成为“思辨概念”的一个“环节”,“思辨概念”“蕴含了”“直观”,“直观”是“概念”的“外化”形式,而并无“独立”的“来源”,“感官”并不“单纯”地向“概念”“提供”“感觉材料”,而是在“概念”的“范导”下为“概念”“充实”“具体内容”: “质料”与“形态”的关系转化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使“概念”不是单纯的“抽象”,也使“感性”不是单纯的“材料”。于是,“思辨概念”使“概念”成为“具体”的,也使“感性”成为一种“显现”。
“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知识 - 科学体系”,“克服”了康德设置的种种“障碍”,“跨越”各种“界限”,使之“归顺”为“绝对知识”的一些不同层次的“环节”。
黑格尔毫无顾忌地做了康德所警告过的“僭越”的事情,使原本有自己的“疆界”的“知识王国”“无限制”地“扩展”自己的“疆土”,“建立”了“知识王国”的“一统天下”。
当然,这个“一统天下”的“绝对王国”并不“绝对”“太平”,“积极 - 肯定”地“对待”“矛盾”是黑格尔“推进”康德“二律背反”的着力之处。
康德所揭示的“二律背反”是一条铁律,康德“知识论”所使用的“接收器 - 观测器”只适用于“在时空中”的“感觉经验世界”,一旦“超越”“时空”之外,则必有“二律背反”出现; 康德为“回避”“二律背反”无使“知性”“僭越”,另设“超时空”的“道德 - 自由”领域。黑格尔不采取“回避”态度,以积极肯定的态度“迎接”“矛盾”,改造自己的“观测器”,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也同时就“建构”了在“知识论”涵盖下的“存在论 - 本体论”。在黑格尔那里,“本体 - 存在”不仅“可知”,而且“哲学”作为“科学”的“知识论”,其任务和目标就是“认识自己 - 认识事物自身 - 认识本体”。
黑格尔做的正是柏拉图“理念论”因缺乏适当的“观测器”想做而未曾做好的事情: 积极、肯定地“建立”“辩证法”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未曾达到“思辨概念”的深度。
“知识”必定要运用“概念( 判断、推理) ”,康德的“知性范畴 - 纯粹概念”一旦进入“本体 - 存在 - 事物自己”立即出现“二律背反”而“毁灭自己 - 自己泯灭”。黑格尔“改造”了这些“纯粹概念 - 知性范畴”,使它们从“必然”的“范畴”“转向”为“自由”的“范畴”,使其不仅在“源头”上具有“不受经验制约”的“先天性”,而且在“进入”“经验世界”之中,仍然“保持”其“独立 - 自由”的特性。于是,“经验”不仅在“形式”上是“合法”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合理”的,“自由”的“范畴”“建构”着“经验”的“合理性”; “矛盾———二律背反”不仅并不“毁灭”“概念 - 范畴”,而且成为“概念 - 范畴”之“自由”的“开显 - 显现”“过程”中的“环节”,“矛盾”“推动”着“概念 - 范畴”的“自由”“发展”。
“自由概念”亦即“思辨概念”,“概念”“本身”的“具体性”,无需从“感官”“引进”“外来”的“材料”。
“必然的概念”“转化”为“自由的概念”,“知性概念”“转化”为“理性概念”,在这个“转化”的基础上“建构”了“思辨哲学 - 积极肯定的辨证科学体系”,黑格尔彻底地完成了“知识论”的“转向”。
于是,在这个“无所不包”的“科学体系”中,“存在论 - 本体论”“建立”在“知识论”的“论证 - 证明”的基础上,在整个体系中,“知识论”“涵盖”着“存在论”,“存在”不“止于”一般的“感性存在”,而是“本质”的“存在”,“理念”的“存在”,“本体”的“存在”。“思辨哲学”的“科学体系”“保证”了“本质 - 本体 - 理念”“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 “思辨哲学”的“科学体系”宣称,单纯“感性存在”处于“存在 - 非存在”的“过渡 - 变化”状态,这个“状态”具有某种“模糊性”,而“唯有”“本质 - 本体 - 理念”的“绝对”“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说,“唯有”“概念 - 思辨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不具有任何“模糊性”,从而回到了巴门尼德的“存在就是存在”。
在这里,黑格尔之所以有可能做出这种“承诺”,其中有一个根据在于他的“存在”“不在”“时空”之中,“本体 - 理念 - 绝对”具有“超时空性”; 而“唯有”“概念”具有这个“超越”的“可能性”。“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是一个“概念”的“逻辑体系”,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体系”也并不例外,只是他的“概念”既非一般的“经验概念”,也非“先天必然”的“知性概念”,而是“自由”的“理性概念”。这个高于“知性必然”的“自由概念”,将“知性必然”“吸收”为“自己”“矛盾 - 发展”的一个“环节”,成为“自己”的“内容”,“摆脱”康德“知性概念”的“形式性”,无需受“时空”中“感觉经验材料”之“制约”,而使这些“感性材料”“转化”成为“理性 - 自由”之“合理性”的一个“显现”,“现象”“显现”了“本质 - 本体”的“存在”,从而对于“思辨理性”来说,它是“可知的”,而且“唯有”“本体”才是克服了那因“受时空条件制约”而具有的“模糊性”成为“绝对”“可知的”。
一切“经验科学”的“知识”都具有“相对性”,而“唯有”“哲学”的“知识”“有可能”成为“绝对”的。“在”“时空”中的“存在”是“相对”的“存在”,具有一切“相对”事物的“模糊性”;“超越 - 脱离”“时空”的“存在”是“绝对”的“事物存在 - 存在事物”,从而也“摆脱 - 克服”了“相对事物存在”的“模糊性”,“绝对存在”乃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没有一个“非存在”与其“相对”,而从“相对”到“绝对”成为一个“矛盾 - 发展”的“过程”,“绝对”“外化”为“相对”,又“复归”于“绝对”“自身”。“绝对”之所以“有可能”“回归”“自身”,乃是因为“在”“相对”中,“绝对”并未“丢失 - 泯灭”“自身”,“在”“时空”中,仍“有可能 - 有权力”“保持”着“绝对自身”的“自由”,这使“绝对”“引领 - 范导”着“相对”的“变化 - 运动”,而不至于“迷失”“自身”,使“在”“时空”中的“相对”“有可能”“摆脱”“时间绵延”中“坏的无限”,使“经验科学”有向着“绝对科学 - 哲学”“回归”的“可能性”。
然则,“绝对”“唯有”以“概念”的形式“存在”,因为“唯有”“概念”“有可能”“不受时空条件制约”,“脱离”“时空”而“自身”成为一个“逻辑”的“体系”。黑格尔的“概念”是“自由”的“绝对概念”,“自由”“自己”“产生 - 创造”“自己”的“内容”,“自由概念”“使”“自己”“存在”,无需“借助”“外来”的“材料”来“使自己”“存在”。“绝对概念”“产生 - 创造 - 外化”“自己”的“时空 - 直观”,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存在”乃是“绝对”的“存在”,也是“概念”的“存在”; 随着“自由概念”的“发展”,“存在”从“抽象”走向“具体”。
不过,“概念”既是“绝对”的,“绝对”“无对”,“概念”自成“体系”,原则上一切无出“概念”之外。“概念”“涵盖”“直观”、“创造”“直观”,于是也“涵盖”“时空”、“创造”“时空”。
“时空”与“逻辑 - 辩证”之“概念”“同一”,“历史”与“逻辑”“同一”。于是,“存在”成为“概念”的“存在”,也成为“存在”的“概念”。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把世间万物都“吸收”到“绝对概念”中来,“概念”犹如一个“黑洞”,“吸收”“万物”而“融”成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一切合理的又都是现实的,换句话说,一切“存在”的都是“概念”的,而一切“概念”的也都是“存在”的。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存在论”被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 绝对知识论”“吞噬”掉了。
然而,“在”云端里的“存在 - 本体 - 本质”并不可能“穷尽”“在”“经验现实”中的“事物”,“自然”和“社会”并不完全“在”“概念”这个“观测器”里,“实际”的“世界”“充满”了“偶然”性。“时间”中的“偶然性”,并不因为被黑格尔斥之为“坏的无限”而顺从地“进入”“合理”的体系。“自然”总是“隐藏着”它的“秘密”( 赫拉克利特) ,“合目的性”又只是“主观”的“反思判断”,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判断”( 康德) ,黑格尔的“绝对哲学”也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观测”方式,是一种“视角”,这个“视角”号称“大全”,却是“挂一漏万”,总会有“东西”从黑格尔精心建构的“绝对”的“黑洞”中“逃逸”出来,被另类的“观测器”“发现”出来。这些“逃逸”出来的东西,对于黑格尔“绝对知识体系”显得那样的“荒谬 - 悖理”。“时间”这个“坏的无限”不可被“吸收”、不可被“驯服”,“存在”不可被“概念化”,“存在”常常是“不合理 - 不合逻辑”。“存在”不可能被以“概念”为“元素”的“逻辑 - 知识”所“穷尽”,“存在”难以被完全“知识”化。
于是,问题又“回到康德”。不过康德的问题是“本体”的“存在”“不可知”,其原因在于这个“本体”乃是“超时空”的“思想体”; 在这层意义上,黑格尔把“思想体”“吸收”到“概念”中来就有充分的理由,“砍掉”康德所留下的“尾巴”,以“绝对思辨”的“知识论”“一统天下”。
然则,康德的问题依然存在: “知识论”不可能“囊括”“本体论”。从某个方面来看,所谓“知识论”的“转向”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因为“本体”既是“存在”,则难以“超越”“时空”。
“存在论 - 本体论”要从黑格尔“绝对概念”的“黑洞”中“逃逸”出来,则要认真严肃地考虑“本体”如何“在”“时空”中 - 不脱离“时空”而“保持”着“存在”,即“在”“时间”“绵延”的“长河”- 黑格尔的“坏的无限”“中”,仍有“本体”“存在”之“可能性”。
“在”“时空”“中”“保持”了“本体”“存在”之可能性是“古典哲学”“知识论转向”之又一次“转向”———“存在论 - 本体论”之“转向”。“知识论”“涵盖”下的“存在论 - 本体论”因其“概念性”-“超时空性”,又会给予“存在论 - 本体论”“重新”的“机遇”。
当然,这个“存在论”“转向”,并不是简单- 单纯地“回到”“朴素 - 常识”的“感觉主义”立场,这样的“重复”“回归”对于“哲学”“学术水平”并未有所“推进”,而只是一种对“从概念到概念”“不满”的一种“发泄”。一个时期,对于黑格尔“绝对哲学”的“厌恶”是一种普遍的“情绪”,而在这个“转向”上有所“推进”的,克尔凯郭尔应是关键的一位。
在这个“转向”中,克尔凯郭尔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他几乎在古典哲学尚在兴盛时期就在哲学层面开始了这个“转向”,尽管由于他写作所用语言和文风使得他在很晚才被欧洲学界普遍发现,而这种现象,实足表明他是这个“转向”的“先知”。
克尔凯郭尔生活的时代丹麦哲学界弥漫着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气息,可以说是德国哲学的“影子”,而克尔凯郭尔为求“影子”的“正面”的“本来面目”,曾几次往返去德国“亲历”德国学界的课堂,充实自己的学问和思想。
对于哲学,应该说克尔凯郭尔有深厚的学养,并不是“天马行空”凭借“想象力”的“小说家”式“天才”。和尼采一样,他对于古代希腊哲学有扎实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已经显示出他对苏格拉底 - 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对“辩证法”的“否定”与“肯定”、“批判”与“建构”的意义,有确切的把握和融会贯通的思考。这篇早期杰作,已经显示对“哲学”的“古典传统”即将在学术的深层次上有一个“突破”。果然,他的《非此即彼》和《哲学片断》展示了系统的成果,尽管按照他的思想,他强调的是一个“片断”,而不是“体系”。
就欧洲哲学这个“转向”来说,克尔凯郭尔把黑格尔的“存在”从“概念”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的“时间”“中”来,使“存在”成为“在”“时间”“中”,而不是“在时间绵延中”的相对于“感官”的“存在”;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是“本体”,或者是“本体论 - 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它“消弭”“感官世界”“存在 - 非存在”的“模糊性”而又无需“超越”“时间”成为“概念”,“存在就是存在”,“存在论就是存在论”,“存在论”不为“知识论”所“涵盖”。虽然已有康德三个不同领域“批判”的启示,但如何克服古典哲学固有的、康德也难以例外的“超时空性”,克尔凯郭尔面临的任务,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而不是“回到”“感官感觉”,“回到”“存在 - 非存在”“交互影响”的“感性”“模糊状态”,是克尔凯郭尔开启的、为以后欧洲哲学遵循的“存在论 - 本体论”道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以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法国激进哲学,尽管各有自己的“视角”和解决之道,但都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
“本体论 - 存在论”所思考的“存在”是不具有“存在 - 非存在”“模糊性”的“存在”,是不受“一物”“必然”“产生”“另一物”之“因果性”“制约”的“自由”的“存在”,是“摆脱”“在时间中”“变异性”的“永久性”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又不是“概念”的“存在”,不是“存在”的“概念”。难矣哉,连维特根斯坦都要求助于“指”,而他“所指”之“物”,“沧海桑田”,如今“安在哉”?
那个“本体”的“存在”,“在”“时间”“中”之“存在”,不发生“安在哉”之怀疑的“确信”之“在 - 存在”,其实也就是“时时”皆“在”,“随时”都“在”,“永远”都“在”,这个“本体”之“存在”,“在”“时间”的“瞬间”“中”。
“瞬间”为“瞬时”,就“空间”而言,乃是“时间绵延”之“断裂”,但也是“纯粹之时间”,是“纯时间”,“时间”“自己”,而无“外在”( 非时间 - 空间) 之“制约”。“瞬时”-“纯时间”则为“自由”,“在”“时间”“中”之“自由”,“存在”的“自由”,“自由”的“存在”,“纯时间”为“纯自由”。这层意思法国柏格森发挥得好,但他把“时间”归于“意识”,在“归属”上不同于克尔凯郭尔。
“纯时间”不是牛顿的“绝对时间”,不是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而是“纯存在”。不是“概念”,“存在就是存在”,是“本体论 - 存在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存在”。“时间绵延”无需“概念”而只在“时间本身 - 纯时间”就有“永恒”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 现时性”,“时间绵延”在“瞬时”意义上就是“永恒”,从而无需“终极目的”就“摆脱了”黑格尔所说的“坏的无限”。“时间”之“本体论”“存在”为后来海德格尔所“揭示”,或可以说,海德格尔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克尔凯郭尔的“任务”,而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公开承认了这种学术上的影响。
“瞬时 - 瞬间”没有“大小”,没有“长短”,“瞬时”不是“阶段”,不是“环节”,一句话,“瞬时 - 瞬间”不允许“空间”化,不允许被“分割”;但“瞬时”“使”“空间”化了的“时间”“断裂”-“终结”,将“时间”“自己”的“不可分割性”凸现出来,“瞬时”不允许再被“空间”“结构”化,亦即“瞬时”不再允许归结为“空间化”了的“逻辑 - 必然”“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瞬时”为“自由”,而“自由”原本是“时间”“自身”的“本性”。并不能像康德那样,把“时间”作为“直观形式”,“等待”着“因果范畴”去“建构”为“知识”。
然而,“瞬时”又不是“内在”的“意识”( 如柏格森理解的那样) ,不是单纯“自我”的“意识”,而是对一个“不同于”“自我”的“他者”的“确信”。是对于“无需”也“拒绝”“证明”的“神”的“确信”,“瞬时”是“本体”的“确信”,对“永恒存在”的“确信”是对“永恒现时 - 永恒现实”的“确信”。
在克尔凯郭尔那儿,“瞬时”“提供”了“永恒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信仰”的“可能性”; 而“信仰”不是“相信”那些“历史传说”和“奇迹”的“故事”,而是“确实”“认识”到“有”一个“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存在”“呵护”着“我”的“存在”,“维护”着“我”的“时间 - 生存”,“维护”着“我的”“自由”,使“我”有可能“不受时空条件”“制约”,“在”“时间”“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瞬间”在“时空”“链条”中“脱颖而出”,显示出“时间”“自身”的“存在”,显示出“自然 - 必然”“长链”“断裂”中“自由”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历史 -经验”“长河”中一个“绝对相异者”的“存在”,“在”“经验”的、即“空间”化了的“过去 -现在 -未来”的“变化发展”中的“永恒现时”的“存在”,“瞬时”就是“现时”。
就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来说,“瞬时 - 瞬间”只是“片段”,一个“点”,一个“即将”被扬弃的“环节”,那个“超越时空”的“神”“需要”“证明 - 论证”; 就克尔凯郭尔来说,那个“瞬间 - 瞬时”“不可”用“理论”“证明”,那个“瞬时 - 时间”“存在”的“神”也“不可”“证明”,因为“瞬时 - 瞬间”而又“永恒”在“哲学”“理论”上本是“自相矛盾”,无论怎样“精致”的“证明”都会“不攻自破”、“自行解体”,都难免苏格拉底的“反讽”。
“瞬时 - 瞬间”不是康德的“知性知识”问题,也不是黑格尔“思辨概念”问题,“时间 - 瞬时”不是“知识论”问题,而是“存在论”问题,不是“概念”的“建构体系”,不是“必然性”的“结构”,而是“存在”“本身”,是“自由”的“存在”,“存在”的“自由”,“纯时间”即是“纯存在”,“存在”“自身”。
“瞬间 - 瞬时”既然是“永恒现时”,“永久”的“现在”,于是“瞬间 - 瞬时”为“同时”。
就某种意义说,“经验”意义上的“时间”,即“空间化”了的“时间”,“时间”被“分割”为“不同”的“时段”,而未曾“空间化”的“时间”,“纯时间”-“瞬间”,则“地无分南北,时无分古今”,“天地一瞬间”,“瞬时”皆为“同时”。
所谓“同时”意味着“人 - 神”“同时”,无论“人”“经过”“千百万年”,“人”与“神”的“关系”皆为“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人”与“神”之“间”,没有“距离”,没有“空隙”,没有“空间”,而“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神”对“人”“一视同仁”地“为人服务”。“宗教 - 基督教”中“主奴”式“神 - 人”关系,在“顷刻之间 - 瞬间”发生了“颠倒”。“神”对于“人”仍然是“绝对”的“他者”,“神”不可能“人化”,但这个“他者 - 异者”只是“显示”一个“永恒”的“存在”,“永恒”的“现时”,“神”不可能“空间化”,这个“绝对他者”“在”“瞬间”中与“人”“没有”“距离”,“人”“因”“神”而“存在”,而“神”也“因”“人”而“存在”,“人 - 神”不可能“合一”,但“神 - 人”却“同在”,“神”和“人”“永远”具有“同时性”。
“人”可以是“经验”的,被允许“占据”“空间”的“位置”,因而“在”“时间绵延”中也“占有”“位置”,“人”是“被”“限定”的,唯有当“人”“在”“瞬间 - 瞬时”中“摆脱”“空间”的“位置”,“人”也“摆脱”了“时空”“存在( 者) ”的“模糊性”,“肯定”了“自己”的“自由”的“存在”,为“维护”这个“自由”,“人”“设定”了一个“他者”,“设定”了一个“神”。“神”作为“他者”与“人”“不同 - 相异”,“神”只是“时间”的,“神”不可能被“空间化”,“他”是“纯时间”,因而没有理由问“神”“在”“何处”,也不允许问“神”于“何时”“出现”,“他者”“永远”与“人”“同在”。
“神”为“人”而“在”,并不意味着“神”“保佑”“人”的“幸福”和“成功”,“保佑”“人”“升官发财 - 消灾免祸”; “神”作为“他者”,为“人”的“自由”而“存在”,“神”的“存在”“保障”了“人”的“自由”的“存在”; “神”的“纯时间性”“显示”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人”有“自由”的“权力”。
“人”的“自由”并非“神”的“赐予”,“人”的“自由”来自“人”“自己”,“神”“呵护”着“人”的“自由”,“他者”“呵护”着“我”的“自由”。“异者”“呵护”着“我”,“他”与“我”“永远”“相异”也“永远”“同在”。
“神”是“为人者”。他( 者) 之所以受到“人”的“崇拜”,乃是因为“神”是彻底的“无我者”,是一个“纯粹”的“( 为) 他者”; 而就“人”来说,“神 - 他者”并无“自己”的“属性”,因而他是“不可知者”,因为所谓“知”,总要“知道”些“什么”,“神”却是“无( 自己) 属性”的“存在”,因此“神”是“纯粹”的“存在”,“永恒 - 不变”的“存在”。
按“道理 - 逻辑”,“此‘神’只应天上有”,“在”“天上”,“神”作为“纯粹概念 - 纯粹思想体”或许说得通,“神”如“在”“时空”中,则当有“自己”的“属性 - 偶性”,于是乎产生与其“格位”相抵触的种种“矛盾”,“人”“要想”“知道”那“不可知者”必产生种种矛盾; “人”不“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坚持“僭妄”地“要”“知”那“不可知者”。“在”“瞬间”中———“瞬时”就“在”“灯火阑珊处”,“神”“瞬时 - 随时”都有“自己”的“格位”,只是这个“格位”是“为人”而“设”,“神”“为自己”“在”“时间”“中”只“保留”了“存在”的“格位”。“人”虽不可以“经验科学”方式去把握“神”的“属性”,但“确信”“神”的“存在”; 而“确信”一个“不可知者”可谓“矛盾 - 荒诞”至极,但这个“荒诞”却确确实实地“可信”。
“在天之父”之“可信”度,只能“建立”在“纯粹概念”的“基础”上,康德第二种意义上的“至善”,黑格尔的“思辨概念”之“绝对”,都“保证”了“神”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当然要经过一番“推理”来“论证”,“神”是“被”“证明”出来的。“神”的“存在”是通过“概念 - 推理 - 判断”的环节“论证”了的,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神”“在”他的“绝对知识”之中,“存在”“等待”“概念 - 知识”的“证明”。
克尔凯郭尔的“在”“时间”“中”的“神”不是“摆脱 - 脱离”“时间”之后的“逻辑推理”的“产物”,“神”之“存在”有“时间 - 瞬间 - 瞬时- 时时”的“保证”,这个“保证”不是“概念”的“产物”,而是“早于”“概念”的“( 纯粹) 存在”。
“纯粹存在”“早于”古典哲学的“纯粹概念 - 纯粹知识”,如果套用古典哲学的话语方式,“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也就是“纯粹概念”向“纯粹存在”的“转变”,而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
“纯粹存在”,如果允许这样的用语的话,不是“时间绵延”中 -“因果连锁”中的“存在者”,“纯粹存在”是“自由存在”,“存在”于“时间”的“瞬间 - 瞬时”,“瞬间 - 瞬时”就是“纯粹存在”,也是“纯粹自由”。“神”作为“纯粹存在”也是“纯粹自由”,是没有任何“欲求”的“欲求”,没有任何“意志”的“意志”,亦不受任何“属性”“限制”的“自由”,“神”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自己”,“神”的“为己”就是“为他”,“纯粹为他 - 纯粹为人”,耶稣“为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纯粹存在”只有是“永恒存在 - 永恒现时”,才是“存在论”所说的“存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出现”才意味着欧洲哲学从“知识论”“转向”了“存在论”,或者说,“回归”到“存在论”,在更为深化的层面“回归”到巴门尼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