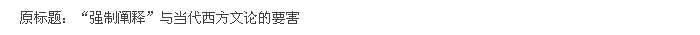
“强制阐释论”是张江教授新近针对当代西方文论提出的一种“论”,与此论针锋相对的也是由他提出的“本体阐释论”.“两论”紧密相关。在张江看来,如何对待文学或文学性,是区分和隔离“两论”的关键所在:前者反文学或文学性,后者则以文学或文学性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旨归。据说,他之所以要提出本体阐释论,原是为了规避当代西方文论无视文学的本质属性,混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以先入之见(前见、先见)强行侵入文学的领地,把文学文本生拉硬扯地拽入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毫不相干的论域加以阐释的“根本缺陷”和“核心缺陷”,借此提醒文论界要高度重视文学的特性,以具体的文学文本为“阐释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逐步建立可以与当代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属于中国自己的文论系统。
(1)根据张江的表述可以发现,本体阐释论是一种畅想式的“重建路径”;强制阐释论也只是以揭示当代西方文论背离文学或文学性的根本缺陷为由,以零星片断的示例方式指出它的若干弊端。
我以为,就此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为何在此时提出“两论”,一个是当代西方文论的要害到底在哪里。
此时中国的 GDP,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已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中国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依据和得出的结论,尽管并不为中国官方所认可,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自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 相继超过英、法、德、日诸国直逼美国。退一步说,即使低调示人,不愿做世界经济的老大,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也当是指日可待。
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中国人看待中西关系的心态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是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有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这另当别论。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都有了相当明显的增强,民族情感愈益激越的中国人不再愿意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而急于强化民族的自信力,不断放出豪言,试图与强大的西方叫板,唱对台戏。这种态势表现在中国的方方面面,是非常清晰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如此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中国的文论界自然不甘落后,不失时机地汇入这股来头不小的民族主义潮流。1990 年代初,东方主义等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话语传入中国,迅速在文论界搅起大浪,文化守成的思潮盛极一时。自那时以来,中国文论界讨论的主要论题,不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现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其间不免夹带着“发现东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类的豪言壮语。进入新世纪,不少人翻出费孝通“文化自觉”的说法来说事。比“文化自觉”更为激进的情绪化表达,是时下十分流行的一个大词---“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的风头上提出“两论”,特别是本体阐释论,用历史的眼光看,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完全是合乎历史逻辑的一种抉择。回归中国本土,回到老祖宗那里去,重建属于中国自己的文论系统。
1990 年代的时候,季羡林发过一番宏论,说十九、二十世纪你们西方是强大,我们让给了你们,但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有这个自信,当仁不让。他说,你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论是多么多么的好,现在搞文论的人为什么不回过头去探宝,反倒去西方捞取那些念歪了的“经”.与季羡林可有一比的是以写现代诗闻世的英文教授郑敏,她甚至整体否定了自白话文运动以来一路西化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诡异的是,她是顺着西方人的思路,拿反欧洲中心论的西方文论说事。她说,你看我们的汉字是如何如何的形象,理性化或逻辑化了的西方文字是如何如何的抽象。(可参看克里斯蒂娃及德里达的相关论述),把富有美感和诗性的象形汉字抽象化,不用典雅优美的文言而用粗放平直的大白话写诗,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南辕北辙,把中国现代诗歌引向了一条不归路。
那么,中国文论的出路在哪里呢?在“转换论”者那里,很简单,在它的源头,即沿波讨源,对中国古代文论实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以彻底消除“失语”的症状。然而,如此这般,难道真能行得通治愈得了吗?讨论的人多了去了,讨论来讨论去,弄出来的无非是一些宏大方案,无论是什么人,不管有多么高明,都没能也不可能端出一桌挂有“中国现代”名头的实实在在的理论大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也许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西来概念)中,论者能够据以为证的实例简直可怜得要命,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重释的那个“境界”,便是其中经常被提及并说滥了的一个。可是,多年前由北大1作,你将会看到,隐含在这个范畴里面的居然主要是叔本华化了的意蕴。中国古代文论里面常见的如“气”“象”之类的术语(又是西来概念),不妨试试,看看该怎样转换,转换后又该怎样用来批评当代的文学文本。
西来的“经”的确不那么好念,如“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生吞活剥,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磕磕绊绊,不问青红皂白地一锅烩,在所难免。从中挑多少刺都是轻而易举的,借以批判和否定它也不是什么难事。
问题在于,豪情易解,壮志可嘉,发通宏论,挑些刺,并不能真正解决重建中国文论的难题。否定什么永远都要比肯定什么来得轻便。割断历史,用历史xuwuzhuyi的态度对待包括文学和文论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演化史,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我同意《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看法。在他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一定的“长时段”内,总是会在一定的区域形成一个文明的中心,这个区域内生成的文明成果总是会向其他的区域扩散,这是历经无数史实验证过的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全球通史》下册的开篇即说,自 1500 年(哥伦布等航海)以来,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是欧亚大陆的欧洲板块。北美是欧洲人的北美,南美是拉丁人(欧洲人)的南美,澳洲是英国人的澳洲,亚洲和非洲虽然不好说是欧洲人的亚洲和非洲,但是就欧洲文明扩散的走向而言,这两大洲因被殖民而成为欧洲文明的试验场,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非洲众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社会制度的安排是照着欧洲的模式打谱。马达加斯加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其政治架构取自曾奴役过他们的法国,是半总统制。亨廷顿说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数不清的事例证明,中国人看待中西关系(“西上中下”)的心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于情,讲民族主义;于理,从世界主义,情理夹杂,很容易把脑子搅昏。然而,正是这夹杂着的情理的冲突,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却一再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重演。我相信,只要世界文明的走势不出现方向性的转换,这种冲突仍然将持续下去。
现在可以谈第二个问题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学或文学性是强制阐释论与本体阐释论相关联的要点。张江在《强制阐释论》一文(2)中把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四点,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非逻辑证明”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你动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批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有可能在逻辑上出问题。余下的三点关系到他对强制阐释的界说。他的界说是:“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文本话语”当指文学文本,“文学指征”当指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性),“前在立场和模式”当指既有的理论立场。从既有的理论立场而非文学文本出发(“主观预设”),无视文学文本固有的“指征”,征用现成的场外理论,根据已有的结论,强行对文学文本作非文学的符合论者主观意图的阐释,这就是张江所说的强制阐释的根本缺陷。
前面也已经说过,文学和文学性,是搞当代西方文论的人来来回回辨识过而心知肚明的东西。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那本名为《文学理论简论》(3)的小册子,起首两章回答的就是什么是理论和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之所以称“理论”而不称“文学理论”,据卡勒解释,是因为近些年来西方学者阐释文学作品,大都利用非文学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史学和哲学等的理论资源,据说,用这样的理论来阐释文学,已经根本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性质。按此,理论便是文学理论。卡勒概括出理论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分析和推测的(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批判的(a critique of common sense and conceptstaken as natural)和反思的(reflexive,think-ing about thinking.这里的反思特指“探询我们在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没有一个不涉及对于文学或文学性别样的理解。
因此,接下来便是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性的问题。卡勒以质疑的方式一一列出现存的多种有关文学或文学性的解释,并一一给出反例和疑点质询,从而使文学或文学性变成了一个面容模糊、十分可疑的概念。譬如,形象性曾经被看作文学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性,但是在宗教教义和史书中,形象化的叙述也是屡见不鲜的……以往对文学作本质主义的理解,认真地理论起来,真的是不大可靠的。当然,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话语实践活动。不过,这种话语实践活动牵连到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领域,则是确凿不移的。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这不就是我们熟透了的一个信条么?既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动用社会各种领域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在二十世纪初欧洲发生物理学、语言学的革命以后,随着在欧洲这个文明中心生成的新的知识成果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人类已经改变了看世界的视角和方式,过往形成的种种学科的种种重要的概念,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不可置疑的自明的概念。
我想,既然张江以文学或文学性为他提出的“两论”的轴心概念,那么他首先需要阐明的就是这个在他心目中不证自明的概念,用铁铸的证据雄辩地证实这个概念无可辩驳的有效性。
我想说的是,在中西文论史上,我们不难看到,为文学奠定理论基础和阐释框架的,即为文学立法的,很多都不是文学的圈内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十八世纪以来的康德、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再往后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和福柯,全不是搞文学的。
有人说中国的美学可分为两路,一路是儒家美学,一路是庄禅美学,而为这两路美学奠基立则的,前者为孔孟,后者为老庄和禅宗,撇去禅宗,也全不是搞文学的。刘勰该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家吧,可是他是舍人而不是文学家。严羽倒勉强可以说是文学的圈内人,但是,他“以禅喻诗”,是不是也犯了“场外征用”“背离文学指征”的错误?更贴近的例子是毛泽东。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人都很清楚,回到历史“现场”,毛泽东可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宗师,他从现实政治需求出发论述和规范文化和文学的文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完全可以说是搞文学和文学(学术)研究的中国人的“圣经”.1980 年代中期以前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理论基础、结构和评价标准就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而易见,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前,治史者就有了“前在立场和模式”,在治史的过程中,当然要“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不能想象,倘若“白板”一块,脑子空空,没有“前在立场”或“先见”,文学阐释将何以发生。
问题显然不在这里。进一步说,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或核心缺陷显然不在背离文学或文学性的“场外征用”之类。如果把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西方文论叫作当代西方文论,那么当代西方文论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它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发挥社会效应的空间,触觉直抵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西方社会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东方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从性别歧视到理欲分裂、从二分的思维传统到扭曲的东西方关系、从阶级压迫的新形式到媒体的官商合谋,可谓揭发伏藏,深入骨髓,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再来看它在文学研究上的进展。它首先突破了仅仅从外部(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进入文学的限制,把文学阐释拓展到了文学文本的层面(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接着又突破了粘滞于文学文本而不能自拔的限制,把文学阐释拓展到了文学接受和文学旅行的层面(如接受美学、读者 - 反应理论和形象学)。文学批评在十九世纪晚期学科化了,那时流行丹纳的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说,还没有为文学批评离开这三要素从别的视角进入文学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文学批评后来发生变化,是与人们改变了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初,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是物理学新思想的摇篮。测不准原理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得益彰。波子与粒子的相对性或不确定性,如同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的相对性或不确定性。彼此相关,由此及彼,由彼及此,不离不弃。在索绪尔那里,词与物的关系并不像过去的语言学所认定的,是固定的,而是随意的、偶然的;而且,词在文本中的意义也不是孤立的,而取决于它在上下文中如何呈现。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辨析或解构,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思维的祖先。卡勒在《文学理论简论》中对德里达如何解构语音中心主义有着扼要和精当的分析。语音先于文字吗?按常识,当然如此,但德里达告诉你,未必如此。这岂不是正好可与卡勒所归纳的理论的第三个要点对应!连思维的起点都有问题,沿着这种思维路径认知的本质化的种种概念难道就不会有问题?摆脱传统思维路径的还有福柯。福柯把话语与权力捆绑起来考察性史、疯癫史等,罔顾性、疯癫等是什么而只看性、疯癫等何以如此,也就是说,只看性、疯癫等的观念如何形成的话语实践,从而建立起性、疯癫等的“知识谱系”.这里是无法觅得本质主义的藏身之地的。德里达和福柯,还有海德格尔,乃至波尔和索绪尔等,在当代西方诸多文论中,我们是不难觅得他们的身影的。这些欧洲精英才是由欧洲延及北美的当代西方文论的真正的奠基人。
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成色和认识论基础,才是其要害所在。
当代西方文论东来,该来的来得差不多了。来中国旅行后境况如何,待遇好不好,能不能客随主便、入乡随俗,与接待的主人相处得怎么样,变声变调了吗,有没有长进,有哪些长进,这些才是我们应该急切关注的问题。大门敞开了,撵是撵不走的。该做的工作是:清仓查库,一样一样地打理清楚,问明用途,该存的存,该放的放,该改进的改进,该另创的另创。
以也许并非题外的话收尾吧。在当今偌大的中国,要找到一样纯粹的国货(限于现代工业和信息产品)无异于痴人说梦。小米是纯粹的国货、纯正的民族品牌吗?不是。雷军说得好,小米没有厂房,它的工厂是世界工厂。小米的芯就不是中国芯,小米的相也不是中国相。那么,中国的现代文论呢……
2015 年 2 月 13 日于武昌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