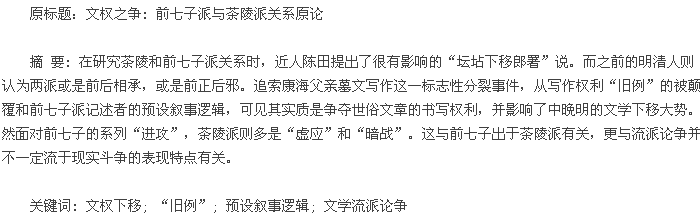
关于前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学界时贤已就古人论述做出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疏解,并得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结论①。本文则从明代文学的写作和品评权利下移的宏观运动趋势着眼,深入到当初两派相争的实际情形,对近代陈田《明诗纪事》就有的“坛坫下移郎署”说再做延伸探讨。指出前七子派从茶陵派的脱垒自立到张大高扬的过程,除关系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格局外,从文学流派的起伏兴衰来说,其实乃是前七子派或主动或被动地向高踞社会政治等级体制之上、又具有文化制度优势的台阁派代表茶陵派争夺文坛话语霸权的过程。这番斗争的结果,是身居郎署的前七子派获得空前胜利,彻底改变了明代文学的书写品评权利一直在高层官僚文人中间相传的发展进程,从而造就了明代文学流派演变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学话语权力交相更替的特殊景象。由此可见,前七子派与茶陵派的文权之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思想价值和文学流派论争研究意义。
一、文权“下移郎署”说的提出
关于茶陵派和前七子派的关系,明清人多纠结于两派是文学同盟还是一正宗一邪派的讨论,还不能特别有意识地从“文权下移”的文学流派发展角度,来看待两派后来确实存在的明显分裂的争论。继承前七子派文学主张而起的后七子派,在看待兴起之初的前七子与主宰文坛的茶陵派关系时,多认为是先后继起的文学同盟关系,主张茶陵兴起了前七子派。王世贞说: “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轻俊者,一时争慕归之。虽楷模不足,而鼓舞攸赖。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1]1044语气确实轻佻,有李东阳茶陵派为草莽、七子派为正宗之意。胡应麟也说: “成化以还,诗道傍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 律 严 整,高 步 一 时,兴 起 何、李,厥 功 甚伟。”[2]345虽放弃了世贞略显露骨的陈涉、汉高比喻,但还是认为李东阳的文学史功劳,除本身的文学成就外,就在于“兴起”了前七子派。这自是为后七子派的再度崛起张本。
其实不独后七子派如此,其他人也多这样认识。在世贞前,即有“论诗不主一格”[3]30的徐泰,海盐人,弘治十七年举人,着《诗谈》称: “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3]1208又有文学主张倾向李梦阳的袁袠,嘉靖五年进士,与唐宋派王慎中为同年,其《少司马陈公集序》一文,被台湾学者判定是“认为李东阳之文学论在于辨体裁,李梦阳则开正宗之途……由此言之,乃欲引二李为前后相承之同派也”[4]227。在世贞后、应麟前,又有穆文熙,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也说: “李公才情兼美,于李、何有倡始功,大似唐之燕、许。”[5]1109正面肯定东阳“倡始”李、何的作用。
而之如此,是这些明人看到了前七子派在兴起之初,确有一段追随李东阳茶陵派文学思想,奉其领袖成员为师友,其实是同派的时段。对此,当代学者或称之为“第一阶段: 在茶陵派卵翼下”[6]74,或称之为“双向接受”期[7]125。在那个时期,按李梦阳的流派意识,都还是“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8]卷二十《徐子将适湖湘》,奉杨一清和李东阳为文坛宗师。但两派到正德三年左右,还是由于政见和文学主张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而发生了本质的裂变,演出了激烈的纷争,导致文学书写权利的下移郎署。
于是,着眼于此者,就分出了派别: 或站在后来居上的前七子派一边,或站在视为文坛正宗大雅的李东阳茶陵派一边。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就是站在李东阳茶陵派一边的代表人物。其言: “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丽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 关陇之士,坎壈失职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为能事。王、李代兴,祧少陵而祢北地,目论耳食,靡然从风。”并攻击王世贞的上述比喻,以为文坛正统仍在李东阳的雅正台阁一系,而李梦阳及所带动的前后七子派,才是窃据一方的草莽,他们干了“诋諆先正”的犯上行为,且声称世贞晚年后悔其早年的这段为争夺文权而发的未定之论[9]254-257。不过,这也是评论者的有意“遮饰”“改造”,遭到曾受其指导奖掖的清人王士禛的揭露。他引徐泰《诗谈》上引之论曰: “当时前辈之论如此。盖空同、大复及西涯之门。牧斋《列朝诗集》乃力分左右袒。长沙、何李,界若鸿沟,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误后学不浅。”
[10]345指出李梦阳、何景明曾为李东阳弟子,两派实有割不开的承传联系。但王士禛也仅是就两派在弘治朝的情况而论,却没有顾及到正德、嘉靖间两派的分裂事实。
再后,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又在王世贞和钱谦益两造之间作调停,以为李、何是继东阳而起,“廓而大之”,造就文学盛世的大好局面[11]75,但也没有直接点明文权的变换问题。
直到近人陈田方揭出这一重要命题。其言:“胡元瑞谓孝庙以还,诗人多显达。茶陵崛起,蔚为雅宗,石淙、匏庵、篁墩、东田、熊峰、东江辈羽翼之,皆秉钧衡、长六曹,挟风雅之权以命令当世,三杨台阁之末流,为之一振。然踪希宋体,音閟盛唐,乐府或创新制,叠韵竞侈联篇。迨李、何起,而坛坫下移郎署。古则魏、晋,律必盛唐,海内翕然从之。譬之力侔贲、育,则勇夫夺气; 音希《韶頀》,则他乐不请。取法乎上,势不得而阻也。”[12]931提出了从“三杨”台阁派到李东阳茶陵派都是达官贵人“挟风雅之权以命令当世”,结果到李、何为首的前七子派崛起,才“坛坫下移郎署”。这就是明代中期的文权下移说。
不过,追论起来,何景明当初似即有了此种自觉争夺文权的意识。他要求在不能“倡于上”之时,要自觉地“倡于下”。其《汉魏诗集序》结尾言: “夫文之兴于盛世也,上倡之; 其兴于衰世也,下倡之。
倡于上,则尚一而道行; 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齐也。故志之所向,势之所至,时之所趋,变化响应,其机神哉! ”[13]卷三十四后来王世贞在为何集作序时也有此深刻感受: “是二君子挟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师友之素,而夺天下已向之利而自为德。於乎,难哉! ”[14]卷六十四《何大复集序》认为李、何等人改变了文权一直在台阁上层间传递的状况,而开辟一个属于“草莽”“微言”风行天下的时代,这其实和陈田的“坛坫下移郎署”说一致,只欠点明而已。
二、为文权而分裂的两派关系指实
两派最为明朗的公开分裂事件发生在正德三年( 1508) ,作为翰林修撰的康海,并没有按“旧例”将去世父亲的各种墓文写作交给同一个体制下的馆阁诸公,而是给了一帮志同道合、品级较低的文社好友,自己作《行状》,王九思为《墓志铭》,李梦阳写《墓表》,段炅作《传》。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记载: “戊辰,先生同考会试。……无何,丁母忧,归关中。往时,京官值亲殁,持厚帑求内阁志铭,以为荣显。而先生独不求内阁文,自为状,而以鄠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表》,皋兰段德光为《传》。一时文出,间者无不惊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见之,益大衔之,因呼为子字股。盖以数公为文称子'故也。若尔,非大衔也耶?”[15]卷五十三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亦云: “其年秋,太安人弃养,公将西归合葬平阳公。诸翰林之葬其亲者,铭、表、碑、传,无弗谒诸馆阁诸公者,公独不然。
或劝之,乃大怒,曰: 孝其亲者,在文章之必传耳,官爵何为?于是自述《状》,以二三友生为之。刻集既成,题曰《康长公世行叙述》,遍送馆阁诸公。诸公见之,无弗怪且怒者。”[16]卷中两文都作于康海去世的嘉靖十八年( 1539) ,距当时事件发生的正德三年,已有三十年之久。即便如此,对于这场有关前七子派和茶陵派、台阁派关系的重要事件,两文还是做了可以互相补充的记载。其间容或有揣度夸张的成分,然据王九思与康海的一世朋友加儿女亲家的交情,则前七子派确曾因为康海父亲墓文的写作问题,而与当时台阁派和茶陵派的双料代表李东阳发生激烈冲突这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并且,这场冲突的本质,是身居下位的前七子派,以关中康海为代表,主动向高据社会政治文化高位的茶陵派、台阁派争夺俗世文章写作权的文权之争,即使为之得罪现管的上级亦不恤。
而这场冲突之发生,关键即在于两文提到的墓文写作必找馆阁大臣的“旧例”。明人提及此点的很多,与李东阳有深厚交情的陆容,讲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都出重金求内阁大臣作墓文的情况: “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遗己也,则以挽诗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
[17]189李东阳门生罗玘,则讲到更为多样的求馆阁大臣写亭台记、器物铭和墓文、寿诗等情形: “有大制作,曰: 此馆阁笔也; 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 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
[18]卷一《馆阁寿诗序》再比照记录康海父亲墓文写作事件的文字: “康对山以状元登第,在馆中声望籍甚,台省诸公得其謦咳以为荣,不久以忧去。
大率翰林官丁忧,其墓文皆请之内阁诸公,此旧例也。对山闻丧即行。求李空同、王渼陂、段德光作墓志与传。时李西涯方秉海内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对山遂落职。”[19]126也称翰林官员丁忧、墓文皆求内阁诸公作是“旧例”。“旧例”和“故事”一样,具有不成文法的威力,破坏它就要冒风险。
康海去破坏了,就可能引起恶果。果然,正德五年,刘瑾以谋反罪伏诛,作为同乡的康海和王九思受到牵连,先后落职还家,从此再没能重返仕途。
其次还在于康海、李梦阳等人由于学习秦汉文而形成的互相称“子”、被馆阁大臣蔑称为“子字股”的文风,迥异于当时以“和平畅达”流行天下的李东阳茶陵派文风。这在七子派的历史追述眼光看来,也是“得罪”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上引张治道文外,还有朱应登之子曰藩也以此重述这段文权斗争史,且涉及的范围更大,扩展到整个前七子派成员:“弘、德时,海内数君子出,读书为文,溯自韩、欧以上,稍变前习,一时士大夫翕然趋焉,而柄文者顾不之喜,目其文曰字子股。乃数君子亦抗颜不之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于世。然以天下公器趋舍相诮,识者非之。”
[20]卷二十八《袁永之集序》何乔远则集中到王九思一人前后学习之变来重述: “李梦阳起而倡古文辞,九思一洗旧习从之。东阳因呼九思、梦阳文为子字股,盖以其互称子为重也。”
[21]李梦阳嘉靖六年为朱应登生平作的《凌溪先生墓志铭》,则将弘治十二年朱氏登第后前七子派所面对的控压目标扩大为两个: 一是以理学着称的台阁派人物,“执政者”刘健,对文学予以彻底地否定,声称李白、杜甫只是酒徒,不足多道; 二是茶陵派首领,“柄文者”李东阳,称前七子派之作是“卖平天冠”。在他们的联合打压下,“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8]卷四十五。李梦阳代表前七子派,发出了对于茶陵派、台阁派的政治和文学控诉。
由此可见,在康海、王九思、李梦阳到张治道、朱曰藩等人的认识里,前七子派的文学宗法和政治际遇确实有一个被茶陵派、台阁派所压抑的艰难过程。而这又和当时本派成员要么多未能融入翰林台阁体制,要么即使进入了也因为政治风波而被赶出( 如康海和王九思) 有关[4]52-81。仕途的隐秘失意和高昂的文学宗法就这样牵连起来,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局面。要具体指实所针对者为何人,又为何事去针对,其中肯定有岁光飘忽、时代抵牾之处。何况这些前尘旧事,被前七子派以一种后知的历史观念进行了筛选过滤,已经融入了一些后来才清晰的历史叙述逻辑。
于是,发生在正德三年的这场本来可能无足多道的寻常墓文写作事件,却因为关涉到前七子派的文学宗法和政治命运问题,而变得意义重大,成为康海等前七子派成员的生平传记写作所必要突出的重要大事,从而体现出叙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
以张治道的康海生平记述为例,他对康海得罪台阁这个后果的前因作了交代说明: 一是早在弘治十五年( 1503 年) 廷试,康海制策得到弘治皇帝的大加赞赏,钦点为当科状元,名震天下之时,即引起了其时台阁诸公包括李东阳等人在内的不满,而种下最初的祸根[4]75-76; 二是到弘治十八年( 1506 年) ,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在京城结“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为其时“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穷仿,以为前无古人”的李东阳所大不满。这就是张治道基于后来的政局和文坛发展情况而做出的一种预设叙述逻辑,意即从康海一登第为状元始,即有提倡 先 秦 两 汉 古 文 和 汉 魏 盛 唐 诗 歌 的 想法[22]卷三《渼陂先生集序》,要与统治文坛的茶陵派一争高低,墓文行动就是实现文权转移的重要举措。结果是前七子派取得了古文宗法的胜利: “一时文出,见者无不惊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 ”
茶陵派则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的李梦阳、康海、何景明、徐祯卿等前七子派中人纷纷被打击,“在仕路遂偃蹇不达”,与茶陵派的“后进有文者”多官运亨通适相反照[19]127。
三、茶陵派的“虚应”和“暗战”
虽然后来前七子派( 尤其是关中派,或称西北派) 一系言之凿凿,将批判锋芒直指茶陵派首领李东阳,但毕竟都是李东阳下世多年后的记载。所以,要寻找李东阳茶陵派对于前七子派系列“进攻”的反应,便非常困难。在此,只能找一些侧面的回应情况。
对李东阳而言,其在正德朝的际遇可谓既喜又悲,喜的可能是个人仕途的飞黄腾达,终于位极人臣,做了内阁首辅,悲的是偏逢艰难时局,宦官刘瑾等颐指气使,又有同年焦芳虎视眈眈,随时欲取而代之,正气日暗,左支右绌,倍感压抑。偏于柔滑怯弱的个性和恋禄保位的心理,使得士林领袖李东阳处于正德初年政局和文坛的风口浪尖下。人们的议论颇为纷纭,甚至连老门生罗玘都不理解他的苦心弥缝、一直不退,而要求解除师生关系,“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
[18]卷二十一《寄西涯先生书》得意弟子乔宇,似也要与他保持距离。李东阳不由得回信乔宇,诉说内心不白之进退苦衷: “近得两书,寒温外别无一语,岂有所惩,故为是默默者邪? 计希大于仆不宜尔。或前书过于自辩,致希大不自安? 盖于希大有不容不尽者。今道路谤责之言洋洋盈耳,仆曷尝置一喙于其间哉? 顾进退之迹,无以自明,如所误极,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悔其误,岂于仆之素心亦有未谅者邪?”
[23]卷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李东阳大概是顾不得与康、李等人做正面的文学反击。所以,除能从王九思、康海等人以刘瑾党羽的罪名被政治打击,落职罢官,而猜测东阳可能是借机报复泄愤外,其他就只能靠一些侧面的评述用语来猜度。黄卓越先生认为李东阳致仕后所写的《瓜泾集序》中的“钩棘晦滞之病”“掇拾剽窃于片言只语间,虽有组织绘画之巧,卒无所用于世也”,《董文僖公集序》中的“诘屈怪诞之语”,《刘文和公集序》中的“朱子深慨夫文之弊,谓今之为文徒得减字法与换字法耳。夫为文而法止于是,又恶知有所谓气者哉”等语句,“均为七子所发,且甚有忿忿不平之念,与其固有的为台阁文时的雍容平正相比已属失格。”[24]53可参。
李东阳本人如此,其他茶陵派成员的反应也多半如是。即有针对,也大抵是推崇维护李东阳的正面高大形象,而偶尔以旁敲侧击的用词,向着前七子派围攻的“虚影”做些“暗战”的工作,这可以李东阳好友谢铎《读怀麓堂稿》和门生梁储《贺阁老西涯李公七十诗序》为例。前文言李东阳: “出其绪余,发而为文,则根据六经,泛滥百家,随所欲言,无不如意。 …… 故 独 立 之 憎,终 不 能 胜 同 俗 之悦。”
[25]卷三十可看作是不满前七子派的群攻,算是为朋友和本派文学宗旨护法。后文则以台阁派一贯的评论尺度,阐明李东阳一生的文学业绩,说其文可分两部分: 一、经世致用之文为大,“若入告奏议之文,代言应制之文,纂修笔削之文”; 二、文学之文,虽为余事,“然叙事如《书》,铭赞如《诗》,简严如《春秋》,雄深雅健如司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余味,或纡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余,溢为奇怪,沛然莫 御,而 皆 安 流。”总 之“不 专 一 能,兼 具 诸体”[26]卷四,包含了前七子派赖以自诩的古诗文才能,又有他们无法写作的台阁用世之文,这无疑是在暗中维护李东阳。而攻击前七子派古文宗法之意较为明显的,则是顾清所言: “近世高才之士,以汉唐而下之文为不足法,而必欲力进于古人。其志甚高,论甚伟。后进习闻其说而不得其所以然,摆落拘缠,自出机杼,往往未及释氏所谓小乘禅、第二义,而骎寻于外道者有之。其剽猎记诵为口耳之资者,又在所弗论也。”
[27]卷三十九《答聂文蔚论文体书》不过时间已到了嘉靖初年,指责的也是生吞活剥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无名”末流。
至于以不与交往的方式表示对前七子派不满,据学者梳理,似只有何孟春; 不过也仅限于与康海、王九思,而与李梦阳则还是维持了相当良好的朋友关系[4]48、78。其他如乔宇、储巏、邵宝等茶陵派人士,与前七子派成员都交情不错,并未因为后人认定的文学流派归宿的不同而互不两立。因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划出的两派对立,更多应该是一种无形的派系观念,不一定要落脚到针锋相对、你嘲我讽的现实层面。何况两派在文学思想观念和创作作风上颇多可交相出入的地方,以至现代人差不多都认为前七子派是宗法严格化了的茶陵派的发展①。只要不去穷究坚执其后来之异,又何妨早期的思想相通? 对立是存在的,但不一定要流于显攻; 斗争是存在的,但多半会是“虚应”。只有尘埃落定,当事人都逝去,对立斗争的真相才由似乎凝定了的历史叙述者之口倾倒出来( 主要是前七子派) ,显得当初的过程就是那么肯定激烈。而其实未必。因为,即使在“矫激取名”[28]1485的明正德时期,也还有比文学更为重要的政治。只有当文学牵蔓到政治,文学之士的命运被关注,文学的宗法权利也才跟着被关注。这是笔者考察了时贤关于两派关系的讨论后得出的基本看法。
[参考文献]
[1]王世贞.艺苑卮言[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2]胡应麟.诗薮·续编[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周维德.全明诗话[M].济南: 齐鲁书社,2005.
[4]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M].台北: 学生书局,1989.
[5]朱彝尊.明诗综[M].北京: 中华书局,2007.
[6]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薛泉.李东阳研究[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8]李梦阳.空同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钱谦 益. 列朝 诗 集 小 传[M]. 上 海: 上 海 古 籍 出 版社,1983.
[10] 王士禛. 池北偶谈[M]. 靳斯仁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11]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何景明.大复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