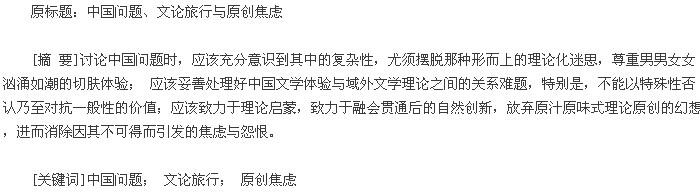
晚清时期,洋人的炮火轰开了古老帝国衰朽的国门,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以后,“中国问题”便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朝野上下,有识之士无不对之念念不忘。无疑,救亡与启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域外的大量理论资源一时间蜂拥而至,它们与中国旧有的知识工具同台竞技、相互博弈。可以说,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不同者,中国问题的内涵在历史行程中不断更新、积淀,知识界也不再盲目推崇旅行的理论,甚至有不少学者呼吁,必须要有与中国崛起相配的、自己的理论原创。
不过,需要给予提醒的是,讨论中国问题时,应该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尤须摆脱那种形而上的理论化迷思,尊重男男女女汹涌如潮的切肤体验; 应该妥善处理好中国文学体验与域外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能以特殊性否认乃至对抗一般性的价值; 应该致力于理论启蒙,致力于融会贯通后的自然创新,放弃原汁原味式理论原创的幻想,进而消除因其不可得而引发的焦虑与怨恨。
一
中国问题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譬如,国际关系、国有企业、思想解放、收入分配、信仰危机、环境恶化、社会舆论、物价、就业、人口、腐败,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深刻地形塑了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刻骨铭心地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的切身感受。让人纳闷的是,有学者竟然把类似的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统统斥为肤浅的问题,认为只有经过“穿越”,它们才能成为所谓“真正的中国问题”.我曾经撰文批评这一说法将中国问题给狭隘化了,并强调把生活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固然重要,但没有必要把现实感受与理论问题截然对立起来.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批评竟被指责为以现实经验否定了理论概括的意义。而理论概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覆盖了“任何问题的思考”,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简化”,“把很多充满生机的东西过滤掉,使留存的东西更适于理论的一般性”,即是说,达到“本质性”①.尽管论者在表态时反对“本质主义”,言之凿凿。遗憾的是,只是表态而已,一俟分析问题就又故伎重演。
这其实还是思维方式、思维范式的问题。就论者追求的理论概括而言,就算经过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那个明艳的本质,然而,跟付出的那些代价---舍弃无数生机---相比,这究竟值不值得? 如果舍弃了无数充满生机的东西,那个干巴巴的教条又有多大意义? 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有一张桌子,按照上述寻找本质的做法,那就一定要从桌子后面找出它的本质来才善罢甘休。至于诸多带有体温的细节,譬如,这张桌子花费主人多少钱,哪里买的,主人如何看重它的收藏价值,因为它惹出了多少悲欢离合等等,就都必须毫不吝惜地割弃。相比之下,反本质主义者会说,桌子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不要再做无用功了。关系主义者会说,我们应该费心考察桌子所处的关系网络,而桌子的性质就蕴含在它与周围事物---譬如,椅子、床等---的关系之中。另外,把它放倒,桌子可以充当椅子的角色; 平躺其上,桌子又暂时发挥了床的功能。
这个时候,本质性的东西又在哪里? 以此类推,我们应该瞩目于那些活生生的中国问题,是否要经过“穿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察中国问题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纠葛。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为全面而透彻地弄清中国问题,进而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策。
不言而喻,当我们描述中国问题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沿用了习得的知识图谱。这些知识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问题,但应当明白的是,既有的描述已然隐含了特定的价值取向,而且,它会与生生不息的经验之间不断地出现不和、摩擦、冲突、对抗。所以,当旧描述无法有效应对新经验时,就没必要、也不能硬撑着,甘做某一简略模式的殉道者。
雷蒙德·威廉斯就此指出,“为了充分地描述经验,我们所需要的术语必须在根本上是起作用的,然而我们创造的每一种新的描述似乎都迅速转变成了对象,因而既很难阐明经验,也很难忠实地保持其原貌。最关键的是,每一种描述以及提供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项。”
换言之,要始终意识到: 已有的描述会固化,会成为知识的对象,与固守一个僵化的教条比起来,有效才是描述的最大美德,而在熙来攘往的经验撞击下---毕竟,所有的描述都是“与我们的部分经验相匹配的,但是在其他部分的经验那里,它们同样也会不断地碎裂”,这种效力有可能减弱、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于是,在旧描述与新经验的往复商谈后,修订的描述或新的描述就应运而生。仿照威廉斯的口吻,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是在抽象化与现实经验之间展开的一场漫长搏斗。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范围广泛、灵活多变的概念性思考,抽象使这种思考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思考要有相关性,我们还需要来自现实关系的持续压力,需要一种能够赋予描述过程以实质内容的实际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说,在抽象化时,需要尊重中国问题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这就意味着抽象的动力不是来自本质的威慑,而是来自新问题与老问题之间互动带来的压力。此时此刻,负责任的学者理应探究它们何以产生、它们的渊源、它们之间的关系; 探究为了解决老问题而给出的新举措解决得怎样,又导致了什么新问题; 探究它究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立足全局、究其根本; 探究它宣扬要实现的目标有否可能完成,它实现那一目标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等。这些剖析的视野是动态的过程与多面的关系,而非固着的状态。
不难看出,哪一个才能真正触及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进行充分的省思。
理论化、抽象化本身很有必要,但它不必兀兀穷年,唯不变的本质是问,痴迷于冶炼出形而上的理论铁律或纯粹的绝对程式。“关于一个社会的真相,似乎要在决策系统、传播与学习系统、维持系统和生育与养育系统之间的实际关系中去发现,而这些关系总是异常错综复杂的。”
绝对程式势必要把上述各种各样的关系抽象化、简单化,抛开各种充满生机的变数。而要想真的直面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就需要铭记: “没有什么形式是可以‘永久不变’的,这样各种变化的形式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
可想而知,如果对此不闻不问,一意孤行,那么,结果只能是简单或暴虐,并不如烟的往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譬如,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人们耳熟能详,历史自此沿着光明的、线性的目的论方向欢歌向前。认识中国问题肯定不能仅仅满足于复述这样的宏大叙述,还需要考察整体的乐观氛围之中,还有哪些微妙的情绪,譬如,欢喜中夹杂的向往、投机、漠然、怀疑、担忧、恐惧,等等。崭新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的那些不宜明示的情绪如何隐藏? 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又得到了怎样的表达? 这些经验又怎样历经淹埋最后重见光明? 等等。审视已逝的历史需要这样关系式的思维,审视正在运行的当下中国亦是如此。
二
晚清以来,域外传入的大量理论资源共时式地平面铺开。就文学领域来说,它们始而在“文学革命”的大旗下精诚团结,一同攻击雕琢、陈腐、艰涩的封建文学,继而在新文学内部为争夺话语权而掀起“为人生”“为艺术”之争。紧接着,“革命文学”勃然而兴,文论的左翼化力量从此渐趋强大,直至最后陷入极“左”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论从最初的“盗火者”一变而成被压抑者,甚至是谈者色变。因此,应该在极“左”文艺难以为继这一大背景下,来看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波澜再起,它以再启蒙为旨归,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如此的历史契机给中国文论打上了浓重的西方色调。历史无法重头再来,我们也不可能紧闭家门、拒绝“睁眼看世界”.作为学者,应该做的是研究如下问题: 哪些历时的西方文论资源被大量引入? 它原来的发言对象是什么? 与中国原有的什么理论资源产生了共鸣? 国人的接受与它在原产地的形象有何差异? 有没有对它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就西方某个流派的文论而言,对中国文论、文学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理论在旅行中释放了怎样的能量?
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文学理论、比较诗学中很有意思的重要课题,需要沉入历史语境,进行扎扎实实的梳理。
谈到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20 世纪西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理论有不少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文论,如海德格尔之于老庄、庞德之于意象、布莱希特之于戏剧理论等。由此,他结论说,中国文论的很多理论与范畴具有全球的普适性---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导致这推理的跨度明显太大。众所周知,20 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边倒式的。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是 80 年代,或是 90 年代以至于迄今为止,西方文化往往是如潮水一般闯入国门,而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则基本上处于雌伏状态。因此,重要的可能还不是为了挽回一些颜面,而去信誓旦旦地宣扬“中国古代文论其实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照此来说,当后者传到中国时不是又返祖归宗了吗?
又何惧西方文论的大举入侵呢? 重要的是考察西方文论进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怎样的接受与嬗变,而不是简单地扣个“盲目追随西方文论”的大帽子了事。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在“洋务派”那里就已经运用娴熟。不同的是,它是为洋务运动造势,针对那些反对洋务论的人所做的辩护。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 “‘西学源于中国’说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也好,都表露了儒家学说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绽,并显示出中国已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西洋的文明即使源出中国,但却由西洋人去发展,中国今日不得不把它学回来。不论怎样自吹自擂,说什么中国之学为本、为道、为体,而西洋之学为辅、为法、为器、为用,说什么中国为主人,西洋为仆人,今天却不得不学习此仆人之文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西学的心态才逐渐蔚然成风。这启示那些关注当代中国经验的学者去思索同样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拒斥外来之物。
在“西学源出中国”看来,西方思维模式给我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它共有三宗罪: “学科化”,“体系化”与“范畴化”.其实,它们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先看学科化,伊格尔顿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指出,literature 在西方也不过几百年的光景。而作为一种建制的文学学科在中国的时间则更短,它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而得以立为一门学科的。扩展开来说,“作为特定建制的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兴起,与人文科学取得其特定地位一样,是相当晚近的事”.而之所以会有诸多的分科,也跟现代社会知识的日益复杂化、不同的研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分工、科学的示范效应等因素直接关联。“如今,如果我们想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获得一种充分的理解,我们得依赖于把我们和大量学科联系起来的传递洞见的复杂之链。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事业,决非单单人文科学所能胜任”.就是说,学科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那么,即便是受了西方思维的影响,文学学科化又何罪之有呢? 关键在于,学科化之后有没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洞察文学、文化、历史与社会的奥妙所在。近现代以来,科学精神成了现代性的高标,其他诸多学科也唯科学之马首是瞻,这里会产生两种结果:
一是合理吸取科学的体系化、系统化、范畴化等思考问题的方式,二是将这种学习推向极端、成了唯科学主义。回首过往,不管是在“五四”时期还是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的文论都曾走过科学主义的岔道。尽管如此,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反对“科学主义”不是要抛弃“科学精神”.体系化、系统化的思路运用到文论中来,是要求把文论当作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范畴化则要求对所使用的术语给出相对准确的界定。古代文论尤其是其中的诗论部分,比较注重直观印象与体悟而分析性较弱,对其进行体系化、范畴化起来有时候不免削足适履。譬如,华裔美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但近现代以来,在吸收域外文论资源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论话语与文论体系。应该说,当代文论话语的成形得益于如下因素: 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学理论课程的开设,当代文学批评的应用,大众媒体的散播等。在承认古代诗论富有浓厚诗性的前提下,也不得不看到,它那种“懒散的、印象主义式的思维习惯的羁绊”对今天需要“更加细致地求索”的我们助益无多.三域外的文论曾经大量涌入中国,现在还在大量涌入中国。于是,有人断言,这就是中国出不了“大师”的根本原因。多数学者整天都在忙于围着洋人团团转,说得好听点儿是“引进”,说得不好听是“贩运”“推销”人家的理论。这样的日子有意思吗?
难道学术界不该好好反省,换一种“活法”吗? 一连串的抨击与质问,听起来义正词严,但令人疑惑的是,每当我们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做痛心疾首状时,有否把文论旅行的问题给简化了? 或者说,能否实现逻辑的自洽? 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一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荒唐透顶的论辩: 我是爱国的,而你反对我,所以,你是卖国贼,应该被踏翻在地.问题是,推论的前提是否成立? 就算可以成立,事情有否简单到二元的势不两立? 简单到或 A或 B? 有没有亦此亦彼的可能? 稍稍在逻辑上自我质询一下,就不难明白类似宣言的可笑: 现在,你们大多数人搞的那一套都不行了,得看我( 们) 的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问题在于,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说别人的路走不下去了? 要不要看看那条路上的理论是否还有阐释的效力? 将要登场的中国理论具备不具备这样的效力? 是理论的商标重要,还是阐释的效力重要?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完全自主”的理论问世之前,有没有可能阻止文论的旅行? 如果不能阻止的话,是不是( 至少) 要分配一部分学者研究研究旅行的文论? 旅行的文论当然没有长脚,不会自己跑到中国来,是不是要考察一下引进的具体情形? 譬如,撇开那种挟洋自重者或生吞活剥者不论,其中有否“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旅行而来的文论是不是就可以为审视并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参照系?
此时,哪怕研究者“言必称希腊”,只要他能把这个“希腊”给真正说清楚,是不是也有其一番不可小觑的作用?
毫无疑问,域外的文论有其生长的现实语境、文化传统、理论谱系,那么,如果用它来看中国问题的话,会不会因为“错位”而产生令人担忧的“理论的幻觉”? 换句话说,看到的只是西方理论中虚构的中国问题,而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首先务必祛除那种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中国问题的奢望---因为中国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它们相互关联、犬牙交错,旧的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会冒出来,旧问题与新问题之间往往也有藕断丝连的纠缠。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文论,都不过是描述中国问题的暂时工具。关键在于,它能否带来新的视野或新的视点。
中国问题是特殊的,但这种特殊是建立在与俄国问题、日本问题、美国问题、法国问题等等相互比较的基础上的,绝非来自某种神秘本质的规定。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如果与同样遭受殖民侵略、殖民统治并争取民族自立、自强的国家相比,与同样经历现代性的诸多国家相比,中国问题又有其一般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之前,尽管改朝换代式的游戏间歇上演,但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压迫势力、建立人民共和的理念却前所未有。马克思主义看到的阶级压迫是虚幻而非真正的中国问题吗? 率先走向现代的国家遇到过环境污染、权力腐败、人性堕落、文化低俗等等问题,这些恐怕也是中国问题的重要组成板块。先行的国家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积累了哪些可供我们学习与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就学术界而言,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话语与权力等理论引入后,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把戏尴尬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福柯分析的虽然不是中国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具有一般性,持续启发着人文社会诸多学科的研究。而文化研究传入中国以后,文学作品接受的惯习被撬动,阅读者的感受经常被刷新。能把这些从中国文学作品中得出的新感受排除在真正的中国问题之外吗?
现今,任何理论都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准确到枝枝节节。在难以逆料的现实经验冲击下,文学理论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调适,否则,难免会胶柱鼓瑟或缘木求鱼。而且,任何理论也不能奢求一家独霸,而必须和思想场域中的其他理论进行对话、辩论。换句话说,理论同样形成了一个繁复交错的关系网络,它们在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中界定彼此的方位与身份。正是上述双重的压力共同塑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也即是说,它是融会贯通后的自然生成,既吸收了理论的一般性,又具备直面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还有其他形色各异的非马克思主义在程度不同地传播,譬如,其时知识界认作“社会主义”来介绍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在仔细对比、分析、辨别并经过多轮激烈论战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个马克思主义在其后的革命过程中也遇到了严峻的现实考验。多次失败的事实证明,仿照苏联式的从大城市发动起义取得革命成功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经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摸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历史启示我们,原汁原味的理论套用会有麻烦,而原汁原味地原创,炼出一尘不染的理论公式则是偏执。如刘小枫所言: “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靠支配中国思想界一百年的民族性比较的辩护心态(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肯定会落空”.原创的焦虑必然会诱发同等乃至更大规模的怨恨,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自尊所孕育的怨恨。显然,一竿子把外来文学理论全部否决,并大力宣扬冰清玉洁的原创,不过是这种怨恨之情的变相抒发罢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为了更好地探究中国问题,与其这样自怨自艾,不如坦然以对。
【参考文献】
[1]王伟。 何谓文艺学论争的“中国问题”[J]. 文艺争鸣,2012( 7) : 15.
[2]李自雄。 值得追问的“中国问题”[J]. 文艺争鸣,2013( 1) : 15.
[3](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M]. 倪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曹顺庆。 古代文论指导当代创作,可行! [N]. 中国艺术报,2012 -01 -09( 3) .
[5]( 日)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修订译本) [M]. 谭汝谦,林启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 -12.
[6]( 挪) G·希尔贝克。 时代之思[M]. 童世骏,郁振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7]( 美) 欧文·白璧德。 文学与美国的大学[M]. 张沛,张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4.
[8]鲁迅。 华盖集[M]/ /鲁迅。 鲁迅全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1.
[9]刘小枫。 “中国问题”与社会理论的牵缠[J]. 花城,1996( 3) :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