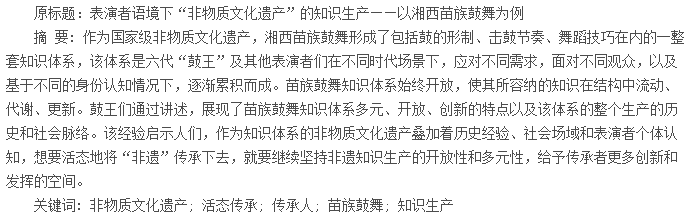
一、问题的引出
2013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 时许,吉首国际鼓文化节“鼓王争霸赛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选拔赛”决赛现场在湘西德夯苗寨表演场地举行,来自贵州、湖南、广西、湖北等省区的 23 支苗鼓队和69 名民间鼓手参加了角逐。经过 3 轮的激烈较量,笔者与现场数千名观众一起,目睹了第三代猴儿鼓王和第六代女子鼓王的诞生,他们是来自德夯代表队的时节海和杨欣。颁奖仪式前,主办方举行了一个神圣而隆重的“请鼓神”仪式,两位获奖者在苗法师面前从第二、三代猴儿鼓王和第五、六代女子苗鼓王手里接过撒过鸡血的鼓槌,猴儿鼓王接受的是龙槌,女子鼓王接受的是凤槌,意味着两位鼓王得到神明的认可和祝福,苗家古老的鼓舞也将通过一代代鼓王传递下去。
这一幕“鼓王争霸”虽然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传承”二字,无论是现场第二代至第五代鼓王的出场见证,还是以仪式方式“请鼓神”传鼓槌,都彰显着对苗族鼓舞古老传统的尊重。然而,在笔者看来,整个过程与其说是对苗族鼓舞“本体”呈现,不如说是对围绕“苗鼓”所建构出的知识体系的再次展演,其现代感和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已经让人充分领略到其中包含的复杂语境和潜藏于背后的社会脉络。
首先,比赛流程参照现代体育的“循环赛”赛制,而对比赛项目的介绍更具有现代感,如“女子单人鼓”、“男子单人鼓”、“女子双人鼓”、“男女双人鼓”等。其次,选手在比赛击鼓过程中,能够做到劈叉、下腰、连续转体,所采用的身手步法,融合了舞蹈、体操和戏剧的元素,观赏性非常强。再次,评比规则方面,裁判需要考虑“技术准确性”、“技术难度”、“时间控制”等方面,以分数呈现最终比赛的结果。这种以现代方式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已经颇为普遍,包括对其内容增删。形式调整、加入投合游客所好的噱头。如果纠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二字,这种改变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如果将“非遗”看作是一套知识体系,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发掘“非遗”知识生产的社会脉络,不难发现,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是在历史某一时刻固定下来的“遗留物”,而是一套身处于各种开放场域,被传承者、观众、专家学者等不断添加、修改的知识体系。
2005 年以来,我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进行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和保护工作,相继推出了三批,共计 121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认定及保护工作调动了学者、官员、民间人士、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参与,人们在保护过程中又搅动起与文化有关的传统保护、经济发展、政绩工程、旅游开发等一系列现实话题,而置身于各种语境中的“非遗”,会从形式到内涵呈现出环境和人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近年来,高丙中等学者主张要以“民族志”写作方法去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深入到“非遗”生产的语境中,将“非遗”与日常生活的常态进行接续,其实也是在倡导以个案的复杂性呈现为前提的学术研究,强调对“非遗”语境的把握,从而建立如何保护“非遗”文化的立场[1]。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为例,展示在“非遗”展演的场域中,个体如何在“非遗”图式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表演来与观众互动以形成一种社会实践[2]。
在一个多月调研期间,笔者对苗鼓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鼓王”进行了近距离接触,获得了深度访谈资料。笔者关注这些肩负苗鼓舞传承使命的“鼓王”们,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中习得、体验并一次次呈现“鼓王”这一角色的? 她们如何运用苗鼓舞这一艺术媒介,实现与观众、与同行、与师者的交流? 她们所身处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 、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 赋予她们何种能动性,又是如何对其结构因素进行内化? 不同代际“鼓王”对于苗鼓舞的理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二、知识的历史场域与现实场域
作为人类最早发明并使用的打击乐器,“鼓”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间,其起源悠久且分布广泛,云、贵、川、湘、桂一带的佤、侗、彝、瑶、壮、傣、水、布依等民族都使用由不同材质制成,带有本民族特色的鼓,及伴随击鼓而形成的舞蹈动作。苗鼓及鼓舞主要盛行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吉首市、凤凰县、泸溪县、保靖县、花垣县、古丈县等。
明清时期史料显示,苗鼓多出现在“椎牛祭祖”的祭祀场合,而且将击鼓起舞的形式固定下来。清人严如煜编纂的《苗防备览·风俗考》中“跳鼓藏”条载: “(苗) 刳长木空其中,冒皮其端以为鼓。使妇人之美者跳而击之,择男女善歌者,皆衣优伶五彩衣,或披红毡,戴折角巾,剪无色纸两条垂于背,男左女右旋绕而歌,迭相和唱,举手顿足,疾徐应节。”清康熙年间《红苗归流图》中的《农毕鼓脏图》之志记载: “苗人于农毕冬月跳鼓脏以祀神,先期设棚于寨外平坦处,预告亲友,至日,邻苗男妇老幼鼓吹而来……抵暮,主人率男妇击金伐鼓,群聚棚下,设位奏乐以迎神。”可见,当时的鼓舞与民间祭祀活动紧密联系,鼓被赋予了神圣性,而舞的目的是为了迎神娱神。民国时期,政府认为“椎牛祭”是淫祀,履出告示禁止,因而“跳鼓脏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也正是该时期,鼓舞逐渐从与祭祀并行的娱神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日常节庆中的娱人活动。
每年正月初二到十五,有持续不断的“年鼓”表演,而逢农历“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七月七”等岁节时庆,各村寨擅长苗鼓的鼓手就汇集在一起,村寨前后的宅场、平坝、场院就成为切磋鼓舞技艺,供人娱乐游艺的场地,苗鼓的神秘感和仪式化倾向越加淡化,逐渐与苗族的生活融为一体,鼓舞合一,苗语称为“保农”(音译) ,即边跳边鼓的意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鼓舞作为湘西苗族本土艺术的精华,多次作为民族文化优秀代表入选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作为比赛项目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苗鼓手、本地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参与到对鼓舞形式、套路的编排改造中,实现对苗族鼓舞知识的“再生产”,所谓“去粗取精”。人们将敬神、驱鬼、祭祖等内容和意涵全部删除,突出并加入模仿生产劳动的内容,如犁地耕田、播种插秧、收割打谷、美女梳妆、绣花纺纱、绩麻织布等,使其成为国家建构民族政治身份框架下,呈现现代民族符号的重要标志,并按照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形式确定下“花鼓舞”、“猴儿鼓舞”、“团圆鼓舞”三大种类,按照参赛人数,再分为“花鼓舞·女子单人鼓舞”、“花鼓舞·女子双人鼓舞”、“花鼓舞·男子双人鼓舞”、“花鼓舞·男女双人鼓舞”、“花鼓舞·四面鼓舞”等。其中“四面鼓舞”形式创新于 1986 年,当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前,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会专家建议将双面苗鼓改变为具有四个鼓面的特制鼓,既可以丰富演出形式和内容,加大比赛难度,又满足观众视觉效果。
根据笔者在湘西搜集到的关于苗族鼓舞的宣传中,其介绍已经显得很文本化了,“苗族鼓舞是从苗族农耕文化中造就出的最为典型的民间舞蹈。一般是一面直径约八九十公分的双面牛皮大鼓,鼓手手执一对长约尺许的鼓槌,将牛皮大鼓置于鼓架之上,按照鼓点常见的节奏 2/4、3/4、4/4 拍进行擂击。……花鼓舞套路繁多,动作丰富敏捷,多以日常的生产生活和劳作为素材,如梳头、纺纱、织布、挖地、播种、插秧等,较多地反映了与农业生产生活有关的内容,表演者肢体形态变换幅度大,节奏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愈渐脱离苗族神圣仪式的苗族鼓舞变得精英化,年青一代愿意学,能够打的人越来越少。而恰逢其时,湘西独特的人文地貌,吸引了一批民族文化旅游爱好者的脚步,旅游业在湘西开始萌发。苗族鼓舞作为带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亮点借助旅游业发展,再次普及,并得到广泛关注,鼓舞频繁地出现在湘西的各个旅游景点。在村寨门口有“拦门鼓”表演,游客婚嫁体验环节上有“接亲鼓”、“拜客鼓”表演,而在旅游旺季时,湘西着名的旅游村寨之一———德夯,每天晚上都在村寨广场上举行篝火表演活动,苗鼓贯穿始终,承担着重头戏的角色。满足市场需求,在苗鼓中添加可观赏性因素就成为“知识再生产”的又一推动力了。
三、通过表演实践的知识生产
1.“鼓王”的身份认定。新中国成立前,每逢“四月八”、“赶秋”、“百狮会”等节日,各村寨鼓手们会聚一起,切磋鼓舞技艺,民间会对这些鼓手的技艺有个高低上下的评比。鼓舞表演者来源广泛,可以是爱好打鼓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是从事主持祭祀活动的苗法师,各个村寨都有擅长打鼓者,在制度层面,没有对其身份的合法性认定,甚至缺乏稳定的师承机制。据第二代鼓王石顺明和民间学者施云生介绍,民间传说有“放蛊婆”会借教鼓之机放蛊害人,所以新中国成立前,苗族人打鼓不拜师,会打鼓的鼓手也不愿意带徒弟。爱好打鼓的年轻人既可以跟随自己喜爱的多位鼓手学习,也可以自己琢磨、发挥,好的鼓手往往都有自己的自创击鼓技法和舞蹈风格。鼓谱也从来都是口传心记,当面传授,从未有纸面记录,所以,苗族鼓舞技法极为丰富多样,每个村寨都有每个村寨的风格,每个鼓手都有每个鼓手的特点,但是,是否有“鼓王”这一称号,并不可考。
第一个被正式命名为“鼓王”的人是湘西人石顺明。石顺明,1949 年出生,幼年从母亲处习得苗鼓,小学毕业后考入吉首戏剧学校,学戏 4 年,之后被分配到吉首市文化馆工作。石顺明将戏曲艺术融入鼓舞表演,尤其是将京剧中“刀马旦”的武术动作结合击鼓,如翻腰、平转身、点翻身、倒踢紫金冠、劈叉和下板腰等,使女性表演者显得轻盈活泼,婀娜多姿,创造性地为苗族鼓舞表演增加了观赏性。1986年,石顺明在新疆乌鲁木齐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鼓舞比赛冠军,国家体委授予全国“苗族鼓王”的正式称号,继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吉首市也向她颁发正式的“苗族鼓王”荣誉证书,至此,“鼓王”这一称号形成了“文本”记录,并具有了官方色彩。
然而,在湘西,石顺明被称为“第二代”鼓王,第一代鼓王是年长石顺明 20 岁,曾被毛泽东称为“鼓王”的湘西女鼓手龙英棠。龙英棠,1928 年出生,她小时候见过很多传统苗族仪式,如“吃牛合鼓”(椎牛祭) 上苗鼓手的表演,耳濡目染,迷上跳鼓,成长为当地数一数二的苗鼓手。新中国成立后,龙英棠参加了乡办的农村俱乐部,到各村寨演出,深受欢迎。1957 年,龙英棠被新成立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点名,调至省城,随湖南省歌舞团赴北京参加少数民族文艺汇报演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首长进行专场演出,毛泽东在接见时亲切称呼龙英棠为“鼓王”。这一称号虽然是毛泽东随口叫出,但深具政治意涵,当官方的“鼓王”称号颁发给石顺明之后,龙英棠顺理成章地被追认为“第一代鼓王”。
“第三代鼓王”龙菊兰,与石顺明一样,通过参加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获奖,1994 年被政府正式授予“鼓王”称号。时隔 8 年,2002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治州人民政府、湖南省民委在德夯景区举办“中国苗鼓节”,当时在德夯旅游公司当演员的龙菊献参加了“鼓王选拔”的比赛,一举夺魁,争夺到第四代鼓王的称号。至此,“德夯旅游公司”接替了政府,成为选拔和认定“鼓王”的合法性代表。第五代鼓王黄娟及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第六代鼓王杨欣,都是通过“鼓王争霸”的比赛,获得“鼓王”称号。
第一、二代鼓王的认定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鼓王”称号所带来的荣誉感极为强烈,鼓王身份认知伴随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石顺明年逾花甲,仍在自己开办的“讲习所”里坚持第一线教学,按照她自己的话说,“以前我的舞台是赛场,现在我的舞台是讲台”,石顺明喜欢别人叫她为“石老师”,认为这是对她最恰当的评价。而第四代鼓王之后,政府不再负责对鼓王身份的认定工作,“鼓王”只是德夯景区民俗表演中的一个角色,第四代鼓王和第六代鼓王都自认为是“一个普通演员”,她们不善言辞,跟笔者交谈时常常表示没啥好说的,对未来的预期也仅仅是能在跳不动的时候,公司安排点轻松的工作。
2. 苗鼓舞知识体系的积累。在德夯,笔者发现德夯苗鼓舞表演痕迹太重,就想了解“传统”打法,但是,谁也说不出“传统”到底是什么。根据矮寨镇文化站站长施云生所说,苗鼓打法并“无一定之规”。施云生说: “解放前,苗鼓表演没有一定之规,大家都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体会边击边舞,技法有的来源于道教驱鬼降魔的法式动作,有的来源于生产生活的常见动作,在现场,鼓手即兴发挥的情况也很常见。可以说,每一个鼓手都有一套技艺,第一代鼓王龙英棠的鼓舞动作选择,严格按照劳作中具体事件的实际过程编排,忠实于劳作本体和逻辑顺序,击打鼓面的节奏实且稳,并跟随情绪有轻重快慢的调节,如同说话一样,舞蹈过程中,她的关注点始终在鼓面上,动作讲究与鼓的对话、合一。”
第二代鼓王石顺明对于苗族鼓舞的改造最具突破性。石顺明是学戏剧出身,本身具备舞蹈功底,在她看来,“本来苗鼓的动作就是比较传统的,东一点西一点,没有成套,那时候(20 世纪 80 年代) 就有一些老师、领导,(如) 省体委的吴主任就找了几个会跳舞会打鼓的人包括我,(来) 编舞,把生产动作编出来。纺线怎么纺,我们穿衣服、吃饭是哪里来的,不能忘,打粑粑怎么打,插秧怎么插,都不能忘,就按那些把它编出来。然后把它变好看,加舞蹈动作。我是学戏剧的,有舞蹈基础,所以加舞蹈技巧对我来说容易。各地(鼓舞动作、鼓点) 还是会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嘛。”
石顺明的花鼓舞加入了很多舞蹈动作,如圆场步、梭步,还加入了鹞子翻身等京剧动作。从她开始,湘西苗族花鼓舞在龙英堂一辈的“传统鼓”上变得更加具有视觉效果,大大增强了苗鼓舞的观赏性。
在石顺明看来,“(第一代鼓王龙英棠) 她那个不好看,站在那里打,手动,过来甩一下,跟男的打的一样,不好看。我不喜欢她的动作。女的就是要打女的动作,男的打男的动作。以前祭祀里打鼓啊,随便打,想打什么动作就打什么动作,像椎牛祭就有打鼓,有唱苗歌,热闹,能把牛鬼赶跑(就是目的) ”,而石顺明则喜欢“自己想动作、想鼓点”。
2009 年,她被认定为苗族鼓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此后,她创办了个人的苗鼓传习所,参与到德夯景区民俗文化表演的鼓舞部分的整个编排过程,并多次参与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比赛。石顺明对于鼓舞动作编排力求整齐、有力,参照武术比赛的动作要求,不仅将一些武术动作融入鼓舞表演中,而且对很多动作都进行了标准化要求和处理,如鼓手站位应距离鼓面多少距离,鼓槌击鼓时与鼓面保持多少度的斜角,抬手的高度要距离头顶多高等,都形成了标准化要求。在石顺明参与编写的《湘西苗族鼓舞项目介绍》中,就对包括鼓槌拿法在内的击鼓技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如“击鼓时,手拿鼓槌末端,用鼓棒顶端击打鼓面。击打鼓面手法有多种,如: 反腕、横击、竖打、斜砍、上提等。无论哪种击法,鼓棒顶端与鼓面所成夹角一般为 30°—45°之间”等。石顺明创办的苗鼓传习所至今已经招收了近千名学员,他们学习鼓舞表演之前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舞蹈功底,如劈叉、下腰,强化身体的柔韧性,使鼓手在表演时能够尽情地舒展身体,增加观赏性。
3. 苗鼓舞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石顺明所进行的标准化工作只是为了将苗鼓表演的观赏性提高到一个层次,却并没有使表演模式固定下来,后几代鼓王都并没有向石顺明正式拜师学艺,而是通过自己努力,不断在表演实践中探索和积累新的表演技艺。第六代鼓王杨欣,19 岁就到德夯旅游公司上班,多年来参加鼓舞表演,从最开始的群众演员打起,她不仅苦练技艺,而且还不断增加鼓舞的难度,独创了许多高难度击鼓动作,如她可以在《团圆鼓》演奏中连续旋转 12 圈,边旋转边击鼓,突破了既往的击鼓模式。这种不断创新的动力,首先源于鼓手对于鼓舞本身的热爱,其次源于观众的观赏需求。从第三代鼓王开始,获得鼓王称号的鼓手直接与湖南省吉首德夯旅游实业有限公司签约,担任德夯景区民俗表演的主演,鼓王们几乎每天都要上台表演,直接与观众互动,为了增加观赏性,吸引游客,鼓舞的难度必须考虑在内。
几乎每天,德夯景区都会进行“苗鼓”表演,演出分为出场、中间和高潮部分,高潮部分《庆丰收》是每个舞者加入技巧自由发挥的地方,也是最精彩的一段。后来这一部分中的女子单人花鼓舞就由通过公司组织选拔的“鼓王”担任,他们将动作进行舞蹈化调整,同时用鼓点的变化来配合调整,每个鼓点基本的套路是固定的,但是舞蹈动作则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尽力发挥,使其变得更丰富、耐看。在景区演出已将近 12 年的杨欣跟笔者说: “我们虽然只是在景区表演,但是也是演员,来看表演的都是外面的游客,他们见多识广,喜欢看高难度表演,表演没有难度,就没意思,吸引不了人,我经常会从电视里面看人家演出,有好的舞蹈动作就借鉴过来。”
在湘西,德夯苗鼓舞已经成为精致化的代表,这引发了人们对于苗鼓舞的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比较普遍,认为这种打法好看,吸引人。第二种看法来自于当地的知识精英,他们认为对苗鼓舞的过分加工和改造,使苗鼓舞失去了原有的古朴味道,尤其在民间仪式上,苗鼓舞越来越少地被运用,这种与信仰脱节的单纯技术展示会使苗鼓舞精髓流失殆尽。然而,德夯之外的其他苗寨并没有因为德夯过于高难度的苗鼓舞表演而停止对苗鼓舞的喜爱,德夯的标准化也没有统一其他地方,跟以前一样,每一区域的苗寨自有自己的特点。随着地方民间宗教的复兴,苗鼓舞的祭祀功能也在苗族法师们的手中被重新发掘。湘西苗鼓舞一直没有停止以多元化的样态进行展演。
四、分析与总结
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是传统假借文本为化身游走于、飘荡于个体之间,而是由于人的主观选择,传统才能延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基于知识生产而非知识保存的角度研究“非遗”,通过对传承者个人生命史的展现,呈现文化事项得以伸展的生活、社会、文化语境(context) ,关注文化事项在每代传承者生命中的实践,将传承者的个人风格、经验、际遇等纳入分析维度。在对苗鼓舞的个案呈现中,笔者有了如下发现。
1. 个体通过实践来突破“非遗”的结构张力
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鼓舞的生成、传承、保存、创新都不是在封闭的框架内进行的,而是要面临着政治、时代、制度、市场、文化等复杂语境的考验,而文化遗产与语境的遭遇则是通过传承人来实现。在鼓王们的实践过程中,苗鼓舞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她们一方面通过学习表演苗鼓舞,接纳和传承着其所沉淀下的既定文本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内涵,体现着苗鼓舞知识体系结构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鼓王们通过一次次的表演,让苗鼓舞获得了新的阐释,赋予着苗鼓舞新的知识内容,突破了苗鼓舞的结构张力,体现着表演者能动性的一面。传承人的个性、技艺、禀赋、家传、兴趣、际遇对文化遗产的表达又不无刻印着个人的痕迹。
2. 知识结构对于个人能动性的规范
民间艺术必须拥有一种结构的稳定性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甚至说,标准化是美的前提。“只要产生出定型的动作、连续的声调或一定的形态,这些本身就会形成一种标准,用来衡量它的完善亦即它的美的程度。”
不同场域的不同要求被稳定为一种表达的规范,作为传承者,她的能动性必须要与身处的社会场域达到契合,才能够作为法定的传承人得以接受。正如杨欣在教笔者打鼓时不断地重复,“(手) 应该这样”、“(脚) 应该那样”……,这一系列的“应该”就是传承者对于结构的主动认知。
综上所述,苗族“鼓王”们将个人体验置身于技艺表达中,又融合了各自身处的时代和地方场域的经验,是她们用一场场的实践,将苗族鼓舞这一“非遗”变成“复数”格式。在与她们的交流过程中,笔者才真正领悟到文化知识生产的内在肌理及其必然性,也就是说,鼓王们扮演着属于她们自己的鼓王角色,并基于个性,创造性地发挥这一角色赋予的积极体验,建立她们在生活世界中的独有位置,成为了拥有创造性、主体能动性的生产者。
参考文献:
[1] 高丙中. 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 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J]. 民间文化论坛,2006(3) .
[2] 赵万里. 生成图式与反思理性解析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J]. 社会,2012(2) .
[3] 刘金吾.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鼓文化[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1) .
[4] 陈蕾.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湘西苗族鼓舞探究[D].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 理查德·鲍曼.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 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 弗朗兹·博厄斯. 原始艺术[M]. 金辉,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