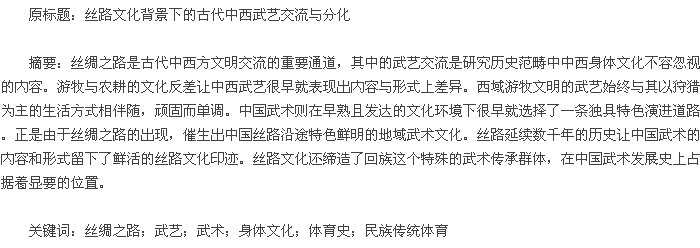
丝路即丝绸之路,它是古代连接中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因由东方中国向西部诸地输送特产丝绸而享誉世界。西域,古代用作泛指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它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聚集地。在古代有限的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使东西方之间有了物质贸易和往来,也让众多原本封闭的文化空间获得了相互沟通和认识的机会。在这条纵横万里的陆地长廊上,来自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系的数百个民族有政治的对话,军事的冲撞,经济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动。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的音乐、绘画、舞蹈、体育等研究时有见闻,然而从武艺这一古老身体运动文化入手的研究极为少见。其实,在古代中国与西域文明的碰撞中,武艺的踪迹曾经十分明显,仔细考察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西方武艺发展态势,既能清楚认识到古代中国与西域在文化上存在的本质差异,也能合理解释此后中国武术最终定型的文化动因。本文将就丝绸之路的历史流变对古代范畴的“中西”即中原与西域武艺的交流与分化做尝试性探究,试图解析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历程对中国武术的形成与演进所产生的影响。
1马战与地斗---文化反差下的古代中西武艺
中国古来曾多次对西域朝廷经略,“保有此地,除了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贡物外,还便于攻略中国内地”.丝绸之路开辟的最初原因是要打开阻隔在中国与西域之间自由交往的障碍。这一障碍从国别的角度看是不同地域间的国与国的政权隔阂,从文明差异的角度看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历史早期的相互抵牾。
秦汉时期,横亘在中西交通上的游牧民族政权极其繁多,其中尤以匈奴最为着名。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实现部落前所未有的统一。匈奴先后征服大月氏、楼兰等二十多个西域小国,并占领了中原王朝的河套地区[2].这个后来被欧洲人惊叹为“上帝之鞭”的民族“尽为甲骑”,“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他们垂涎早熟的农耕文明之富足,一心南下以牧马。自此,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间的军事对抗接连不断。在双方的冲突中,文化差异表现在武艺上的对比差别十分明显。汉政治家晁错曾有精辟分析:“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远及疏,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不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交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农耕民族在马战、骑射上与匈奴人相比劣势尽显。但是他们擅长构造劲弩、长戟等装备,强于战阵的布置,而且士兵掌握有“剑戟交接,去就相薄”的长技。此处的中原长技显然与游牧骑射有很大不同,它应是早期的武术,与荀子所言的“齐之技击”(《荀子·议兵》)当属同类。体格相形弱小的农耕汉人为了应对强悍野蛮游牧人的入侵,发挥动作灵活、武艺纯熟的特点。撇马战为地斗,这是汉人先辈战略的精妙之道,也是“技术反映文化,文化影响技术”原则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真实体现,也应当是引导早期中国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
2胡人善扑---政治博弈背后的身体文化交流
自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与西域间在各个层面的交流日增。汉代称西域人为“胡人”.据吕思勉先生考证:“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 异者,兴 以 是称焉。”[5]
古代史籍中不乏“胡人善扑”的描写,其中可以找到胡人与汉人身体文化交流的凭证。据许多记载看,胡人在赤身肉搏的武艺造诣上水平不低。《汉书·金日磾传》记载,马何罗入宫刺杀汉武帝,“日磾得抱何罗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6].金日磾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后流落到汉室为武帝所重。
“捽胡”被认为是勾扭颈项的摔打动作,胡人金日磾无疑是摔跤能手。《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载,南阳王高绰深得北齐后主宠爱,后绰被告谋反,“后主不忍显戮,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7]
何猥萨也是善扑之胡人。《续高僧传·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是提到,时任信州刺史的綦母怀文曾评论蠕蠕客“此所知当与角伎赌马[8]”.蠕蠕客即是柔然人,当时西域诸胡之一。怀文言语虽轻薄,却可看出柔然人当时多精于角力的事实。生长于西域游牧环境下的胡人多以肉食为主,体形高大、力量惊人,摔跤角力的能力强于中原汉人实属正常。
正是由于胡人体格矫健、勇猛难敌,汉人常以与胡人角力获胜为殊荣,并上升到极高的政治高度。《晋书·庾阐传》中称“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庾阐之父庾东“以力勇闻”,“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9]
《续高僧传·唐京师法海寺释法通传》中记隋文帝时,“有西蕃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敌者。文帝患之,诏通令与胡人角力。”[10]后法通赢下大壮后,“举朝称庆”.《云溪友议》所载,李绅在督大梁时挑选和考核镇海军所进“悉能拔撅角抵之戏”的四名健卒富苍龙、沈万石、冯五千、钱子涛,其目的居然是“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胡丑夷”[11].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解读出自汉代始,西域胡人与汉人间的身体交流并不少见。庾东、释法通因扑杀胡人受到褒奖,李绅选拔健卒以应对西胡,东西武艺对抗的背后有着极强的政治动机---在胡汉相争的立场上,除在战场上与胡人争斗以取胜为目的外,个体的较量中也要能以武力战胜对手。因为体形、力量上总体处于劣势,中原汉人要想在单个比试中赢取胡人,精研武术是其必要途径。有学者指出,丝路沿线“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当地各民族形成一种强悍、勇猛、好武的习性,构成了武术发展极其紧密的文化渊源关系”[12].
3停留与演进---文化差异造就中西武艺分化
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令游牧与农耕政权为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始终保持时战时和的局面,这条贯通东西的通道也处于时断时续的态势。隋唐时期通过征伐突厥曾保证丝路的长期通畅,但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要道,东西交通一度受阻。加之隋唐航海技术提高,海上丝路兴起,陆上道路地位日颓。此后的五代政权割据严重,宋代经营西域能力有限,丝绸之路虽然存在,但其影响力大不如前[13].在此期间内,交流的减少造成中西间武艺上的分化。自宋代开始,在空前繁荣的商业经济背景里,不但军事武艺继续精进,民间武艺形式如相扑、角抵等形势大好,勾栏瓦舍中还出现了“与相扑曲折相反”的“使拳”即“套子武术”.(《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使》)武术套路被认为是“中华武术集中体现的活动形式”,古代中国武术逐步走向成熟期[14].而与其同时,西域各地的游牧政权虽更迭交替,但游猎习性与农耕民族仍然不尽相同。以战马创造的机动性为作战基石的游牧人,“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武技文化多凝固于弓箭和马刀之上。即使是下马地斗,仰仗体力的徒手角力也是主体,远不及中原农耕武艺丰富。
元代的建立是古代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第一次彻底的胜利。蒙古勃兴后在掌控中原前已举族西侵荡平了西域。同在蒙古势力范围之内,东土至西域畅通无阻,丝绸之路再度激活,但是极端的民族政策和复杂的社会局势令中西武艺间的分化从此更为严重。一方面,同为马背民族的生活习性让蒙古时期的东方与西方在武艺上的公开对抗多表现为摔跤比赛。如《多桑蒙古史》中窝阔台和部将伊勒赤歹互相选派力士比拼摔跤:“翌日,伊勒赤歹以其队中一人至,与比烈角力。
二人相扑时,蒙古力士投比烈于地。比烈曰:‘坚持我,否则我将脱身而起。’语甫毕,亟反执蒙古力士而投之地。用力巨,闻骨骼相触声。”[15]比烈是来自西域的波斯人,他与蒙古人的比拼竞力成分大于竞技,与武术的精彩纷呈相比相去甚远。
而另一方面,随着元代官方的禁武法令,汉人公开习武受限,缺少宽松环境却已具有相当基础的武术的习练和传承被迫转入地下状态。武术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下的秘密传承是造就武术形成众多门派的社会动因[16].武术门派的大量出现则又被认为是“中国武术最突出、外显的文化现象”[17].蒙元禁武效果虽是有限,但自此之后的中国武术转变极大,除在技术上更为精进和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外,在武术的内涵上更彰显中国文化特点,直至明清时期呈现繁荣之势,定型为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
4遗产和见证---丝路文化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4.1催生出鲜明的地域武术文化
地域武术文化是当前中国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由于承认构成文化的元素如器物、制度、精神等各层面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因而认为武术以及对武术有影响的诸多文化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永久性的整体,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特征[18].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比今天的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更大[19].丝绸之路串联的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类型风格迥异,它们之间的文化对碰激烈而长远。大漠草原与农田水乡孕育的文明在对接时必然被迫做出多重应激反应。这表现在身体文化上的就是催生出了丝路沿途较强的地域武术文化形态。
唐代李筌《太白阴经》中总结有“秦人劲”、“崆峒之人武”、“凉陇之人勇”等地域居民个性特征,认为此乃“地势所生,人气所受”[20].此处影响秦、崆峒、凉陇等地的地势、人气与丝绸之路所处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应该密不可分。离丝绸之路越近的地域,生活于其间的民众群体感受到的文化差别更为直接。从生存角度出发,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为应对异族的侵扰,争夺必要的生存空间,习武自保、击退强敌是必要之举,勇猛善武正是环境逼迫使然。此外,武术谚语云“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为何西方以棍术最为突出?有学者言:棍术之发达与兵战之中应对北方游牧的重甲骑兵有极大关联。《北史·尔朱荣传》中所论“人马逼战,刀不如棍”便是例证[21].直到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的棍术内容仍以内容丰富、风格独特而着称,其原因被归属于古代战场的锤炼和丝绸之路文明的影响[22].所以说棍术之所以在西北地区相当普遍和繁盛,这本身就是丝绸之路文明给武术留下的地域历史文化印迹。
4.2丰富了武术的内容和形式
文化的交往是相互的,丝绸之路给中国武术带来的外部元素并不罕见。相扑是我国古代摔跤名目之一,但相扑出现与丝绸之路有极深渊源。朱庆之先生在《相扑语源考》一文中论证最早记有“相扑”名称的文献是在东汉竺大力与康孟详所译《修行本起经》卷上之中:“……调达到场,扑众力士,莫能当者,诸名勇力,皆为摧辱。王问其仆:‘谁为胜者?’答言:‘调达。’王告难陀:‘汝与调达二人相扑。’难陀爱教,即扑调达,顿辟闷绝。以水灌之,有许多乃稣。王复问言:‘谁为胜者?'
其仆答言:’难陀得胜。‘”此外,他还列举了东汉失译的《兴起行经》、东汉支谶译的《杂譬喻经》和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等佛经的大量事例来说明,按汉译佛经之一般规律,原典中所指某物若中印皆有的,汉语也取相应表达方式。若译者语言系统中没有表达方式,他们会选择新造、音译或意译。因而,“相扑”一词并非汉语固有,而是来源于印度古代一种搏击术[23].我国最早的佛经从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已是人所共知,竺大力、康孟详、支谶等着名译经者也多是西域僧人。如若“相扑”词源由印度循丝绸之路东来的推断不误的话,那么盛行于唐宋的相扑中极有可能沾染有西域身体文化的痕迹。
前文已经论及棍术兴盛缘起于丝路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其实在游牧骑兵隳突南北之时,他们创造过许多用于战阵的武器,后来保留并传袭为今日的武术器械。一个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连枷棍。《武经总要》中载:“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连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武经总要·前集·器图》)连枷本为游牧骑兵创始,配合战马奔驰击杀敌人。但之后很快被汉人接受和练习,以至“善用者巧于戎人”.
明清之时,连枷已成为军队装备之一,后又演化为当今风靡全球的双节棍。在元、明、清三代的军旅武艺中米昔刀曾占一席之地,它来自于埃及,元代时便见于史籍,其传入途径也应是丝绸之路。因为史籍中有关西域人携刀剑入贡的记载不在少数[24].其他如脱胎于敲棒的狼牙棒和至今仍流行于西北的鞭杆等武械都是丝路文化背景下传入并保留的,中国武术的内容与形式由此得到了丰富。
4.3造就了独特的武术传承群体
丝路通达后,大批西域胡人往来其间。隋唐时期,成规模的来自于波斯、中亚等地的胡人侨居于汉地。这些阿拉伯、波斯族系为主体的“蕃客”兼容吸收了蒙、汉、维、藏、傣、白等民族,以伊斯兰为强有力核心而凝结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四夷馆考》云:“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在丝路文化环境中,回民先民未入中原前便容身西域,服役于多个军事集团。蒙古西征后,回民因勇武善战被编入“探马赤军”、“回回亲军”之中,成为蒙古治下重要军事力量。军事需求、宗教信仰、聚坊而居的习俗及民族特殊行业等因素,形成回民尚武的风气[25].许多长期效力军旅回民后又流落民间,但族群对于武术的研习和传承之习俗始终未变,历经元、明、清,一起到民国和现当代。后世回民群体中创编出了六合心意拳、查拳、八极拳、六合大枪、天启棍等诸多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拳械武艺,同时诞生出大量彪炳史册的军事武将和一大批对武术传播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武术家、摔跤家。从某种意义上,回族是丝绸之路造就的民族,因而也可以说这一特殊的武术传承群体的出现也得益于丝绸之路特殊文化背景的熏陶和孕育。
5结语
从丝绸之路的开拓和贯通历程中,来自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体系的各民族文化交汇、对话、融合,政治、军事、宗教等外部因素的参与,让中原与西域武艺因文化的反差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西域游牧文明的武艺始终与其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相伴随,简洁实用,却又顽固单调。中国武术则在早熟且发达的文化环境下很早就选择了一条独具特色演进道路,强调自身特长的发挥,注重个体极限的延伸,产生出大量凝结有中国文化本质特点的外显特征。然而,由于丝路文化的出现,催生出中国丝路沿途特色鲜明的地域武术文化。丝路延续数千年的历史让中国武术的内容和形式中留下了鲜活的丝路文化印迹。丝路文化还缔造了回族这个武术传承群体,让中国武术绚烂的篇章里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设想已经提出,经济的发展应当以文化为先导,丝路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必将成为一个研究重心。武艺是古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兵器和相关武艺的交流同样是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26].我们今天可以从丝绸之路上曾经辉煌一度的敦煌发现的壁画中识别出大量体现武术特征的图像,分辨其中的徒搏、武舞、剑术等等多姿的武艺形式,这是中西武艺交流不容轻视的史实依据。可是,古代中西间的武艺交流畛域与影响意义决非此一斑可窥,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地探究其中的奥妙,希望能为今后丝路文化发展做出更有价值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耿世民,译。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出版社,1981:1-2.
[2]张一平。丝绸之路[M].北京:五洲出版社,2005:17.
[3]《晁错集》注释组。晁错集注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5.
[4]张胜利,郭志禹。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模式构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5(4):73-77.
[5]吕思勉。吕思勉说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7.
[6]班固。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4:2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