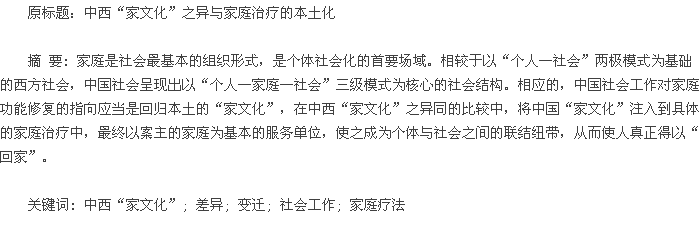
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引介过程中,中国学者已经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西方之所学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境与经验方可对症下药,有所疗效。在这种共识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在诸多学人的努力下不断发展与完善。其中,对家庭疗法的反思与改造成为这一趋势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新取向,而这种尝试往往失之于两端而阐之未尽,这关键在于文化自觉与技术理性两者之间的区隔,这种断裂与张力需要在明晰中西家庭文化之异的基础上,与家庭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形成相应对话,在统一文本下达成融合。
一、中西“家文化”之异———动静结合的变迁视角
在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个共通的困惑,为什么已被西方社会认同并发挥功效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具体问题时却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甚至有的时候陷入某种伦理困境。技术论者将其归因为没有得其精髓,当新生的社会工作者面对浩若烟海的西方社会工作文献时,其庞大、严谨的话语体系很容易征服草创之初正寻求发展路径的探索者。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为止,有些社会工作者还在复制西方社会工作疗法,将其贯彻于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中。当然,其基础作用对于以后社会工作的开拓具有重大意义,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对此反思的时间拐点,并不是截然的抛弃,而是有所扬弃的融合。
( 一) 考察中西“家文化”之异的路径选择
在田毅鹏先生看来,中西家庭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融合要建立在中西社会结构之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相对于西方‘个人—社会’的两极思维模式,中国社会明显呈现出‘个人—家庭—社会’的三维思维模式,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必须结合其独特的家文化,衍生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在中国推行和发展的社会工作本土理念和操作模式,而不能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
[1]这种理念既解释了社会工作本土化困境的核心之处,又提出了破解之道在于中国独特的家文化对于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注入。但是,在西方家庭疗法方兴未艾的当下,这一观点面临着挑战: 一是西方社会工作者也是在强调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上,发展了蔚为大观的家庭疗法理论流派; 二是如果说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不在于对家庭功能的忽视,那么应当是更深层次的不同,也就是需要指出中西家文化到底有何不同。沿着这一思路,有些学者的概括与总结可以部分地填补这一空缺。他们认为,从家庭的结构出发,中国人更在乎家庭的整合作用,即家庭的完整性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非常重要,西方则强调个人的满足感和个性的发展; 从代际关系来看,中国家庭强调“和合”与等级,要求下一代完全顺从上一代,以服从为标准,只有做到完全认同才称作是“孝”,西方家庭则立足培养孩子独立的精神,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对待儿童,以便形成“人格平等”的氛围;[2]从家庭与社会工作治疗的关系着眼,中国家庭排斥“外人”介入,家庭冲突是隐匿于和谐幸福的表象之内的,而西方家庭是勇于自我批评并主动向外寻求帮助的,与社会工作治疗在内在驱动力上有天然的契合。
[3]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难免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但其目的是为了凸显中西家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所引发的社会工作实践问题是他们更为关注的,例如,对婚姻问题的介入,发现的确是使得案主的自我意识加强了,但最终结果是婚姻解体,社会工作者陷入了“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自责中。所以,他们在伦理困境中,将问题指向中西家文化的差异。但相比这一非常有益的问题意识来说,这种对于中西家文化的划分还是有缺憾之处。
首先是,姑且不论缺乏动态的视角是否全面,这种静态中西“家文化”的差异性比较缺乏一定层次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家文化”的片面认识,会将家文化的表层现象与内在机理混为一谈,在成为人们不言自明的存在之时,中西家文化的不同与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勾连缺失具体的结点。更为重要的是,家文化的变迁需要予以一定的考量。一方面,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变动不居的,家文化的概括不仅有其传统沉淀,也有其面对社会的发展自我不断的文化调适,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家庭疗法对于中国家庭问题的介入有其应用的可能,因为很多家庭冲突是西方家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另一方面,家庭是有生命周期的,在家庭的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的各个阶段家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家文化在家庭不同的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所以,在文化变迁的视角下,中西“家文化”之异需要在纵横结合的考察下予以界定。
( 二) 结构与变迁视角下的中西“家文化”之异
在论述“何谓东方文化之所有、西方文化之所无”时,杨效斯将东西“家文化”的差异隐喻在这样的话语中: “西方人要家更多地是为了社会。孩子在家,被个人化、社会化。在家更是为了离家,生活更是为了工作,夜晚更是为了白天。对东亚人,则出外是为了家内。孩子在家,被家庭化。于是,出门更是为了回家,工作更是为了生活,白天更是为了夜晚。”
[4]可以说,中国家文化在传统的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梁漱溟先生曾说: “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
[5]那么何谓“家文化”? 一些学者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这种结构很清晰,但会缺失“家文化”对行为规范的强调。行为规范的内化对于家庭成员尤为重要,所以,笔者根据广义的文化观,将“家文化”分为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与物质产品三个层面[6]。价值理念层面的“家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心理上所共同理解和接受的,并能广泛传播的象征符号和意义体系,是用来建构人们的经验和知觉的伦理价值与道德规范,是家庭成员心理结构的表征,对家庭成员具有价值取向上的制约与引导功能; 生活方式层面的“家文化”是指那些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和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是成员间双方的参与,是家庭成员关系结构的表征,这部分是“家文化”的核心,是其价值理念的行动体现以及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对家庭成员具有行为上的规范与精神上的激励功能; 物质产品层面的“家文化”是指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的物质空间、依赖的物质基础与生产出的物质成果,是一种家庭成员周围的环境结构,发挥着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与提高家庭成员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功能。
在厘定家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家文化”变迁关注家庭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所体现的文化特质,同时,将其纳入历史演进的范畴中进行讨论。所以,对中国“家文化”的深层理解将以西方“家文化”为参照谱系,从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这样六个阶段展开,围绕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从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与物质产品三个层次考察“家文化”变迁。当然,对中西“家文化”差异的关注消解了文化相互渗透的共性,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家文化”面临的时代冲击。
1. 家庭的形成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学会独处和共处、分配权力、聚集物质和情感资源、过性生活、共享亲密和平常的感情,对此,西方“家文化”的价值理念是夫妻双方都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我们”中的一部分而没有牺牲“自我”,即保持自我的独立和自主; 生活方式是给予对方足够的自由,保持各自的隐私空间; 家庭产品有明晰的夫妻所属。在这一阶段,中国传统“家文化”的价值理念是“夫唱妇随”“男主外、女主内”; 生活方式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同时,需要长幼有序地适应对方的亲属关系;物质产品层面关注的是成家立业,男方应当作为主力营建爱巢,为孩子的出生做准备。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家文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女性主义的崛起使传统家庭夫妻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2. 家庭的扩展与稳定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孩子的到来,夫妻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孩子成长以及自身事业的发展。中西“家文化”之异在价值观念上体现在: 前者强调家庭本位,“一屋不扫,何以平天下”,家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安身立命之本,是最初之地也是最终归宿。后者强调个人本位,家庭的社会化是为了脱离家庭,从而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成为独立自主个体。在不同价值观念下,中国“家文化”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重视家教、家规。这在中国古代的家训里有充分的体现,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王守仁家训等等。这种家训是家庭经验的凝结与传承,相比生活技能的教育,更在乎道德主体的养成。一言一行,皆有深意,如“克己复礼为仁、入则孝出则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仁义礼智信”是教育子女的最高境界。西方“家文化”则推崇父母于子女间交往的自由与平等,认为每个家庭成员不论长幼,都可以享有家庭主人的地位与权力,对子女的教育相比中国“天人合一”的道德主体,更在乎的是“征服自然”的理性逻辑。体现在物质产品上,中国“家文化”对于私人房产的购置是将家作为归宿来打造,而西方对于房屋的租赁取向则体现了家庭被认为是社会化过度的驿站。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生育观的变化,这一阶段的中国“家文化”对于子女教育也需要变通,融入新观念,如“父母在家庭化孩子时,孩子也在家庭化父母”等等。
3. 家庭收缩、空巢与解体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家庭成员的离开,对此,中国“家文化”的价值理念是“养儿防老”,这种反哺文化观在于以前阶段的“父母有亲”,对子女的养育贯穿生命的始终,而非西方“家文化”终结于子女的独立养成,这也是为何西方“家文化”在这一阶段的价值理念是“孤独为美,尽享生活”。没有谋生的忙碌,远离了社会竞争,他们认为可以平静地、自我地享受人生。这种差异,体现在中国则是老人认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与儿孙在一起,四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以儿孙为中心,儿孙的幸福就是他们的幸福。西方老人很少与子女共同生活,老年人格外重视自己人格的独立性,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把独处看成是一种独立的人格美。他们尽量回避来自城市、人群的喧嚣,有的甚至喜欢在没有人迹的山间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反而很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意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体现在物质产品上,中国“家文化”表现为对家庭老物件的珍爱,这里面凝结着对过往的回忆。西方“家文化”在乎对外部物质的追求,例如,老年人既愿意修剪、浇灌自家庭院的花草来打发时间,也喜欢去图书馆阅读,或者享受旅游的快乐,他们多数人有着宗教信仰,教堂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一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也被西方文化的洒脱所感染,在中国老年人中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 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
对“家文化”变迁的此种序列解读是一种尝试,其局限性在于对家文化变迁以线性思维展开,而针对各个家庭来说,更可能的是反复徘徊的螺旋上升。同时,阶段性表达指向的是主流、核心家庭的家文化发展,而对少数联合家庭、单亲家庭、重组家庭、丁克家庭等家文化的变迁历程则需要部分或全部重新诠释。但是,以核心家庭的“家文化”变迁为例,可以看出“家文化”这一绵延之流需要注入在具体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中,从而焕发其本土活力。因此,应当在个人、家庭、社会之间寻找平衡,不能一级独大,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之时,也不可否认夫妻双方对于家庭的忠诚与责任这一共性。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的理想境界,两千年“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是“家文化”超强生命力的明证,这种生命力在于对自身的改造与再生。
二、回归何种文化———家庭疗法的印记
对中西“家文化”之异的界定,在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复制于中国缘何水土不服的追问。这一问题,表面上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政策倡导,专业发展突飞猛进,民营社工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但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工作者之所学与所用发生了隔膜,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异质性,也就是说,无论何种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都是内生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反思,社会工作者的理论与实务应当回归何种文化? 以家庭治疗为例,这种回归在于对中国“家文化”的认知。
( 一) 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对象而实施的社会工作方法,协调家庭各成员间的人际关系,通过交流、扮演角色、建立联盟、达到认同等方式,对家庭各成员的个性、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改进其家庭功能,促进家庭成员的成长。家庭治疗的产生将心理问题的成因从“内心冲突”扩展到了家庭层面,20 世纪 50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是家庭治疗的探索期,70 年代出现了以米纽琴( Minuchin) 为代表的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80 年代则以策略式家庭治疗的发展为代表,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家庭治疗终于挑战了个体治疗的霸权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广开来。
[7]家庭治疗兴起于西方世界,带有西方“家文化”的印记,那么,家庭治疗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家庭问题? 答案是可行的。可行性在于其理论的前提预设是: 个人或家庭问题是由于家庭功能缺失所造成的,治疗的指向是修复或再造家庭功能。中西家庭治疗应用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回归何种社会认同的“家文化”。不对家庭的文化背景做具体分析就采取某种家庭疗法,很可能会陷入家庭治疗的技术神话,技术需要与“家文化”结合。那么,这种结合如何体现“家文化”的内嵌性? 这里以米纽琴的家庭疗法为例,通过一个具体案例予以展示。在此之前,需要明确这一疗法的基本理论预设与核心概念。
结构式家庭治疗法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就是: 个人问题和症状的产生是家庭结构缺失和结构不良、家庭功能失调导致的,对个人问题和症状的解释要在家庭交互作用的模式和背景中寻找。如果要解决个人的问题和症状,必须改变家庭结构和互动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家庭结构、家庭子系统、界限、权力、结盟和同盟。
( 二) 案例分析
对结构式家庭治疗核心概念的运用,笔者以曾经看到的一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体现家庭治疗技巧的文化面向。
1. 案例介绍
母亲年逾五十,城市人,年轻时因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边远山村,多年来返城无果,只能嫁给当地的农民,婚后育有一子一女。“文革”结束后,随着“知青回城潮”,丢下丈夫和儿子,将女儿带回城市。由于母亲没有一技之长,且较为懒惰,因此,一开始只能靠东拼西凑维持生计,但久而久之,因交往不慎,牵扯进入传销,并被传销所害,负债累累。女儿难以忍受贫寒,回到父亲家中。母亲因为传销外出躲债,债主便向父亲家讨债,使父亲一家很憎恨。母亲现在身患绝症,后悔当初的选择,想回到前夫家中度过最后的日子,并希望能葬入其家族的祖坟,但又担心自己不被原谅。
女儿现在三十岁,已经结婚,偶尔会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母女之间关系不好。当年女儿离开母亲时,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曾把女儿的书撕碎以示威胁,母女间发生过激烈冲突。女儿回到农村父亲家后,一次生病住院时,看到其他孩子都有母亲照顾而自己却没有,特别怨恨母亲的离开。但得知母亲病重,依然立刻赶到医院看望。父亲虽然对母亲回家的想法表示反对,但反对得不强烈,且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再婚,还存有感情。他认为自己没能给妻子富裕的生活,有些惭愧,也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母亲求助于社工,社工联系到父亲和女儿,他们同意和母亲一起来做家庭治疗。儿子因为母亲当年的离开而对女人有不正确的观念,导致婚姻不幸,对家庭治疗异常反对,不愿配合。[8]
2. 结构家庭分析
如果仅按照结构家庭的分析模式,对于此案例的一个经典分析范本是: 首先,如果把该家庭分为两个子系统,母亲处在一个子系统,父亲、儿子和女儿处在另一个子系统,则可以看到,这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一层较牢固的隔阂,对于一个健康的家庭,这样的隔阂是不应该存在的。母亲想打破这层隔阂,而父亲则想维持这层隔阂。打破隔阂是本家庭治疗的重点任务。从女儿对母亲病危时会立刻赶到医院、父亲没有再婚和他反对母亲回家的态度不是十分坚定等细节,可以看到打破隔阂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如果考察夫妻、母子、母女这三对关系的界线,则可看到夫妻、母女之间的封闭界线较容易转化为正常的渗透性界线,母子之间则隔阂较深。可尝试先打破夫妻、母女的隔阂,以此带动母子隔阂的消除。
再者,考虑家庭的角色与结构,这个家庭常年缺失母亲角色,虽然需要这个角色,但毕竟家庭对于此角色的缺失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习惯,或者是其他成员在分担着母亲角色的任务。现在如果重新接纳这一角色的加入,其他家庭成员的角色都需要有所改变,因此,帮助整个家庭适应新的结构也是应该重点关注的。
最后,对于联盟的考虑,现状是父亲、儿子和女儿联盟排斥母亲进入家庭,治疗时可能会出现母亲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社会工作师应考虑适当和母亲结盟,或是给予支持。
[8]基于以上的分析,对于这一案例的治疗准备使用拟剧表演的方式进行,但如何才能发挥结构家庭疗法的功用,这就需要“家文化”的注入,谨记“家内讲情先于讲理”。
3.“家文化”的注入
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这个家庭的问题贯穿于该家庭生命周期的始终。在家庭形成之际,需要夫妻二人学会独处和共处、分配权力、聚集物质和情感资源、过性生活、共享亲密和平常的感情。在本案例中,如果按照西方“家文化”强调夫妻个体自由的价值理念,妻子的做法没有错。但是,中国传统“家文化”的价值理念是夫唱妇随,生活方式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因此,女方抛弃家庭奔向自由,是被他人所鄙视的。另一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男方应当作为家庭主力营建爱巢,在这一点上,案例中的丈夫并没有做得很好。这样打破家庭结构已有平衡的关键在于夫妻二人角色的回忆以及自我认同评估,从而寻找消解矛盾的突破口。
家庭扩展与稳定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孩子成长。中国“家文化”是以“严父慈母”式的双重教育将社会规范、行为方式、生活技能通过潜移默化、说教等方式传承给儿童,使儿童逐渐获得知识和技能,掌握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发展成为一个合乎社会角色要求、被其所在的社会环境认可和接纳的人,从而满足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需求。而母亲的离去,对于尚处于幼年的儿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这也间接造成儿子的婚姻失败。但中国“家文化”与西方社会更注重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同,它也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生育之恩,这也许就是打开儿子心结的关键,社会工作师应当从此打开缺口,这也是为何母亲没有给予女儿很好的照顾,但女儿依旧在母亲最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
家庭收缩、空巢与解体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家庭成员的离开。中国“家文化”推崇的是“发小夫妻老来伴”,案主中丈夫与妻子再度联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社会工作师应当在对“剧本”的设计中将这一因素纳入脚本。同时,“百善孝为先”,中国“家文化”对于儿女的行为模式是有严格的规范,在“剧本”中应当加入社会舆论的天然压力。
三、结语: 家是目的,而非手段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域。相较于以“个人—社会”两极模式为基础的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呈现出以“个人—家庭—社会”三级模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家文化”源远流长,“家”的意义尤为深远。相应的,诸多失能或问题群体也正是源于“家文化”在某些层面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应当融入这一独特的“中国情境”,以案主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使之成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纽带,从而更好服务于社会建设。
诚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家庭在我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也需要清楚了解“家文化”带给社会工作服务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家文化”中注重私领域的“家丑不可外扬”等文化规则使许多本源性问题沉积,甚至隐匿,社会工作者的介入颇有难度; 另一方面,急剧的社会转型也使传统的“家文化”受到冲击,涌现出家庭结构多元化、家庭形态多样化等现象,这些新旧问题的交叠赋予了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新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努力在动静结合的视角下对中西“家文化”之异做了具体的界定,同时,尝试着将中国“家文化”注入到具体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中。
本文后续工作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的“家文化”建构、接续与传递等,通过服务失能案主,重建健康家庭,预防和消解本源问题,从而服务社会建设。最后,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家文化”在社会工作中运用的核心理念是“家是目的,而非手段”。
参考文献:
[1]田毅鹏,刘杰.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本土化[J]. 社会科学,2008( 5) .
[2]陈红莉. 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1) .
[3]舒敏,饶夏溦. 论结构家庭治疗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及其本土化途径[J]. 交流论坛,2007( 7) .
[4]笑思. 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11.
[5]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7:35.
[6]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
[7]赵芳. 家庭治疗的发展: 回顾与展望[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3) .
[8]家庭治疗案例[EB/OL]. 东方社工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