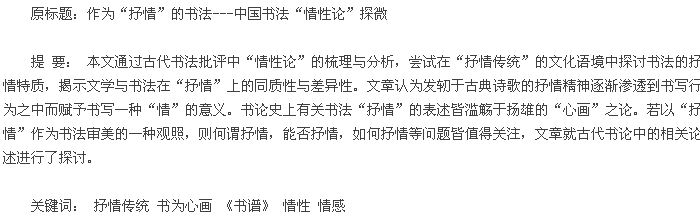
中国的“抒情”观念由来已久,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以来即有一个以“抒情诗”为主而形成的“抒情传统”.无论是中国诗论“诗言志”的开山纲领,还是“诗缘情”文学观念的演进,都以“抒情”为其核心思想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是“抒情传统”论述晚近以来逐渐成为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范式。① “抒情诗”之作为主导本是中国文学史的现象,但由此传统酝酿出来的“抒情精神”却无往不入,浸润深广,以致自古代雅乐以迄后来的书法、绘画等艺术皆有所体现。因此,在这一文学传统中来探讨古代书法理论对“抒情”观念的认识必能丰富我们对这一“抒情文化”的理解。
一
众所周知,书法是一门由汉字的书写而派生出来的艺术,但书法之成为艺术并非“古已有之”,汉代以前的历史文献还未将书法视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没有学者着文讨论其美学价值。正是在汉代,随着书体的演变和成熟以及当时书写工具、材料的改善,对汉字自身美感的体认逐渐从实际的用途中分离出来,汉字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尤其是东汉末期,文人书家的兴起、对书法理论的研讨,更是促使了书法走向艺术化的自觉时代。在此历史进程之中,对汉字形态美的发觉和对书法性质的思考是考量此“自觉意识”的两个重要因素。
对文字形态美的讨论在迄今可见的第一篇书论文献《草书势》中即有体现,崔瑗认为草书的笔画和字形较之篆隶更富于飞动变化的形态美,所谓“方不中矩,圆不副规; 抑左扬右,望之若欹”云云; 关于书法性质的思考,我们发现在早期学者的观念中作为一般书写、记录语言的文字与作为艺术的书法常常混杂在一起,并未有明晰的界定。例如西汉扬雄《法言·问神》中的一段论述虽不是专论书法,却常常被古今书家津津乐道而奉为论书的经典。其言曰: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着古昔之□□,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 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②在扬雄看来,人们通过“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和交流思想,“书”则记载古往今来的天下之事,由此可以沟通古今、联络四方。既然“言”和“书”都是人们心灵的表现,由此即可窥见人的内心世界,并据此来衡量品德的优劣,这就是着名的“心画说”.虽只有只言片语,却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尤须注意的是,扬雄在提出“心画”的同时亦指出语言文字的情感作用,所谓“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正契合了当时儒家诗论与乐论的观点。就诗论而言,“诗言志”的观念在汉代已不陌生,《诗大序》中有一段关于诗之本质的阐述为文学研究者所熟知: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大意是说“情”与“志”皆由心生,“情、志”的外化即有了诗之形式。所谓“情”、“志”,在传统儒家诗学话语中,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孔颖达谓: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是两者又各有侧重,“志”侧重合乎理性的意志,“情”则侧重发自本性的感情。近代学者方东美即认为,“心”既作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综合,可从“理”与“情”两方面来观察心所发泄的生命功能①。若从中国诗论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以“情”为诗之本质和动力的基本原则更为大家接受,由是抒情诗逐渐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②。正如后来文学与书法在诸多艺理上的互相借用、互相参透一样,《诗大序》中的这段论述亦不断被书论家提及。唐代孙过庭“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的表述,元代盛熙明“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于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的观点,等等,可以说都源自《诗大序》的诗学观念。由此,从抒情之“情”的生成意义而言,书之“情”与诗之“情”显然是同源的,既然诗书皆为表现心灵情性的艺术,那么,书法之“涵情”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自扬雄的“书为心画”之说始,历代书家在书写的实用意义之外,都颇为关注“书”与“心”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认识在不断的思考之中被强化成一种“书写我心”的观念。
如宋代朱长文《续书断》谓“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 ”即从颜真卿的书法中体会到“心画”的意义。清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则从训诂的角度论述了“画字”与“写字”的区别,以为两义兼备则为书法,而尤以“写心”为贵。其论曰:上世结绳而治,自伏羲画八卦,而文字兴焉。故前人作字,谓之画字。……后人不曰画字,而曰写字。写有二义: 《说文》“写,置物也。”《韵书》“写,输也”.置者,置物之形; 输者,输我之心。两义并不相悖,所以字为心画。若仅能置物之形,而不能输我之心 ,则画字、写字之义两失矣。③可见,书法于“置物之形”的“形学”之上,更是一种“输我之心”的“心学”.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明确了这种观点: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④与文学中“诗言志”的观念相关,刘氏又进一步将其推演为“书如其人”之说,认为书法亦可以“写志”,所谓: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即书法直接源自人的内心,书法作品的高下与作者的学识、才能、志趣密切相关。实际上,这已拓宽了扬雄“心画”之所指,不仅看重心的情感意义( 动情) ,而且注重从心的伦理意义( 写志) 来品评书法了。亦因此,由“心画”衍生出的“人品”观念一直是传统书法品评中衡量书法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书学发展史上,尽管后世论者对书法遣情达意性质的探讨见解纷纭,但都可以从扬雄这里寻到源头。简而言之,书法“抒情”之所以可能即因为书学乃是一种“心学”.我们知道,扬雄在学问上继承了儒家传统,提倡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其“心声心画”之说正是儒家“诗言志”文学观念的体现。因此,书法之“抒情”今天看似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但探本寻源,我们自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抒情文化”的背景与影响。
此外,“心画”说对书论的意义还在于,在早期书论关注字形体势之际,“心画”观念对书法美学关注创作主体心灵情感的理论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示。早期书论( 如崔瑗、蔡邕) 虽然对书法流露出来的情感特征着墨不多,但毕竟已经萌生“情”的意识,而实用的汉字一旦被注入了主体的“情”,汉字就不仅仅是表示概念的一个抽象符号,而成为一种具备“情性”和“精神”以表现生命的艺术,这不能不说是书家对文字的一种觉醒。
二
作为深藏于作者内心之中的思想情感,不仅旁人无从捉摸,连作者本人也往往不易清晰把握,要让内心的“情”呈现为可供观照和感受的对象,必须赋以情“物化”的形态,使之转化为“象”,故中国古典文学讲究“情以物兴”、“神与物游”、“睹物兴情”、“情景交融”等观念,重视“意象”的作用。作为“有情”的书法,其“表情达意”看似一种常识,细究之下实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要将心中的“情”( 意) 体现于文字的“象”( 所谓“立象以尽意”) ,全凭心手之间的配合,以动人的作品来完成这种体现。不同于诗歌意象可以在想象中完成,书法点画的变化、运笔的收放、书写的节奏都是瞬时变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巧的熟练。诗书虽都以表情达意为目标,但其“表情”之意义又不尽相同。张怀瓘在《文字论》中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①正好说明了“文”和“书”在表情达意上的差异。就一般汉字的形义关系来说,自然都是一字见意,可是文章之表意在句义层次,故须数字以成其意。可是书法之表意,不在字所代表的字义上,而在字形本身的形象。可见在艺术的层次上,书法的意义已经摆脱了字义、句义的限制,而直接以形式美为其意义。就“抒情”而言,同样是“抒情”,文学要透过文字去感觉,而书法则是对文字的直接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果真能脱离字义吗?
书法作为一种书写文字的艺术,其“抒情”特质必然受制于与书写有关的一切因素。
汉字的基本构成是点画、线条,字有字法,笔有笔法,墨有墨法,作品亦有章法,所以表达何种情意最终要落实到对这些具体要素的把握上。如宗白华先生所言: “( 书法) 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表现作者对形象的情感,发抒自己的意境,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②故书写过程中笔法的轻重缓急、墨法的浓淡燥润、结体的欹正疏密、章法的承接呼应都要服务于情感的表达。我们看到,古代书论在探讨书法作为一种抒情媒介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关注中心。一种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侧重于抒情之情境和心境的强调,可称之为以作者为中心的观照; 一种是以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为关注点,侧重于书法作品给人的审美体验,可称之为以作品为中心的观照。也就是说,以作者而言,“抒情”的意义在于如何将“情”赋予书写的过程并将其物化为作品的形式; 以作品而言,“抒情”则意味着如何通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来触动观者的情感共鸣。具体而言,我们结合古代书论分别论之如下。
自创作而言,早期书论如东汉末年的蔡邕即指出书法创作与作者情性之间的关系,传其所作的《笔论》指出: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也; 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邕所言的“散”源自庄子“散木”、“散人”的思想,意指作者性情的散淡、神情的舒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书法艺术独立性的强调。“散怀”作为作书之际的准备,可谓是“抒情”的前奏,与其所论作书时的心理状态一致: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有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①这显然又与庄子的心斋、坐忘等虚静状态相通,是对创作主体创作心境的强调。受其影响,此后传为王羲之所论“凝神静思”、“意在笔前”以及李世民“收视反听,绝虑凝神”的诸种说法都是对这种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则提出着名的“五合五乖”理论,以“得时”、“得器”与“得志”三者的辨证关系更是将这种观念发挥到极致。孙氏认为作者主观情性只有和客观的条件相统一融合,才能创作出畅情达意的作品。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 神怡务闲,一合也; 感惠徇知,二合也; 时和气润,三合也; 纸墨相发,四合也; 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 意违势屈,二乖也; 风燥日炎,三乖也; 纸墨不称,四乖也; 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②显然,五者之中,其一、二两项说的是作者的精神、情感,其三、四两项说的是作书时的外部条件,而“偶然欲书”则意味着内外之结合---心情既佳,笔墨精良,环境宜人,自能触发心中作书的欲望,作出畅情达意的作品。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专列“性情”一条,征引孙过庭上述内容并提出“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的看法③,足以说明创作心境对书法“抒情”的重要意义。
对创作者而言,书写是一种“情”的寄托与抒发,这是书法艺术的“娱己”功能; 对欣赏者而言,则是通过作品的审美来体会其中的情怀和意蕴,这是书法的“娱人”功能。朱光潜先生说: “艺术的任务是在创造意象,但是这种意象必定是受情感饱和的。情感或出于己,或出于人,诗人对于己者须跳出来视察,对于人者须钻进去体验。”④就书家而言,“创造意象”即意味着创作优秀的书法作品; 就欣赏者而言,作品所负载的情感显然是需要“钻进去体验”的,以作品呈现出来的面貌来推想作者创作时的心境和情感,以获得审美的愉悦,这是一种“情”的沟通与交流。对书法作品之“有情”,早期的书论即有发觉,崔瑗在《草书势》中说: “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蓄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而惴栗,若据槁而临危。”⑤显然,在崔氏看来,草书丰富的形态美也具有某种感情色彩,书家借此可宣泄心中的某种情绪,而观者亦能于此感受或想象某种情绪。又如元人陈绎曾《翰林要诀》言: “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⑥更是将情感与字形紧密相连在一起。不过,欣赏者未必真能从字之“敛舒险丽”中看出创作者的“喜怒哀乐”,而更多的是作品触动欣赏者的一种情感想象,朱光潜先生称之为“移情现象”,即“把字在心中所引起的意象移到字的本身上面去”,故朱先生说: “字也可以说是抒情的,不但是抒情的,而且是可以引起移情作用的。”⑦书法史上大凡能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都具有这种“动人”的品质,比如备受推崇的颜真卿《祭侄文稿》,欣赏者大多认为其字里行间的哀思郁勃和悲愤交加以至于情不能禁,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黄庭坚“鲁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①或许代表了多数欣赏者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动人”一读便知,但字法的笔墨本是无情物,何来“动人”之说? 这就回到前面的问题,字形之“情”真能摆脱字义之“情”的暗示吗? 汉字的“音美”、“形美”、“义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也许很难清楚地割分,故欣赏者从颜真卿字法中获得的“动人”或许只是文章动人的一种“移情”.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朱良志先生的观点: “书法的表现是一种显现',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显现,不表现具体的情感内容,只具有某种情感趋向。这种情感趋向是通过书体线条组合形成的特有风度气韵来显现的,即由书之情性来显现情感.”②因此,一件优秀的作品打动观者的就不仅仅是点画之间的形式美,而更在于作品所传达出的人格美和情感美。正如文学批评中有“知人论世”的方法,如果缺乏对一件书法作品的背景认识,仅仅从字形之中能就看出作者的喜怒哀乐,不能不说是对书法“抒情”的一种过度阐释,难免有穿凿之嫌。正因为书法艺术在表情达意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不可能同文学语言那样清晰,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像“心电图”那样来解读书法中点画、线条的情感意义,但它却因此而更有引发联想和想象的功能而获得一种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情”是一个指向多端、内涵丰富的概念,既可指向情性、情志、情理等较为抽象的内容( 如《荀子·正名》篇对性、情、欲三者的讨论: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不免也。”) ,亦可指向具体的情感、情绪、以至情欲等人之常情。( 如《礼记·礼运》篇中“七情”的说法: “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情”的多义性,增加了对其把握的难度,若未加分析和界定,势必有指涉含混而论说无效的风险。那么,当我们将书法看作一种“抒情”活动时,其中的“情”所指涉的范畴又究竟如何理解? 书论史上虽然不同书家,在不同的论述语境之中,对“情”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大致可以从隐性的“情性”和显性的“情感”两方面来把握书法之“有情”.其中,“情性”的概念虽然早在蔡邕的“恣情任性”说中即有提及,但以唐代孙过庭的说法最具系统性。孙氏认为书写即是一种抒情活动,并且以“情性”为核心形成一套书法审美理论。其《书谱》曰: “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③显然,“情性”与“哀乐”虽同为人类心理经验的表现形式,内涵却又不尽相同,故有论者指出: “其内在的含义还在于: 他已经摆脱了泛泛的情,而把情作为一个整体分为更细的类型: 情性与哀乐.”④对书法艺术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它体现了书家对“情”认识的深化。
“情性”一词源自中国哲学中“性情”的概念,亦是文学批评中常用的理论范畴。何谓性情? 《白虎通·性情》篇云: “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 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又曰: “夫人性内函,而外着为情。其同焉者,性也; 其不同焉者,情也。惟情有不同,斯感物而动。性亦不能不各有所偏。”①看得出,哲学中的“性”为本源,“情”是“性”的延伸,“性”感物而生“情”.由哲学的“性情”到文艺的“情性”,凸显的正是对创作主体情感的强调。
作为同是发自主体内心的“情性”,诗人以言“吟咏情性”和书家以书“达其情性”,方法途径虽异,其理却无二致。那么,具体到书法作品之中,“情性”又该如何理解? 孙过庭《书谱》曰: “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 质直者则径庭不遒; 刚狠者又倔强无润; 矜敛者弊于拘束; 脱易者失于规矩; 温柔者伤于软缓; 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 迟重者终于蹇钝; 轻琐者染于俗吏。”②看得出来,这是“书如其人”观的一种逆向表述,所谓“质直”、“刚狠”、“矜敛”、“脱易”、“温柔”等均指向作者的个性与性格,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由这些性格而创作的作品,很有可能呈现出诸如“径庭不遒”、“倔强无润”、“拘束”、“软缓”、“滞涩”等不同的“面目”.对于“情性”的讨论,我们从孙过庭的分析中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其在比较真、草两种书体时说: “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 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③,“形质”可以通过具体的要素来体现,“情性”则是要素所要表达的意义。清代包世臣对此的解读为: “书之形质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语默。”④孙过庭所谓真之情性在使转、草之情性在点画,是说真书的点画确定形式框架,而其妙韵在使转的起伏变化中。
而草书反之,草书飞动流转,笔意相连,惟其点画处见沉稳,故点画成了决定草书韵致的关键。然笔墨之情性,根之于人之情性。情性之流露,必依赖于对艺术的精熟把握。钱锺书先生曾论作诗之“性情”曰: “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⑤作诗如此,书法中“情性”的自然流露亦不是毫无规矩地宣泄感情,而必以精深的功力为前提。明人祝允明曰: “有功无性,神采不生; 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兼此二者,然后能齐古人”,可谓是对“情性”与“功力”辩证关系的最好表达。
和“情性”相比,“哀乐”是一种“弗学而能”的显性情感,而“形其哀乐”也是一种最易为人理解的关于书法“抒情”的表述。在《书谱》中,孙过庭关于“哀乐”的阐释可以从临写王羲之的作品中来体会: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⑥在孙氏看来,王羲之的每一件作品由于其文学内容、书写情绪的不同,便导致作品风格的差别以及情感抒发的不同表现。这是一种喜怒哀乐比较明显,感情色彩比较具体的抒情方式,它借助《乐毅论》、《东方朔画赞》、《黄庭经》、《兰亭序》等在内容上对情感的不断提示,从而在作品中呈现出怫郁、瑰奇、怡怿虚无、纵横争折、思逸神超、情拘志惨等具体的作品风格,虽同为王羲之一人,作品也会因为创作心境、作品内容等外在的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不同的风格。正因王羲之作品呈现出丰富的情感指向,因此对学习者而言,对王羲之的学习就不仅仅在点画的临摹之上,而要体会点画之中的情感意义,唤起内心的情感共鸣,只有这样,书法才不致失去灵魂,笔墨才有情采。因此,孙过庭说:“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 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 ”①这显然是借用文学批评中“诗缘情”的观念来说明情感对书法风格的影响,以为探讨书法风格的根源还应向作者的情感中去索解。
在表达“哀乐”式情感的效果上,草书往往占有特殊的地位。张怀瓘谓草书“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骋纵横之态,或托以散郁结之怀,虽至贵不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量其力”②,草书的放纵是最具动感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中,“抒情”亦最能体现其“抒”的内涵③。例如唐代韩愈以夸张的文学语言描述了张旭草书中所寄予的情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④张旭借鉴物象创作抽象的书法,寓情于象,情象相生,情与象的高度统一才使他的书法具有如此强烈的“抒情”效果。
和书家“情性”的相对稳定性相比,这种喜怒哀乐式的“抒情”具有自然、即兴、稍瞬即逝的特点,正因如此,作品引起作者的情感共鸣才显得真切可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书法史上最受推重的两件作品《兰亭集序》和《祭侄文稿》都是即兴表达的稿书类型。
以上我们在“抒情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了书法“抒情”观念的来源、“抒情”实现的途径、“抒情”指涉的内涵等与书法“情性论”相关的几个问题,虽不全面,却也说明了书法与文学在“情”理上的相通与互释。正如文学的抒情观念在历史的传承中发展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传统,作为“有情”的书法,在笔墨情性的流转之中,其“情性论”和“抒情”阐释亦自成体系,深刻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创作与审美,亦成为中国“抒情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