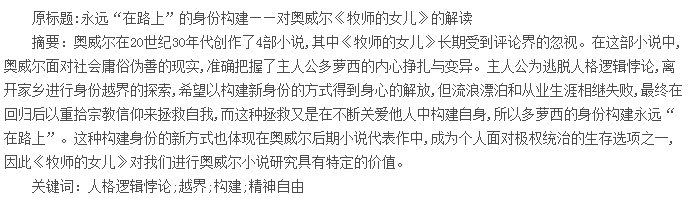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着名小说家,其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影响久盛不衰,但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却少人问津,尤其是他1935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牧师的女儿》,国内外真正阅读和研究过原着的人少之又少。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主人公多萝西·黑尔是偏远小镇尼普山镇一个穷牧师的女儿,母亲早亡,父亲冷酷自私,她自己又没有稳定独立的经济收入,生活困顿、前途黯淡。此外她还受到镇上浪荡子的性侵犯,令她原本毫无自由的身心更加苦不堪言,对基督教的信仰也产生了怀疑,竟突发失忆症,恍惚间踏上流浪的旅程:到乡下的啤酒花采摘地当起了临时工,在伦敦和一群流浪汉为伍,忍受着饥寒交迫的折磨,后来又在一家女子学校当教师,在受到校长和学生家长的非难后,被扫地出门,只能回家。然而,通过几个月的流浪生活,让多萝西在历经磨难后,体悟到只有精神信仰才能超脱贫困和庸俗的人生,由此她开始以平和、淡泊的心态迎接生活的挑战。
一、困局:主人公的人格逻辑悖论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基本围绕主人公多萝西展开,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缺少鲜明个性的扁平人物,过多带有奥威尔本人的痕迹,思想行为毫无独立性可言,是个不真实的人物。侯维瑞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将《牧师的女儿》界定为奥威尔关于贫困题材的自传小说。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在奥威尔的小说人物中,“多萝西是最消极的一个人物”[1]。奥威尔本人也对自己的这部作品不满意,甚至不允许出版社重印。然而,我们阅读奥威尔的代表作和理解他的思想观念,又绕不开《牧师的女儿》,它是奥威尔反思现代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主人公多萝西和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奥威尔面对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英国,一方面,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口尚未愈合,经济大萧条的阴霾又笼罩不散;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上下弥漫着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的伪善拜金、虚荣享乐的风气。戴维·罗伯茨在《英国史:1688至今》中认为,这种风气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对于精神信仰,“是低层阶级的人置之不理,漠不关心,而高层阶级则假冒伪善、虚于应付。”[2]
小说中的尼普山镇是衰落中英国的缩影,人们奉行拜金主义和享乐之风,金钱成了衡量爱情与亲情的唯一尺度,小镇居民大多沉迷于俱乐部聚会、地区议员的选举、制造和散布小道消息,精神萎靡地打发死气沉沉的生活。简言之,尼普山镇人的生活状态折射出现代英国社会过度追逐物质利益和丧失精神活力的现实。
尼普山镇的现实和多萝西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格格不入,在她心里,社会应该按照上帝规定好的自然法则运转,可实际上她陷入两种生活模式的冲突中难以自拔:一方面要按照理想的应然状态生活,无休止地操持家务、尽心照顾冷酷无情的父亲、有条不紊地处理繁重的教区事务、在清贫中坚定信仰;另一方面要面对生活的实然状态,强迫自己接受俗不可耐的街坊邻里和黯淡无光的未来,还要在遭受恶棍的性侵犯后与其保持肉体关系。这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部分居家女性在物化现实中形成的“人格逻辑悖论”。正由于理想的应然状态与现实的实然状态严重错位,造成多萝西思维和情感的扭曲,让她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跌入精神分裂的深渊,最终导致“失忆”,进而“走失”。可以说,“失忆”是多萝西人格逻辑悖论的必然结果,隐喻其被动地放弃原有身份;“走失”是摆脱悖论、重塑自我的出路,但却隐喻了一种没有方向和计划的自我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牧师的女儿》所把握的多萝西人格逻辑悖论,并不是血腥暴力的急剧冲突,但却是一战后英国人深陷庸常世界的精神困局,如何对其破解对现代人具有鉴戒意义。
二、破局:主人公在身份越界中奔向他者
多萝西闯入了流浪无产者和职业女性的世界,她以身份越界进行人格逻辑悖论的破局。这意味着,人构建自身必须呼唤他者的出场,只有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生活方式的场域中才能定位自我。然而,在身份越界中,多萝西所奔向的他者并不是她心中理想的他者,她没有成为他者中的一员,这就导致身份越界必然以回归为结局。
1.在流浪无产者的多声部中“失声”
我们在这里说的“无产者”取其广义的概念,包括一切没有“产业”的职员、工人、农民、无业者。多萝西在流浪中最先接触的无产者是社会底层的流浪汉,他们既不同于威尔斯、萧伯纳、赫胥黎笔下用以讽刺社会不公正的穷苦人,也不同于同时代的英国工人小说家们刻意净化提升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而是被社会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人、多余人、末等人,是最彻底的“无产”者。
多萝西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生活中,无依无靠、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她不仅在经济上赤贫如洗,更在精神上萎靡困顿,成为一个地道的女流浪者,但这并没有让她成为流浪无产者中的一员。在流浪无产者这个集体中,作为女性和“新手”的多萝西比其他流浪者更易遭受歧视和人身威胁,她不得已以沉默应对,并掩盖自己受过教育的口音,最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多萝西的声音彻底湮没于其他流浪无产者话语组成的“多声部”中,完全进入“失声”状态,成为一个处于旁听和旁观状态的“哑巴”。相应地,文本中描述性语言几乎全部替换为对话,仅留旁白为辅助说明,小说呈现出戏剧剧本的特征,这种“文体越界”现象使小说渲染出后现代主义的杂糅品质,而对话构成的多声部状态,不仅在历时和共时的层面突出了流浪无产者的语言特色和内心意识,也建构出多萝西异于流浪无产者的身份差异。爱德华·奎因认为:“奥威尔在1933年读过乔伊斯《尤利西斯》并深受启发,作为影响源泉,乔伊斯的小说带来的启迪是多方面的。”[3]
尽管有的评论者对这种模仿不以为然,但语言学家罗杰·富勒认为,奥威尔进行的多声部实验十分恰当地表现了同时出现的多种对话,“这种同步效应产自于同一空间许多人的混音杂语,可称为鸡尾酒效应。
所有东西都是模糊的,除非你集中关注其中一点。”[4]
而在洛兰·桑德斯看来,这种奥威尔式的多声部将“人物的声音代替了全知全能叙述者的声音”[5],这既是奥威尔在声音方面从单一性向多重性的突破,也是在塑造人物方面从单人独语世界向多人众语世界的突破,体现了多萝西和普通人物的对话性、奥威尔和所有人物的对话性,不仅实现了多种意识的“面对面”,而且揭示出生活和艺术的本质特征———“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6]
我们进一步认为,多萝西的教育背景与成长经历使她与流浪无产者存在交流障碍,因此她处于患上失语症的弱势地位,更多地以沉默作为对话的“语言”,这导致她不可能真正深入到无产者的世界,更无法认同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无论对多萝西还是对我们来说,流浪无产者的群体都是一个陌生的多声部世界。
首先,复杂交错的表达构成多声部的语言迷宫。流浪汉在夜晚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挨饿受冻,却展开了自由的诉说,想理清他们对话的脉络是极为困难的,其话语中称谓少,主题变换快,且常出现俚语和省字丢音现象,增加了理解难度,如坠迷宫一般。中老年男性基本上是在自言自语,三位中年女性轮流出场,几位年轻男性则捉对儿闲聊。流浪汉的话语在多萝西脑海里像声音记录,一段表达段落分成若干的句子单元,可记录在案的只有残缺不全的少量句子单元组成的表达片段,但这种片段却营造出现场感,使我们处于信息集中同时的“轰炸”中,无法有效分辨信息的发出者和确切含义,正是由于言语意义上的不确定才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道格拉斯·卡尔认为:“这是奥威尔作品中令人震撼和至关重要的地方,这群人是伦敦的最底层,多萝西与之截然不同,他们除了声音以外一无所有,奥威尔让他们自说自话,叙述者的声音沉寂了,复调产生了。”[7]
其次,声音追溯故事,形成流浪汉个体的潜文本。流浪者通过对话和自语在交流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他们自己的经历,多萝西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追查到许多信息,包括他们的往昔生活、年龄爱好、性格特征和身份职业,这些可以称为潜文本。多声部的语言迷宫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高宝先生,其身份是位牧师,从头至尾基本沉浸在回首往昔好时光的迷梦中;本地狗太太,对负心的丈夫大加痛责,是位受遗弃的怨妇;麦克爱丽高特太太,对心上人念念不忘,和本地狗太太的情感遭遇正相反。这三位都人过中年,历经坎坷,他们的经历也在暗示宗教信仰的衰弱和女性地位的低下。相对于这几位“流浪界前辈”,金杰、查理、凯科、“长鼻子”和“包打听”沃特森堪称“小五义”,偷窃、卖唱、乞讨,底层世界的营生几乎样样精通,相互结伴而且都有前科,对社会怀有敌意和敬畏。“小五义”早已被卑贱的生活打磨成处乱不惊、得过且过的老油条,成为反社会的存在。
最后,多声部表达一致话题。尽管流浪汉们的经历各不相同,表达也各具特色,但他们谈话的主题却极其一致:饥饿与寒冷,这是由于流浪汉的基本生存资料极度匮乏造成的。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34年,当年10月伦敦气温降低至零度以下,还不时飘起微雪。在这样的环境下,处于露天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流浪汉们食不果腹,处境极其堪忧,找到吃的和住处是度过漫漫寒夜的首要问题。所有人的谈话内容都包含食品和饮品的主题,而女性流浪者对低温比男性更敏感,因而抱怨寒冷的次数也更多。这一夜流浪汉们根本没有食物可吃,唯一的饮品就是金杰弄回来的茶水,但是每个人分到的也极为有限,凯科为此埋怨道:“我的天,你连半杯都没有给我倒满。”[8]
流浪汉们的愿望,只是第二天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睡个好觉,这是他们最现实的生存理想,冻饿难以成眠,睡眠不足更加重流浪之苦,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身体和精神上都会遭到严重的摧残,健康无从谈起,活下去的希望都更加渺茫,生存的意义和美好的愿望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淡如云烟、恍如隔世。
由此可见,小说中出现的多声部是通篇结构上的“断层”,按照我们的“期待视野”,情节发展至此应该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为主,然而小说文本却以构建流浪无产者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小说“意外地”用多声部构建流浪无产者的世界,表明多萝西与流浪无产者的重大差异,她的“失声”体现出她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她所闯入的场域对她构建新的身份是无效的。
2.对职业女性身份的逃离
在意外结束流浪后,多萝西应聘到英木女校当教师,但是,职业女性的新身份虽然使多萝西获得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在身份越界中她遭遇到等级体系的伤害。英木女校校长克里维的原型,是给奥威尔造成童年创伤的圣西普里安中学校长威尔克斯太太。她不学无术,治校无方,却通过讨好家长捞取金钱。
克里维将学生按照其家长的经济实力分成三等,“好主顾”、“中不溜”、“讨人厌”,区分了巴结、冷遇和排斥的对象。家长的要求就是她教授课程的“硬指标”,家长要求她教什么她就设置什么课程,家长厌恶什么她立即严加禁止、改弦易张。
多萝西来到之后,带领学生开新课、学新知,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可家长们却认为新课没有计算、抄写那样有实用价值,横加指责,克里维不问青红皂白,当着众多家长的面羞辱多萝西并终结新课,随后又找借口将多萝西赶走。
经济利益驱遣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克里维所招收的学生,多出身商人家庭,克里维的学校实际是他们出钱供养、培养商业奴隶的培训机构,克里维不过是为商人阶层敲边鼓的小丑。因此,表面上是克里维辞退了多萝西,实质上是多萝西对职业女性身份的逃离,英木女校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氛围和尼普山镇没有本质区别。尽管多萝西作为教师是合格的,并因此获得了独立的经济能力,但她的道德良知与丑恶现实仍然是对立的,这就是说,职业女性生涯提供的经济基础不是解决人格逻辑悖论的唯一条件,女性获得解放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女性的地位虽然已经大大改善,但社会对女性的关爱、保障仍然十分有限,人们在道德上推崇温惠驯良的淑女,在思想意识上要求女性绝对地服从男性权威,这就使女性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甚至因生活压力走上歧途,如同克里维那样不择手段地行骗捞钱,表现得比“男性”更“男性”。可以说,多萝西在英木女校的身份越界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他者,教师职业只是她进入社会的预演。在多萝西意识中,将职业女性作为自己未来的选择是令她难以信任和适应的,职业女性生涯的结束使多萝西只能回到家乡,这场由突然“失忆”造成出走的身份越界之旅,以突然被解雇、被迫回家而终止。
三、结局:没有完结的身份构建
在这场身份构建的旅程中,原为居家女性的多萝西并没有在流浪结束时递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从流浪无产者到女教师,再回到尼普山镇重新过以往的生活,主人公又回到了故事的起点,这就意味着,多萝西的新身份的建构没有最终完成,因为在多萝西看来,伦敦的流浪无产者们虽然拥有人身自由,可以到处飘荡,但地位低下,没有经济基础;而英木女校的教师职业,虽然给予自己经济能力,却必须服从强权的统治,从而丧失了身心自由———这两种经历都不能令多萝西破解人格逻辑悖论。更为严重的是,多萝西除了这两个选项已经无法找到其他途径来重构身份,社会没有给她更多的机会面对他者,无论她如何反抗命运,她所做的似乎都是在重复流浪和工作这两种各有残缺的生存方式。我们看到,不是多萝西自身造成的这种困境,而是商品社会以等级制度将人们割裂成不同的群体,彼此无法对话,多萝西就成了下不到底层社会、上不了上流社会的“悬空人”,因此,在社会的重压下她只能退回到熟悉的环境中。
但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多萝西发现在困境面前精神信仰的可贵。她意识到,社会的阶级划分已经严重到,即使同一个阶级中也存在多层结构,但共同的价值取向弥合了经济差异的不断扩大,而自己所在的阶层既有拜金主义的享乐之风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有比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更为强烈的基督教信仰传统,而这可以成为摒弃现有人生困境、超越庸常世界的精神武器。
因此,基督教信仰在归来的多萝西这里又焕发了新的光彩,这已经不是教会组织形式的基督教,而是一种德里达所说的“个人的宗教”,是人在经历苦难后对信仰最真挚的呼唤,正是有了它,多萝西的人生才有了意义。因此,原先的“牧师的女儿”,现在成为作为女儿的牧师,多萝西刚回到家,就开始打扫原本厌烦的教堂,探访教区里的信众,筹备募捐活动。我们由此看到,多萝西的独立人格已经出现:对与她地位、经历相似的人抱以真挚感情,向信众传教的尽职尽责,倾听他人话语所组成的多声部,将乞讨流浪作为参照因而能更从容地面对清贫生活,这些都是多萝西从走失、流浪、从业中习得的生存技能。而对于她的人格逻辑来说,已经不存在应然与实然的悖论:基督教的信仰高于现实存在,换句话说,正因为现实的种种不堪,使人的信仰弥足珍贵,物质社会矛盾的化解必须从精神世界的超越开始,健全独立的人格构建唯有启于思想观念的更新。
总之,多萝西的身份越界行动遭遇的是两类与己截然不同的他者,她不可能放弃原有的道德原则成为其中任意一方的成员,因此她没有成为他者的身份。但是多萝西仍然构建出了新的自我,这就是不断用精神信仰克服现实的种种不如意,她不断将信仰由己及人,也就是持续构建新的牧师身份,因而她的自我拯救也就永远“在路上”。
可以说,多萝西的自我拯救是现代人摆脱日常苦闷心境的选项之一,在左右为难、欲罢不能的情况下,走出去经历苦难,又返回起点,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妥协或倒退,而是超越矛盾后的反思与实践。奥威尔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是以主人公心力交瘁、挣扎失败,悲惨自杀而告终,而在《牧师的女儿》中奥威尔尝试一条新的排解现代人精神困局之路,在《牧师的女儿》的结尾,多萝西以一种平和淡泊的心境较为自信地展开新的人生,这是激烈反抗与平和构建两种不同的路线。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多萝西的身份构建并非起于她的主观自愿,而是以一种“失忆”和“走失”的方式开始的,而在小说结尾,对精神信仰的重新认识也不能夸大到代替无需经济基础的地步,这实际上是奥威尔有意留下的余绪。从文本中叙述者的强势地位看,奥威尔始终没有将平和构建进而拯救自我的这条路线奉为圭臬,从因良心谴责辞掉英帝国驻缅殖民警察的职务、与殖民主义划清界限,到回国立志当作家并走上探访无产阶级生活状态的道路,再到赴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军队负伤、遭西班牙共产党追捕逃回英国,直至熬过二战岁月后写就《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表达对极权统治的愤恨和忧惧,在奥威尔整整20年(1929—1949)的艰辛探索中,有一条红线贯穿他46年短暂的生命历程,那就是他始终以一己之力试图揭开不公正、不人道的社会制度对无辜个体的伤害和压迫。因此,他认为,人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进行自身我拯救在多大程度上可行,这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难题,将《牧师的女儿》与《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进行叠置,则是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显现出这部小说在奥威尔创作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