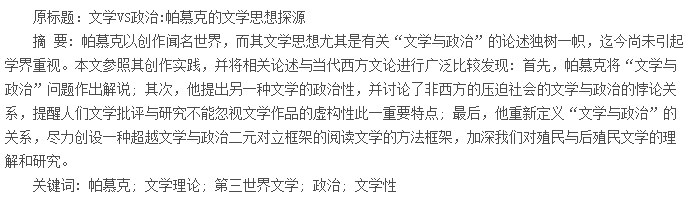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以下简作“帕慕克”) 是饮誉当代文坛的着名作家。1952 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23 岁从土耳其科技大学退学,矢志成为一个小说家,7 年之后发表处女作《塞夫得特先生》,此后共创作出版了以《我的名字叫红》(1998) 为代表的长篇小说 8 部、随笔集 2 部、讲演集 1 部和电影剧本 1 部。200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世界瞩目。迄今为止,已有 11 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不仅激发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促成了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为新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笔者查阅中国知网的论文统计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帕慕克的研究论文有 600 余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其小说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的探讨; 第二,对其小说主题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身份危机的分析; 第三,对作家的乡愁情怀(“呼愁”) 与其创作之关系的论述。然而,有关其文学、艺术理论的研究尚未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从正面研究帕慕克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并将其相关论述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相关阐释进行对比,以期更好理解帕慕克的文艺理论。
无论是按照中西文艺理论的历史脉络来观察,还是依据无数经典作家的“现身说法”,我们都能发现,任一作家的创作历程与其文学、艺术理论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研究作家的文学、艺术理论便尤为必要。帕慕克亦非例外。他的《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别样的色彩: 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入口。2009 年,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邀请,帕慕克发表了 6 次着名演讲,后据此结集出版的《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一书相当完整地表达了作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复杂性的理论思考。帕慕克说: “我希望谈论我的小说创作旅程,沿途经过的站点,学习过的小说艺术和小说形式,它们加于我的限制,我对它们的抗争和依恋。同时,我希望我的讲座成为小说艺术的论文或沉思,而不是沿着记忆的巷道走一趟或者讨论我个人的发展。”
借助于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对“天真”(naive) 作家与“感伤”(sentimen-tal) 作家所作的着名区分,帕慕克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与阅读过程。但毫无疑问,将自己对文学与艺术的理解统摄在“天真与感伤”这一主题之下,也是受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 的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The Song of Innocence and The Song of Experience) 启发的结果。然而我们深知,包括作家本人在内,乐于承认自己受启发、被影响这个事实,不能削弱我们对其创造性的评估。事实上,尽管开拓传统与对传统的继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开拓传统时所彰显的创造性却构成了帕慕克之为帕慕克的根本。
一、“文学与政治”的历史语境
帕慕克首先反对将作家的政治意识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政治性等而同之,并且将文学的政治性概念泛化,推论出文学即政治、一切即政治的判断———例如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在撰写《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时即宣称“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帕慕克在纽约告诉美联社的特稿作者娜哈尔·图西(Nahal Toosi) : “政治没有影响我的作品; 不过,政治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事实上,我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作品远离政治。”
他还以那种认真而又不无揶揄的口吻说道: “写作小说的创造性冲动源自用词语表述图画性物品的热情和意志。每一部小说背后当然也有个人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可以通过别的渠道得到满足,如回忆录、访谈、诗歌或新闻报道。”
在《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第五章,帕慕克重申了这一判断: “说到小说,我们却不经常谈政治或小说里的政治,在西方尤为如此。……政治小说是一种有局限的体裁,因为政治包含一种不去理解非我族类者的决断,而小说艺术则包含一种要去理解非我族类者的决断。但是政治可以被纳入小说的程度是无限的,因为当小说家努力理解那些异己的人,以及那些属于不同社会、种族、文化、阶级和国家的人们之时,他恰恰具有了政治性。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那些没有政治主题或动机而尽力观察一切事物、理解一切人并且建构最大整体的小说。因此,那种努力实现这种不可能任务的小说具有最深沉的中心。”
通过上述的描述,我们似乎会得出一个结论: 哪怕是“纯文学”作品中,其政治性无处不在,而且这种政治性是小说家而非小说中的人物在理解另一个人时所赋予的。但是,这种政治性如何为读者心领神会,或被误解? 另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是: 为什么那些我们通常见到的最具政治性的文学却因为“文学性”不足而被指责? 归根结底,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的“政治性”?
以 2002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雪》为例,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部被帕慕克认为是自己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创作的政治小说里,诗人卡和大学女同学伊佩珂的故事串联起他们对理想的人性与爱情的追寻,而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卡尔斯等地的选举、政变、宗教冲突,则凸显出小说主人公难以排解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危机,暗含作者希望伊斯兰社会能够自我反省的呼吁。小说一经问世,即在土耳其引起巨大争议,但在国际范围内却赢得了广泛支持。可以说,这部最具有政治性的小说不仅没有损伤其“文学性”,反而因为着意处理而非回避政治的纠葛而别具魅力。那么,这一“政治小说”的魅力源自何处? 作家在“诺顿讲座”上予以明确回答: “小说艺术不是在作者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在我们努力理解某个与我们在文化、阶级和性别上不同的人之时才具有政治性。这意味着我们在作出伦理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判断时,要怀有同情之心。”
我们平常所说的政治性,实际上有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作家关注表现的是一种政治社会性的题材,其二则是指文学为政治服务。”
追溯帕慕克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出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 对他的重要影响。但帕慕克对“文学的政治性”的理解超越了奥威尔所谓的、显而易见的“作家的政治动机、政治意识”的层面,并且重新定义了“文学与政治”关系: 文学中的政治性,只有在作家对异己之人的书写中才能体现出来,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没有明显地处理任何政治主题、事件、行为的小说。这一洞见首先有助于修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传统理解,特别是我们一贯所提倡的那种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与现行政治意识形态相配合的政治性的理解以及过分拔高,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那种“立场”(alignment) 和“党性”(commitment) 非常明显的“倾向文学”数次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
重要的是,帕慕克的思索还有助于我们对题材、主题批评的限度进行反思。可以说,包括聚焦于一部作品的政治性在内,任何聚焦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和主题的批评与研究,固然有助于我们定位一类相同题材、主题的作品中的某一部的特性,但它几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这局限性即是未能充分体贴、讨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它的成功往往是以牺牲有关“文学性”的讨论作为代价的。以至于我们不禁想问: 形形色色的题材批评、主题批评,而今依然大行其道,但它们真的像它们所表现出的那样关心文学? 假如有一种最具政治性的文学,它又岂能那么容易被我们解读出? 甚至,为何我们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如此执迷于“政治性”?
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奥威尔之类的独立作家不同,帕慕克除了将自己对“文学与政治”的理解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亦即在 20 世纪东西方政治冲突、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被殖民国家和地区意欲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同时还须着手如何走向现代。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一定程度上,“西方”即等同于“现代”“进步”,被殖民国家和地区则是“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
被殖民国家和地区到底是向西方学习,完成西方式的现代进程,还是立足传统,开拓传统,从国家和社会内部寻找现代的可能性,是这个语境中社会、经济和文学革新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当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目睹宗主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实施的血腥与残暴统治,而且牢牢控制着何谓文明、何谓野蛮的话语权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无疑将更为痛苦,甚至可能被道德上的正义感和情感上的厌憎所统驭。
但是,文学难道不可以超越地域、国族和社群的界限? 真的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第三世界文学吗? 在不堕入粗俗和狭隘的前提下,有没有什么可能为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其文学的基本特点?
帕慕克曾以秘鲁作家马里奥·马尔巴斯·略萨(以下简称“略萨”) 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他发现,还是“有一种叙事小说很明显是特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小说的创意与作家生活的地方关系不大,而主要是因为作家知道他的写作远离世界文学中心,并能在内心感觉到这种距离。如果第三世界文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决不会体现在它赖以产生的贫穷、暴力、政治或国家动乱上,而是体现在作家意识到,他的作品多少远离了中心,并在作品里反映了这种距离。在这里,他的艺术史(小说艺术史) 由他人来撰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作家有着从世界文学中心被流放出来的感觉。”
这种被流放的感觉与精神状态,让第三世界的写作免于“影响的焦虑”而能全心全意探索自己的独创性和真实性,汲取本国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的灵感,并将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与技巧完全翻转过来,服从于自己不同的目的(比如像略萨那些书写反抗殖民的历史) ,很有可能铸就自己特立独行的文学。此时的略萨尚未获诺奖,而帕慕克却能独具慧眼,发现略萨笔下那非比寻常的文学创造力,显出其一流的文学批评眼光。饶是如此,就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以及我们熟悉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总体而言,究竟是执着于批判“西方文学”“现代文学”的政治性,还是同时有力地揭露本国和本地区的残忍和罪恶,抑或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去政治性、无对抗性的文学,这一不得不直面的生存境遇恐怕决定了我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既执迷其中又倍感困惑的复杂情绪。我们还必须接着思考,如果有一种崭新的去政治性、无对抗性的第三世界文学,可否被我们察觉、认知?
二、“非西方的压迫社会”的“文学与政治”
帕慕克谙熟于笛福、菲尔丁、塞万提斯以来的西方现代小说传统,使他深感不满的是,“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小说在英国和法国兴起的历程,知道了小说观念是如何在这些国家形成的。但是,我们并不太熟悉作家们将小说艺术从英国和法国进口到自己的国家后,所做的种种发现和解决办法———特别是,他们如何让西方人赞同的虚构观念适合本国的阅读群体和民族文化。这些问题的中心以及由此兴起的新声音和新形式,就是西方的虚构性观念为适应本土文化所经历的创造性的并且合乎现实的改造过程。”
也就是说,当第三世界的作家将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与技巧翻转过来,努力使之服从于自己不同的目的时,他们还要向读者告白并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基本观念———小说(文学) 是虚构的产物。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 “非西方的作家觉得自己有义务反抗独裁政权的诸多禁令、禁忌和压制,”但“反抗独裁政权的诸多禁令、禁忌和压制”恰恰是不被第三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欢迎的“政治性”,因此,为了书写和表达的自由,他们就不得不“用舶来的小说虚构观念,以说出无法公开表达的‘真理’———就像小说以前在西方使用的情形”。只有文学的“虚构性”(承认文学是虚构、想象的产物,是早期现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得以展开的基础) 这一看法被人们广泛接受,另一种文学的政治性,亦即文学对政治(不止是本国政治) 的反抗,才得以幸存。
长期生活于土耳其且一直使用土耳其母语创作的帕慕克,之所以能作出这一深刻的判断,或是由于目睹了自己和同时代许多作家因为一部大胆的作品而面临巨大风险的结果,但他对文学的“虚构性”的推崇正是因为他摆脱了“单语主义”作家的局限,察见“殖民主义”和“殖民”的深渊,清醒地认识到不独土耳其、印度等东方国家,也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甚至是整个“非西方的压迫社会”里,依赖于“虚构性”的保证而生发的与另一种文学的政治性有关的文学革新现象其实相当普遍: “如果我们能够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一位作家接一位作家,彻底研究在那些非西方的压迫社会中从 19 世纪末一直到 20 世纪末,虚构性是如何被小说家们运用的———一个复杂而又非常令人着迷的故事———我们将看到创造性和独特性大多产生于对这些矛盾愿望和要求的反应。”
此处帕慕克虽引而未发,但循其思路,我们当能推知其要义: 正是非西方的压迫社会对文学的“虚构性”的坚持,保证了这另一种文学的政治性的存在,大多时候也为文学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准备了必要条件。
我们注意到,这里帕慕克在完成了对“文学与政治”的重新定义之后,还指出了两者之间难以回避的悖论和张力,即一方面,在非西方的压迫社会,以反抗政治为宿命而开端的“虚构”文学,固然已成为文学革新的源头,生生不息,成绩斐然,但文学的“虚构性”却要求它尽量远离“政治”,避免“政治”的过度介入,稍有不慎,则可能陷入图解现实或政治宣传的泥淖。举例来说,面对一部作品,批评家们无论持何种观点,至少首先都对虚构场景、人物、事件以及对话和叙述者自己对世界、人生或人类境况的认识作重要区分,然后展开自己的文学批评,但批评家也好,普通读者也罢,“读者自己的道德观、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与一部作品所肯定或暗示的道德观、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一致或相异的程度决定着他对作品的解释、接受程度和评价。”
职是之故,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如果不能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能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对作为批评家或普通读者自身的立场予以反思,而是幻想着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评价标准,视文学为社会现实的忠实反映,从而套用于任何一部作品,又何异于缘木求鱼? 奥威尔也曾指出,在西方文学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作品,往往是教诲、训诫文学的末流,充满了陈词滥调和浮夸之辞,等而下之者则堕入宣传品一流。
另一方面,“政治正确”的文学又被非西方的压迫社会的意识形态召唤,“虚构性”除了可以部分地保护文学的纯粹审美价值乃至文学家的创作自由,其实不得不与主流的政治文学展开竞争。因此,无论文学的“虚构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帕慕克的这一发现,提醒我们: 在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非西方的压迫社会,文学的“虚构性”具有不同功能与不同读者接受基础,但有一个共通的特性是,文学作品的“虚构性”无论被强调到何种程度,仍对于构建、重构现实具有重要作用。按照帕慕克服膺的“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的看法,我们可以将文学视为现实、虚构与想象“三元一体”(a tried) 的融汇,那么,在现实、虚构与想象之间的越界书写,正充当了文学的开放结构的意义之源,向读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经验和诠释的空间。
而将文学定义为人类的表演行为之后,文学的“虚构性”的重要地位在伊瑟尔的论述里固然有所削弱,但他通过对文学固有的多义性、非确定性等维度的强调,在事实的层面依然表现出他对文学的虚构、幻想、想象这一根本特点的尊重,而这也呼应了 20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那种呼吁让“文学性”回归的观念。诚然,当世人饱经政治危机、军事冲突和流离失所之痛,只有“文学性”可以安抚人们久已疲惫不堪的身心,文学(这里不单是指纸质文学作品,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应是一切具有“文学性”的艺术,乃至新媒体艺术) 则成为人们最后守望的精神家园。
正如帕慕克的创作所示,他不仅能够突破 19 世纪以来的土耳其文学传统,且能师法于东西方文学传统而开拓创新,其文学与艺术理论虽非如出一辙,亦能因故就新。探究其所以别具一格的原因,首先无疑是受益于其创作实践,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仍然是他开拓文学传统的结果。在与歌德、席勒、威廉·布莱克、E·M·福斯特、奥威尔等人的对话中,与西方音乐美术等领域的经典作品、中国山水画作的“朝夕唔对”里,他的思考、质疑、辩难既深深地根植于传统,又不断地努力从传统中挣扎而出,进行自我的革新与创造,最终收获了有关文学与艺术的卓思特识。
三、超越“文学与政治”的阅读框架
在我们认识帕慕克文学与艺术理论的过程中,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辨析,对“非西方的压迫社会”的“文学与政治”发表的相当独特但也可能引起争议的看法,已经予以探讨,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他试图由此创设出一种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阅读框架,提出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应是在理解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反应之间取得平衡。这与我们熟悉的文学的政治读法(如毛泽东解读我国四大古典小说) 、寓言读法(如詹姆逊将鲁迅及第三世界文学视为“民族创伤的寓言”,精神分析一派的批评家最擅长将一部小说中的诸多意象轻易判定为“阳具的拥有或匮乏”) 等取向颇为不同。
帕慕克自陈,这种反思性的认识的建立是源于他数十年来的阅读经验: “四十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小说。我知道,我们可以对小说采取多种姿态,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把我们的灵魂与意识投入到小说之中,既可以轻松地,也可以严肃地对待小说。正是这样,我已亲自体验获知阅读小说的多种方式。
阅读小说,我们有时候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有时候只以目视,有时候要用想像力,有时候半心半意,有时候以我们自己希望的方式,有时候以小说要求我们的方式,还有的时候则需要拨动我们生命的所有脉络。”然而,“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意识和心灵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内在的感觉与看电影、看油画、听诗朗诵或者是史诗吟诵有什么不同?”
带着对两个问题的思考,他逐渐体会到,能够体会阅读与创作乐趣的读者首先需要区分想象与基于体验的不同,“绝对天真的读者”和“绝对感伤 - 反思性的读者”注定都无法拥有文学的美好体验: “1. 绝对天真的读者,他们总是把文本当做自传或乔装的生活体验编年史来看,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是一部小说。2. 绝对感伤———反思性的读者,他们认为一切文本都是构造和虚构,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是你最坦诚的自传。”
然而,仅凭这两点就能帮助我们认识“文学与政治”的纠葛吗? 如所周知,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西文论家早已有过探索,在此我们无须赘述,而诸多作家也不乏深入探讨。这中间,尤其以创作《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反映政治主题的作品而驰名世界文坛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讨论最为重要,前文曾一再提及。但此处若将奥威尔与帕慕克的相关论述作一比较,或许会指引我们对文学的阅读、创作体验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了然。
早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奥威尔就曾反复地思考上述我们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在论述作家的创作动机之一———政治方面的目的时,他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政治———最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这里所有的‘政治’一词是指它最大程度的广义。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对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再说一遍,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是有明确意识,你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而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完整。”正是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驱使着奥威尔进行文学创作,《动物庄园》就是他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努力融为一体的第一本书。那么,奥威尔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识是什么? 我们知道,是同时批判英美等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天真,批判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对于这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如果不是在西班牙看到左翼政党的内部运行情况,被打成托派实施清洗的话(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大屠杀也在同时发生) ,他不会在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就有如梦初醒的感觉: “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党标签才能保持正直。”也就是说,只有摆脱了党派偏见,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宣传,才有可能获得文学作品所必需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这也正是文学作品与宣传品根本不同的地方。
奥威尔还举了一个特别的细节让我们弄清楚那种表面几乎看不出什么政治性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的“纯文学”) 里隐藏的政治性。例如,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的欧美的主流文学传统之中,有一类以埃及、印度、非洲等异域风情和殖民者在当地的残暴统治为主题的作品如康拉德《黑暗的心》、吉卜林《基姆》《丛林之书》,E·M·福斯特《印度之行》向来备受关注,然而自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启发我们,尽管美国和欧洲对“东方”的定义不同,但他们的“东方主义”想象却从未褪色,“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
从此出发,我们方能对这类作品的政治意识———或隐或显的殖民主义意识,乃至来自宗主国的作家身上无法掩藏的优越感和对殖民地人民毫不犹豫的贬低———有所体悟。在奥威尔看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反证作家自身的阶级意识或在阶级问题上的真正感情,也会让我们对作家的政治意识作出准确而有效的观察。反过来,那种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识的文学又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好的文学? 依据自己的创作经验,他对这一问题予以断然否定: “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
这暗示出他心目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识的文学不会是好的文学。然而,奥威尔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把握全部建立在一个预设之上,即作家的政治意识等同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可是,这个预设真的正确吗?
显然,帕慕克同意奥威尔对于文学的“政治性”的定义,甚至连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表面几乎看不出什么政治性的判断都是继承了奥威尔的论述,但他企望建立的一种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框架,以及在理解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反应之间取得平衡的阅读方法,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对文学的阅读、创作体验不同于对音乐、美术、电影、戏剧等艺术品类的阅读、创作体验。换言之,如果完全相同,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那种将文学与政治联接起来,反复辨析二者应该如何和谐、或如何冲突的论述是不是忽视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创作体验,混同了文学与政治宣传品、音乐、美术、电影、戏剧等艺术品类的根本差异? 帕慕克比奥威尔走得更远,他在揭示文学的政治性与文学性无法剥离这一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之后,还提醒我们,接下来,重要的不是去区分、辨别这两者的楚河汉界,而是在经验、审美、感性的层面承认文学“虚构的真实”,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保持一个开放、流动的立场;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在尊重“虚构性”的大旗下文学关注政治,但不过度介入政治,从而有可能保持文学的纯粹审美特性的同时获得文学的政治性。换言之,对文学的阅读、批评可以因人而异,不必强求定于一尊,而文学创作的新机或也内蕴其中。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亦宜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1]奥尔罕·帕慕克. 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M]. 彭发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96.
[3]康慨. 奥尔罕·帕慕克———政治没有影响我们的作品[N]. 中华读书报,2006-11-15(08) .
[4]杨中举.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创作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195.
[5]迟梦筠,王春林. 重建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从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说开去[J]. 名作欣赏,2011(1) :114-115.
[6]雷蒙德·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 王尔勃,周莉,译. 洛阳: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211-212.
[7]奥尔罕·帕慕克. 别样的色彩[M]. 宗笑飞,林边水,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奥尔罕·帕慕克. 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M]. 何佩桦,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德希达. 他者的单语主义———起源的异肢[M]. 张正平,译. 台北: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0: 26-27.
[10]M·H·艾布拉姆斯. 文学术语词典[M]. 7 版. 吴松江,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3.
[11]沃尔夫冈·伊瑟尔. 虚构与想象[M]. 陈定家,汪正龙,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83.
[12]帕慕克,陈众议. 帕慕克在十字路口[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9: 35-49.
[13]周小仪. 文学性[J]. 外国文学,2003(5) : 51-63.
[14]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
[15]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文集[M]. 董乐山,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