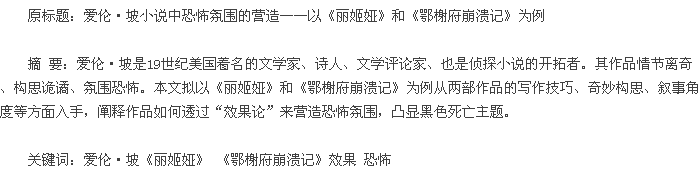
埃德加·爱伦·坡是 19 世纪美国着名的文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他生前命运多舛,三岁丧母,后被一位商人收养,但与养父的关系并不和谐,后与之关系彻底决裂。 他的写作生涯同样也不平坦,从十几岁开始写诗,但遭到的总是冷漠与无视,他的作品在其死后甚至遭到“至友”的窜改,人格遭到侮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们理解。直至后来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及马拉梅等人首先发现了他,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世人所认识。 在其身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他的作品被纳入不同的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作品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坡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怪诞恐怖小说,第二类为侦探推理小说。而在他怪诞恐怖小说中,《丽姬娅》和《鄂榭府崩溃记》为公认的佳作。这两部作品情节离奇、构思诡谲、氛围恐怖,令人读后不禁毛骨耸立。本文拟就两部作品的写作技巧、奇妙构思、叙事角度等方面来阐释作者如何透过“效果论”来营造恐怖氛围,凸显黑色死亡主题。
一、制造恐怖效果的大师
坡在其小说创作中十分注重“效果”的营造,强调对作品要首先进行“设计”。 他在《创作的哲学》中写道:“人们通常构思故事时抑或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抑或由作者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整合后构成自己的叙事基础,这都是错误的”,“我(在构思故事时)首先会考虑效果……之后再考虑故事选用的素材、确定作品的风格,以达到这一预期效果”。[1]191-192坡在《评霍桑<重述的故事>》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小说应具有适当的长度,可以让人一次读完,以确保完整性,小说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应为其最后的“唯一”效果服务。[2]110坡在《诗歌的原则》(Poetic Princi-ples)中都有同样的论述。
坡认为,作品的内容完全服从于艺术效果,主张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形象,总之写到纸上的一切都要为预期效果服务。他还主张,无论小说还是诗歌,都要力求短而精,以达到预期效果。[3]144坡的创作正是其“效果说”的真实体现。坡的故事长短适中,情节环环相扣,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让人一口气读完作品方能罢手。 坡认为最能给人以震撼的“效果”是恐怖,因而为了制造预期效果,坡竭力营造小说的恐怖氛围,在上述两部作品中,“死亡”是营造恐怖氛围的核心要素,而如果说“死亡”还不够恐怖的话,那么借尸还魂、死而复生则是带给人灵魂震颤的恐惧。除此之外,作者还调动声光色彩等手段,在哥特式恐怖氛围的渲染、人物刻画、叙事手法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竭力营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效果。
二、哥特式恐怖场景
坡的小说场景多为哥特式恐怖场景,或是发生在阴森的地窖(《一桶酒的故事》),或是发生在破败的寺院(《红死病的假面舞会》)或者异域的古城堡里(《鄂榭府崩溃记》)。在《丽姬娅》中,故事发生在“人烟稀少的荒芜地方的一座寺院”,这里是“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寺院外部是“满目苍凉”。而寺院内部,布置虽华丽,却十分怪诞,“光怪陆离的花幔”,“怪诞的壁沿和家具”,帷幔后面阴风阵阵,给房间“平添一种可怕的、不安的活力”。[3]26-27作者使用大量辞藻来描写寺院内部及外部环境,描写的基调是昏暗的、压抑的,房内的陈设也给人以恐怖怪诞的感觉。
同样,在《鄂榭府崩溃记》中(以下简称《鄂榭》),环境也同样阴森恐怖。 “整整一天, 我孤单单地骑着马。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荒野;暮色渐渐降临,满目苍凉的鄂榭府终于望见了……荒凉的垣墙,茫然眼睛似的窗户,两三枝有臭味的芦苇,两三棵枯萎的白树——— 这份惆怅,无法以凡人的情绪来比拟。 ”而古堡内部,高大的房间、细长的窗户、黑色的帷幔,更给人以沉郁之感。家具古老残破,“各处笼罩着阴森、深沉、万难弥补的郁郁气氛,一切都浸透了这种气氛”。[3]41而最为恐怖的是活埋玛德琳小姐的地窖。 “又小又湿,没缝没隙,透不进一丝光来,深深地埋在地下……门一开, 擦着铰链, 就嘎嘎发出尖得出奇的一声。 ”[3]52通常,阳光、绿树、鲜花等事物会唤起人们心中的美好意象;而在这里,无论寺院还是古堡,都给人以阴暗、压抑之感,作者不惜笔墨,首先从场景的外部环境描写入手,继而进行内部环境描写,使用大量辞藻,对环境进行了细腻、深入的描写,凸现了故事阴沉晦暗的色调,就像舞台打上了一层灰黑色的光,把读者也带到了阴森恐怖的环境中。 这阴冷的色调、诡异的造型、哥特式场景,投射在人心理上的便是无尽的恐惧,令人神经为之紧绷,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坡有意将故事场景设定在人们并不熟悉的环境中,从而使读者产生陌生感和神秘感。而正是这种陌生感在读者的心里造成恐惧与不安, 为后续故事的发生做好了铺垫;而神秘感又促使读者产生好奇心,读者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更容易被猝不及防地带入即将发生的恐怖情境当中,从而更深切感受到作者预设的恐怖“效果”,为展现黑色死亡主题埋下伏笔。
三、人物刻画推进了恐怖氛围的营造
坡恐怖小说中的人物, 或是心理扭曲的癫狂者,抑或是行为异常的瘾君子, 或是神经质的体弱多病者。他们孤僻、冷漠、神经过敏、内心世界混乱迷惑,此种人物的刻画技巧,也使读者常处于不祥和恐惧的预感当中,调动了读者潜意识中的恐惧意识,更加渲染了小说的恐怖氛围。
在《丽姬娅》中,叙事者“我”是一位因失去爱妻而神经质的瘾君子,“任性”又“反复无常”, 恨新婚妻子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这愤恨只有魔鬼才有”。[3]21他心里扭曲, 终日沉浸在吸食鸦片后的意识模糊状态,为怀恋故去的亡妻而不能自拔。而故事中的两位女主人,前妻丽姬娅和新娘罗维娜虽然都很美丽,但却病弱不堪,面色焦黄,疾病缠身,与黑色的死亡纠缠在一起。 这种异于常人的精神特质,超出了读者的常规意识底线,在潜意识中给人以恐惧之感,使读者在压抑的氛围中透不过气来,并为将故事推向终极恐怖———诈尸做好了铺垫。
在《鄂榭》中,两兄妹都是神经质的人物,鄂榭“面如死灰,眼若铜铃,水汪汪,亮晶晶;嘴唇不厚,没有一丝血色”,[3]44对很多声音气味都感到神经过敏。 作者对鄂榭的妹妹玛德琳着墨不多,她在故事中只出现三次,第一次身穿白裙,在屋角一闪而过;第二次出现时已经躺在棺木中,“嘴唇上留着那令人生疑的永恒微笑”;[3]52第三次出现则是在故事的最后,死而复生,身披白色裹尸布,出现在“我”的房门口。 虽然作者对她着墨不多,但她孱弱的身影如幽灵一样时时飘荡在额榭府中。
鄂榭和玛德琳是一对孪生姐妹,他们在故事中互为映射,这一对兄妹正如舞台剧中的一明一暗、一主一辅两个角色, 在明处的哥哥已经令人极为不安,而身处暗处的妹妹更加重了人物的神秘感,读者急欲揭开帷幕后面这个人物的真面目, 而她偏偏若隐若现,调动读者的胃口,牵动读者的神经。 她在故事中只出现过三次,而直至最后她从棺木中爬出,身披血淋淋的白色裹尸布出现在读者目前时,故事才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在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具有相似的特点,即神经过敏、病态焦虑、忐忑不安,他们的精神世界好似蒙上了阴影,时刻被死亡和不祥追逐。 而这些人物的设计正是为故事的恐怖氛围进行的渲染。
四、独特的叙事方法营造了恐怖氛围
坡在营造恐怖氛围上的另一技巧当数叙事者的选择。 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法。 这种叙事方法一方面如同电影中的主观镜头,可以使领读者随着叙事者的视角进入一个个恐怖场景当中,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耳闻其声,获得更加真实的恐怖体验;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人物细腻深刻的内心描写,使读者不自觉地进入“我”的内心世界,将叙事者的心理活动内化为读者自身的内心体验,将恐怖体验层层推进,加重了读者的恐惧感。
在《丽姬娅》中,“我” 在一个漆黑阴沉的夜晚守在刚亡故的新娘尸床旁。 在吸食鸦片后模糊的意识中,听到尸床上传来低低的啜泣声,“我”睁大眼睛,看到尸体“微血管突然泛出微微一层红”,但没多久,尸体又呈现出“一幅狰狞的死相”。[3]30“我”在这恐怖的夜晚经历了死者数次亡妻死而复生的险象,最后故事推向高潮,死尸复活,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我的前妻丽姬娅,当叙事者的恐怖感受达到极限时,读者也汗毛倒立,惊出一身冷汗。
在《鄂榭》中,“我”本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但随着故事的推进,“我”越来越感受到一切的诡异、怪诞和恐怖。 “我”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恐怖氛围的营造者,在这里,“我”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恐怖的体验者;“我”成为连接外部世界和鄂榭府的纽带,也是连接正常人和精神委靡的鄂榭的桥梁,“我” 的感受正是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所经历的变化,当“我”受到越来越多的恐怖事件后惊吓后,精神几乎崩溃。故事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玛德琳小姐身披裹尸布站在房间门口,并和她的哥哥一起倒地身亡后,“我”的恐怖体验也达到高潮。 最终逃离鄂榭府,而鄂榭府也最后崩塌。
在这两部作品中,读者潜意识中将叙事者的恐怖体验内化为自身的恐怖体验,与叙事者一起经历了极为诡异怪诞的借尸还魂、诈尸的过程。 这实为作者的精心安排设计,使故事的恐怖氛围的营造达到极致。
五、嵌套式叙事结构营造恐怖氛围
坡在小说中还巧用文中诗、嵌套故事的写作技巧来营造恐怖氛围。诗歌与嵌套故事与故事本身的主题相互辉映,更凸现了故事的恐怖氛围。
在《丽姬娅》中,“我”坐在濒死的前妻的床前,为她阅读一首意乱情迷的诗歌。 诗歌描写的一群仙子在观看一出名叫“人生”的悲剧,舞台上“凌霄的天帝” 是个傀儡,“听凭无形巨掌牵上牵下”, 最终却被巨大的毒虫咬死。 诗歌的情节与故事情节相互映衬,凸现了主人公恐惧绝望的心理,诗歌中的死亡也调动了读者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同时,诗中“血淋淋”“灵柩”“战栗”“毒蛊魔王”等字眼无不渲染了故事的恐怖氛围。[3]17在《鄂榭》中,插入了名为《群魔闹金癜》的诗歌,诗歌描写了宫殿的辉煌壮丽,“有座宫殿巍巍耸立,辉煌宫殿矗向天宇”,[3]47然而魔鬼“无常”占据了宫殿,如今却鬼影憧憧,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 诗中的宫殿正是鄂榭府的写照, 也是故事主人公鄂榭的内心写照。 它曾经洋溢着一派盎然生机,然而如今却荒凉破败,走进鄂榭府正如同走进了鬼宫。
在《鄂榭》中,插入的另一个故事是《疯子屈里斯特》。 在一个狂风大作、乌云低垂的夜晚,古屋的主人鄂榭精神溃散,来到叙事者房间,为了安慰他,叙事者给他读这个故事。当读到侠客艾特尔瑞德为了进入隐士的居处,手举钉锤,将门砸穿,干裂的木头发出“噼里啪啦”“声震丛林”的声响时,远处传来了和故事中丝毫不差的闷声闷气的声响;当读到勇士击中龙首,巨龙发出尖利的哀嚎时,分明又听到地窖里传来“刺耳的尖叫”;[3]55此时,读者的神经和故事中人物一样绷得紧紧的,恐惧的心理越来越强烈 。 叙事者听到这些声响后,强作镇静,而鄂榭已左右摇晃,浑身颤抖,已几近崩溃。 继而当读到盾牌落地,发出震天声响时,顿时听到现实中传来一声“清晰、空洞的铿锵声”。故事中的三声巨响与鄂榭府内发出的响声相吻合, 这正是玛德琳冲破棺木,拉开铁门,冲向屋里的声音。在这里,两个故事中的情节相互映衬,达到完美的统一,如波浪般把恐怖的氛围层层推进,把故事逐渐推进高潮。在这里, 故事与嵌套故事和诗歌构成了互文性,即在文本中一个能指体系向另一个能指系统的过渡和易位。[4]111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一个原本已经十分恐怖的故事显得更加恐怖诡异。
六、利用声光色彩营造恐怖氛围
坡还运用了舞台艺术手法, 巧妙地利用声、光和色彩来烘托气氛。[5]91在《丽姬娅》中,“我”不时听见深夜的尸床上传来的呜咽,“低低的”,“柔柔的”, 继而又传来“幽幽的”声音;在《鄂榭》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鄂榭凄惨的挽歌声,木门爆裂声,铰链的摩擦声,主人公垂死时的呻吟声,窗外的风雨声;这些声音的描写,使读者如同身处其中,切身感受着恐怖的氛围。
在描写光线和色彩方面,在《丽姬娅》中,室内的光线也十分诡异,“房里一切物件都蒙上了阴森森的光”;家具的颜色“死气沉沉的”,床是漆黑的乌木。[3]26而在《鄂榭》中,整个鄂榭府内外都笼罩在一片黑灰的色调中,幽暗的湖水,漆黑的橡木地板,玄色帐幔,“几道红艳艳的微光, 透过格子玻璃射进来”,“整个房间就此浴在一片不相称的阴森森的光辉中”;[3]42而鄂榭苍白的脸、玛德琳白色的血迹斑斑的长袍,却与这些灰黑色形成强烈反差。
在这里光线色彩使得故事的场景更为丰富、细腻,铺设了故事的基调:冷、暗、阴、怖,成功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立体饱满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阴森昏暗的视觉印象。调动了读者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取得了独特的舞台效果,营造了恐怖的氛围,也与死亡的主题紧密相连,互为呼应。
七、隐喻与象征的艺术效果
在坡的故事中充满了丰富的文学隐喻与象征。在《丽姬娅》中,昏暗的建筑、破败的寺院、怪诞的家具恰恰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映射和象征,他的精神世界是灰暗的、意志是颓丧的。美国诗人兼批评家理查德·维尔伯指出: “从喻象层面上看,厄舍古宅可视为罗德里克·厄舍的躯体,其幽暗的内部,则是他头脑中的幻念。”[6]21这所宅子的衰颓,象征了心灵的分裂和解体过程。 D·H 劳伦斯认为:“坡笔下的‘地窖’之事是潜意识的象征。 表面上,一切都简单易懂;可在深层中,竟是这种活埋人的极端行为。 ”[7]76这些文学隐喻和象征调动了读者潜意识中对于破灭和死亡的心理反射,使得故事彻头彻尾地成为了一个恐怖的泥淖,随着故事的推演,也一步步把读者带进了恐怖的深潭。 坡紧紧围绕主题,在以情节为主线推演故事的同时,也透过文学隐喻营造着一个令人无法超拔的恐怖的氛围,实现其精心营造的艺术“效果”。
八、结语
坡的小说以离奇、怪诞而着称,他调动了一切手段,营造其追求的“效果”。 在上述两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哥特式场景的描写、 人物外表及内心世界的刻画、文中文的手法、舞台艺术的应用、独特的叙事手法以及文学隐喻和象征,成功地营造了恐怖诡异的氛围,取得了坡所精心营造的 “效果”。 小说中萎靡颓废的主人、昏暗阴冷的色调、哥特式的神秘背景无一不与死亡主题相关;而独特的结构与叙事手法也与小说的黑暗死亡主题相契合。小说结构紧凑、气氛阴森、一气呵成,令人不忍释卷。坡不愧为驾驭文字的大师。坡的恐怖小说与一般的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故事不仅让读者感到情节的恐怖,而且给读者带来灵魂的震颤、内心深处的恐惧。 正如 D·H 劳伦斯所说:“坡像科学家在坩埚中溶解盐一样把自己化为灰烬。这几乎是对灵魂和意识进行化学分析。在真正的艺术中颤动着创造与毁灭的双重节奏。”[7] 62坡在恐怖小说的创作上无疑是一位大师,他的作品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探索人类的潜意识活动及变态心理方面,无疑也开创了先河。
参考文献
[1] Allen Poe.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美国文学名着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常耀信 . 美国文学简史 [M].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3]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 徐显静.试论 《厄舍府的倒塌 》中的隐含结构[J].电影文学,2008(22).
[5] 曹曼.追求效果的艺术家 ———爱伦·坡的 《厄舍古屋的坍塌》[J].外国文学研究,1999(1).
[6] 刘俐俐.《厄歇尔府的倒塌 》的现代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3(4):21.
[7] D. H. 劳伦斯.劳伦斯文艺随笔[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