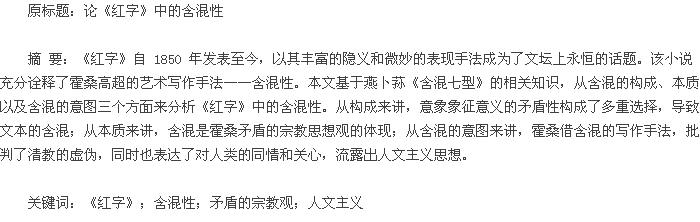
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与梭罗、惠特曼一起开创了美国本土文学的新天地。
评论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曾高度赞扬了他的创新精神,“他的小说属于艺术的最高层次,一种服从于非常崇高级别的天才的艺术”。
他的代表作《红字》,想象丰富、写作手法独特,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突破。他无疑是美利坚民族第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小说家。《红字》自发表以来,国内外从未间断过对它的评论,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像《红字》这样的小说需要代代相传的阅读才能显示其价值。总体来看,学者主要从它的主题、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展开研究,或从跨学科领域切入文本。兰德尔·斯图尔特(Randall Stewart)对《红字》的高度评价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他的《霍桑传》是关于霍桑的批评史中最经典的专着。
笔者认为《红字》最大的特点是含混性(ambiguity),也是该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含混”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ambiguitas”,其原意为“更易”(shifting)或“双管齐下”(acting both ways)。
在普通用法中,它一般用来指涉“文本的错误”,即“本想明确具体表意时却表达地含混多义”。威尔弗雷德(Wilfred L Guerin )认为,“含混”就效果而言,是指“意义的模糊性、游移性和歧义性”;就方法而言,“常常是故意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以便产生多种可能的解释,从而丰富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加强戏剧性效果和审美效果。”
1930年,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 在他的巨作《含混七型》中将“含混”细分为七种类型。本文将基于燕卜荪的《含混七型》的相关知识,从“刑台”与“森林”两个意象着手,重读经典并解读其含混性。意象之相互矛盾的象征意义构成了文本的含混性,是霍桑矛盾宗教观的反映。作者运用含混的写作手法批判了清教势力的虚伪与黑暗,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关怀。字里行间,霍桑流露出了人文主义情怀。
一、含混的构成——模糊的象征意义
霍桑是位象征主义大师,善于运用各种意象。
雷塔·科·戈林(Rita K Colin)在《纳桑尼尔·霍桑》中评论道“读者很快就发现霍桑很多反复出现的意象:光明与黑暗……心灵的隐秘, 可对这些意象几乎没有固定的阐释。于是红字是耻辱的象征,却又变成了胜利的标志,它本身不仅暗指奸妇,也暗指其他一系列的意义。”
这一评论充分生动地描述了《红字》中意象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本文将解读“刑台”与“森林”的象征意义并分析其含混性。
1. 刑台:死亡与重生
刑台,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用来规约人们的道德行为。刑台在文中出现了三次,小说以它开始,并以其结尾。它既是惩罚的工具又是赎罪的平台,也是肉体死亡与灵魂重生的媒介。
一开场,刑台是惩罚的工具。在宗教文化深厚的萨莱姆,“作为惩罚机器的这架绞刑台在经过两、三代之后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传统,但在古老的时代则是教育优秀公民的一个有效工具。”(14)由此可见,刑台在古老的清教徒眼里,就像法国的断头台一样,是最凶残的死亡机器,是惩罚罪人的地方,没有什么装置比这种更羞辱人格和违背人性了。由于海斯特犯了“通奸罪”,必须站在刑台上向世人公布自己的罪行。然而,海斯特勇敢地承受着这一切,并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当上千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她高贵典雅的风度和无罪的母性的圣象”。(15)她就像监狱门前那只野蔷薇,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并散发出芬芳和妩媚。在此,作者借野蔷薇表达了对海斯特勇敢反抗的怜悯和赞扬之情,同时对黑暗残酷的清教社会表示批判与讽刺。
接下来的情节中, 刑台是忏悔的平台。由于丁梅斯代尔无法承受内心道德的谴责和齐林沃斯对其心灵的鞭策,在 12 章中,他夜不能寐如同梦幻般来到海斯特当年示众的刑台上演了一场自欺欺人的忏悔表演,徘徊在“悔恨”与“胆怯”之间,历经二者之间的挣扎带来的痛苦。刑台就像拷问灵魂的道德法庭,鞭笞着他脆弱的心,但是他的怯弱最后又占了上风,“每当‘悔恨’这种冲动强逼他供认真相时,它的嫡亲姐妹‘胆怯’,便总要用它颤抖的手掌将他拉回去。”(164)在黎明之前,海斯特与珠儿来到刑台,丁梅斯代尔做了光天化日之下不敢做的事情,邀请拥抱母女俩,“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电路”。(173)但是,在破晓之前,他又落荒而逃。他的这种懦弱与胆怯与海斯特七年之前站在刑台上的勇敢与从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充分展示了清教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与压抑以及揭示了人性的自私和虚伪。
在小说进入尾声时,刑台是救赎的象征。牧师用尽最后残余的一点力气,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向刑台,向世人承认罪行。他说:“你们曾经爱过我的人……看看我这个世人的罪人吧!”最后扑倒在地,胸前露出红色的烙印“A”,在众人面前,三口之家在刑台上相互依偎。此时,丁梅斯代尔得到了救赎,以肉体的死亡获得了灵魂的永生。
总而言之,刑台不仅充当了惩罚工具,也充当了赎罪的平台。既象征着死亡,又代表着重生。海斯特在刑台上,公然反抗教会,与残酷的社会顽强地做斗争;丁梅斯代尔在最后也实现了道德升华与灵魂解放。通过描写海斯特在刑台上的公然反抗,作者批判了清教势力对人性的压抑,肯定了人有追求自由和爱的权利。
2. 森林:邪恶与纯洁
森林意象是美国文学中重要的母题之一,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如:威廉·布雷福德的<<普利茅斯种植园记事>>以及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等……在霍桑的小说中,森林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恩地科特与红十字>>中,塞勒姆第一代移民约翰·恩地科特描述道:“这荒野有多凄凉!我们走出屋外没几步,就会碰上狼和熊……我们想犁地,可硬梆梆的树根把犁头都弄折了……”在《小伙布朗》中,森林作为重要的场景,作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深刻地阐释森林所代表的邪恶涵义。布朗刚踏入森林时,“阴森森的树木遮天蔽日,挤挤挨挨,勉强让狭窄的小径蜿蜒穿过。人刚过,枝叶又将小路封了起来,荒凉满目。”
暗示着人一旦踏入了邪恶的世界就无法再回到纯洁的世界了。然而,在《红字》中,神秘阴森的森林是善与恶的双重象征,是纯洁与邪恶的化身。
一方面,它是魔鬼出现的场所,笼罩在邪恶与危险的气氛之下。它的阴森与黑暗象征着人类内心的邪恶。西宾斯太太是个典型人物,她经常去森林与魔鬼会面。有一次,她邀请海斯特和她一起去森林参加聚会。她说:“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去?在森林里将有一次快乐的聚会呢。并且我已经答应了黑男人……”(113) 后来,她作为女巫被处决了。此外,罗杰·齐林沃斯在小说开始时是被印第安人从荒原里带出来的,他经常去森林采集药草然后折磨牧师的心灵。在小说结尾时,就连森林里的溪水也总是郁郁寡欢,笼着这阴森的气息,“珠儿与那溪水颇为相似,因为他的生命和她的生命一样,也是从同样的一个泉源涌出来的,并流经了同样沉重的阴影笼罩的暗淡景色。”(228) 这里所说的同一源泉,指的是罪恶的源泉,因为珠儿一生下就贴上了海斯特与牧师的“罪恶之果”的标签。
由上可知,森林在小说中彰显了黑暗与邪恶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森林象征着纯洁与善良。在这里,没有残酷的清教教义约束,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向大自然倾诉自己压抑的情感。因此,森林在某种程度下是那些受宗教迫害的人们的心灵庇护所,为他们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对海斯特而言,是爱之方舟,她与牧师在森林里相遇、相识到相爱。对牧师而言,森林是他精神的寄托。只有在森林里,他才免于饱受心灵的挣扎与折磨。珠儿,天生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但却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那座阴黯的大森林---虽然对于那些把认识罪恶与烦恼带到她胸怀里来的人们显得严峻,但对这个孤独的孩子而言,却尽可能变成她的游伴……却露出最亲切的心情来迎接她”(258) 此外,海斯特是在森林里劝说牧师一起逃离这块耻辱之地,“这种振奋人心的决定对于一个刚刚逃脱自己心灵禁锢的囚犯来说:犹如踏上一片未受基督教化、尚无法律管理的荒土……”(253) 因此,只有在森林里,海斯特和牧师才能放下心灵的负担,才能解脱,也只有在森林里,他们一家三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森林成了他们的快乐家园。不受世俗和法律制约的森林在这方面与残酷黑暗、虚伪的现实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它象征着纯洁与自由。
综上所述,森林是恶与善的化身,是邪恶与纯洁的象征。一方面它代表危险阴暗,是收容罪犯、孕育邪恶之地;另一方面却象征纯洁与自由,给压抑的人类提供了释怀空间。
二、含混的本质:矛盾的宗教观
纵上所述,“刑台”和“森林”各自的象征意义是多义的,更是相互矛盾的,构成了文本的含混。
笔者认为这种含混的本质是霍桑思想上的含混,反映了他矛盾的宗教思想观。燕卜荪把这种含混归纳为《含混七型》中的第四类“一个陈述的两层或更多的意义相互不一致,但结合起来形成作者的更为复杂的思想状态。”
由于作者深受家族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他对清教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萨勒姆,深受宗教文化的熏陶,再加之,他祖辈中两代人曾参与臭名昭着的“驱巫活动”,这些都使得他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清教教义影响,他坚信原罪意识和赎罪论。
因此,他的作品逃脱不了救赎、罪与罚、原罪等一些宗教主题。《红字》中,海斯特犯了“亚当夏娃”式的原罪,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并走上救赎之路;丁梅斯代尔必须依靠“刑台”这一平台经历死亡才能得到灵魂的解放。另一方面来讲,当时美国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哲学派提倡个人主义和自助精神,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思想在《论自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超验哲学的盛行使霍桑对清教伦理以及人性进行反思,他看到了清教统治者的黑暗、虚伪以及对人性的残酷压抑,同时肯定人的价值,鼓励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教会势力强大的社会里,丁梅斯代尔每天都忍受着心灵的折磨,饱受痛苦,最后走上了死亡之路,这充分说明了清教的虚伪以及对人性的摧残。海斯特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心灵的救赎,胸前的“A”从“adultery”演变成了“Angel”,这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霍桑借海斯特的勇敢反抗,强烈地批判了宗教势力。
霍桑想寻求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方法,想打破清教社会的旧秩序。但是在清教势力严厉的社会,他无能为力改变这一现状,同时自己不能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清教思想。当这种矛盾与困惑的思想状态融入到作品中时,就往往会十分隐晦,意义含混。
三、含混的意图:人文主义思想的流露
人文主义思想是 14—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和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尊重人、关怀人,强调人能创造一切,歌颂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反对蒙昧主义对人的贬抑;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现世享受,颂扬爱情,要求面向现实人生。从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美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美国,深受清教思想的熏陶,文艺复兴运动宣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仍是举步维艰。尽管霍桑洞察到了清教的虚伪和残酷,仍然力量单薄、不敢与之公然反抗。因此,作者借助了“含混”这一写作手法间接地鞭策了虚伪的清教势力,传达了他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与女性命运的关注,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关怀。
首先,霍桑借助了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曲折的爱情故事,深刻地批判了清教鼓吹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的价值与追求自由爱情、幸福的权利。“海斯特”偷吃了禁果,受到了清教势力的严重惩罚,成了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但红“A”从“adultery”演变成“able”至最后的“angle”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小说安排了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合葬在一起的结局,表达了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赞扬与同情。其次,霍桑通过塑造了海斯特这一勇敢、坚强且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他对生活在清教偏见下的女性的担忧与同情。独立运动后的美国开始兴起了强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激进派提出要解放女性,并且要独立于男性。伯科维奇认为霍桑对这些言论是非常关注的。霍桑极力鼓励女性追求自己的价值,希望她们能够获得解放。因此,霍桑想借助海斯特这一形象为正在觉醒中的女性树立榜样和指明方向。
在小说中,霍桑呼吁人们去追逐幸福与自由的同时,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展示和批判了清教主义的虚伪残忍和对人性的压抑,他严厉批判了清教教规,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性对爱、幸福的追求。在探索对人性的认识与理解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路上,他成了一位孤独勇敢的探索者。
结语
《红字》是部倍受争议的作品,主要源于其含混性。这种含糊来源于其思想上的含混,是矛盾宗教观的体现,正如埃默里·埃利奥特所说,“霍桑与其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人物,他是温和的叛逆者,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的和社会的信条,他又遵守;又嘲讽地破坏。”
他无法抛弃扎根于他脑海中的宗教教义,如原罪、预定论等;但又无法忍受清教的虚伪与残酷,对人类社会充满同情。然而,恰是这种说不明道不清的“含混”成就了霍桑,体现了他高超的创作艺术手法,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正如马丁评论, 霍桑经典之作的特殊之点正存在于“这种内在的双重性和模糊性”。
参考文献:
[1]罗伯特·E·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周期[M].王长荣,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64.
[2]殷企平.含混[J].外国文学,2004,(02):54-60.
[3]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Z].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F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 2004:10.
[4]威尔弗雷德,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M].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444.
[5]Colin, Rita K.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Heath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Lexington:D.C. Heath and company, 1994:2116.
[6][7]霍桑.霍桑短篇小说集[M].陈冠商,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252, 143.
[8]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M].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0:133.
[9]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朱伯通,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336.
[10]Terrenc, Martin. Nathaniel Hawthorne [M]. New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56:119.
[11]书中所有《红字》的引文,均引自以下文献,不再一一注明.Hawthorne,N. The Scarlet Letter[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Press, 1992.





